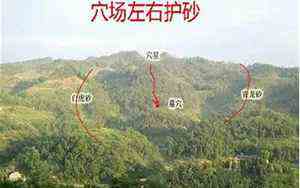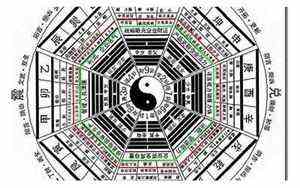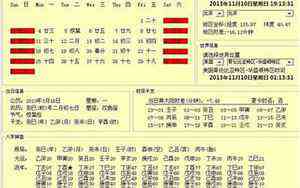
本文目录一览:
郭纯:一个“新青年”之死,让人看到一个知识群体的分裂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认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势,“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中国需要这些青年们 “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而至于如何抉择,他提出了以下这6条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标准不仅仅是陈独秀借以唤醒中国青年,期待他们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行动纲领,也投射出了他心目中这本杂志的理想读者——一个“自由、进步、积极、开放、务实、科学”的“新青年”形象。
掩卷之余,有人会问,当时中国真的存在着这样的“新青年”吗?他们是谁?
今年上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算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形象的解答,在这部“正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的电视剧中,编剧们构建了一组“新青年”群像,给观众列出了一长串“新青年”名单: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郭心刚、赵世炎、邓中夏……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在这部电视剧中,每一位历史人物出场时都会在一旁配上解说词,介绍其姓名、生卒年、出场时的身份等重要信息。与之对应的是,那些为了剧情需要虚构出来的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其中,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这部长达43集电视剧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里频频露脸、戏份颇为吃重的“郭心刚”,竟然也是一位虚构的人物。
不同于其他点缀型的虚构人物,观众能够在剧中感受到编剧对“郭心刚”这个人物的偏爱,他在《觉醒年代》里不仅是一个“参照物”,穿针引线连接了众多主角的出场,他自己也是一个拥有独立主线故事的重要人物:东渡日本求学,正值袁世凯要接受 “二十一条”而义愤填膺,甚至面唾发表“消极言论”的陈独秀,却与其不打不相识,还意外见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来到北大求学,深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熏陶,成为“文学改革”中支持白话文的急先锋;是山东登州总兵之子,中国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痛失山东,他也因未能完成父亲的遗愿而一夜白头,拖着病躯参加了五四游行示威运动,最终吐血身亡。这个充满古典悲剧式的结局令无数观众动容,然而这并非是创作团队一时的神来之笔,而是真实的历史原型赋予这个角色的高光时刻。
“郭心刚”这个角色的原型名为“郭钦光”,1895年出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6岁进学堂读书,12岁毕业于文昌县罗峰高等小学,其后负笈赴穗,考入广东省立师范学校。在广州,他确实曾因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而愤恨不已,在东园举行的“国耻大会”上慷慨陈词,以“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候外人侮之我国”之言立下以死报国的志向。1917年,郭钦光从广东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继而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学习。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眼界的开阔,郭钦光对国家危亡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13所在京大专院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郭钦光当时已身患肺病,同学都极力劝阻他不要再参加游行,但他执意不肯。当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后,他马上登台演讲,随后又和同学们赶往赵家楼搜寻卖国贼,期间因过度劳累,加上情绪激动,当场呕血不止,一度陷入昏迷。之后虽被送往北京法国医院救治,但由于其病情迅速恶化,医生也回天乏力。5月7日,郭钦光因病去世,时年仅24岁。
郭钦光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他的死在学生中引发激烈反响,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的学生均为他举办了悼念活动,并将追悼活动发展为政治动员大会,进一步推动五四运动的广泛发展。1998年5月4日,正值北大百年校庆之时,“郭钦光”的名字被补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真正的“郭钦光”只活了短短二十余年,后人只能凭借其族人的回忆及其同时代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在地方县志和英烈传里草草拼凑出一两页他的生平。“五四”举起的旗帜上也许有他洇红的血迹,但后人遗憾的是只能悲叹他的命运,却永远无法理解他的苦恼和遭遇。这一大块的“留白”,倒是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机会。编剧们通过择选和提炼文献材料,将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新青年”和用文本、史料构建的“新青年”重合起来,揉捏出了一个全新人物“郭心刚”。戏假情真,创作团队用虚构的角色丰富了英雄的人生,。
一说到 “新青年”,我们往往会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衍生品,但这似乎有潦草定性的嫌疑。《觉醒年代》的处理就较为巧妙,它将1915年初留日中国学生的一场辩论作为第一幕,让“郭心刚”在此登场,为剧情的开启铺设了合理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清政府发起“新政”改革,试图挽救已岌岌可危的政权。然而,在长达近十年的改革中,只有废科举、兴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出国三项得到了贯彻。清政府没有迎来帮手,却培养出了对手: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集体诞生——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他们不断疏远传统思想和统治阶级;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出国留学,又使得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接触。“新青年”就来自于这些知识分子。自备思想武器的他们渴望变革。同盟会作出了最先的尝试,但惨遭失败,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南北军阀所窃取。革命陷入瓶颈,苦闷的知识分子重新思索中国的命运。
正是这一时期,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因其经济便利,文化相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郭心刚”所见证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不全是创作者的艺术想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在早稻田大学接触到了“日本社会主义之父”安部矶雄的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这两位“新青年”未来的领路人心中埋下种子。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种子破土,宣告“新青年”诞生了。新生的力量需要精心的呵护和滋养,更渴望严格的磨砺来增强生命力。《觉醒年代》选择北京大学作为主场,来展示中国思想界新旧两股势力的交锋,自有其道理:作为“戊戌变法”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机构,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现代大学,随着国子监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取消,它逐渐演变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最高学府,成了一个既是学习也是储备官僚的机构。这也印证了《觉醒年代》中的反面角色“张丰载”那句话:“去北大读书就是去做官。”
而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力促改革,他在就职演说中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为了一个新的北大,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换一个角度来看,陈独秀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新文化”而站到北大的讲台上。以文学改革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需要主将和先锋——剧中“郭心刚”与黄侃就“尊师重道”争论,就像是先锋上场,凭借年轻人的冲劲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也需要马前卒——排演活报剧《红楼钟声》,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新青年”在各种摩擦冲突中愈战愈勇,为今后的斗争积攒下了经验和勇气。
1919年5月4日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让北洋政府看到了“新青年”的决心和行动力。《觉醒年代》将“郭心刚之死”安排在此处,既尊重了客观历史事实,又能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也被巧妙地展示在故事情节中:游行过后,北京政府关押“闹事”学生,整顿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损失惨重,再加上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之职,令众人觉得学校恐有被解散的危险,此时的胡适萌发了将“北大南迁”的想法。陈独秀与胡适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前者更是喊出了:“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而胡适之太多”之语。
一个“新青年”以斗争的姿态死去了,他的死让他的导师从一开始高谈“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到最后喊出了“不辩,不争,不可以”,确认了“新文化运动离不开政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政治”。他的死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将高举着“新青年”的牌子会继续前进,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一个文化运动不应该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告诫自己远离这些是是非非,“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为《觉醒年代》中郭心刚的原型郭钦光所作的诗:郭钦光:第一牺牲
郭钦光,男,1896年生。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龙尾塘村人。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牺牲,年仅23岁。
你,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你的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正直与刚硬
你喜欢阅读中国历史
痛恨卖国奸贼
更钦佩里面的民族英雄
面对近代中国政治的腐朽和列强的入侵
你的心像南中国海的波浪
总是难以平静
当袁世凯用丧权辱国的笔
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
你义愤填膺,登台演讲
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
全然不顾台下军警狰狞的刺刀
越演讲越慷慨,越演讲越激动
你激愤过度,当场呕血
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917年,儿子刚满一岁
你再度离乡渡海,求学京城
1919年,中国,“一战”的战胜国
却还要咽下耻辱,在巴黎和会上
还要继续《二十一条》的不平等
终于,中国人民再也无法沉默
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5月4日那一天,在北大爱国学生游行队伍中
你虽然患病,仍奋袂前冲
你和13所高校3000多名师生一起高喊
“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你像一枝利箭,射向赵家楼
射向汉奸卖国贼的心胸
你以血肉之躯,抗击反动卫兵的殴打
你以铮铮铁骨,反击反动政府的暴行
你激愤不已,你呕血不止
同学的声声呼唤
仍旧没能唤回你年轻的生命
你,成了黎明前黑夜里的一颗明星
你,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牺牲
“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
你实现了少年时立下了的誓言
你以鲜血换来了亿万人民的觉醒
“疾风劲草”
这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你题写的悼词
无数爱国青年
将沿着你的道路
继续奋力前行
郭纯:一个“新青年”之死,让人看到一个知识群体的分裂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1915年9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第一期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认为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势,“惟属望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中国需要这些青年们 “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而至于如何抉择,他提出了以下这6条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条标准不仅仅是陈独秀借以唤醒中国青年,期待他们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行动纲领,也投射出了他心目中这本杂志的理想读者——一个“自由、进步、积极、开放、务实、科学”的“新青年”形象。
掩卷之余,有人会问,当时中国真的存在着这样的“新青年”吗?他们是谁?
今年上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算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形象的解答,在这部“正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的电视剧中,编剧们构建了一组“新青年”群像,给观众列出了一长串“新青年”名单: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郭心刚、赵世炎、邓中夏……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在这部电视剧中,每一位历史人物出场时都会在一旁配上解说词,介绍其姓名、生卒年、出场时的身份等重要信息。与之对应的是,那些为了剧情需要虚构出来的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待遇”。其中,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这部长达43集电视剧中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里频频露脸、戏份颇为吃重的“郭心刚”,竟然也是一位虚构的人物。
不同于其他点缀型的虚构人物,观众能够在剧中感受到编剧对“郭心刚”这个人物的偏爱,他在《觉醒年代》里不仅是一个“参照物”,穿针引线连接了众多主角的出场,他自己也是一个拥有独立主线故事的重要人物:东渡日本求学,正值袁世凯要接受 “二十一条”而义愤填膺,甚至面唾发表“消极言论”的陈独秀,却与其不打不相识,还意外见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来到北大求学,深受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熏陶,成为“文学改革”中支持白话文的急先锋;是山东登州总兵之子,中国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痛失山东,他也因未能完成父亲的遗愿而一夜白头,拖着病躯参加了五四游行示威运动,最终吐血身亡。这个充满古典悲剧式的结局令无数观众动容,然而这并非是创作团队一时的神来之笔,而是真实的历史原型赋予这个角色的高光时刻。
“郭心刚”这个角色的原型名为“郭钦光”,1895年出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6岁进学堂读书,12岁毕业于文昌县罗峰高等小学,其后负笈赴穗,考入广东省立师范学校。在广州,他确实曾因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而愤恨不已,在东园举行的“国耻大会”上慷慨陈词,以“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候外人侮之我国”之言立下以死报国的志向。1917年,郭钦光从广东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继而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学习。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眼界的开阔,郭钦光对国家危亡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首的13所在京大专院校的三千余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郭钦光当时已身患肺病,同学都极力劝阻他不要再参加游行,但他执意不肯。当游行队伍在天安门集齐后,他马上登台演讲,随后又和同学们赶往赵家楼搜寻卖国贼,期间因过度劳累,加上情绪激动,当场呕血不止,一度陷入昏迷。之后虽被送往北京法国医院救治,但由于其病情迅速恶化,医生也回天乏力。5月7日,郭钦光因病去世,时年仅24岁。
郭钦光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他的死在学生中引发激烈反响,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的学生均为他举办了悼念活动,并将追悼活动发展为政治动员大会,进一步推动五四运动的广泛发展。1998年5月4日,正值北大百年校庆之时,“郭钦光”的名字被补刻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真正的“郭钦光”只活了短短二十余年,后人只能凭借其族人的回忆及其同时代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在地方县志和英烈传里草草拼凑出一两页他的生平。“五四”举起的旗帜上也许有他洇红的血迹,但后人遗憾的是只能悲叹他的命运,却永远无法理解他的苦恼和遭遇。这一大块的“留白”,倒是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机会。编剧们通过择选和提炼文献材料,将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新青年”和用文本、史料构建的“新青年”重合起来,揉捏出了一个全新人物“郭心刚”。戏假情真,创作团队用虚构的角色丰富了英雄的人生,。
一说到 “新青年”,我们往往会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衍生品,但这似乎有潦草定性的嫌疑。《觉醒年代》的处理就较为巧妙,它将1915年初留日中国学生的一场辩论作为第一幕,让“郭心刚”在此登场,为剧情的开启铺设了合理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清政府发起“新政”改革,试图挽救已岌岌可危的政权。然而,在长达近十年的改革中,只有废科举、兴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出国三项得到了贯彻。清政府没有迎来帮手,却培养出了对手:一个全新的知识分子集体诞生——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他们不断疏远传统思想和统治阶级;新式学堂的建立和出国留学,又使得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接触。“新青年”就来自于这些知识分子。自备思想武器的他们渴望变革。同盟会作出了最先的尝试,但惨遭失败,中华民国虽然建立,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南北军阀所窃取。革命陷入瓶颈,苦闷的知识分子重新思索中国的命运。
正是这一时期,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因其经济便利,文化相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的云集之地。“郭心刚”所见证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性会面,不全是创作者的艺术想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在早稻田大学接触到了“日本社会主义之父”安部矶雄的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这两位“新青年”未来的领路人心中埋下种子。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种子破土,宣告“新青年”诞生了。新生的力量需要精心的呵护和滋养,更渴望严格的磨砺来增强生命力。《觉醒年代》选择北京大学作为主场,来展示中国思想界新旧两股势力的交锋,自有其道理:作为“戊戌变法”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机构,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现代大学,随着国子监的废除以及科举制度的取消,它逐渐演变为中国唯一的官方最高学府,成了一个既是学习也是储备官僚的机构。这也印证了《觉醒年代》中的反面角色“张丰载”那句话:“去北大读书就是去做官。”
而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力促改革,他在就职演说中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为了一个新的北大,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换一个角度来看,陈独秀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新文化”而站到北大的讲台上。以文学改革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需要主将和先锋——剧中“郭心刚”与黄侃就“尊师重道”争论,就像是先锋上场,凭借年轻人的冲劲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也需要马前卒——排演活报剧《红楼钟声》,为白话文摇旗呐喊。“新青年”在各种摩擦冲突中愈战愈勇,为今后的斗争积攒下了经验和勇气。
1919年5月4日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让北洋政府看到了“新青年”的决心和行动力。《觉醒年代》将“郭心刚之死”安排在此处,既尊重了客观历史事实,又能将观众的情绪推向高潮。“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也被巧妙地展示在故事情节中:游行过后,北京政府关押“闹事”学生,整顿宣传进步思想的刊物,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损失惨重,再加上蔡元培请辞北大校长之职,令众人觉得学校恐有被解散的危险,此时的胡适萌发了将“北大南迁”的想法。陈独秀与胡适因此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前者更是喊出了:“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就是因为郭心刚太少,而胡适之太多”之语。
一个“新青年”以斗争的姿态死去了,他的死让他的导师从一开始高谈“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心致力于启发国民的思想”到最后喊出了“不辩,不争,不可以”,确认了“新文化运动离不开政治,甚至它本身就是政治”。他的死让人们意识到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其中的一部分人将高举着“新青年”的牌子会继续前进,而另一部分人则坚持“一个文化运动不应该转变为一个政治运动”,告诫自己远离这些是是非非,“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分界线》主要剧情拖沓不前,柳眉承担了一切
《分界线》看到这里,已经过了弃剧那个阶段,因为柳眉这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要看下去,看看她到底要干什么,她会是什么结局。
柳眉跟马东升的案子没关系,跟毒品案子也没关系,如果非要扯上一点点关系,那么她只是幕后毒枭“博士”的初恋情人,其实这个剧情是可有可无的,开始几集马东升近乎完美的反侦察戛然而止,于队长案子也不破了,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这件事一样,导演反而在柳眉这个角色上“精雕细琢”。
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人,一个温度的家庭,跟老公没啥共同语言,心里惦记着初恋情人,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一次次的往“博士”家跑,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但这个行为对她老公来说已经够了,有没有实际发生意义不大,反正就是多次去初恋男人家,还都是晚上。
就这么一个普通的女人,跟剧情主要脉络没啥关系的人,把小陶送进监狱,把小武送进监狱,以后初恋情人要么去监狱,要么拘捕被击毙,自己老公车祸昏迷不醒,所以就问问导演,柳眉这个角色到底是要传达什么价值观呢,是红颜祸水吗?
陈独秀为什么离开北大?
数年前,适逢五四百年,笔者曾分别撰文对“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和胡适二位先贤进行追忆。(《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五四人物评述之胡适的改良主义思想》)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电视剧《觉醒年代》的热播,当年的那一段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恢弘历史再次勾起人们的思考。当然这其中见仁见智,思考的路径和方向就各有千秋了。
电视剧或许只是为了突出先贤们的“高大”形象,对正面人物在人格和品性方面“去劣存优”地拔高就在所难免了。同时也为了增强故事的冲突性,使其更加引人入胜,剧中还特别虚构了几个脸谱化的反面人物,比如那个一直变着花样跟独秀先生死磕,不断诋毁、攻击、迫害先生,必欲置之死地的张丰载和他的二叔张长礼。
之所以大家并没有象对待“抗日神剧”那样对此感到不适,那是因为,在那个历史转折的伟大时代,大师们的确足够“伟光正”,必要的反衬和拔高并无不可,加之多年来被污名化,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不平,使得整部剧看起来清新脱俗,意境独到。
不过,提起张丰载这个人物,说他是虚构,事实上也并非全是。他是剧中少有的未使用真名的人物之一,但历史上确有原人,只不过不象剧中人物那么品行低劣到天人共愤。
这个人物原型就是我在前述《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一文中所提到过的“守旧派北大学生‘半谷通讯’主持人张厚载”。一字之差,却都是导致北大去陈,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关键性“小人物”。
张厚载作为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无意中改变了中国历史,而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原本他也是个有大才之人,他对旧戏造诣极深,读书期间就经常写戏评在南北报刊发表,胡适称其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若不是造化弄人,或许他会象与他同时代的北大学子傅斯年等人一样,尔后成为名声显赫之“大人物”。
盖因其时,张厚载于戏剧改良的方法方面与几位大师意见相左,在以《新青年》为载体的旧戏改革笔战中,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对敌新文化运动诸位主将,加之他本是守旧派核心人物林纾的门生,致其最终从拥护文学革命,不经意间走到新派的对立面去了。
1919年3月末,张厚载被北大除名,布告中所列原因为“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
那么所谓“传播无根据之谣言”,自然是指他在报刊上大肆渲染仲甫先生“狎妓”一事,以抹黑新派,并无中生有地散布“北大文科学长将易席,陈独秀即将卸职”的谣言。致使北大一时成为各方保守势力攻击的目标,蔡元培先生本人也面临着来自政府和议会的多方施压。
当然,张厚载在林纾与蔡元培的论争中,也起了策划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或许是让蔡先生痛下狠手,令其退学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亦未可知。
年轻的张厚载为了意气之争,卷入了彼时已具有政治意味的新旧文化冲突,充当了“递刀者”,最终也让自己身败名裂。张厚载离开北大后,又经蔡元培先生推荐,进入北洋大学学习。毕业后投身戏剧评论,先后又入职银行,兼任各大名报的编辑,笔耕不辍,直到1955年于上海病逝,总算是寂寂无闻。(不象剧中演绎的那样回头进了京师警察厅,继续与新派为敌。)
然而,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并非张厚载的八卦,而是关于北大去陈的因果。
电视剧中,在有关守旧派诬蔑、诋毁、攻击仲甫先生方面,没少着墨,甚至不只是报端登载,他们还把侮辱性的标语张贴到陈家门口,直令高君曼女士备感屈辱,这些当然是有意夸大敌方进攻态势,以让故事更具可看性。
不过尽管如此,观众也只是看到守旧派在反复攻击仲甫先生“私德”,骂其是“伪君子”,至于具体是哪方面的私德,让人家抓住了什么把柄,似乎语焉不详。反正守旧派就不是好东西,只会无中生有,造谣中伤。
而且剧中没有3.26秘密会议一节,甚至也没有明确陈被停职,并给假一年之说。看起来似乎是陈主动提出辞职,蔡挽留不下,只得忍痛割爱,放虎归山了。
故而有观众看后对陈离开北大极为不解。我就看过有观众发的贴子,先是困惑陈何以会离开北大?接着就从剧集中自己找到了答案:
一是仲甫先生自己所言,“北大已经形成了各个学派,蔡公,您当年安排我做的事情,也都已经实现了,这个时候,该是我离开北大的时候了”。
二是蔡先生所言,“我明白北大这个舞台太小了,你是一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人,应该到更大的地方去发展。”
想必大多数人观看此剧,都是处于这样的认知,毕竟了解这段历史,并有意严肃探究历史的人并不多见。
关于北大去陈的真实原因,我在前文已经探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不过对于狎妓一事,一如前文所述,就凭仲甫先生一生狂放姿肆的性格,以及其它友人的相关记述,笔者依然相信张厚载的披露并非完全无中生有。这样说并非有意中伤先生,毕竟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大贤,内心格外崇敬。只所以探究历史真实,就是要说明历史决定论之谬,历史总是充满着无数的巧合与偶然。何况对于创造了历史的历史人物而言,人性上的些许瑕疵,何足道哉。
1919年3月26日深夜,蔡元培等人在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汤尔和家里开的一个小会,最终改变了陈独秀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会议决定,以体制改革为名,罢免陈的文科学长职务,让陈“体面”下台。陈虽被解职,仍是北大教授,只是被学校给假一年。但以陈的狂傲,岂肯再留,闻讯后第二天便离开了北大,并再未参加过北大“教授治校”的“评议会”。
而在剧中,仲甫先生直至离京去上海前都始终与北大同人在一起,从事各种活动。倘真如此,作为堂堂北大教授,青年领袖,完全犯不上于6月11日,以身涉险,亲自到街上散发传单,以致被捕入狱。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后来出版的《胡适书信集》中可以找到一些佐证。作为老友,胡适先生终生都在为陈惋惜,每当提到1919年3月26日晚上的那一次密谋,就愤愤不平。按照他的理解,倘若仲甫先生一直留在北大、生活在那批信奉自由主义的“老朋友”中间,是不会思想严重左倾并成为中共创始人的。陈独秀如不离开北大,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缰而演变为“五四运动”。倘仍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应当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即使去散发传单,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即使被捕了,出狱后仍可回到北大。(注意了,这里胡适记述的是“去独自散发传单”,而非象剧中与李大钊、高一涵、赵世炎等一起。)
1935年12月28日,胡适在致汤尔和信中,再次表达了对汤尔和、沈尹墨在那晚的主张去陈的强烈不满。他称,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时任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在胡适看来,3.26密会,对后世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以后中共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是夜先生(蔡元培)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馀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诚如胡适先生所言,北大去陈,是陈的思想发生戏剧性转变的重要起点。此前,陈独秀一直倡导的是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信奉法国卢骚的“自由平等博爱”,对马克思主义并无多少认知,更加谈不上信仰。在回到上海之前,陈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是一位后进。”(《胡适口述自传》)
客观地说,既在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还对杜威的“民治主义”思想称赞不已,并声称“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
你可能会说,彼时杜威博士正在中国访问,加之好友胡适,杜威博士的门生,为之奔走,陈独秀此文不过是应景之作,不必过度理解。那么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每当李大钊跟他探讨布尔什维主义时,他也是一再谦虚地表示,“我对此研究不多”。由此可见陈独秀此时思想倾向处于何种状态。
“正值人生低谷,遭遇失业,生活困顿,情绪低落的时候,1920年5月,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来到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通过这次接触,双方达成了合作意向,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自此,陈独秀全面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和建党理论,向德先生那面旗帜说再见,踏上了一条曲折、漫长、而又痛苦的革命之路”。(《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
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就公开亮明了自己全新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通篇充满了俄式的语言和特有的“阶级斗争”逻辑。他声称,“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那么,要彻底改造这个社会,就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
而在此文中,他一直倡导的德谟克拉西(民主),已不再是改造中国的利器,而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肇始于1915年的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新文化运动“命名的思想启蒙,历经四年,最终湮灭在新的俄式革命的历史大潮之中,他的倡导者和送葬者都是陈独秀。他亲手创造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亲手毁掉了他们。
至于陈独秀晚年,经过了失败和磨难,历经痛苦的反思,被他抛弃十数年不用的“德谟克拉西”,又再次被祭起,在思想上绕了一个大圈子,又重新回到民主与科学的轨道上来,则是后话。更多内容请参阅《可还记得一百年前的德赛先生》。
(我本聪聪 202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