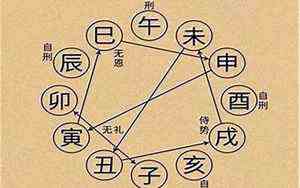Zeno集团将负责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公关工作
根据来自芝加哥的消息显示,本月18-19日,美国奥运会和残奥委员会(United States Olympic & Paralympic Committee,简称USOPC)已聘请芝诺集团(Zeno Group)处理20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公关工作。
即将到来的赛事支持
实时公关通信技术集团芝诺(Zeno Group)声明,此次合作离不开福莱国际(FleishmanHillard)与各路公关策划团体的支持,能够为美国国家体育队争取到2024年各大赛事尤其是巴黎奥运会与残奥会的机会。
芝诺集团的职责重点是重振美国国家队的品牌形象,并吸引现有的奥运会赛事粉丝,以及更多新来的粉丝。芝诺将与USOPC的传统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包括USOPC的基金会(USOPF)、合作企业和私人赞助商,乃至国家管理机构(NGB)等。
明年残奥会将于明年夏天在巴黎奥运会后举行,并支持美国队在2023年的里程碑时刻,这项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芝诺在USOPC进行的竞争性审查后,赢得了这项业务,直到2024年夏季奥运会,将始终处理美国国家奥委会与残奥委会指派的营销和传播工作,并且名列USOPC专属代理机构名单的一部分。
同时,公关机构Wieden+Kennedy(WK)负责创意策略,包括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首次亮相的广告;体育和娱乐公关机构CSM正在处理体验式营销,营销机构Next League正在改造美国国家队的官方网站。
芝诺集团驻芝加哥消费品牌负责人执行副总裁艾莉森·麦克拉姆洛克(Allison McClamroch)将领导从现在开始到2024年的客户工作。
“从USOPC方面而言,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未来有很多机会,”USOPC的首席对外事务官凯特·哈特曼说,“当我们寻求借助美国国家队鼓舞人心的故事进行讲述工作以推动文化驱动力时,很高兴能够与芝诺集团合作,帮助我们在奥运会和残奥会运动与下一代美国体育粉丝之间,建立和提升有意义的联系。”
“疯狂”科学家菲尔·肯尼迪:为了研究“脑机接口”,他切开了自己大脑
编者按:这篇讲述了神经科学家菲尔·肯尼迪(Phil Kennedy)为了推进“脑机接口”研究,决定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的故事。作者是丹尼尔·恩贝(Daniel Engber),他从肯尼迪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你不能总是规划你未来的道路。有时候你必须先建立它。文章发表在《连线》杂志,由36氪编译。
脑部手术一共持续了11个半小时。从2014年6月21日下午开始,一直延伸到第二天的加勒比海上太阳升起。当天下午,麻醉药效过后,神经外科医生走了进来,摘下了他的金属框眼镜,把它举起来给那个脑袋上缠满绷带的病人辨识。“这叫什么?”他问。
菲尔·肯尼迪盯着眼镜看了一会儿。然后,他的目光飘到天花板上,然后又转移到了电视上。“呃......呃......呃......呃,”他过了一会儿结结巴巴的说道,“......呃......呃......呃......”。
“没关系,慢慢来,”外科医生乔尔·塞万提斯(Joel Cervantes)说,并尽量表现得很冷静。肯尼迪再次试图回应。他看起来就像是在强迫自己的大脑工作,就像一个喉咙痛的人忍受下咽一样。
与此同时,外科医生的脑海里一直在飘荡着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我不应该这样做的。”
几天前,肯尼迪抵达伯利兹市的机场时,他非常清醒,没有任何问题。塞万提斯没有任何医疗需要来打开他的头骨。但肯尼迪想做脑部手术,他愿意支付3万美元来完成这项工作。
肯尼迪曾经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一名瘫痪患者的大脑中植入几个电线电极,然后教导患者用他的意念控制电脑光标。肯尼迪称他的病人是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媒体称赞他的壮举是人类第一次通过脑机接口进行交流。从那时起,肯尼迪将他的一生奉献给建造更多更好的半械人的梦想,并想要开发出一种将个人思想完全数字化的方法。
到了2014年的夏天,肯尼迪决定,推进他的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它变得个人化。为了实现下一个突破,他将试着在一个健康的人类大脑上做实验。也就是他自己。
因此,肯尼迪的伯利兹之行就是为了做手术。当地一位前夜总会老板保罗·鲍顿(Paul Powton)负责管理肯尼迪行动的后勤工作,塞万提斯是伯利兹的第一个本地出生的神经外科医生,负责操作手术刀。鲍顿和塞万提斯是Quality of Life Surgery的创始人,这是一家治疗慢性疼痛和脊柱疾病的医疗旅游诊所,也提供腹部整形,鼻子整形,胸部缩小和其他医疗增强服务。
起初肯尼迪聘请塞万提斯进行的手术——在他自己的大脑表面下植入一组玻璃和金线电极——似乎进展得相当顺利。手术过程中没有出太多血。但他的复苏充满了问题。两天之后,肯尼迪正坐在他的床上,突然间,他的下巴开始发抖,他的一只手开始抖动。鲍顿甚至担心这次癫痫发作会破坏肯尼迪的牙齿。
他的语言也一直存在着问题。“他不能表达想法了,”鲍顿说。“他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因为他什么都说不出来。”肯尼迪仍然可以说出音节和一些零散的单词,但是他似乎已经失去了把它们绑定成短语和句子的胶水。当肯尼迪抓起一支笔并试图写出一条信息时,只写出了一堆随机凌乱的字母。
起初,鲍顿对他所谓的肯尼迪的《夺宝奇兵》的科学方法印象深刻:他长途跋涉去了伯利兹,打破了标准的研究规则,用自己的大脑去赌博,现在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认为我们毁了他的后半辈子,”鲍顿说。“我在想,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当然,出生在爱尔兰的美国医生要比鲍顿和塞万提斯更了解其中的风险。毕竟,肯尼迪是发明了这种玻璃和电极的人,并监督了其他近六个人的植入过程。所以问题不在于鲍顿和塞万提斯对肯尼迪的做了什么——而是菲尔·肯尼迪对自己做了什么。
自从有了计算机以来,就有人一直在想办法用意念控制它们。1963年,牛津大学的一位科学家报告说,他已经想出了如何使用人类的脑波来控制一台简单的幻灯片投影仪。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西班牙神经科学家何塞·德尔加多(José Delgado)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一个斗牛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活动,上了头条新闻。德尔加多发明了一种他称之为无线电收发器的装置——一种无线电控制的大脑植入物——可以收集神经信号, 并对大脑皮层产生微小的冲击。德尔加多踏入斗牛场后,他亮出一个红色的斗篷来刺激公牛发起冲锋。随着公牛靠近,德尔加多在他的无线电发射机上按下了两个按钮:第一个触发了公牛的尾状核,使它停了下来;第二个按钮让它转身,向墙壁冲去。
德尔加多梦想着用他的电极直接触及人类的思想:阅读它们,编辑它们,改进它们。“人类正处于一个进化的转折点。我们非常接近有能力构建我们自己的精神功能了,”1970年,尝试在精神病患者的大脑里植入相关的植入物后,他对《纽约时报 》说。“问题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想建造什么样的人类?”
毫不奇怪,德尔加多的工作让很多人感到紧张。在随后的几年中,他的计划逐渐淡出,饱受争议,研究资金匮乏,并且受到大脑复杂性的阻碍,这种复杂性不像德尔加多想象的那样,容易受到简单的热线的影响。
与此同时,其他较为温和的科学家们——他们只是想破译大脑的信号——继续将电线放在实验室动物的脑袋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发现,如果你使用植入物来记录来自猴子运动皮层的细胞群的信号,然后你将他们所有的发射平均到一起,你可以找出猴子移动它的肢体位置的方法——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人类病人开发大脑控制假体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但是,这项研究中使用的大部分传统电极植入物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缺点:它们接收到的信号非常不稳定。因为大脑是一种胶状的介质,细胞在被记录的过程中有时会漂移到一定的范围之外,或者最终会因为与尖锐的金属碰撞而死亡。最终,最终电极会被疤痕组织卡住, 信号也会完全消失。
菲尔·肯尼迪的突破——决定了他在神经科学领域职业生涯,并最终使他走上伯利兹手术台的道路——是解决这个基本生物工程问题的一种方式。他的想法是将电极放到大脑内部,这样电极就可以安全地固定在大脑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把一些裹着特氟隆的金线的尖端固定在一个中空的玻璃锥体内。在同一个微小的空间里,他插入了另一个关键部分:坐骨神经的薄片。这种生物材料的碎屑将使附近的神经组织受精,吸引来自局部细胞的显微臂展开到锥体中。肯尼迪并没有将一根裸露的电线插入大脑皮层中,而是诱导神经细胞在植入物周围编织它们的赘生物,把它锁在一个位置上,就像长在常春藤里的棚架一样。 (对于人类受试者, 他会用一种化学鸡尾酒取代坐骨神经来刺激神经生长。)
玻璃锥体的设计似乎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好处。使研究人员可以长时间将电线放置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不用在实验室的单个会话中捕捉大脑活动的片段,而是可以收听到大脑电波的终生音轨。
肯尼迪称他的发明是神经营养电极。在想出这个主意后不久,他辞去了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学术职位,并创办了一家名为Neural Signals的生物技术公司。在1996年,经过多年的动物实验,Neural Signals得到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允许将肯尼迪锥形电极植入人类患者体内。1998年,肯尼迪和他的医学合作者埃默里大学神经外科医生罗伊·贝凯(Roy Bakay),接待了那个将使他们成为科学界名人的病人。
52岁的约翰尼·雷(Johnny Ray)是一个石膏板承包商,也是一个中风的老兵。受伤后,除了脸部和肩膀能轻微抽搐外,其他地方都瘫痪了,他只能用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他可以通过眨眼来回答简单的问题,眨两次表示“是”,一次表示“否”。
由于雷的大脑无法将信号传递到肌肉中,肯尼迪试图窃听雷的大脑信号,以帮助沟通。肯尼迪和贝凯在雷的主要运动皮层中放置了电极。(他们首先把雷放进核磁共振成像仪里,并要求他想象着移动他的手,然后他们把植入物放在他的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中最明亮的部位。)一旦锥体到位,肯尼迪将它们连接到植入在雷头盖骨顶部的发送端上,就在头皮下方。
肯尼迪每周与雷一起工作三次,试图解码来自他运动皮层的波,然后将其转化为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雷学会了通过思考来调整植入物的信号。当肯尼迪将他连接到一台电脑上时,他能够使用这些来控制屏幕上的光标(尽管只是一条从左到右的线)。然后他可以通过抖动肩膀触发一个鼠标点击。通过这种设置,雷可以从屏幕键盘上选择字母,并慢慢拼出单词。
“这就是最前沿的东西,是星球大战里的东西,” 贝凯在1998年10月对一群神经外科医生说。几个星期后,肯尼迪在神经科学协会的年度会议上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足以让约翰尼·雷的神奇故事——基本全身瘫痪,现在能用大脑来打字——出现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报纸上。那年12月,贝凯和肯尼迪受邀做客《早安美国》。1999年1月,他们的实验新闻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上。“在医生和发明家菲利普·R·肯尼迪准备让一位瘫痪的人用他的想法操作电脑时,”文章开头写道,“在这间医院的房间里,历史性的一幕似乎正在展开,肯尼迪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在约翰尼·雷身上获得成功之后,肯尼迪似乎处于一个大事件的边缘。但是当他和贝凯在1999年和2002年为两名患者植入大脑植入物时,并没有推动该项目向前发展。(一名患者的切口没有愈合,植入物必须得移除;另一名患者的病情发展很快,导致肯尼迪的神经记录毫无用处)。 2002年秋天,雷死于脑动脉瘤。
与此同时,其他的实验室在大脑控制的假体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设备——通常是几毫米见方的小接头,上面有几十条裸露的导线伸入大脑中。 在微型神经植入领域的战争中,肯尼迪的玻璃和锥形电极看起来越来越像Betamax:一种可行的、有希望的技术,但最终没有成功。
肯尼迪与其他研究脑机接口的科学家相比,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硬件。他的大多数同事都专注于单一类型的神经控制假肢,五角大楼喜欢通过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来资助这种研究:一种帮助患者(或受伤的老兵)使用假体的植入物。到2003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已经在猴子身上植入了一套植入物,使它能够用精神控制机器人手臂将一块橘子送到嘴里。几年之后,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报告说,两名瘫痪患者已经学会使用植入物来精密地控制机器人手臂,其中一个甚至能够从瓶子里喝咖啡了。
但肯尼迪对机器人手臂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雷的精神光标显示,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电脑分享他们的想法,即使这些想法像沥青一样以每分钟三个字符的速度流出。如果肯尼迪能够建立一个像健康人的演讲一样流畅的脑机接口呢?
肯尼迪面临着很多方面的挑战。人类的言语比肢体的任何运动都复杂得多。在我们看来,一个基本的行动——措辞——需要协调收缩和释放超过100多块不同的肌肉。 为了构建肯尼迪想象的那种工作语言假体,科学家必须找出一种方法来从少数电极的输出中读出所有精细编排的声音语言。
所以,肯尼迪在2004年尝试了一些新的东西,当时他将他的植入物放入了最后一名瘫痪病人的大脑中,这个年轻人名叫埃里克·拉姆齐(Erik Ramsey),他曾经因车祸而遭受像约翰尼·雷一样的脑干中风。这次,肯尼迪和贝凯没有将锥形电极放置在控制手臂和手的运动皮层部分。他们把电线沿着大脑边缘的一条大脑组织的条带推向更深的地方。在这个区域的底部有一块神经元,它向嘴唇、下巴、舌头和喉咙的肌肉发出信号。
使用这个装置,肯尼迪教拉姆齐通过合成器发出了简单的元音。但肯尼迪不知道拉姆齐的真实感受,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拉姆齐可以通过向上或者向下移动眼睛来回答是或否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因为拉姆齐眼睛有问题而改变了。肯尼迪也没有办法证实他的语言试验。当他记录拉姆齐大脑的信号时,他曾要求拉姆齐想象一些单词——但肯尼迪无法知道拉姆齐是否真的在默默地“说”了这些单词。
拉姆齐的健康状况下降了,植入他头部的电子设备性能也下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尼迪的研究计划也受到了影响:他的资助没有得到续约;他不得不让他的工程师和实验室技术人员离开;他的合作伙伴贝凯去世了。肯尼迪只能单独工作或临时雇用一些人来帮忙。(他仍然在他的神经科诊所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治疗病人)。他确信,如果他能找到另一个病人的话,他肯定会取得另一个突破——理想的情况是,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说出话来。通过在ALS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早期阶段测试他的植入物,他有机会在人说话时将神经元的活动记录下来。这样,他就可以找出每个特定声音与神经线索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将有时间训练他的语言假体——改进其解码大脑活动的算法。
但在肯尼迪找到ALS患者之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撤销了对他植入物的批准。根据新的规定,除非肯尼迪能够证明它们是安全的和无菌的。他表示,他被禁止在更多的实验对象身上使用电极。
但肯尼迪的野心并没有减弱。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溢出来了。在2012年秋天,他自己出版了一部名为《2051》的科幻小说,讲述了像肯尼迪一样的爱尔兰出生的神经电极先驱者阿尔法(Alpha)的故事:大脑连接在一个2英尺高的生命支持机器人上。这部小说为肯尼迪的梦想提供了一个轮廓:他的电极不仅仅是帮助瘫痪病人进行交流的工具, 而且还将成为一个强化和控制的未来的引擎,在这个未来里,人们的大脑可以在金属外壳中存活下来。
在出版他的小说时,肯尼迪已经知道他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了。这个以在病人体内植入第一个脑机接口而闻名的人,将再次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管他呢,”他想。“还是我自己来吧。”
在伯利兹进行手术几天后,鲍顿每天都会去肯尼迪康复的宾馆进行一次日常访问。肯尼迪的恢复情况继续恶化:他越努力说话,就越觉得自己被“关”起来了。显然,美国没有人愿意来接替鲍顿和塞万提斯。当鲍顿打电话给肯尼迪的未婚妻,并告诉她并发症时,她并没有表示太多的同情。“我试图阻止他,但他不听,”她说。
然而,在这次的访问中,情况开始好转。那天天气很热,鲍顿给肯尼迪买了一杯酸橙汁。当两个人走进花园时,肯尼迪仰起头,轻轻地叹了口气。“感觉很好,”他喝了一口橙汁后,脱口而出。
研究人员作为实验对象2014年,菲尔·肯尼迪在伯利兹聘请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他的大脑中植入几个电极,然后在他的头皮下面植入一组电子元件。回到家中,肯尼迪利用这个系统在数月的实验中记录自己的大脑信号。他的目标是:破解人类语言的神经编码。
在那之后,肯尼迪仍然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他可能会看着铅笔,称之为钢笔——但他的流利程度有所提高。在塞万提斯觉得他的患者已经恢复一半了的时候,他就让他回家了。他最初害怕自己会毁掉肯尼迪的生活的结论毫无根据;使他的病人短暂被“锁”在里面的语言缺失只是术后脑肿胀的一种症状。如果能控制住,他就会没事的。
几天后,当肯尼迪回到办公室给人看病的时候,他中美洲历险的最清晰的痕迹是一些挥之不去的发音问题,还有他剃光的、缠着绷带的头,有时他把它藏在一顶五颜六色的伯利兹帽子下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肯尼迪一直在服用抗癫痫药物,等待他的神经元在头骨中的三个锥形电极内生长。
然后,在同年10月,肯尼迪飞回伯利兹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是将一个电线圈和无线电收发器连接到从他的大脑中伸出的电线上。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尽管鲍顿和塞万提斯对肯尼迪想要塞在头皮下的部件感到迷惑不解。“我有点惊讶它们竟然这么大,”鲍顿说。这些电子产品有着笨重的复古风格,让在闲暇时间摆弄无人机的鲍顿感到不解的是,怎么会有在他的脑袋里缝上这么一个老式的小玩意儿:“我想说‘你没有听说过微电子吗,老兄?’”
肯尼迪第二次从伯利兹回到家后,就开始了他伟大的自我实验的数据收集阶段。感恩节前一周,他走进实验室,开始记录自己的大脑活动,大声地对自己说不同的短语,比如“我认为她觉得动物园很有趣”和“工作的乐趣让男孩说哇”,同时轻按一个按钮帮助他的单词与神经轨迹同步,就像电影制片人的拍板同步图片和声音那样。
在接下来的七周里,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半给病人看病,然后在下班后的晚上自己进行一系列测试。这个实验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持续太长时间。他头皮上的切口从来没有完全在庞大的电子产品堆上愈合。在脑袋里植入完整的植入物仅88天之后,肯尼迪又回到了手术刀下。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去伯利兹:保护他的健康的手术不需要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而且还能用医疗保险报销。
2015年1月13日,一位当地的外科医生切开了肯尼迪的头皮,剪断了他大脑中的电线,并取下了电线圈和收发器。他并没有试图将肯尼迪的皮层中嵌着的三个玻璃锥形电极挖出来。让它们在那里,沉浸在肯尼迪的脑组织中,可能会更安全。
失去语言是的,通过脑电波直接交流是可能的。但是它的速度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其他替代语言的方法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
肯尼迪的实验室坐落在亚特兰大郊区,当我在2015年5月的某一天在那里与肯尼迪会面时,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夹克,打着蓝色斑点的领带,他的头发整齐地分开,并从前额梳过来,显露出左侧太阳穴的一个小凹陷。“把电子产品放进去的时候,”肯尼迪略带爱尔兰口音说道。“牵引器拉动了我颞肌的一根神经,使我无法抬起眉毛。”的确,我注意到了手术使他的脸上出现了不对称的下垂。
肯尼迪同意给我看他在伯利兹的第一次手术的视频,这个视频被保存在一个老式的 CD-ROM 中。当我做好心理准备去看站在我旁边的人的大脑后,肯尼迪把将光盘放入运行Windows 95系统的台式计算机的驱动器中。它散发出一种可怕的噪音,就像某人正在慢慢磨刀一样。
光盘的加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有时间开始谈论他这个非常规的研究计划。“科学家必须是个人,”他说。“你不能通过委员会来做科学研究。”当他继续谈论美国是如何由个人而不是委员会建立的时候,光盘驱动器的噪音就像一辆马车沿着岩石小道滚滚而下。“来吧,机器!”他说,当他不耐烦地点击屏幕上的一些图标时,打断了他的思路。“哦,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刚刚已经插入的光盘!”
“我认为‘脑部手术是非常危险’的看法太狭隘了,”他继续说道。“脑外科手术并不困难。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做,你只需要去做就行了,不要听反对者的意见。”
最后,个人电脑上出现了一个视频播放器窗口,显示出肯尼迪头骨的图像,他的头皮被钳子拉开。磁盘驱动器的噪音被骨头上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摩擦声音所取代。“哦,所以他们在钻我可怜的脑袋,”当我们看着他的开颅手术开始在屏幕上播放的时候,他说。
“帮助ALS患者和瘫痪患者是一回事,但这不应该是我们停下的地方,”肯尼迪说。“第一个目标是恢复说话。第二个目标是恢复运动,很多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会变成现实,他们只是需要更好的电极。而第三个目标就是开始强化正常人。“
他打开另一个视频,我们看到他的大脑暴露出来——一片闪闪发光的组织, 上面布满了血管。塞万提斯将电极刺入肯尼迪的神经胶状物中,并开始拉扯导线。每隔一段时间,戴蓝手套的人都会停下来,用明胶海绵擦大脑皮层来止血。
“你的大脑将比我们现在拥有的大脑要强大得多,”当他的大脑在屏幕上跳动时,肯尼迪继续说。“我们将把我们的大脑提取出来,并将它们连接到为我们做所有事情的计算机上,而大脑将继续存在下去。”
“你对此感到兴奋吗?”我问道。
“是啊,我的天啊,”他说。“这就是我们的进化的方向。”
坐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盯着他的旧电脑显示器,我不太确定我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看起来,技术总是会找到新的、更好的方式让我们失望,即使它每年都变得更加先进。我的智能手机可以从我粗糙的手指滑动中打出来单词和句子。但我仍然会诅咒它出现的错误(该死的自动更正!)。我知道,即将到来的技术远比肯尼迪笨重的电子设备、以及我的谷歌 Nexus 5手机都要好。但是人们真的愿意把他们的大脑托付给它吗?
在屏幕上,塞万提斯戳穿肯尼迪皮层的另一根导线。当我们接着看视频时,肯尼迪开始偏离我们关于演化的讨论,他就像在电视机前的体育迷那样,对着屏幕发号施令。“不,不要那样做,不要把它举起来,”肯尼迪对在他的大脑上操作的那双手说。“它不应该从这个角度进入,”他回到电脑前向我解释道。“推,还要加大力度!”他说。“好吧, 那就足够了, 足够了。 不要再推了!”
现在,侵入性大脑植入物已经过时了。神经假体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赞成一种方法,即在脑的裸露表面上铺设一个8×8或16×16的平面电极网格。这种被称为脑皮层电图记法(ECoG)的方法比肯尼迪的方法更加敏感、覆盖面更加广阔、但在某些方面会更加模糊:它不是调谐到单个神经元的声音,而是听一个更大的合唱团的声音,每次多达数十万个神经元。
ECoG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合唱曲可以传达足够的信息,让电脑能够解读大脑的意图——甚至是一个人想要说的单词或音节。一些数据的模糊可能是好事:当你需要交响神经的声音来移动你的声带,嘴唇和舌头时,你并不想只注意到一个不靠谱的小提琴手。ECoG网格也可以安全地在头骨下保持很长时间,甚至比肯尼迪的锥形电极时间更长。“我们不知道极限是多久,但几年或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外科医生和神经生理学家爱德华·常(Edward Chang)说。他已经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正在研究自己的语言假体。
当肯尼迪收集他的数据,以便在2015年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展示的时候,另一个实验室发表了使用计算机和颅骨植入物来解码人类语言的新程序。被称为Brain-to-Text,它是在纽约的Wadsworth Center与德国和奥尔巴尼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的,在对7名植入 ECoG 网格的癫痫患者身上进行了测试。每个研究对象都被要求大声朗读大量的内容,同时将他们的神经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研究人员使用ECoG曲线来训练软件,将神经数据转换为语音,并将其输出转化为预测语言模型。 这个软件的工作原理有点像你手机上的语音转换引擎,可以根据之前发生的事情猜测出哪些单词会出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系统起了作用。“我们建立了一种联系,”这项研究的合著者、 ECoG 专家格温·沙尔克(Gerwin Schalk)表示。“我们发现它能更好地重建口语文本。”早期的语音假体研究工作表明,单个元音和辅音可以从大脑中解码出来,现在沙尔克的小组已经证明,尽管困难而且容易出错,从大脑活动解码出完整的口语句子是可能的。
但即使是沙尔克也承认,这充其量只是对概念的证明。要让人们把完整的想法发送到计算机上还需要很长时间,他说——甚至在人们发现它真的有用之前,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想一下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语音识别软件吧,沙尔克说。“1980年是80%的准确率,在工程方面,80%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但它在现实世界中毫无用处,“他说。“我还是不用Siri,因为它还不够好。”
与此同时,还有更简单和更实用的方法来帮助那些说话困难的人。如果病人可以移动手指,他可以用莫尔斯电码键入信息。如果患者可以移动眼睛,她可以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眼球追踪软件。“这些设备很便宜,”沙尔克说。“现在你想用10万美元的大脑植入物取代其中的一种,只是为了取得比这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你会去做吗?”
我尝试着将这个想法与过去几年进入媒体视野中的所有令人惊叹的机器人示范结合起来——人们能用机器人手臂喝咖啡,人们在伯利兹将芯片植入大脑。未来似乎总是近在眼前,就像半个世纪前何塞·德尔加多进入那个斗牛场时一样。很快,我们的大脑会生活在计算机里面;我们的想法和感觉很快就会上传到互联网上;我们的心理状态将被共享和当做数据被挖掘。我们已经可以在地平线上看到这个可怕而惊人的轮廓——但是我们往前走,它就会往后退,似乎永远不可触摸。
肯尼迪已经厌倦了这种类似于芝诺(Zeno)与乌龟赛跑的人类进步悖论;他没有耐心总是走到一半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不懈地向前推进:让我们所有人做好准备,迎接他写下的那个2051年的世界,德尔加多认为这个世界即将到来。
肯尼迪最终展示了他从自己那里收集到的数据时,他的一些同事初步表示支持。通过自己承担风险、单独工作和自掏腰包, 肯尼迪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大脑语言记录。常说:“这是一组非常宝贵的数据,不管它最终是否能为一个语言假体的保留秘密。这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其他同事发现这个故事令人激动,但他们有些不理解:在这个不断遭遇道德障碍的领域,这个他们认识多年、一直喜欢的人做出了大胆而出人意料的努力,已经开始了迫使大脑研究走向自身的命运。还有一些科学家只是吓呆了。“有人认为我很勇敢,有人认为我疯了,”肯尼迪说。
我问肯尼迪他是否会再做一次实验。“在我自己身上?”他说。“不。我不应该再这样做。我的意思是,不能在同一侧。“他敲着他的太阳穴,锥形电极尖仍然在那里。然后,就好像是被将植入物植入他的大脑另一边的想法所激励,他开始制定新的电极和更复杂的植入物的计划;为他的工作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而努力;他也在寻找资助资金,让他能够支付开展这一切的费用。
“不,我不应该在另一边做手术,”他最后说。“不管怎样,我没有这方面的电子设备。等我们建好了再问我吧。”这是我从肯尼迪身上学到的东西:你不能总是规划你未来的道路。有时候你必须先建立它。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