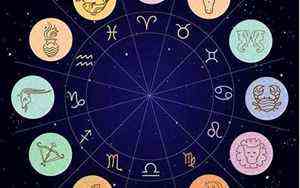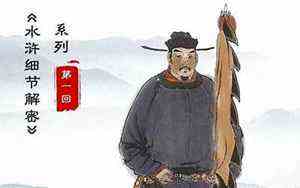“彼、此”释义
什么是“彼”,什么是“此”,这两个字是如何表意的?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先来看一下“此”字的演变图。
来自百度百科
“此”字从止从匕,止即人的脚印或脚之象形,匕字乃一个右向立人的侧视图。就这两个字符的组合,就被人们解读的七零八落。有人说是刑法,踩人的刑法,可在下就知道踩背是现代的一项保健手段,享受的很,哪儿来的什么刑法。[呲牙]
还有人说“此”字是柴字的省写,柴又是古代一种祭祀名称。对此解在下亦禁不住又要发笑了,对他们来说,好象古人除了祭祀就什么事儿就不会干了,什么不解的字都能向祭祀上靠!这些酸腐文人的思想真是可笑![偷笑]
面对奇妙的汉字,后人的智力水平似乎就降到了零点!
对于“此”这个字,我们首先要知道“匕”字的正确意义。人字,左向的字形是阳性的,表示前进的人、活动的人、劳动的人等等乾卦意象,后来即写成了“人”。
右向的人形则表示阴性意象的人,主要就是站立不动的人或死亡的人,坤阴性质的意象。比如考妣之妣就指故去的女性祖先。这个右向侧立之人就演变成了“匕”。
在“此”字中,这个右向立人匕,就表示站立不动的人。
而“此”字中的脚或脚印,就是匕字这个人的脚,在“此”字中就表示该人所站在的地点,也就是说“此”字就表示的是一个人站立的地点,也即说话人站立的地点。
因此,“此”字即非什么脚踏之刑法,亦非祭祀之名!!!
接下来再看看“彼”字。
来自百度百科
“彼”字从彳从皮,彳表示道路和行动,皮表示剥皮,剥动物或植物的皮。那么“彼”之含义又是如何得来的呢
我们还是先研究一下“皮”字。
来自百度百科
“皮”字上的革字头是兑卦意象的字符,表示头部有开口的意义,下部一竖表示某个物体,皮与肉或皮与杆一体的物体。一竖侧面的环状物表示已撕开了部分的表皮。下部的手形表示用手撕开表皮。所以“皮”字就是撕开动植物等的表皮的意思。
“皮”字,含有两者(皮与皮下之物)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分开成两者的意义,所以加上表示行动的彳字,“彼”字就主要取“皮”字的这种动词性意义。
这种动词意义的最终结果,就是分开的两者,即某主体对象与有关联的另外的对象,而这个另外的对象就是彼。
由此可见,“彼”字并非是什么形声字,而是典型的会意字。
“德”的概念史︱“德”是如何拥有超凡力量的?
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极其注重“德政”和“德治”。儒家强调,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天命、德政与君主的个人品德。至迟到西周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就已是“德”,施政着重于“敬德保民”。自此之后,几乎历代相沿。
不夸张地说,“德”的观念深深渗透在中国文化的肌理之中。其实“德”经还在“道”经之前,而儒家文化特别推崇修身“立德”,以“德”为做人立身之本。美国汉学家艾兰给它作了一个谨慎的界定:“‘德’是某种人所特有之事,是其他生命所没有的人心的一个表现方面。”确实,龚鹏程也注意到,中国“讲人的尊贵,主要是从才德能力上说,希伯来则首先由形体上说”,所谓“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
这个概念,由于在后世经过儒家、道家的阐释与演绎,常被世人普遍理解为“道德”。但另一方面,汉语中又有诸如“积德”这样的说法,历代还将王朝兴衰以“五德终始”来解释,如果说“德”仅指“道德”,或是某种人所特有的品质,显然无法解释诸如“土德”、“木德”这类用法。这都表明,在古人的心目中,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很可能是理解中国文明的一把钥匙。
研究先秦思想史的西方学者早就意识到,“德”是中国思想中特别复杂难译的概念之一,“有一系列难于理解的意思”,列文森认为它“意味着围绕‘美德(virtue)’或(美德的)‘力量(power)’这一概念的一堆意义”,很难确切对译。以往一般英译为“virtue”(性能,德性,美德)或“inner power”(内在力量)。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则将之译为“potency”(超凡力量),并强调指出,这和拉丁文中表示“德”的virtus一样,是指称某种内在的本质(intrinsic),而且它“传统上用作某种无需运用肉体力量便可促使他人行动的善良或邪恶的力量。孔子在赢得普遍效忠的周代‘神授力量’的意义上使用它,但把这个概念道德化并拓展宽泛,以至于使之成为自我遵循并使他人遵循‘道’的能力”。
包括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这种“超凡力量”含义上的“德”,可与波利尼西亚土著社会中的“神力”(mana)参照。在波利尼西亚文明中,mana表示神灵附体,是社会地位、权威和力量的来源,也常译作“魔力”或“魅力”。由此解释“五德终始说”即可豁然贯通:所谓“五德”即天地之间五种循环交替的神秘力量,而每一个朝代、帝王即是其代表和化身。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庸》第十六章孔子所说的话:“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朱熹注解认为此处“鬼神”指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而“德”乃指“情性功效”。这当然是理学家的解释,但究其原始本义,恐怕此处“德”便是指某种神秘莫测的超个人力量(vast impersonal forces)。
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德”字,含义不明,岛邦男认为其意与“循”相近,李泽厚认为其与礼仪规范有关。但这应该都已是后起之意,从存世文献来看,《庄子·天地》所论恐怕最近于其本来面目:“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这里明白指出:“德”是天地之间化生万物的原始力量,而只有顺应天道,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一个人才能成就“德全”。
这又涉及另一层意味:人可以获得“德”这种天地之间的神秘力量。据许慎《说文解字》:“德,升也。”段玉裁认为训作“登”与“得”,从甲骨文字形看,“德”的声旁“彳”表“获得”之意,而右边则是“直”与“心”,其本义应指内心获得的特殊魅力。周策纵在《古巫医与六诗考》中认为,“德”最初的含义应比“道德”或“德性”这样的抽象概念更为具体:“德字所从之直,可能说成从目之直视,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象种子的发芽,所以古时这字既有徼循之意,而更常有生殖潜力的含义,从植、殖、值诸字还可见到一些端倪。德字早期即表示这种繁殖的潜能,《韩非子·解老篇》:‘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可能还保存这初义。德字因此也就有得来之意。”
在此不妨参见英语“德”(virtue)的语源含义:它源于拉丁语词根vir(“man”,男人),现在英语中仍有一系列词与此有关,如virile指“有男性气概的;有生殖能力的;精力充沛的”、而virtuous(有德行的)源出晚期拉丁语virtuosus,本义也是“道德力量;(战争中的)勇气;男性气概”。但在汉语中有所不同的是,“德”不仅表明一种内在的潜能,还尤其强调这是得自天地之间所蕴藏的神秘力量,相当于说“天赋异禀”,因此许景昭《禅让、世袭及革命》一书中认为,在某些语境中,“德”最好译为“favor”(天赐的德性)或“grace”(天赋的德行)。对此种力量,所侧重的与其说是繁殖力、男性气概,不如说是一种能通过无形的感化,促使人顺从的力量,所谓“以德服人”。一言以蔽之,一个人有“德”,就意味着让人看到超凡力量附体显灵(hierophany),即神圣事物通过此人向我们展示它自身。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能将超凡的宇宙力量内化,那自然便是人中最杰出者。据《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这里明确指出:宇宙中有一种无形的精气,能将之内化于心,就是圣人,做到这一点便是“成德”,相当于拥有了鬼神一般的力量。
《说文解字》释“德”为“升”,或许是因登高能更接近于“天”,从而获得这种超凡力量。据《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此处“德”所呈现出来的,几乎像是某种降神的感觉,具有令人敬畏的神圣性,由此才缔造出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礼”。
显然,这样的“德”绝不是普通人都能具备的,它在起初是神王(god-king,或中国所谓“圣王”)的特质与专属。侯外庐则根据西周时期的文献与铜器铭文中,“德”往往与“孝”连文并称这一点,认为“德是先王能配上帝或昊天的理由,因而也是受命以‘我受民’的理由”、“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毛公鼎》也有“丕显文武,上天引厌其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的词句,特指周文王、周武王。王和在仔细辨析后主张,“西周时期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为君者应当具有的品质’。从客观上讲,‘德’是指以‘民’为主体的整个社会对于君主个人的素质要求”,这是“专门为为君者亦即统治者设计的一种角色观念”。
这里他已经点出“德”最初是专就王者而言,但受其唯物史观所限,未能意识到“德”原本并不只是“品质”或“个人素质”,而是一种天赋超凡魅力。这正如“命”在西周时也都是上天对周王之命,专指国祚,不关个人寿命,“德”最初也是上天所赋予统治者的,其个人之“德”即关系到共同体的兴衰。在彝族文献中有一个特殊概念,常被汉译为“威”,有威力、权威、威势的意思,常常用来形容宇宙、祖先、英雄人物、政权、制度等,视为共同体的根本(“彝威、彝荣,不可丢下”),这其实很可能接近于“德”的原始含义。
很多后世所使用的概念,起初都具有宗教意涵。如“福”的本意是上苍所赐的神佑;“礼”则是敬神,《说文解字》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甚至“性”,也与天命观有关,所谓“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上古邦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统治者的“德”,恐怕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见的品质让人相信,此人已被上天赋予超凡魅力,所谓“天命有德”(《尚书·皋陶谟》),故理论上天子必有德。换言之,这是一种基于君权神授的观念,而“德”是统治合法性的资格证明,它论证了权力的合法性,证明上天已经选择此人,这既是个人的特质,又关系到整个共同体的兴衰。《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即是说,只有依靠德治,才能承受天命,保持国祚。
既然如此,就可理解,在古人心目中的“圣王”,起初本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强调他如何协调宇宙秩序,因为“天事”与“人事”是一体的,均为圣王之职责。东汉时成书的《白虎通》中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这里的“天子”就是一个交接天地、接受其超凡力量并理顺所有事物秩序的巫王形象,而“明堂”就是它与宇宙枢纽交通的仪式中心。
如何才能证明一个人具备“德”?对此或许可以类比藏传佛教中找寻转世灵童的过程:通过此人的种种作为与事迹,观察他身边的神性征兆,可以判定他已被上天赐予“德”。此类记载极多,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白虎通》认为可以感应天地,自动召唤祥瑞涌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反过来说,一个人“有德”,即证明他已将天地之间的超凡力量内化为自己的禀赋,而民众的使命就是识别出这样的人物,并追随他,将共同体治理的权力交予此人手中。
公元前655年,晋人假道伐虢,宫之奇劝阻虞公时说了一番话:“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左传·僖公五年》)在此可以明白看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鬼神、上天、人民这决定邦国命运的三者,都以君主的“德”为转移,所谓“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记·乐记》)。
由此来看,中国人所说的“德治”,其实就其本源而言是出于“君权神授”的观念,然而,到后来则演变出复杂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一切的变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生态文明关键词】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生态文明关键词】之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确立的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环境难题、实施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基本原则或“绿色政治共识”。大会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的第七项原则称:“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关系的精神进行合作,以维持、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鉴于造成全球环境退化的原因不同,各国负有程度不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其社会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压力和它们掌握的技术与资金,它们在国际寻求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承担着责任。”它的更直接体现是该大会过程中签署的环境三公约之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该公约的支撑性前提正是世界各国“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依据该公约的第四条,“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基本涵义,首先是指“共同的”责任,即当今世界每个国家都要承担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义责,但与此同时,这种“共同的”责任的大小与分担(理应)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它们也拥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能力),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仍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
应该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与现实责任和当时人均排放上的成员国(区域间)巨大差异,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这一原则以及得到国际社会主体认可的主流性阐释。那就是,发达国家率先实质性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的扶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1997年,该《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上述“有区别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构成了此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法理基础。但是,这一原则规定及相应的“双轨制”减排方案的缺陷是明显的,表面上看是《京都议定书》本身在责任分担上的“厚此薄彼”,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未能充分估计到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迅速崛起而改变着的世界经济格局和温室气体排放形势。结果,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承认或接受这种“有区别的责任”——小布什政府终未批准这份法律文件,而包括欧盟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当它们发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5~2012年)结束后仍不想承担任何约束性的减排任务时,就把关注的重点从第一承诺期指标的落实转向了对条约本身的修改,以达到让发展中国家也尽快参与强制性减排的目的。
2009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本意,是落实两年前巴厘岛会议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即在2012年前达成一个《京都议定书》关于温室气体削减的第二承诺期具体方案,但事实上却成为了《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后国际社会进一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分担与制度设计问题,也就是一种所谓的“后京都时代”问题。国际社会主要集群之间存在着明显而严重的利益与立场分歧,欧盟苦心劝压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弃暗投明”,重新我为全球气候变化政治的领导者,而它们又都强烈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增长国家,开始承担受约束的和可核查的减排责任,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国际社会最事携群体,即所谓的全球气候变化最脆弱国家,像马尔代夫、尼泊尔和蒙古,则同时要求西分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切实履行自己抑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与义务。结果,贯本哈根会议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气候变化脆事国家之问的“立场表白”及其辨护,焦点是《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主流性国释及其双轨制框架的存废守合。西方国家不是把关注重点放在对《京都议润书》减排茶。落实的检查评估,而是如何使发展中国家明确承诺具体而且可核查的减排责任,这在发属中国绿着来无异于对《京都议定书》的期量而另起炉灶。最终,哥本哈根会议只纯强达成了一个遭到各方批评的、虚弱的《哥本哈根协议》。
经过2010年墨西哥坎昆会议和2011年南非德班会议的过渡,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选择了里约峰会20周年这一契机举行了“里约+20峰会”。该会议有两大主题,二是总结与反思1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可持续发展”相关公约及其战略的实际进展,二是倡导与推广欧美国家所青睐的新概念“绿色经济”。对于前者来说,自哥本哈根大会起,国际社会对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共同政治和治理努力的热情与预期巨空前降低,因面,各界人士对于这次会议的“成果”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对于后者来说,“绿色经济”概念前加了“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修饰性限制,可以大致理解为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核心欧盟国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利益关切和目前它们自身也深陷经济衰退困境现实的“双重妥协”。因此,在理念层面上,“绿色经济”相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次等级意义上的概念,因为后者要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的可持续性等更多的目标性内容(尤其是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之后);在实践层面上,“绿色经济”只有解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度、路径与手段探索时才具有实质性积极意义。因而,“里约+20峰会”也许更应理解为国际社会重聚“可持续发展”目标共识的一种努力,而对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也只是在最一般意义上得到了艰难确认与重申—“绿色经济”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主要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依然主要是一个消除贫困的问题。
可以看出,从里约再到里约,“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理论阐释与贯彻实践,呈现为一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甚至矛盾性的图画。一方面,它在外延上不断扩展或“回归”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关涉的诸多领域(比如,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中就已强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有区别的责任),而这有助于矫正过去数年中国际社会过分局限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尤其是节能减排这一议题。更为重要的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基本意涵已渐趋清晰化。首先,这是一种共同的责任,表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大力倡导绿色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努力致力于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文化转型,等等;其次,这是一种“有区别的责任”,表现在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认可并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区别;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责任区别;能力强国与脆弱国家之间的责任区别;道德层面与现实层面之间的责任区别,等等。而且,尽管民族国家是主要的责任主体所指,但上述划分也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其他行为主体比如国家集团、社会群体或种族等。例如,对于那些生活在极地周围的少数种族或群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存与延续问题,而不能简单用维持生物多样性或生态可持续性,来划定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或可持续发展转型上的“共同责任”。正因为如此,尽管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代表在谈判阶段提出的异议,2012年里约峰会通过的《我们期望的未来》宣言,仍特别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对于可持续发展总目标、而不只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适用性和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在政策意蕴及其贯彻机制层面上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模糊性或“弹性”。这具体表现在:任务的确定及其分配或认领(如何来分担或分享责任?);任务或目标实现的时间表(何时实现哪些阶段性的任务或目标?);各国行动的约束性(力度)与自主性(透明度)(由谁来监督谁的实质性工作与进展?)。从表面上看,这三个方面都更多是从属性的(问题是责任的担当方式而不是有无)和技术性的(如何进行可行性操作),但很显然,正是政策意蕴及其贯彻机制层面上的“共识缺乏”,造成了国际社会制度化“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努力上的“囚徒困境”—谁都希望他方成为违背其现实利益追求的公益捍卫者,或者通俗一点说,“很好,但你先请”。
信息来源:中国林业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生态文明关键词》(主编:黎祖交 本条作者:郇庆治 编辑 吕子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