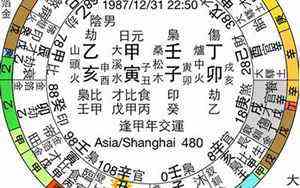回不去的故乡之:破相
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都留有几块疤痕,或被摔的,或被镰刀割的,或被开水烫的,或被伙伴打的,或长疖子留下的,这是出身的一种标志,女孩也不例外。
我曾经和两个农村女孩谈过恋爱,她们脸上皮肤洁白细嫩,但身上某处都留有疤痕。爱美自尊的她们总在被发现疤痕那刹那花容失色。我就轻轻地抚摸她们的疤痕,轻言细语地说:我爱你,包括你的一切,爱你的缺陷超过爱你的优点。
那一刻,她们感动得眉眼含泪,柔情似水,像巧克力在烈日下慢慢融化。
我身上有很多疤痕,腿上,胳膊上都历历可数。最明显的是脸上也有两块。脸上有疤,俗称破相。这对爱美的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经常在电视里看武侠小说,看到破相女子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找一块黑纱,把脸蒙起来,只露出两只黝黑发亮的美丽眼睛,顿添神秘美感,让人浮想联翩。
我是一个破相之人,脸上的两块疤痕,照镜子的时候,都能清楚地看到。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爱照镜子,又怕照镜子。爱照镜子,是盼望奇迹出现,期待一觉醒来,疤痕突然消失不见了,哪怕变小了;怕照镜子,是因为我知道这种奇迹是不会出现的。照镜子时,第一个闯入眼帘的,不是那对浓眉大眼,不是那张堂堂正正的国字脸,而是脸上那两块疤痕——尽管两块疤痕在脸上占的比例并不大。
脸上的两块疤痕,曾让我饱受打击,痛不欲生,而且老担心前途受到牵连——同村一个女孩,考上了师范大学,体检时,就是因为脸上有一块疤痕,就让学校退档了,我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我已经年过不惑,经历了沧桑,对脸上两块疤痕,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两块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时代在我身上做下的记号,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一块疤痕横在两只眼睛之间的鼻梁凹陷处,是一岁多的时候留下的。
当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劳动,奶奶一个人在照看姐姐,哥哥,我,三个孩子,手忙脚乱的。姐六岁,哥三岁,正是调皮的年纪,到处乱跑,奶奶的主要力都放在他俩身上。
我被放在木制的摇篮车里。一岁多,也是喜欢到处乱动乱爬的年纪。不知道是因为摇篮车禁锢了我的自由,还是摇篮车外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挣扎着从摇篮车里爬了出来,在站在摇篮车上那一刻,车倾覆了,我面朝下,重重地摔了下来,鼻梁正好磕在石头做成的门槛边沿,细嫩的皮肉和骨头抗不过坚硬锐利的石头,我的鼻梁被切成两截,血如泉涌。
母亲闻讯赶回来,帮我把断裂的鼻梁用手捏在一起,也没有去医院——当年穷得也没有那个条件。小命是捡回来了,但疤痕就此留了下来。那道疤痕一直随着我成长而成长。当年鼻子小小的,疤痕是横断面,现在鼻子长大了,疤痕仍是横跨过鼻梁。
现在小孩,是几代人的掌中宝,生怕磕着碰着。我们那时候,两三岁就没人管了。再大一点,父母出工,把你反锁在家,到处乱爬。渴了,没人倒水;饿了,没人管饭;病了,没人送医院;拉屎了,没人擦屁股。感冒之类,能拖则拖,不能拖了,父母找些草药喂你吃下,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看医生。
大舅三个女儿,小时候生病,无钱看医,半年内相继夭折。一个儿子,值钱一点,拖不下去了,抱进医院。病是好了,可落下了耳聋后遗症。比起夭折的那些农村孩子,能够活下来,就算幸运了,一两块疤痕算什么?
另一块疤痕是五岁那年留下的,在左脸中央。
那年秋天特别苦,记忆中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生产队的甘蔗大丰收,熬出了一块块又大又方的蔗糖。生产队征集劳动力外出卖糖。卖糖的,工分比跟随生产队出工的高。为挣多几个工分,父亲报名要了一担蔗糖。蔗糖有多重,生产队都是称了的,前后重量要对得上。否则,会扣工分。所以,尽管那晚家里有两箩筐蔗糖,但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落,却没有被赏赐一点点。父亲把那担蔗糖放在他们的房子里管理着,我们几个流了一晚上的口水,下巴处的被单被弄得湿漉漉的,好大一片。
第二天清早,哥姐上学去了,我还在吃饭。父亲挑起蔗糖,跨过门槛,准备出去卖蔗糖了。看着父亲要走,我的心都碎了——我确实太想得到一块蔗糖尝尝,哪怕只有指甲那么大小。
在父亲出门那一刻,我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但被脚下的门槛绊倒了。当时我手里端着碗,嘴里含着筷子——仿佛那筷子就是蔗糖。结果一根筷子折断,一根筷子从嘴里刺破脸颊,钻了出来,一半留在嘴里,一半露在脸外。
这件事弄得一个家庭差点分崩离析。母亲很伤心,带着我回了外婆家,半年没有回来,非要和父亲离婚不可——在母亲看来,父亲没有人情,儿子的份量连 一块手指大的蔗 糖都不如。
伤好后,筷子刺破的那边脸留下了一道疤痕。
两块疤痕,尽管不大,可由于生长的地方不对,损害了我的光辉形象,也在心里留下阴影。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情窦初开的中学和大学,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心理障碍。从小到大,我在班上的成绩是很不错的,但那两块疤痕让我非常自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在心仪的女生面前,尽管自己长得并不丑。
我很想和别人一样,有一张光洁的脸蛋,意气风发,洒满青春阳光,不用躲躲闪闪,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甚至有时候,别人看我一眼,我就下意识地以为他是冲着我脸上的疤痕来的。这两块疤痕助长了我的自卑,学生时代,我静静地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不敢抬头,不敢回答问题,不敢看别人一眼,甚至不敢看黑板。课堂内外,我的眼睛始终落在书本上——在书本上花费的功夫多,成绩自然好,也算是没有自暴自弃。
我也想过一些办法来掩饰那两块让我烦恼不堪的疤痕。首先是像女孩子那样买回擦脸用的什么霜,希望借霜来掩盖。霜是白的,脸是黑的,擦霜后,疤痕是不那么明显了,可弄得一张脸黑白分明,比疤痕显现时更难看,只好作罢。后来想到戴眼镜。镜框边沿和连接两个镜框的眼镜鼻梁刚好把两块疤痕遮住了。起初我的眼睛并不近视,家里也没有近视遗传,戴上眼镜,我就慢慢地习惯了它,从假性近视演变成高度近视了。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人,除了我,都不是近视眼——为遮掩那两块疤痕,我牲牺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记得高中,班上有位漂亮女孩喜欢我,有事没事找我。但因为害怕她看到我脸上躲在镜片后的疤痕,我始终不敢抬头看她一眼。我的自卑让她很无奈,吃的闭门羹多了,她就不和我来往了,后来她转学了。
走的那天,她塞给我一封信,大致意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彼此喜欢,但都是自卑的人,在我漂亮的外表前,你自卑脸上的疤痕;在你优异的成绩前,我自卑自己的平庸。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希望你我都能从作茧自缚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也希望下一个喜欢你的人不要像我,那样辛苦,那样无助。
那封信,对我心理影响很大。晚上躲在被窝里,流了一晚上的泪。那封信,启发了我,也给了我自信。第二天,我摘下眼镜,勇敢地迎着别人的目光,与人对视;勇敢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后来由于高中学习用功了,没有眼镜还真不行,不得不重新戴上眼镜。
但那次感情经历,真让我破茧而出,从自我修砌的阴暗房子中走了出来,不再为脸上有疤自卑。
上了大学,换了一个环境。很多同学都是城里人,细皮嫩肉,光洁如玉,且聪明伶俐,见多识广。在他们面前,我还真有些自卑。但这种自卑,已经不是那两块疤痕带来的了,而是知识能力,品格修养。我努力完善,希望出类拔萃,至少不要离他们太远。
四年大学,我确实做到了,成为所在专业的风云人物。再照镜子,读着脸上那两道疤痕,我已经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的珍惜。
后来参加工作,也看到一些广告,说能治愈疤痕,有时候也有点儿心动,毕竟有瑕的玉与无瑕的玉还是有区别。但只是想想,并没付诸行动。
那两块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有它们,我是完整的; 没它们,我才是残缺的。 我已经习惯了,有一天真没有它们了,我还真不习惯了。 没有了,再找回来,就不容易了。 何况现在没人再在意我脸上的疤痕了——记得有段感情,那个女生摘下我的眼镜,轻轻地吻在那疤痕上,那感觉至今还在,让我感动难忘。
克巴世家|过了二十多年,决定修复脑门上的凹陷疤痕
王小姐是一名宝妈,脑门上有小时候水痘留下的痘坑,也有小时候因为玩耍被小伙伴用石头砸的坑(我在想,王小姐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
随着年龄的增长,疤痕和痘坑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严重的凹陷,但是因为王小姐大大咧咧的性格,啥都不放在眼里,这七个小坑跟随了二十多年 。
(克巴世家|小时候脑门上留下的坑)
啥都不放在眼里的王小姐,在2019年的时候曾在别人的鼓动下到一家问题性肌肤修复机构修复脑门上的小坑,在修复过程中疼的咬牙切齿,遭了这么大的罪,后期也没有看到效果,就这样放弃了修复痘坑、凹疤的念头。
(克巴世家|修复脑门上的凹陷疤痕)
到了2022年,王小姐看着镜子里日渐变老的自己,翻着手机里几年前的照片,顿时万般心酸涌上心头,这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吗?经过三分钟的思考,王小姐决定改变形象,修复痘坑!修复疤痕!
经过上网多方查找、分析对比,最后锁定克巴世家。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王小姐开始了第二次的修复。尽管技术老师说无痛修复,但是介于上一次修复的感受,王小姐还是很紧张。
(克巴世家|修复脑门上的凹陷疤痕)
令王小姐没想到的是,疤痕修复的过程中她竟然睡着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操作,王小姐脸上的凹坑平了,但会有一个结痂掉痂的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尴尬期",过了尴尬期,就是完美的蜕变。
(二百八十九)破相
来娣还在莫名其妙,前面的彩云阿姑的姆妈正好开了后门出来喂鸡,听到叫声也颠着小脚过来。看到来娣的脸后,急切地催着阿爹,“大堂,快用毛巾给来娣脸上擦干净!”
来娣的脸上,还残存着一些被姆妈用扫帚的竹枝戳出来的血迹,没用阿爹动手,来娣用毛巾给自己好好洗了个脸。
脸上残存的血迹
随着她的手逐渐的移动,场上众人的目光也一上一下地游移,他们脸上的表情却很是晦涩,不过来娣在专心擦脸,并没注意。
彩云阿姑的姆妈凑了过来,细看了一番,柔声安慰着道,“丫头,没事,你还小呢,再长长,慢慢印子就淡了。”
说罢,又对阿爹说道,“大堂啊,叫梅英做饭时注意着点,别让丫头吃酱油,深颜色的东西都别吃,说不定还能养得过来。”
只是,大伢却似乎格外兴奋,还在叫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呀,不得了,数都数不过来!”
来娣的好心情突然就飞走了,数都数不过来?那就是说,她脸上的不是血迹,真的是麻点?那不是要比春英姨婆婆做的芝麻食团还要密集了?
芝麻食团
而此时,玉芹家大伢的叫声也引来了施家的两个小伢,他们背着书包正要去念书,也比大伢有教养得多,正在相互咬着耳朵,“来娣阿姑脸上的印子比麻子阿爷的还多还大呢。”
“是呀,以后来娣阿姑就不好看了,是破脸了。”
“笨呀,那叫破相!”
其实来娣并不是太在意自己的脸。那时的农村,人们看重的是女性能不能干,而不是漂不漂亮。不过阿爹脸上的麻子她是天天都看到的,如果真像那些小伢说的,自己的脸变得比阿爹的还要难看的话,总还是不太让人舒服的,尤其这脸还是别人打成这样的。
这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东头港。下午,来娣拿着扫帚在扫场时,刚刚放学回来的章女,连书包都没来得及放下,就跑来将她拉到夕阳底下,细细地查看了一番她的脸。看着看着,泪珠便滚落下来。
泪球滚落
来娣正想安慰一下章女,告诉她自己并不在意,没想到章女却自己抹去了泪水,郑重其事地对她说道,“来娣姐,你别担心,只要你回了魂,慢慢好起来就好。”
小丫头拍着身侧的书包,“以后我每天放学了都来教你识字,你放心,脸漂不漂亮都没啥,你那么能干,如果又识字,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你的。”
来娣一头黑线,章女这说的都是啥?她为什么要让别人喜欢?她已经决定了,以后不讨好任何人。
不过她没有反对识字,现在她每天能做的事屈指可数,剩余的时间也挺无聊的,如果识个字,正好可以打发空闲时间。再说了,她本来就盼望能够念书,只是姆妈没有答应,阿爹也没坚持。既然书念不成,能识字也是好的。
识字
老瘸子早就跟她说过,只要识字,就能走遍四方。如果她识了字,姆妈以后再打她,她就能离开东头港,哪怕不回油坊桥,她也不愁无处可去。
来娣笑了,“好,以后我天天都跟你学字。”
只是来娣不知道,她这一笑,扯动了脸上的肌肉,那些麻点也在夕阳下跳动了起来,一颗颗呼之欲出,变得更大更明显。章女见了,原先已经抹去的眼泪,不由得又涌了出来。
章女跟她姆妈一样,本来就爱美,由己推人,越发得替来娣姐难过起来。多好的来娣姐啊,可惜命不好,挨了大姆妈的一顿打,不仅魂丢了,连相也破了。以后要是嫁不出去,该怎么办?
自己在学堂念书时,可一定要认真,把学到的都教给来娣姐,要帮她长本事!
念书长本事
不管来娣是如何想的,但是村里的大人们自有他们的想法。
有人说,三亭姆姆不道义,就为了一点小事,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害得三麻子家的压子丫头被打得丢了半条命,还破了相,以后东头港又要多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有人说,章梅英是天煞孤星,自己命里没有小伢,连压子丫头都容不下,这样的人黑心黑肠,任何跟她接近的人,不是被她害了,就是被她同化了。没看见那三麻子也变得狼心狗肺了吗?章梅英做下这样丧良心的事,他居然都没有好好调教一下自己老婆,就是因为他已经变得跟章梅英一个样了。
有人说,来娣那个小丫头,生来就是来受罪的,明明家境富裕,偏偏亲生阿爹姆妈狠下心来把她送给三麻子家。来了东头港,三天一小打,五天一狠打,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还要忙着做这做那,一个靠十岁的小丫头,倒是要倒过来贴补三麻子夫妻俩。
挨打
有人说,叫魂那天,步根姆妈将三麻子骂了个狗血淋头,两家人已经彻底恶了,再不走动了。连章春英都受了章梅英的影响,天天得不到步根姆妈一个好眼色,原本因为肚子里又有了小毛头,步根姆妈还算是顾念着,可偏偏弟媳妇沈岚也怀上了。这下子,两个孕妇的待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气得章春英差点动了胎气,而章梅英更是就差鼻子里没冒火了。
这些传言,都是章女放学后来教来娣识字时告诉她的,不过来娣并没有管。她现在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帮着做做饭、喂喂猪羊鸡。这些活,用一只手,慢慢来,都是可以做的,但是草她是不去割的。
然后,便是每天傍晚跟着章女识三个字,她学得很快,章女本想教她更多,但被她拒绝了。章女也要每天割草喂猪呢,不好耽误她太多的时间,每天三个就好。只是她的字写得不太好,没有左手的辅助,要把字写好有点难。
而且,她也没有钱买铅笔和本子,只能用竹枝在门口的场地上练,那字就更丑了。不过她不贪心,能够识字就很好了,写字还是等她的左手好了后再说吧。
写字
回不去的故乡之:破相
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都留有几块疤痕,或被摔的,或被镰刀割的,或被开水烫的,或被伙伴打的,或长疖子留下的,这是出身的一种标志,女孩也不例外。
我曾经和两个农村女孩谈过恋爱,她们脸上皮肤洁白细嫩,但身上某处都留有疤痕。爱美自尊的她们总在被发现疤痕那刹那花容失色。我就轻轻地抚摸她们的疤痕,轻言细语地说:我爱你,包括你的一切,爱你的缺陷超过爱你的优点。
那一刻,她们感动得眉眼含泪,柔情似水,像巧克力在烈日下慢慢融化。
我身上有很多疤痕,腿上,胳膊上都历历可数。最明显的是脸上也有两块。脸上有疤,俗称破相。这对爱美的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经常在电视里看武侠小说,看到破相女子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找一块黑纱,把脸蒙起来,只露出两只黝黑发亮的美丽眼睛,顿添神秘美感,让人浮想联翩。
我是一个破相之人,脸上的两块疤痕,照镜子的时候,都能清楚地看到。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爱照镜子,又怕照镜子。爱照镜子,是盼望奇迹出现,期待一觉醒来,疤痕突然消失不见了,哪怕变小了;怕照镜子,是因为我知道这种奇迹是不会出现的。照镜子时,第一个闯入眼帘的,不是那对浓眉大眼,不是那张堂堂正正的国字脸,而是脸上那两块疤痕——尽管两块疤痕在脸上占的比例并不大。
脸上的两块疤痕,曾让我饱受打击,痛不欲生,而且老担心前途受到牵连——同村一个女孩,考上了师范大学,体检时,就是因为脸上有一块疤痕,就让学校退档了,我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我已经年过不惑,经历了沧桑,对脸上两块疤痕,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两块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时代在我身上做下的记号,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一块疤痕横在两只眼睛之间的鼻梁凹陷处,是一岁多的时候留下的。
当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劳动,奶奶一个人在照看姐姐,哥哥,我,三个孩子,手忙脚乱的。姐六岁,哥三岁,正是调皮的年纪,到处乱跑,奶奶的主要力都放在他俩身上。
我被放在木制的摇篮车里。一岁多,也是喜欢到处乱动乱爬的年纪。不知道是因为摇篮车禁锢了我的自由,还是摇篮车外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挣扎着从摇篮车里爬了出来,在站在摇篮车上那一刻,车倾覆了,我面朝下,重重地摔了下来,鼻梁正好磕在石头做成的门槛边沿,细嫩的皮肉和骨头抗不过坚硬锐利的石头,我的鼻梁被切成两截,血如泉涌。
母亲闻讯赶回来,帮我把断裂的鼻梁用手捏在一起,也没有去医院——当年穷得也没有那个条件。小命是捡回来了,但疤痕就此留了下来。那道疤痕一直随着我成长而成长。当年鼻子小小的,疤痕是横断面,现在鼻子长大了,疤痕仍是横跨过鼻梁。
现在小孩,是几代人的掌中宝,生怕磕着碰着。我们那时候,两三岁就没人管了。再大一点,父母出工,把你反锁在家,到处乱爬。渴了,没人倒水;饿了,没人管饭;病了,没人送医院;拉屎了,没人擦屁股。感冒之类,能拖则拖,不能拖了,父母找些草药喂你吃下,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看医生。
大舅三个女儿,小时候生病,无钱看医,半年内相继夭折。一个儿子,值钱一点,拖不下去了,抱进医院。病是好了,可落下了耳聋后遗症。比起夭折的那些农村孩子,能够活下来,就算幸运了,一两块疤痕算什么?
另一块疤痕是五岁那年留下的,在左脸中央。
那年秋天特别苦,记忆中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生产队的甘蔗大丰收,熬出了一块块又大又方的蔗糖。生产队征集劳动力外出卖糖。卖糖的,工分比跟随生产队出工的高。为挣多几个工分,父亲报名要了一担蔗糖。蔗糖有多重,生产队都是称了的,前后重量要对得上。否则,会扣工分。所以,尽管那晚家里有两箩筐蔗糖,但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落,却没有被赏赐一点点。父亲把那担蔗糖放在他们的房子里管理着,我们几个流了一晚上的口水,下巴处的被单被弄得湿漉漉的,好大一片。
第二天清早,哥姐上学去了,我还在吃饭。父亲挑起蔗糖,跨过门槛,准备出去卖蔗糖了。看着父亲要走,我的心都碎了——我确实太想得到一块蔗糖尝尝,哪怕只有指甲那么大小。
在父亲出门那一刻,我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但被脚下的门槛绊倒了。当时我手里端着碗,嘴里含着筷子——仿佛那筷子就是蔗糖。结果一根筷子折断,一根筷子从嘴里刺破脸颊,钻了出来,一半留在嘴里,一半露在脸外。
这件事弄得一个家庭差点分崩离析。母亲很伤心,带着我回了外婆家,半年没有回来,非要和父亲离婚不可——在母亲看来,父亲没有人情,儿子的份量连 一块手指大的蔗 糖都不如。
伤好后,筷子刺破的那边脸留下了一道疤痕。
两块疤痕,尽管不大,可由于生长的地方不对,损害了我的光辉形象,也在心里留下阴影。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情窦初开的中学和大学,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心理障碍。从小到大,我在班上的成绩是很不错的,但那两块疤痕让我非常自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在心仪的女生面前,尽管自己长得并不丑。
我很想和别人一样,有一张光洁的脸蛋,意气风发,洒满青春阳光,不用躲躲闪闪,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甚至有时候,别人看我一眼,我就下意识地以为他是冲着我脸上的疤痕来的。这两块疤痕助长了我的自卑,学生时代,我静静地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不敢抬头,不敢回答问题,不敢看别人一眼,甚至不敢看黑板。课堂内外,我的眼睛始终落在书本上——在书本上花费的功夫多,成绩自然好,也算是没有自暴自弃。
我也想过一些办法来掩饰那两块让我烦恼不堪的疤痕。首先是像女孩子那样买回擦脸用的什么霜,希望借霜来掩盖。霜是白的,脸是黑的,擦霜后,疤痕是不那么明显了,可弄得一张脸黑白分明,比疤痕显现时更难看,只好作罢。后来想到戴眼镜。镜框边沿和连接两个镜框的眼镜鼻梁刚好把两块疤痕遮住了。起初我的眼睛并不近视,家里也没有近视遗传,戴上眼镜,我就慢慢地习惯了它,从假性近视演变成高度近视了。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人,除了我,都不是近视眼——为遮掩那两块疤痕,我牲牺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记得高中,班上有位漂亮女孩喜欢我,有事没事找我。但因为害怕她看到我脸上躲在镜片后的疤痕,我始终不敢抬头看她一眼。我的自卑让她很无奈,吃的闭门羹多了,她就不和我来往了,后来她转学了。
走的那天,她塞给我一封信,大致意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彼此喜欢,但都是自卑的人,在我漂亮的外表前,你自卑脸上的疤痕;在你优异的成绩前,我自卑自己的平庸。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希望你我都能从作茧自缚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也希望下一个喜欢你的人不要像我,那样辛苦,那样无助。
那封信,对我心理影响很大。晚上躲在被窝里,流了一晚上的泪。那封信,启发了我,也给了我自信。第二天,我摘下眼镜,勇敢地迎着别人的目光,与人对视;勇敢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后来由于高中学习用功了,没有眼镜还真不行,不得不重新戴上眼镜。
但那次感情经历,真让我破茧而出,从自我修砌的阴暗房子中走了出来,不再为脸上有疤自卑。
上了大学,换了一个环境。很多同学都是城里人,细皮嫩肉,光洁如玉,且聪明伶俐,见多识广。在他们面前,我还真有些自卑。但这种自卑,已经不是那两块疤痕带来的了,而是知识能力,品格修养。我努力完善,希望出类拔萃,至少不要离他们太远。
四年大学,我确实做到了,成为所在专业的风云人物。再照镜子,读着脸上那两道疤痕,我已经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的珍惜。
后来参加工作,也看到一些广告,说能治愈疤痕,有时候也有点儿心动,毕竟有瑕的玉与无瑕的玉还是有区别。但只是想想,并没付诸行动。
那两块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有它们,我是完整的; 没它们,我才是残缺的。 我已经习惯了,有一天真没有它们了,我还真不习惯了。 没有了,再找回来,就不容易了。 何况现在没人再在意我脸上的疤痕了——记得有段感情,那个女生摘下我的眼镜,轻轻地吻在那疤痕上,那感觉至今还在,让我感动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