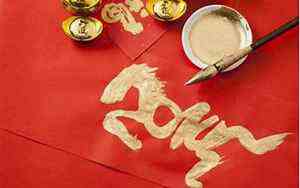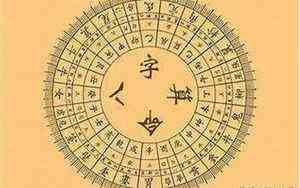“愿将一生献宏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于敏(左一)和同事常铁强(左二)、贺贤土(右一)讨论工作。 图片由于敏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提供
于敏在欣赏京剧海报。 图片由于敏生前工作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提供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就在被授予勋章前几个月的1月16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93岁。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60年代初,钱三强找到已在原子核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的于敏谈话,安排他参与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从那时起,于敏便转入了绝密的国家科研工作,开始了隐姓埋名的28年奋斗生涯。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此后,在一系列尖端的国防科技研究中,于敏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队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实现了一项项重要突破,为我国国防力量的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望于敏93年的人生,在科研工作之外,便是与家人的相处。从于敏与家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中,我们似乎可以读懂些什么……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已是一名小有成绩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的于敏,由于整日埋头科研,一直没有机会谈恋爱。转眼间就过了而立之年,家人都很操心他的终身大事。
于敏的姐姐于愫在天津工作。在其托管孩子的保育院里,有位端庄秀丽的姑娘让她眼前一亮。那是孩子的保育员老师,名叫孙玉芹。
在姐姐的安排下,于敏和孙玉芹见了一面。双方的感觉都很好,从此便确立了恋爱关系。一年后,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58年冬天,孙玉芹调入北京,进入于敏所在单位从事行政工作。
婚后,孙玉芹操持起了全部家务,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丈夫。于敏则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科研工作中。
孙玉芹知道,丈夫从事的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但是,她从不过问他的具体工作,只是默默地担负起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她明白,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让于敏不必为家务分心,就是对丈夫工作最大的支持。平时在家,也是孙玉芹一个人忙前忙后,于敏安安静静地工作。
几年后,家里先后添了一女一儿。
那些年,于敏一家包括老母亲在内的五口人,住在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房间里除了一张书桌外就是床,十分拥挤,人来回走动都有点困难。晚上,于敏回到家,女儿要用书桌做作业,于敏只好把桌子让给女儿,自己趴在床上去推导方程或者做计算。
孙玉芹心疼丈夫,担心他劳累过度。于是,有时到了周末,她就硬拉着于敏,带着孩子一起去逛公园,想让他稍稍休息一下。但于敏总是沉浸在对问题的思考里,常常和妻儿不合拍。后来,再去逛公园的时候,于敏就干脆自个儿找个安静的亭子,独自坐在那里看书。
有一次,孙玉芹好不容易说服丈夫陪自己一起去逛百货大楼。到了百货大楼门口,于敏却不愿意进去,说自己坐在门口等她。然而,等孙玉芹买好东西出来时,却找不见于敏,她只好一个人先回家。到家后,还是没看到于敏,孙玉芹就到所里办公室去寻找,也找不见。
人到哪儿去了呢?孙玉芹有点生气,又有点担心。
一直等到天完全黑了,于敏才姗姗而归。
孙玉芹问他:“你去哪儿了呢?我都找你半天了,找遍了单位和家里,也没找到你。”
于敏这才回答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便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去琢磨。没想到天黑得这么快。”
孙玉芹又心疼,又无奈。
还有一次,于敏看见妻子实在太忙,感到很内疚,于是主动提出,要帮忙洗衣服,就是用盆往洗衣机里加水。
一盆、两盆、三盆……他不停地往洗衣机里加水。“加了这么多盆水,怎么洗衣缸里的水还没加够呢?也没见水涨上来啊?”于敏心里好生奇怪。
妻子也觉得纳闷,走过来仔细查看。这才发现,洗衣机的排水阀门还开着,于敏完全忘掉了要先关上排水阀门,加进去的水全都流走了。
眼前的场景,让孙玉芹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两人就这样携手走过了一辈子。
年逾古稀后,于敏开始有更多的时间待在家里,陪伴妻子。
2012年8月的一天,81岁的孙玉芹突然心脏病发作。孩子们赶紧送母亲去医院。于敏颤颤巍巍地跟在后面,目送着他们离去。
当天,孙玉芹就去世了。
这,对于于敏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么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妻子陪伴在身边。从那时起,他似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对于妻子,于敏经常说:“我觉得我对不起她。我总是有许多愧疚。”
二
于敏一生都忙于科研工作,对子女的照料常常不够,关心和培育也不够。
在女儿于元和儿子于辛的成长过程中,于敏几乎很少有时间陪伴。因此,孩子们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永远在忙碌的背影。
但是,妈妈却一直叮嘱他们:“爸爸在忙工作,不要去打扰他。”孩子们从小都很懂事,尽量不去影响爸爸的工作。
当于敏转入研究氢弹之时,已经有了女儿。每当同事来家里讨论工作,为了保密需要,于敏就让妻子带着女儿到外面去转悠。这样的习惯,以致孩子长到很大的时候,仍然一见生人就会躲起来。
于元上学后,父亲一有同事来访,于元就得带着弟弟离开房间。
有一次,小于元站在门口,偷听爸爸和叔叔们的谈话,听到爸爸时不时说到一个字“肉”。
孙玉芹看见了,赶紧把孩子拉开:“大人谈事情,小孩子不要偷听!”
没成想,于元却很开心。她兴奋地告诉妈妈:“妈妈,爸爸说‘肉’,我们有肉吃了!”那时候生活很艰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平时吃肉不多,因此孩子对“肉”这个字眼很敏感。
到了吃饭的时候,于元却发现桌上并没有肉。于是就问爸爸:“爸爸,您不是在说‘肉’嘛,为什么我们没有肉吃呢?”
于敏愣了一下,随即反应了过来,孩子说的一定是希腊字母ρ。
他笑了,告诉孩子:“我说的不是吃的肉,而是一个希腊字母。它表示的是物体的密度。体积相同的前提下,密度越大的物体越重。”
“我明白了!越重的物体,它的‘肉’当然就越重。”于元天真无邪地说。于敏和孙玉芹都被逗乐了。
由于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少,因此几乎每一次,于辛都记得特别清楚。他最难忘的是有一回,读小学时,全家人一道去颐和园游玩。那天,一家人沿着昆明湖畔的彩绘长廊缓缓地往前走。看到长廊的梁栋上画满了图画,于元和于辛姐弟俩都很好奇。于敏仔细打量这些彩绘,一幅幅地给孩子们讲解:这幅画讲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那幅画讲的是“三顾茅庐”的故事,还有“岳母刺字”……
时隔多年,于辛回想起来那一天的经历,仍历历在目。那时候的他多么希望,父亲能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啊!
在于辛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出差,有时一出差就是两三个月。在家里也多半都关在房间里,和叔叔们探讨科研的问题。他知道,父亲很有学问。
有一次,上物理课,老师讲到电路图这一章节。那时,对于复杂电路里的串联和并联究竟是怎么回事,于辛一直都弄不懂。回到家,正好父亲有时间,他就向父亲请教。
于敏便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幅图,给于辛讲解起来。父亲这样一讲,于辛一下子就明白了。从那以后,他对电路图、接电线、动手做物理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老师教大家自己动手制作收音机。于辛对此特别感兴趣。父亲给他买来了磁铁、线圈、电容器,然后指导他如何将这些器件组装起来,如何通过调节电容调出声音来。于辛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台能够收听广播的收音机,心里很得意。
直至今日,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于辛感到,父亲确实很有本事,也很爱他和姐姐,只是父亲的工作实在是太忙,因此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母亲去世后,为了照顾好父亲的生活,于辛一家搬了过去,和父亲住在了一起。
那时,于敏的卧室里,用的依旧是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铁床、油漆剥落严重的老式写字台和书柜,还有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于敏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就是在这个无比简朴的房间里度过的。
书柜里,有几本于敏亲自整理的手稿,那是为学生做学习研究参考用的。每一页上,每一个字,一笔一画都写得工工整整。客厅里,一直悬挂着一幅书法——“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每天,于敏都按时早起。先打一打太极拳,做一做健身操。吃过早饭,看一些科技资料、电视新闻。接着看看书,写写材料。午饭后,要小睡一会儿。然后起来看看报纸和专业书籍。剩下的时间大都花在看资料、跟踪国际最新科技进展上。同时,他依旧保持着对史书、古典文学和京剧的热爱,会看《三国演义》《资治通鉴》《史记》《红楼梦》等书籍,有时间还会听听京剧。
三
于确是于敏的堂弟,比于敏小26岁。虽然兄弟俩年龄悬殊,却始终保持着手足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老家,于敏的父亲和叔叔两家九口人一直吃住在一起。可是,由于两家老人年纪大了,没有正式工作,家里孩子尚小,所以基本上没有经济来源。
1951年,于敏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后,每月15日都会给天津的家人汇款。
刚开始工作时,于敏的工资并不高。等到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后,工资才高了一些,一个月180元。除了自己小家的日常开销外,剩下的钱几乎全都寄回天津。孙玉芹贤惠明理,对此毫无怨言。每次汇款,都是孙玉芹去邮局办理。
有一次,已经过了每月预定的时间,汇款单还没寄来。又过了一周,汇款单才寄到。后来,家里人才知道,那一次,于敏的工资丢了,只得想办法把钱凑足了,才给家里汇过来。
这些汇回老家的款项,既是给老人的赡养费,也有全家人的生活费。于确和弟弟妹妹的学杂费,都是用哥哥寄来的钱付的。
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他还继续给老家寄钱。一直到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再三坚持下,于敏和孙玉芹才停止了汇款。
在于确的记忆里,他只在春节期间偶尔见到过于敏。那时,年幼的于确特别盼着过年,因为堂哥于敏回家过年时,总会给他们带来许多好吃、好玩的东西。
平日里,于敏则会给家人写信。据于确统计,家里断断续续收到了于敏200多封家书。后来,这些家书都被家人珍藏在了一个专门的箱子里。
每一次收到于敏的书信,于确便会和家人一同凑在父亲身边,听父亲念信。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孩子学习教育和健康成长的内容,鼓励弟弟妹妹好好学习。
于确说:“哥哥谦虚谨慎的性格,对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影响非常大。我们都以他为榜样,心怀真诚、善良,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前,于确只知道哥哥从事的是需要保密的工作,但哥哥究竟具体做什么工作,他一直都不清楚。直到1986年,他在电视上突然看到了于敏的名字,才知道原来哥哥做的事情这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于敏作为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被表彰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确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无比激动,倍感自豪。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拨通了于敏家的电话,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电话那头,于敏反而很平和。他说,自己为国家做点儿事是应该的。
还有一回,于确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于敏的报道,便给于敏写信,大意是想和那位记者联系一下,聊聊哥哥孝敬老人的事。然而,于敏却回信说,国家弘扬的是“两弹一星”精神,不要宣传自家私事。
2006年,于确到北京探望于敏。提到叔父时,于敏流泪了。这是于确平生第一次看到哥哥落泪。于敏愧疚地对于确说:“真对不起叔父,没能在他弥留之际见上一面。”
随着年纪渐长,于敏的身体状况也成了于确心中的牵挂。2018年底,于敏入选“改革先锋”。当于确得知哥哥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非常担心。“他为了国家强盛,兢兢业业,是为国家尽了忠;27年汇款赡养老人,是尽了孝。哥哥是这世上忠孝两全的人!”于确这样评价堂兄于敏。
在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之后,73岁的于敏曾写了一首七言《抒怀》,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壮丽的一生。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这,正是这位杰出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情告白!
版式设计:赵偲汝《 人民日报 》( 2022年07月06日 20 版)
从唐家岭到于辛庄,北漂们的下一站在哪里?
2023年9月12日,昌平区沙河镇于辛庄村贴出了拆除村中违建的公告。这意味着租住在于辛庄村的北漂们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搬离于辛庄,重新寻找落脚点了。
于辛庄村的拆违会影响多少人的生活?从昌平线沙河站的客流数据就可以直观感受一下。2012年以后,沙河站就开始对地铁进站进行限流,至2018年,在所有车站中沙河的早高峰进站客流量位列12位,达到了1.54万人次/h,同比增加30%,在网上没有查到最近几年的数据,但是从各种报道中也可以感受沙河客流量的情况:早高峰从开始排队到进站需要等20多分钟,尽管地铁昌平线做了一定的分流措施,但如果进站后想要挤上去地铁起码要等个好几趟。
沙河站进站的队伍
大量的客流不仅来源于周边建成的小区,更多的客流来自于像于辛庄这样的村庄。村子里房租1000来块钱,电费1.5元一度,水费差不多20一个月,网费一个月100,取暖费一间20多平的屋子1200-1800之间,这就是于辛庄的公寓花费。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靠近地铁较为便利的出行条件,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刚到北京或者积蓄不多的北漂们理想的居住地。
于辛庄街道
其实,于辛庄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北漂们外溢之地,唐家岭才是北漂们见证北京崛起的肇始之地。
唐家岭
唐家岭位于中关村软件园的北侧。在2010年前后,唐家岭是北京著名的流动人口聚集地。全村户籍人口不足3千,流动人口却达5万多,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和今天的于辛庄没什么差别。
2000年以后,唐家岭村边的中关村科技园、上地软件园发展了起来。随后,民办的中国软件管理学院,在唐家岭村西落户,该校学生成了唐家岭最早的一批租户。在2003年“非典”之后,来村里租房的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为了挣租金,村民纷纷在自家宅基地盖起了二层小楼。随着上地软件园的成熟,越来越多的求职大学生来到唐家岭。村民们也开始把二层小楼改成四层,甚至七层,以容纳更多租户。
从1999年开始,教育产业化,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了1000万。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大量涌入了一线城市。来到北京以后两手空空,只能是先找个便宜的住处。彼时计算机、软件、信息技术等在中国发展势头强劲,中关村各个大楼中组装电脑的柜台人声鼎沸,中关村吸引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唐家岭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外来年轻人,唐家岭村挨着上地软件园。往南是中关村,往北是永丰科技园,往东就是昌平线城铁西二旗站。于是,这些年轻人一窝蜂似的,扎进了唐家岭村的出租房里。
租金的驱使下唐家岭村平房的地基改成了楼房,临街房改成了铺面房,几乎每户村民年收入房租达十几到几十万之多。有些无力翻盖楼房的村民宅基地,被江浙来的人以年租金二十万左右承包下来,这些江浙人将平房拆除,盖起了五层楼房出租给外来人员,当起了二房东。这样一来,原本干净整洁的唐家岭村,逐渐变得污水横流、垃圾遍地、道路狭窄、治安混乱……,每天晚上,水压不够,电压不稳成为常态,无论是租户还是房东,苦不堪言。拥挤杂乱的生活空间以及为了生活每天着急奔忙地工作,在唐家岭生活的北漂们有了一个名字叫蚁族。经过各种媒体的宣传放大,唐家岭就成立首都北京不得不清除的一个城市病灶。
唐家岭
唐家岭
唐家岭
唐家岭
唐家岭
(2010年的唐家岭,图片来源于跟随高建走昌平)
2010年4月,启动了唐家岭地区整体腾退改造工程,在航天城南侧新建农民回迁安置房35万平方米。2012年至2014年,在唐家岭村旧址上建起了2356亩的中关村森林公园(其实应该叫做唐家岭遗址(蚁族)公园)。
唐家岭新城
中关村公园
在唐家岭生活的蚁族们只能迁移到唐家岭向北约5km的北四村,在2010年昌平线建成后由于交通的改善也有很多人进入到了沙河站东侧的于辛庄和松兰堡。2019年北四村拆迁后,更多的人进入于辛庄,沙河站的进站排队问题终于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其实类似唐家岭、于辛庄这样的外来人口聚集的村庄远不止这几个,围绕北京五环甚至六环路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分布着很多这样的村庄。亦庄比较著名的马驹桥前段时间拆违还上过北京卫视向前一步栏目,天通苑的各个车站客流量远大于沙河,客流量一直是北京地铁站进站客流量的前几名,除了天通苑社区自身客流量大的原因,周边还分布了东三旗、半截塔、白庙等多个类似于辛庄村规模的村子,这些村庄都居住了大量的北漂。
像唐家岭、于辛庄这样居住成本低廉的城中村或者城外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也需要出现的存在。一方面,城市的房价高企,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以及各种各样怀揣梦想以及仅仅想打工挣钱的各种人群一段时间内不具备购买或者租住条件好一点的正规的居住小区的条件,只能与人合租或者居住在于辛庄一类的村庄中,而村庄中除了成本较低,重要的是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这更容易吸引租客。城市的规划建设也不愿意为这些人口提供过渡的居住空间,民间自发的逐利就很容易形成于辛庄这样的廉价居住地。另外一方面,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如果让这些相对便宜的劳动力都有能力在北京这样房价很高的城市中买房,劳动力的价格一定会被推高,整个城市的各种成本也会水涨船高,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所以城市是非常需要于辛庄这样的地方的,但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虽然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们受到一些道德或者政治正确方面的约束,不会在城市规划中考虑特别规划出这样的功能区,对于民间自发出现的于辛庄村们,也不会出面进行管理和规范(避免有官方背书的嫌疑),等到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后,一拆了之。北漂们只能打包行李,寻找下一个于辛庄。
其实政府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道德洁癖,给经济能力有限的年轻人规划建设一些租金便宜,交通方便的过渡性公寓,对于周边村庄自发形成的居住地,制定政策给予规范,满足消防等的基本要求。提供上下水、公交出行等方面的支持。北漂人太难了,前有“哪李贵了”的灵魂逼问,后有不断被驱赶越来越远的安身处,,政策的一个小调整对每个北漂人的生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需要年轻人注入活力和创新动力,给年轻人减轻压力,给北漂人提供有尊严,负担得起的生活环境,是城市管理着者的责任,也是北京能够吸引人才,保持不断创新,不断发展需要付出的。
昌平这片区域发布腾退拆除公告!涉及多个社区公寓——
于辛庄村其他区域的腾退计划也公布了——
致于辛庄村计划拆除区域全体商户、居民的一封信
昌平区沙河镇于辛庄村广大商户、居民朋友们:
你们好!昌平区近几年响应北京市创建“基本无违法建设区”行动规划,全面推动优化改造,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整治违建乱象,获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目前,沙河镇于辛庄村正在开展对集体出租土地上建设的以出租住人为主的非宅基地地块地上物进行腾退,镇政府也在根据上级政府要求开展违法建设集中整治活动。本次计划先行腾退或查处整治的主要区域包括都市青年公寓、七号公寓、八达公寓、福有公寓、温馨家园、闽辉公寓、如意家园、鑫源公寓、德会家园、三瑞酒家、永利农庄、富地家园、众鑫合公寓、天利合、阳光家园、晴天家园、美好家园公寓、贵明公寓、永旺家园、佳和公寓一部、龙乡公寓等。
根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市禁止违法建设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属于违法建设,镇政府有权查处违法建设并实施强制拆除。同时,对于妨碍和阻挠行政执法工作的有关人员,公安机关有权作出处理。
建议以上区域商户、居民朋友们抓紧时间,及时进行核查,搬离确无手续的房屋,另行寻找合法房屋合法经营或租住,避免因房屋租赁资源紧张带来生活不便。
最后,作为承租人的商户、居民朋友,租赁违法建设的合同涉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构成无效合同,如因此产生任何经济损失,可以与出租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同时,也有群友发布了现场拆除的视频~
,时长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