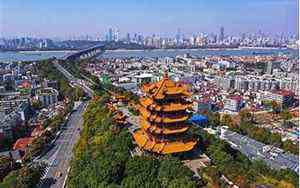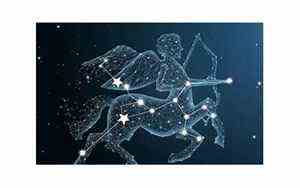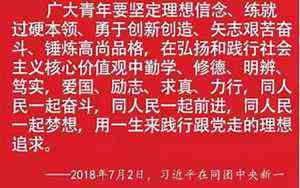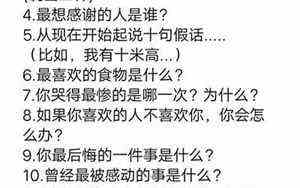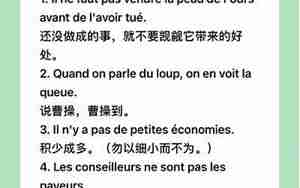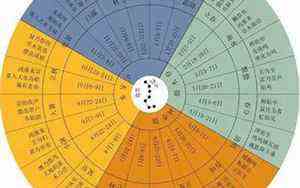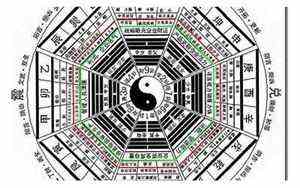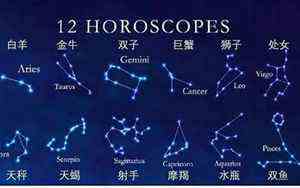外国小说鉴赏之《在桥边》
恢复与重建
“我”因伤被分配去数新桥上走过的人,但是“我”因不满单调枯燥的生活而敷衍了事。在这样乏味的环境中,“我”遇见了一个美好的姑娘,不肯将她归入自己所数的人数之列,因为“我”不肯将自己心爱的姑娘列入无意义的数字中。后来却鬼使神差走鸿运,去数马车。
根据文章的写作背景,作者想表达的是:重建的目的是恢复,但如果重建的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么这个恢复就失去了意义。
在作者眼里,德国的重建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做到了物质建设。而“我”发现目前恢复的并不是当初所拥有的,即“有——无——有——无”。重建的和之前的并不符合,“我”需要去寻找之前的“有”,即“有——无——有——无——有”。
同时“我”发现,以个人力量根本无法抗拒强大的政治机构,甚至有失业的危机。然而当“我”面对主任统计员的检查时,“我”虽然很认真地数人,但还是将“我”心爱的姑娘漏数。
漏数是有危机的,却表现着对美好事物的维护、坚守,表现着一种精神追求。
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地交了“鸿运”,作者要透露的是,一旦人们发现目前所恢复的并不是当初自己所拥有的,需要反思和追寻,但没有必要革命。
因为初衷是重建,不需要再一次战争和毁坏。因力量有限,所以需要智慧,用智慧再次恢复起初的“美好”和拥有。这才是作者在重建和恢复中所要透露的真正理智的思考。
1.故事与情节
情节是小说叙事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文学作品中的事件、主要故事的策划或设计。它是按照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系列事件的逐步展开。
被讲述的事情,凡有情节、有头有尾皆称故事。
情节对讲故事的小说意义重大,是成就小说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精彩的故事源于精彩的情节。情节是故事的核心,它在整体上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和发展。
《在桥边》一开始的情节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姑娘的出现给波澜不惊的情节注入了活水,也给主人公的情感注入了活水。情节的变化是情感变化的契机。最后有惊无险地去数马车,似乎给了希望,但仔细想想,这种无意义却是没有尽头的。他的姑娘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但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美好的呵护,仍然是可以打动人的。
2.情节的生发
含有前因后果的情节本身就具有黏附能力。它是可以生发的,像核爆炸,把整个小说牢牢地聚拢在它的张力之中。“我”对姑娘的暗恋与对记数工作的职业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姑娘在“我”看来是一抹生机,不应被看作毫无意义的数字。可数错人数就会影响“我”来之不易的饭碗。在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作者的情感被强烈激发,对重建精神废墟的渴求也凸显了出来。
3.情节和细节
富有表现力的动人细节几乎可以覆盖我们对一部小说的全部印象。细节与情节密不可分。细节有极强的表现力,对情节、人物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比起情节,细节更具体,也更有针对性。情节是骨架,细节是血肉。
“我”数人数的细节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工作的枯燥和战争后遗症的严峻。“我”看到姑娘的心理活动细节又体现出“我”对生命的关注和对无意义生活的反抗。细节要有选择性地添加,根据文章的详略轻重布置来进行细节的刻画,这样才能突出重点,加深印象。正是这些具体的细节,才使得整个情节丰满、充实起来,小说也显得活起来。
4.情节运行的基本模式
发生——“我”爱上了一个过桥的姑娘,险些因她打碎自己的饭碗;
发展——“主人统计员”的检查;
高潮——“我”如何应对上司和压抑住自己对姑娘的感情;
结局——“我”终于度过考验,交上鸿运。
5. 摇摆
在一个小说中,即使开端和结局都很简单,作家也绝不会让人物选择捷径一口气跑到终点,而是让他百转千回,最终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所以小说在很多时间里是呈现犹疑不定的状态。
在摇摆的过程当中,人物在小说世界中不停地碰撞。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碰撞就会展现出人物不同的特点,从而使读者看到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不是绝对的非黑即白,也不是单调的非好即坏。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摇摆中推进文章增强了文章的可观看性,充分吸引读者注意力,让读者欲罢不能。我们期待主人公和姑娘有一段美好的爱情,期待这一段爱情能成为主人公灰暗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当这个爱情无疾而终时,我们深深地为主人公的无力感而叹息,也更加深入地思考战争带给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伤害是多么深远。情节就像一条线索,带领读者感悟主人公、乃至作者的隐秘的内心世界。
面对摇摆不定的情节和越来越清晰的主人公,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情感也越来越明朗。战争摧毁的不只是肉体,精神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弥补。颓唐或生无可恋,及时行乐或醉生梦死,这样的生活状态让人如同行尸走肉。活着,不仅仅是呼吸。痛苦和灾难不应当阻挡生活的脚步。被战争烟雾遮挡起来的生命之光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擦拭干净。当少数人为了利益发动战争时,请考虑一下世间的生灵,他们水深火热哀鸿遍野的代价,你们付得起吗?
外国小说鉴赏之《在桥边》
恢复与重建
“我”因伤被分配去数新桥上走过的人,但是“我”因不满单调枯燥的生活而敷衍了事。在这样乏味的环境中,“我”遇见了一个美好的姑娘,不肯将她归入自己所数的人数之列,因为“我”不肯将自己心爱的姑娘列入无意义的数字中。后来却鬼使神差走鸿运,去数马车。
根据文章的写作背景,作者想表达的是:重建的目的是恢复,但如果重建的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么这个恢复就失去了意义。
在作者眼里,德国的重建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只做到了物质建设。而“我”发现目前恢复的并不是当初所拥有的,即“有——无——有——无”。重建的和之前的并不符合,“我”需要去寻找之前的“有”,即“有——无——有——无——有”。
同时“我”发现,以个人力量根本无法抗拒强大的政治机构,甚至有失业的危机。然而当“我”面对主任统计员的检查时,“我”虽然很认真地数人,但还是将“我”心爱的姑娘漏数。
漏数是有危机的,却表现着对美好事物的维护、坚守,表现着一种精神追求。
而结果却出人意料地交了“鸿运”,作者要透露的是,一旦人们发现目前所恢复的并不是当初自己所拥有的,需要反思和追寻,但没有必要革命。
因为初衷是重建,不需要再一次战争和毁坏。因力量有限,所以需要智慧,用智慧再次恢复起初的“美好”和拥有。这才是作者在重建和恢复中所要透露的真正理智的思考。
1.故事与情节
情节是小说叙事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文学作品中的事件、主要故事的策划或设计。它是按照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一系列事件的逐步展开。
被讲述的事情,凡有情节、有头有尾皆称故事。
情节对讲故事的小说意义重大,是成就小说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精彩的故事源于精彩的情节。情节是故事的核心,它在整体上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和发展。
《在桥边》一开始的情节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姑娘的出现给波澜不惊的情节注入了活水,也给主人公的情感注入了活水。情节的变化是情感变化的契机。最后有惊无险地去数马车,似乎给了希望,但仔细想想,这种无意义却是没有尽头的。他的姑娘注定只是昙花一现,但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美好的呵护,仍然是可以打动人的。
2.情节的生发
含有前因后果的情节本身就具有黏附能力。它是可以生发的,像核爆炸,把整个小说牢牢地聚拢在它的张力之中。“我”对姑娘的暗恋与对记数工作的职业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姑娘在“我”看来是一抹生机,不应被看作毫无意义的数字。可数错人数就会影响“我”来之不易的饭碗。在这种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作者的情感被强烈激发,对重建精神废墟的渴求也凸显了出来。
3.情节和细节
富有表现力的动人细节几乎可以覆盖我们对一部小说的全部印象。细节与情节密不可分。细节有极强的表现力,对情节、人物起画龙点睛的作用。比起情节,细节更具体,也更有针对性。情节是骨架,细节是血肉。
“我”数人数的细节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工作的枯燥和战争后遗症的严峻。“我”看到姑娘的心理活动细节又体现出“我”对生命的关注和对无意义生活的反抗。细节要有选择性地添加,根据文章的详略轻重布置来进行细节的刻画,这样才能突出重点,加深印象。正是这些具体的细节,才使得整个情节丰满、充实起来,小说也显得活起来。
4.情节运行的基本模式
发生——“我”爱上了一个过桥的姑娘,险些因她打碎自己的饭碗;
发展——“主人统计员”的检查;
高潮——“我”如何应对上司和压抑住自己对姑娘的感情;
结局——“我”终于度过考验,交上鸿运。
5. 摇摆
在一个小说中,即使开端和结局都很简单,作家也绝不会让人物选择捷径一口气跑到终点,而是让他百转千回,最终才能抵达胜利的彼岸。所以小说在很多时间里是呈现犹疑不定的状态。
在摇摆的过程当中,人物在小说世界中不停地碰撞。在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碰撞就会展现出人物不同的特点,从而使读者看到一个更加立体、丰满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更加接近现实生活,不是绝对的非黑即白,也不是单调的非好即坏。
文似看山不喜平。在摇摆中推进文章增强了文章的可观看性,充分吸引读者注意力,让读者欲罢不能。我们期待主人公和姑娘有一段美好的爱情,期待这一段爱情能成为主人公灰暗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当这个爱情无疾而终时,我们深深地为主人公的无力感而叹息,也更加深入地思考战争带给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伤害是多么深远。情节就像一条线索,带领读者感悟主人公、乃至作者的隐秘的内心世界。
面对摇摆不定的情节和越来越清晰的主人公,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生活的情感也越来越明朗。战争摧毁的不只是肉体,精神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弥补。颓唐或生无可恋,及时行乐或醉生梦死,这样的生活状态让人如同行尸走肉。活着,不仅仅是呼吸。痛苦和灾难不应当阻挡生活的脚步。被战争烟雾遮挡起来的生命之光需要强大的内心才能擦拭干净。当少数人为了利益发动战争时,请考虑一下世间的生灵,他们水深火热哀鸿遍野的代价,你们付得起吗?
藏而不露,寄物咏怀,《乌衣巷》何以流传千年
刘禹锡是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今天的这首诗可谓是脍炙人口,老少皆知。
这首是就是《乌衣巷》:
乌衣巷
唐代: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是一首怀古诗。凭吊东晋时南京秦淮河上朱雀桥和南岸的乌衣巷的繁华鼎盛,而今野草丛生,荒凉残照。感慨沧海桑田,人生多变。以燕栖旧巢唤起人们想象,含而不露;以“野草花”、“夕阳斜”涂抹背景,美而不俗。语虽极浅,味却无限。
白话翻译朱雀桥边一些野草开花,乌衣巷口唯有夕阳斜挂。当年王导、谢安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寻常百姓家中。
注释【朱雀桥】在金陵城外,乌衣巷在桥边。 在今南京市东南,在文德桥南岸,是三国东吴时的禁军驻地。由于当时禁军身着黑色军服,所以此地俗语称乌衣巷。在东晋时以王导、谢安两大家族,都居住在乌衣巷,人称其子弟为“乌衣郎”。入唐后,乌衣巷沦为废墟。现为民间工艺品的汇集之地。
【乌衣】燕子,旧时王谢之家庭多燕子。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横跨秦淮河。
【寻常】平常。
【王谢】王导、谢安,晋相,世家大族,贤才众多,皆居巷中,冠盖簪缨,为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先后建都于建康即今之南京)巨室。至唐时,则皆衰落不知其处。
【旧时】晋代。
这首诗写诗人对盛衰兴败的深沉感慨。朱雀桥和乌衣巷依然如故,但野草丛生,夕阳已斜。荒凉的景象,暗含诗人对荣枯兴衰的敏感体验。
《乌衣巷》在艺术表现上集中描绘乌衣巷的现况;对它的过去,仅仅巧妙地略加暗示。诗人的感慨更是藏而不露,寄寓在景物描写之中。因此它虽然景物寻常,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蕴藉含蓄之美,使人读起来余味无穷。
参考资料:
徐中玉 金启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631-633
农村建房俗语“坑塘屋,桥上房,必有伤亡”,啥意思?有道理吗?
导读:农村建房俗语“坑塘屋,桥上房,必有伤亡”,啥意思?有道理吗?
春天是农村建房的好季节,对于盖房子向来都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修房建屋不但要花费很多的钱,而且还要耗费很多的时日才能完成,所以对于房屋的要求精益求精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对于房屋建造的要求有很多,其中房屋的坐落位置尤其是重要,并非什么地方都可以建房的,而是要选址适宜的地方建房。好的位置修建的房屋不但环境适宜、出路便捷,而且安全系数高,这样的房屋住在里面不但舒适性优,而且还能够有好的运势,农村素来有“一命二运三风水”的说法。所以房屋对于家庭运势相当重要。
农村有句建房的俗语叫做“坑塘屋,桥上房,必有伤亡”,这句老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过去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坑塘,这些坑塘是作为雨季到来之际贮水使用,能够把雨水汇入到坑塘之中,让村里不积水。有的坑塘会常年有水存在,但有的坑塘也会连年的干涸,所以就会有人把那些常年干涸的水塘,垫土填平之后作为宅基地使用。
坑塘垫平之后看起来跟平地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也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由于坑塘的深度存在,即便是使用泥土、沙石等填埋,但由于时间短暂,在加上过去机械化落后,很难真正的做到夯实,所以这样的地方修建房屋。地基是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尤其是遇到雨季有水的存在,更是容易产生地基变形,严重的还会让房屋产生裂缝、甚至倒塌。有的水塘过去常年有水,在这样的地方盖房子,房屋里面会经常出现返潮的现象,而且无法根治。
过去建造房屋的技术和建材有限,在坑塘填平的地方修建房屋,哪怕是做到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根基不稳的存在,很容易就会产生诸多的突发状况。至于桥上房,则是把房屋修建在了原本的桥梁之上,向有的桥梁由于河内常年无水,桥梁就处于无用的状况,或者是桥梁修建的地理位置原因,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直接以桥为基出,把房子建立在了桥梁之上。
这样的桥上建房,也是具有极其不安全的因素,桥梁的修建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过去的桥梁,由于技术以及材料的原因,修建的承载能力相对较弱。如果在这样的桥梁上面加盖房屋,势必增加了桥的承重,这样的房屋显然是不安全的,桥会在承受不了房屋的重量下,产生倒塌,势必会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也就演变成了这句俗语:“坑塘屋,桥上房,必有伤亡”。
这句俗语老话也是结合实际情况。以及对于修建房屋多年得出的经验,进而产生的俗语老话,也颇具一定的道理存在,是值得借鉴和参考使用的,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大家补充评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