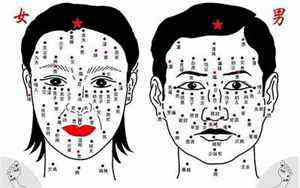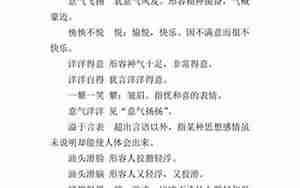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佞臣
赳赳将军,豼貅绝羣。 世代相传的血统,忠贞不灭的亡魂,漫漫官途,她已踏上,不得回头。 貔貅性凶,若利用得当,便可福泽万民。 屠戮中,她被救起,却也铭记着故人这句话,直到科举之后,遇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故人,原本高升无忧的仕途之路因为他而变得坎坷,充满荆棘。 他说,你仍不聪明。 他说,你信我。 可最终,她坠火涅槃之后,才真正明白了,那所谓的君臣之道。 以阿谀谄媚为荣者,视为宠。 以小人之道上位者,视为佞。 她既已走到了这一步,便得坐实了这名分。 ——圣上,微臣甘愿为佞,扫除所有不忠不敬之臣,睥睨天下。数九寒天,微凉的月光,洒在墙壁上的几个大字上——凉州地牢。
飞扬的檐角,都在寒夜里折出彻骨的凉意。
牢狱的门被由着窄小的窗户偷进来的风吹得“哐啷”响,穿着囚服的女人都围成一圈,相互取暖,即便在这深冬,也要有些暖意来苟延残喘。
唯独那一人,长衫褴褛,靠在带着潮意的墙面上,稚嫩的脸上,死灰一般寂冷。
“吃饭了。”
围成一团的几个女人总算有了点动静,纷纷走向门边,却不敌那人身手,行走带风,就连脚步都轻的没声,到门边后,蹲下用十根冻得如同青紫的萝卜般的指头,细细拨开绑住食桶的铁丝,清亮的眸中却闪过一丝错愕。
她,没有看到那一角熟悉的布衣。
“牢头!”
她喊住了没走多远的牢头,双手紧抓着铁栏,不顾那上面冻如冰渣,捏得指尖泛白。
牢头不耐嚷了声,却没有停住脚步,这大冷天的,他还急着回去烤火。
“要吃快吃,不吃便早些死!”
“我娘亲呢?”
在这阴冷潮湿的地牢,久不言语,就连稚嫩的嗓音都变得沙哑无比,却急切依旧。
牢头回头看她,觉得有些眼熟,凑近了一眼,却是那再熟悉不过的凌厉的面庞,忍不住冷嗤一声,“你且吃你的吧,欺君罔上还好意思问这些,若不是你那不经打的娘亲,你早到阴曹地府去了。”
她眼疾手快地穿过铁栏抓住牢头的衣服,下了狠劲,连声音都变得粗犷有力,“我娘亲呢?”
就算下了狱,这狠劲依然不输从前,长睫毛落下的阴影都像是杀人的利器,锋利无比。
牢头下劲扯了扯,竟扯不开她的手,当即嚷嚷道:“不想落得跟你娘亲一样早死的下场,就快给我放手!”
早死?
娘亲……早死!
手中蓦地收紧,长期未修剪的指甲几乎要穿破牢头的衣服——
“呵——”
身后女人们的冷抽声响起,她们看到牢头的双脚已经离了地,而抓住他衣领的不过是个刚及他肩膀的半大孩子!
“你你你……你抓我也没用,是你娘亲自己不经打,昨天晚上就没熬住死了,你再不放手,我叫你也早早地去见你娘亲!”
她的手一松,牢头跌坐在地,赶紧爬起来拍了拍衣服,逃也似的走了。
和她同一牢房的女人们仿佛躲瘟神一般,离她老远,却都不敢再轻易开口,生怕她们命丧于一个孩子手中。
而她,却仿佛回到了刚才的模样,只是那清亮的双眸,再无神采,长长的睫毛掩下,细看才能看清那微微的颤抖。
这种沉默,竟是一种比哭还让人难过的悲伤。
翌日。
冬日的暖阳,稀少得可怜,投过窗户洒进牢房,女人们也懒洋洋地伸着懒腰,拨弄着本就脏乱不堪的发髻。
“诶,这个孩子去哪儿了?”
牢房中再没见那个孤瘦的小身影,却只见地上那一枚小小的令牌。
微胖的女人走过去捡起来,仔细看了上面的字,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招呼了瘦高个的女人过来,“快瞧瞧,这是个什么物什?”
牢房中唯一认得字的瘦高个一字一句地念道:“凉州,营,兰翎长……”
微胖女人一声冷抽,“呵,这丫头竟然是个官儿!”
“怎可能,这丫头才九岁的模样,怕是她家谁人的吧?”
“前些天这丫头进来之前,不就有个啥兵头给当街立斩了吗?这丫头莫不是那人的女儿……?”
瘦高个摇头叹息,“她爹是个官儿又如何,还不是惨死了,这丫头落入这死囚牢中,不是死也是一辈子困在这里不见天日咯……”
一句话下,四下皆沉默。
凉州集市,城门之下,有钟鼓长鸣。
行刑台上,数十名戴罪之人一字排开,一声锤鼓落下后,戴着厚厚枷锁的囚犯们纷纷跪下,面如死灰,只等待着刽子手那果决的一刀。
却独独有一人,傲然立于刑台之上,脏乱的发遮不住她带着光芒的眸子。
“何人?为何不跪!”
她想开口说话,想喊冤,想让乡亲父老们相信,她秦氏,冤枉至极。
然而两名大汉的桎梏之下,她的双膝砸在了冰冷的地面上,她似乎听到了,骨头碎裂的声音。
她紧咬着牙齿,众人皆低头,唯她抬着头。
只因,她没犯错,她命不该绝与此。
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听信她的话,只因她是一个孩子,一个家中无权无势的孩子,就连唯一能站出来为她说话的父亲,也死于了这帮白眼狼的剑下!
她的倔强和傲骨,在刽子手的刀下,一文不值。
“行刑——”
随着判官的一声令下,刽子手的刀在冬阳的照耀下折射出冰冷的光,恍得她微微眯了眼……
这就要死了,她还未及笄便要死了吗。
她的头重重的垂下,认命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恍惚间,却听到了“哒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随后便是刀入鞘的清脆响声,再然后……就陷入了长久的黑暗之中。
……
建元十三年,腊月初三。
东邑皇逢知天命,遂,大赦天下,以庆万世万代,昌合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