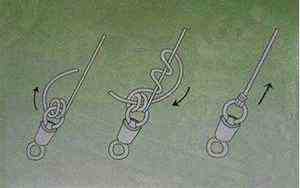“朱衣点头”
作者:王充闾
由于兼任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曾参加几次博士生、硕士生答辩。记得一次在答辩委员会的晚餐席上,一位老教授说,这是“朱衣人”的聚会,大家会心地笑了。原来,这里有个著名的掌故——
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时,每阅试卷,常觉座后有朱衣人时复点头,然后其文必入选。始疑其为侍吏,及回顾之,一无所见。尝有句云:“唯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当时的一种幻觉。
到了南宋文学家曾丰笔下,开始把“朱衣点头”同遴才取士联系起来。他有这样两首七绝:“坡老不期遗李廌,欧公犹误取刘晖。点头道有朱衣吏,今古相传未必非。”“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生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说当年苏东坡主持礼部贡试时遗漏掉了李廌,出乎意料,深为自责。而欧阳修担任主考时却误取了刘晖。欧阳公倡导古文运动,刘几为文不合要求,被淘汰出局。时隔两年,刘几易名刘晖,文风丕变,欧公大为赞赏,遂得进士及第。针对这两件公案,曾丰说,看来“朱衣点头”之说所传非误。但接下来,他又补充论述:科考取士有如结网,网眼疏漏,遗才也是难免的。唐代诗人陈陶就有“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之句,意谓:不要说华夏大地上没有奇才异能之士,是皇家科考的结网出了毛病,以致漏掉了英才。至于导致“网疏”的因素那就多了,比如主考官“看走眼”了,造成取舍失当——“眊矂”意为眼睛没有看清楚。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里,借丑角胡颜之口,说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和“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两句话,又使“朱衣点头”成为旧时科考中主考官掌控举子命运的同义语。这样,“朱衣”也就实实在在地成为考官以至权贵的代名词了。徐渭为世所公认的奇才,少有“神童”之誉,九岁能为举子文,却八次“举于乡而不售”,一生久困科场。所以,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指出,《四声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说到科考中的衡文取士,这里的文章可就多了。大而关联整个科举制度,对人才以及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小而涉及对举子及其程文(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这一具体对象的评鉴,集中体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只说一句“文章中试官”,未免过于情绪化、简单化。
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其客观性表现为,作为竞争择优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从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体现了社会公正性。包括科目设定、试场管理、遴选标准、考评程序,都有明确的规范化、程式化要求;在“以程文定去留”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也是客观衡定的,比如宋初就以“右文、崇儒、通经”为宗旨。而其主观性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且不说试卷本身所形成的特殊质素(苏轼应礼部进士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独创性与唯一性,即其显例),单就评判主体讲,由于评鉴试卷属于价值判断,必然要受制甚至取决于认知主体的文化水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心理素质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就带来了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
《儒林外史》里讲,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在了一边。又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上了第一名。
前人指出,取士、审美、衡文,往往存在慕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偏向,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当然,就精神产品的特质来说,评判、鉴赏确实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诗圣”杜甫的诗,在与其同时代的选本《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中,无一入选,以致到了晚年他曾悲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西方这种情况也不鲜见。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完稿后,勉强印出750册,无人问津。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朽价值。
衡文、审美,以及各类精神产品的生产、鉴定与流传,固然离不开个体性与主观性,但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就失之偏颇了。要言之,文章的创作与赏鉴都是有规律、有标准、有章法可循的,所谓“文有律则,而无定体”。中国最早的文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尚书·尧典》;迨至三国时期出现了曹丕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传诵至今的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名著,单是创作论就有二十篇,分析研究文思、风格、体势、通变、谋篇、情采、修辞、声律、章句等各类问题,还有四篇阐述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人品与文品等。
不过,莫说实际把握,哪怕是精准地表述这些准则,都颇为不易,连刘勰都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见识浅陋,怎能讲出规矩法则呢)?”为文亦然。我们不能因为说不清楚,便否定客观“凭据”的存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5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朱衣点头”
作者:王充闾
由于兼任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曾参加几次博士生、硕士生答辩。记得一次在答辩委员会的晚餐席上,一位老教授说,这是“朱衣人”的聚会,大家会心地笑了。原来,这里有个著名的掌故——
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时,每阅试卷,常觉座后有朱衣人时复点头,然后其文必入选。始疑其为侍吏,及回顾之,一无所见。尝有句云:“唯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当时的一种幻觉。
到了南宋文学家曾丰笔下,开始把“朱衣点头”同遴才取士联系起来。他有这样两首七绝:“坡老不期遗李廌,欧公犹误取刘晖。点头道有朱衣吏,今古相传未必非。”“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生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说当年苏东坡主持礼部贡试时遗漏掉了李廌,出乎意料,深为自责。而欧阳修担任主考时却误取了刘晖。欧阳公倡导古文运动,刘几为文不合要求,被淘汰出局。时隔两年,刘几易名刘晖,文风丕变,欧公大为赞赏,遂得进士及第。针对这两件公案,曾丰说,看来“朱衣点头”之说所传非误。但接下来,他又补充论述:科考取士有如结网,网眼疏漏,遗才也是难免的。唐代诗人陈陶就有“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之句,意谓:不要说华夏大地上没有奇才异能之士,是皇家科考的结网出了毛病,以致漏掉了英才。至于导致“网疏”的因素那就多了,比如主考官“看走眼”了,造成取舍失当——“眊矂”意为眼睛没有看清楚。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里,借丑角胡颜之口,说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和“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两句话,又使“朱衣点头”成为旧时科考中主考官掌控举子命运的同义语。这样,“朱衣”也就实实在在地成为考官以至权贵的代名词了。徐渭为世所公认的奇才,少有“神童”之誉,九岁能为举子文,却八次“举于乡而不售”,一生久困科场。所以,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指出,《四声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说到科考中的衡文取士,这里的文章可就多了。大而关联整个科举制度,对人才以及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小而涉及对举子及其程文(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这一具体对象的评鉴,集中体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只说一句“文章中试官”,未免过于情绪化、简单化。
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其客观性表现为,作为竞争择优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从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体现了社会公正性。包括科目设定、试场管理、遴选标准、考评程序,都有明确的规范化、程式化要求;在“以程文定去留”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也是客观衡定的,比如宋初就以“右文、崇儒、通经”为宗旨。而其主观性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且不说试卷本身所形成的特殊质素(苏轼应礼部进士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独创性与唯一性,即其显例),单就评判主体讲,由于评鉴试卷属于价值判断,必然要受制甚至取决于认知主体的文化水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心理素质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就带来了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
《儒林外史》里讲,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在了一边。又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上了第一名。
前人指出,取士、审美、衡文,往往存在慕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偏向,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当然,就精神产品的特质来说,评判、鉴赏确实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诗圣”杜甫的诗,在与其同时代的选本《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中,无一入选,以致到了晚年他曾悲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西方这种情况也不鲜见。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完稿后,勉强印出750册,无人问津。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朽价值。
衡文、审美,以及各类精神产品的生产、鉴定与流传,固然离不开个体性与主观性,但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就失之偏颇了。要言之,文章的创作与赏鉴都是有规律、有标准、有章法可循的,所谓“文有律则,而无定体”。中国最早的文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尚书·尧典》;迨至三国时期出现了曹丕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传诵至今的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名著,单是创作论就有二十篇,分析研究文思、风格、体势、通变、谋篇、情采、修辞、声律、章句等各类问题,还有四篇阐述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人品与文品等。
不过,莫说实际把握,哪怕是精准地表述这些准则,都颇为不易,连刘勰都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见识浅陋,怎能讲出规矩法则呢)?”为文亦然。我们不能因为说不清楚,便否定客观“凭据”的存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5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朱衣点头”
作者:王充闾
由于兼任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曾参加几次博士生、硕士生答辩。记得一次在答辩委员会的晚餐席上,一位老教授说,这是“朱衣人”的聚会,大家会心地笑了。原来,这里有个著名的掌故——
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时,每阅试卷,常觉座后有朱衣人时复点头,然后其文必入选。始疑其为侍吏,及回顾之,一无所见。尝有句云:“唯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当时的一种幻觉。
到了南宋文学家曾丰笔下,开始把“朱衣点头”同遴才取士联系起来。他有这样两首七绝:“坡老不期遗李廌,欧公犹误取刘晖。点头道有朱衣吏,今古相传未必非。”“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生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说当年苏东坡主持礼部贡试时遗漏掉了李廌,出乎意料,深为自责。而欧阳修担任主考时却误取了刘晖。欧阳公倡导古文运动,刘几为文不合要求,被淘汰出局。时隔两年,刘几易名刘晖,文风丕变,欧公大为赞赏,遂得进士及第。针对这两件公案,曾丰说,看来“朱衣点头”之说所传非误。但接下来,他又补充论述:科考取士有如结网,网眼疏漏,遗才也是难免的。唐代诗人陈陶就有“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之句,意谓:不要说华夏大地上没有奇才异能之士,是皇家科考的结网出了毛病,以致漏掉了英才。至于导致“网疏”的因素那就多了,比如主考官“看走眼”了,造成取舍失当——“眊矂”意为眼睛没有看清楚。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里,借丑角胡颜之口,说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和“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两句话,又使“朱衣点头”成为旧时科考中主考官掌控举子命运的同义语。这样,“朱衣”也就实实在在地成为考官以至权贵的代名词了。徐渭为世所公认的奇才,少有“神童”之誉,九岁能为举子文,却八次“举于乡而不售”,一生久困科场。所以,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指出,《四声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说到科考中的衡文取士,这里的文章可就多了。大而关联整个科举制度,对人才以及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小而涉及对举子及其程文(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这一具体对象的评鉴,集中体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只说一句“文章中试官”,未免过于情绪化、简单化。
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其客观性表现为,作为竞争择优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从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体现了社会公正性。包括科目设定、试场管理、遴选标准、考评程序,都有明确的规范化、程式化要求;在“以程文定去留”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也是客观衡定的,比如宋初就以“右文、崇儒、通经”为宗旨。而其主观性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且不说试卷本身所形成的特殊质素(苏轼应礼部进士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独创性与唯一性,即其显例),单就评判主体讲,由于评鉴试卷属于价值判断,必然要受制甚至取决于认知主体的文化水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心理素质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就带来了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
《儒林外史》里讲,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在了一边。又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上了第一名。
前人指出,取士、审美、衡文,往往存在慕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偏向,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当然,就精神产品的特质来说,评判、鉴赏确实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诗圣”杜甫的诗,在与其同时代的选本《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中,无一入选,以致到了晚年他曾悲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西方这种情况也不鲜见。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完稿后,勉强印出750册,无人问津。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朽价值。
衡文、审美,以及各类精神产品的生产、鉴定与流传,固然离不开个体性与主观性,但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就失之偏颇了。要言之,文章的创作与赏鉴都是有规律、有标准、有章法可循的,所谓“文有律则,而无定体”。中国最早的文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尚书·尧典》;迨至三国时期出现了曹丕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传诵至今的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名著,单是创作论就有二十篇,分析研究文思、风格、体势、通变、谋篇、情采、修辞、声律、章句等各类问题,还有四篇阐述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人品与文品等。
不过,莫说实际把握,哪怕是精准地表述这些准则,都颇为不易,连刘勰都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见识浅陋,怎能讲出规矩法则呢)?”为文亦然。我们不能因为说不清楚,便否定客观“凭据”的存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5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