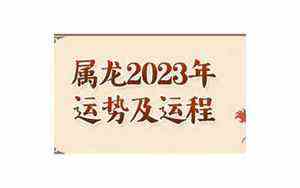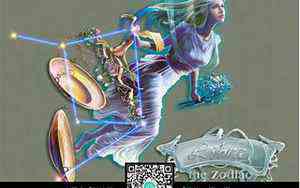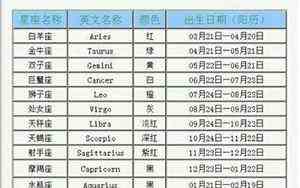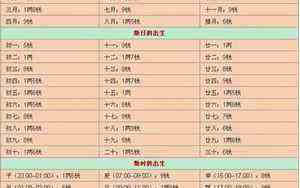
但愿众生悉离苦
节选自郑伟宏所著“神功奇气,放净光明”一文:
天道酬勤。金字塔倘没有壮阔厚实的塔基,它的尖顶是放不上去的。在孔宪德先生的“血液成份”中,儒、释、道三家“化合”在一起。古人有言,“三教合一”。儒、释、道三家的气功理论和实践本来就是相通的。
孔宪德,“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后裔,悠悠千载,屈指算来,已是孔氏余脉中的第72代。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练静功刚入定,突然感觉从自己身上飞出两把宝剑,在头顶上盘旋缠绕,两剑格斗正酣,幻觉中又突然出现孔圣人,交战双方顿时握手言和,干戈化为玉帛。孔宪德领悟道:“儒家就是主张‘和为贵’嘛!”打那以后,他常以此情此景自诫。
在气功前辈眼中,孔宪德先生是一位学而不厌、恭敬有礼的好弟子。许多气功同道都乐意与他切磋技艺,道心相见,各自倾其私囊,这就难怪众人心目中的这位“谦谦君子”常常能吸收到八方的雨露和养份了。
他说,儒、道、佛三家气功之中,他自己还是以佛家气功见长。乍看上去,本文的主人公与仙风道骨的气功大师对不上号。
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一副眼镜平添三分文弱。刚刚进入“知天命”的年头,已是满头灰白。然而,他那玉质的肤色,奕奕放光的眼神又仿佛把岁月扣去了二三十年。还在青年时代,他就陷入了艰难困苦。
20几岁的小伙子,本该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却过早地“白了少年头”。走上课堂,拿起粉笔想睡觉;头发一撸,一把把往下掉;眼睛渐渐近视、渐渐加深;最槽糕的还是他那嘭嘭跳动的心脏,响音之大,连睡在后客堂的姐姐都能听到……
他到底是生活中的强者。他开始了锻炼。从复兴公园到杨树浦上班,每天来回步行4小时。一个多月过去、体质慢慢起了变化。
后来,一位太极里手成了他的发蒙之师。
丁受三,是位可尊敬的老律师,70多岁了。“文革”中辍业在家,常教人打太极拳。孔宪德每天教课之余,便与丁师傅纠缠在一起。老先生喜欢钻研拳论,咬文嚼字,颇有心得。“两军对峙,喉头不可抛!”老拳师常以此古人警句告诫自己的学生。意思是说打拳时要做到下领回收,下颌回收的目的是虚领顶劲。古人不是直道其详,说话含藏得很,要靠自己领悟。
几易寒暑,勤奋结硕果,他的太极功夫和理论修养都打下扎实的功底。身形活了、圆了、灵了。
在公园里,又有一位80多岁的王伯,为他个别传授道家功法,帮他把两眼之间的祖穴窍,还有神阙、膻中、印堂、会阴依次一一打通。
他开始读气功书,与同好们探讨道家采气方法。起初学采树木之气,继之学采日月之气,接着又广采宇宙之气。他说,每次采气之后都要回向,否则不平衡,“采了树木之气不回向,鸟雀也会有意见。”
1981年,一代宗师阙阿水公开传授武林中素享盛名的少林内劲一指禅功。孔宪德师从名家,功夫更上层楼。
内劲一指禅功的最大特点是顺乎自然,生根于地,长劲于身,练气于脏腑,营养于天地。一般练至二三年,还会有意透功能,不知不觉察知对方有什么毛病,亦能用无意识方法为他人推拿按摩,点穴导引,功夫熟练时,还能自发地打出一套罗汉神拳。阙大师对孔宪德说:“孔老师,你是读书人,我没文化,教不好。”话虽这么说,一招一式,教得却特别认真。
三九严寒,夜深人寐,万籁俱寂时,孔宪德遵师嘱练托天罗汉桩。每天凌晨从2点到4点,就练这么一个招式,单调而乏味。无人陪练,无人督促。可运动量却很大,常常站得浑身上下湿透。其勤奋、其毅力可以想见。
一个春秋过去,他觉得气血畅通了,力量增强了。身体感到上轻下重。脚下出现灵根,脑子也灵敏多了。没料到一代宗师因劳累过度溘然长逝。
痛失良师。从此他益发刻苦练功。在师兄弟们的帮助下,日进有功。1983年,成人中还很少见的特异功能在他身上也慢慢诱发出来。他当时的透视功能虽不算强,但毕竟轰开了天目穴。1984年,他修习佛教净土法门。
清灯长夜,对着《观经》中十六观想图,面壁静坐观想。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把墙壁看穿。尽管是眼睁睁的,墙壁似不复存在,远处出现一幅“落日悬鼓”的美妙景象:夕阳西垂在海平面上,晚霞满天,水中一个圆球,火红火红的。从此他具备了遥感功能。
到了1986年,孔宪德皈依佛教密宗,师从清定上师,他的功夫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清定上师向他传授了“白骨观”密法。这是一种静坐功。在禅坐中,内视白骨,达到贪欲休止、浑身光明的效果。习练此法后,孔宪德的透视、遥视功能得到增强,图像变得清晰起来。
一次,清定上师为弟子们摩顶加持。孔宪德与上师一碰头,自己头右边有一火球热乎乎地往下落,直往右脚心钻,刹时全身火热。他心里明白:“师父给功夫了。”
孔宪德推心置腹地对同道们说,他自己的很多功夫是“飞”来的。这几年,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江浙的佛教名山,常常留下他朝圣的足迹。
夏日的雁荡山,悬崖飞瀑,山灵水秀,吸引得游人如织。寺庙中有位年近百岁、功深德厚的老法师,他欣慰地接纳了一位不出家的徒弟。
慧眼识英才。气功界里有种说法,高功夫的人收徒,实际上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
山上这位高僧有自已的择徒标准。人生在世,要多行善,莫作恶。他说。“一个人做了坏事,身上会留下一个黑点;做了一件好事,身上会留下一点红光。”
一个人,就是一个发光体。是作恶多端,还是乐善好施,是功大过小,还是功不抵过,有神通的人一目了然。
孔宪德身体力行的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悉离苦”。他那外清内澄、九窍光明之躯就是他清朗品格的见证。老法师收他为徒当在情理之中。
孔大师说,红光、黑点出现在人体的各个部位,是全息反映的。好事做得多的人,心花开得好,遍体是红光。一个人肝有毛病,把肝放大来看,倘做过几件坏事,便会有几个黑点。查查胃,也会有同样发现。
“练功先练德,做起来难啊”他感叹地说。阙师傅给我讲得最多的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清定上师则谆谆告诚我们要`以善为上,有菩提心’。”
近几年来,孔宪德和他的夫人曹雪萍,接待了数万人次的来访者。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不论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还是海外来客,上层人士,他们都一视同仁,尊为上宾。许多人都愿意到他们家这快“风水宝地”中坐一坐。有病治病,无病长功。
他们夫妇上班忙,下斑更忙。孔宪德先生在学校里,教学之余还常常有人见缝插针找他诊治。下班回家,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已是高朋满座了。
成年累月,他总是百问不厌,几乎有求必应。人人都说孔老师心地真好,没有一点火气,从不怕麻烦。
别人上门求医或者请他出诊,他从不收费,义务诊治。有时应单位之邀,教功、治病,推辞不掉,得些报酬,也大多用来捐赠。他认为,评价一个气功师,不光看你功夫深浅,更重要的是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他视一己之名利有如淡水,把利乐有情作为终身之大业。日本有家电视台要来采访报道,他婉言谢绝。他从不图虚名,与世无争。宁静淡泊,似芙蓉出于清水。
在气功大师孔宪德的家中,国际业余泳联执委梅振耀先生所赠的一个条幅,上有四个大字:放净光明。
真是“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光明广大。”他就像一朵莲花,是那样的清净、纯洁、秀美。
但愿众生悉离苦
节选自郑伟宏所著“神功奇气,放净光明”一文:
天道酬勤。金字塔倘没有壮阔厚实的塔基,它的尖顶是放不上去的。在孔宪德先生的“血液成份”中,儒、释、道三家“化合”在一起。古人有言,“三教合一”。儒、释、道三家的气功理论和实践本来就是相通的。
孔宪德,“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后裔,悠悠千载,屈指算来,已是孔氏余脉中的第72代。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练静功刚入定,突然感觉从自己身上飞出两把宝剑,在头顶上盘旋缠绕,两剑格斗正酣,幻觉中又突然出现孔圣人,交战双方顿时握手言和,干戈化为玉帛。孔宪德领悟道:“儒家就是主张‘和为贵’嘛!”打那以后,他常以此情此景自诫。
在气功前辈眼中,孔宪德先生是一位学而不厌、恭敬有礼的好弟子。许多气功同道都乐意与他切磋技艺,道心相见,各自倾其私囊,这就难怪众人心目中的这位“谦谦君子”常常能吸收到八方的雨露和养份了。
他说,儒、道、佛三家气功之中,他自己还是以佛家气功见长。乍看上去,本文的主人公与仙风道骨的气功大师对不上号。
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一副眼镜平添三分文弱。刚刚进入“知天命”的年头,已是满头灰白。然而,他那玉质的肤色,奕奕放光的眼神又仿佛把岁月扣去了二三十年。还在青年时代,他就陷入了艰难困苦。
20几岁的小伙子,本该朝气蓬勃,风华正茂,却过早地“白了少年头”。走上课堂,拿起粉笔想睡觉;头发一撸,一把把往下掉;眼睛渐渐近视、渐渐加深;最槽糕的还是他那嘭嘭跳动的心脏,响音之大,连睡在后客堂的姐姐都能听到……
他到底是生活中的强者。他开始了锻炼。从复兴公园到杨树浦上班,每天来回步行4小时。一个多月过去、体质慢慢起了变化。
后来,一位太极里手成了他的发蒙之师。
丁受三,是位可尊敬的老律师,70多岁了。“文革”中辍业在家,常教人打太极拳。孔宪德每天教课之余,便与丁师傅纠缠在一起。老先生喜欢钻研拳论,咬文嚼字,颇有心得。“两军对峙,喉头不可抛!”老拳师常以此古人警句告诫自己的学生。意思是说打拳时要做到下领回收,下颌回收的目的是虚领顶劲。古人不是直道其详,说话含藏得很,要靠自己领悟。
几易寒暑,勤奋结硕果,他的太极功夫和理论修养都打下扎实的功底。身形活了、圆了、灵了。
在公园里,又有一位80多岁的王伯,为他个别传授道家功法,帮他把两眼之间的祖穴窍,还有神阙、膻中、印堂、会阴依次一一打通。
他开始读气功书,与同好们探讨道家采气方法。起初学采树木之气,继之学采日月之气,接着又广采宇宙之气。他说,每次采气之后都要回向,否则不平衡,“采了树木之气不回向,鸟雀也会有意见。”
1981年,一代宗师阙阿水公开传授武林中素享盛名的少林内劲一指禅功。孔宪德师从名家,功夫更上层楼。
内劲一指禅功的最大特点是顺乎自然,生根于地,长劲于身,练气于脏腑,营养于天地。一般练至二三年,还会有意透功能,不知不觉察知对方有什么毛病,亦能用无意识方法为他人推拿按摩,点穴导引,功夫熟练时,还能自发地打出一套罗汉神拳。阙大师对孔宪德说:“孔老师,你是读书人,我没文化,教不好。”话虽这么说,一招一式,教得却特别认真。
三九严寒,夜深人寐,万籁俱寂时,孔宪德遵师嘱练托天罗汉桩。每天凌晨从2点到4点,就练这么一个招式,单调而乏味。无人陪练,无人督促。可运动量却很大,常常站得浑身上下湿透。其勤奋、其毅力可以想见。
一个春秋过去,他觉得气血畅通了,力量增强了。身体感到上轻下重。脚下出现灵根,脑子也灵敏多了。没料到一代宗师因劳累过度溘然长逝。
痛失良师。从此他益发刻苦练功。在师兄弟们的帮助下,日进有功。1983年,成人中还很少见的特异功能在他身上也慢慢诱发出来。他当时的透视功能虽不算强,但毕竟轰开了天目穴。1984年,他修习佛教净土法门。
清灯长夜,对着《观经》中十六观想图,面壁静坐观想。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把墙壁看穿。尽管是眼睁睁的,墙壁似不复存在,远处出现一幅“落日悬鼓”的美妙景象:夕阳西垂在海平面上,晚霞满天,水中一个圆球,火红火红的。从此他具备了遥感功能。
到了1986年,孔宪德皈依佛教密宗,师从清定上师,他的功夫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清定上师向他传授了“白骨观”密法。这是一种静坐功。在禅坐中,内视白骨,达到贪欲休止、浑身光明的效果。习练此法后,孔宪德的透视、遥视功能得到增强,图像变得清晰起来。
一次,清定上师为弟子们摩顶加持。孔宪德与上师一碰头,自己头右边有一火球热乎乎地往下落,直往右脚心钻,刹时全身火热。他心里明白:“师父给功夫了。”
孔宪德推心置腹地对同道们说,他自己的很多功夫是“飞”来的。这几年,上海的玉佛寺、静安寺、龙华寺,江浙的佛教名山,常常留下他朝圣的足迹。
夏日的雁荡山,悬崖飞瀑,山灵水秀,吸引得游人如织。寺庙中有位年近百岁、功深德厚的老法师,他欣慰地接纳了一位不出家的徒弟。
慧眼识英才。气功界里有种说法,高功夫的人收徒,实际上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
山上这位高僧有自已的择徒标准。人生在世,要多行善,莫作恶。他说。“一个人做了坏事,身上会留下一个黑点;做了一件好事,身上会留下一点红光。”
一个人,就是一个发光体。是作恶多端,还是乐善好施,是功大过小,还是功不抵过,有神通的人一目了然。
孔宪德身体力行的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悉离苦”。他那外清内澄、九窍光明之躯就是他清朗品格的见证。老法师收他为徒当在情理之中。
孔大师说,红光、黑点出现在人体的各个部位,是全息反映的。好事做得多的人,心花开得好,遍体是红光。一个人肝有毛病,把肝放大来看,倘做过几件坏事,便会有几个黑点。查查胃,也会有同样发现。
“练功先练德,做起来难啊”他感叹地说。阙师傅给我讲得最多的是`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清定上师则谆谆告诚我们要`以善为上,有菩提心’。”
近几年来,孔宪德和他的夫人曹雪萍,接待了数万人次的来访者。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不论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还是海外来客,上层人士,他们都一视同仁,尊为上宾。许多人都愿意到他们家这快“风水宝地”中坐一坐。有病治病,无病长功。
他们夫妇上班忙,下斑更忙。孔宪德先生在学校里,教学之余还常常有人见缝插针找他诊治。下班回家,晚饭还没来得及吃,已是高朋满座了。
成年累月,他总是百问不厌,几乎有求必应。人人都说孔老师心地真好,没有一点火气,从不怕麻烦。
别人上门求医或者请他出诊,他从不收费,义务诊治。有时应单位之邀,教功、治病,推辞不掉,得些报酬,也大多用来捐赠。他认为,评价一个气功师,不光看你功夫深浅,更重要的是看你做了多少好事。他视一己之名利有如淡水,把利乐有情作为终身之大业。日本有家电视台要来采访报道,他婉言谢绝。他从不图虚名,与世无争。宁静淡泊,似芙蓉出于清水。
在气功大师孔宪德的家中,国际业余泳联执委梅振耀先生所赠的一个条幅,上有四个大字:放净光明。
真是“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光明广大。”他就像一朵莲花,是那样的清净、纯洁、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