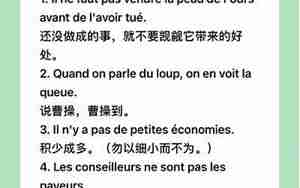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西周史话·礼乐制度:礼仪之邦的形成,影响中国三千年
中国是文明世界的礼仪之邦,这里的礼仪指的就是礼乐制度。礼乐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明特征,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一套完善的等级制度。“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是天地之间的秩序,象征着威严的等级;乐是天地之和,能够调节社会矛盾。礼乐文化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萌芽,经过夏商两代初步发展,到西周完备。春秋战国以后,礼崩乐坏,但是礼乐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深远,一直存在于几千年的社会中。
祭祀活动
礼本是古人事神祈福的一系列原始宗教仪式的总称。乐则是在宗教祭祀仪式上的歌舞表演。礼本写作“禮”,从示,从豊( lǐ)。“示”指祭祀中的祭品,“豊”是祭品的器具,延伸为祭祀礼仪。《礼记》提到礼是“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礼记·礼运》记载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就是对人们祭神的描述。
祭祀活动
到了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私有制出现,阶级开始分化。宗教也逐渐被王权垄断,祭祀活动作为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自然被王权垄断。《国语·楚语》记载了昭王问观射父关于“绝地天通”的事情,观射父解释道: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也就是说普通百姓也能够和神进行沟通,使得君王“无有严威”,于是颛顼禁止了普通百姓的祭祀权。在原始社会的墓葬中,只有地位高的墓葬中才会出土玉器、斧钺等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礼器。到了夏朝建立后,祭祀仪式和器具已经有了严格的等级规定。大禹垄断了青铜器的制造,铸造九鼎,以彰显自己的权威。
夏商的礼乐制度都比较原始,其目的也就是垄断宗教解释权,形成了王权神化的现象。商朝贵族宣传天命观,认为这是天帝派遣来统治百姓的命令。而商朝贵族则通过祭祀活动和占卜活动垄断和天帝的沟通。
夏商时期,乐舞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传言“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这些乐舞就是在神祀、社祭、鬼享、军事、宴乐等大型的活动中使用的仪式。和礼器一样,乐舞也是有等级规则,不同的人使用的乐舞规模和形式都不同。
周人是一个十分重视人伦道德规范的民族,早在先周时期,周族就开始建立一套礼乐规范。在周朝建立后,周公就开始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之上,建立一套严密的礼乐制度。《尚书》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
乐舞
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在继承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夏商的礼乐,主要表现为“尊天事鬼”或者“尊天事神”,而周代的礼乐更加强调对黎民百姓的关注,表现了“尊天事人”的德政和民本思想。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配合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等,成为维护周朝统治秩序的主要制度,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法则,同时也能和谐贵族之间的关系。周礼规定了贵族的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诸多项目。礼和乐配合使用,不同尊卑的人使用不同规模的礼,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例如祭祀活动中,天子使用“太牢”,而诸侯则只能使用“少牢”。
傩戏
礼乐制定之后,西周前期采取礼治,也就是德政或者仁政。《史记》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是中国古代礼治社会的高度赞扬。但是礼始终只是在贵族之间使用,贵族都是一家人,因而使用礼能够和谐大家的关系,增强凝聚力。但是针对黎民,则采取刑法,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能很好的体现礼乐的本质,就是维护贵族的等级地区。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周室衰微,诸侯崛起,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的霸主尚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匡正当时的局面。到了战国时代,诸侯纷纷称王,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诸侯和卿大夫僭越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是一切以权力说话。在王权衰落的情况下,礼乐制作无法维系,最终走向了衰亡。而秦汉统一后,又建立了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礼乐制度,那边是礼乐制的另一种发展了。
“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作者:华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礼关系下的《礼记》礼义学研究”负责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通情达礼”的基本内涵
称情立文。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古人以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故《礼记·曾子问》言:“君子礼以饰情。”正所谓“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不过,古人很重视人情之真,对矫饰之情则持批评态度,故言“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外,古人还言道:“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真情成为善、贵、信等价值评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人对脱离人情的礼表达了质疑,如《礼记·檀弓上》言:“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总体来看,古人以为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所谓“情具于人,先王制礼以顺之,而喜怒哀乐由此而和”;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所谓“好恶正则天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礼的教化作用就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实现“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不逾矩”。概言之,人的好恶之情与礼之间存在顺与节两种关系,其间的分别就在于好恶之情的发动是否合于礼。合则顺行,逆则有节。所谓“克己复礼”,即是“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究其实就是贬抑自身膨胀的欲望,约身合礼以待人行事。古人一则从利生成人的角度讲求“以礼达情”,一则从养生合道的角度强调“以礼节情”。二者可谓一体两面,共同服务于立人成德这一人文化成的目标。
礼者理也。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是情理关系。情理关系可概括为好恶之情与所以然、所当然的关系。所以然可谓是好恶之情得以形成和展开的现实因,是促成好恶之情的现实诸因缘合称,恰如朱熹所言:“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从所以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受制于外物刺激和自我感受,正所谓“感于物而动”。所当然则是指好恶之情的本质规定,亦是所以然中确定不移的部分,对此古人言“有物有则”。从所当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有其内在规定。《论语·卫灵公》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种对好恶之“察”即意味着对于情感发动的所当然之理的发明。对此古人又言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由此可见,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好善而恶恶”的人道原则为思想基础。所谓仁者乃是人道的人格体现,他以行仁为人最本己的存在;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忠恕之道为实践沟通原则。尽己以立身,推己乃成德,忠恕即为立身成德之事。从立身成德之完成上讲,尽己之忠是推己之恕的前提基础,而推己之恕则是尽己之忠的外在展开实现。故忠恕实为立身成德的一体两面。古人内外合一、成己成人的道德内涵即在此中得以一贯。换言之,人自身都有“所欲”和“不欲”,得乎“忠恕”就在于理解人皆有“所欲”与“不欲”而求得彼此一贯的通情;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又以无过犹不及的中和之道为价值实现原则。礼乃称情立文,中礼本质上是得其情实,其外在特征在于“别”,即“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目的在于体现存在之实。但是礼这一目的的实现最终则需落在“和”上,否则就会落入“礼胜则离”的境地。
以礼达理。“理”为事物之条理、秩序,莫非自然,要在于顺。“礼”与“理”的关系是粲然之“文”与内涵之“理”的对应关系。古人言:“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又言:“礼由外作,而合乎万事之理。”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言,特定的事物蕴含着特定的理,事物与理应,如程颢曾言:“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相对于礼而言,则特定的礼与特定的理对应,其目的就在于以文相别。“礼”与“理”的关系建基于具体事物之上,故绝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言“理”与“礼”,正所谓“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对应于具体事物之理的礼文虽然“至繁”,然如能规约于理,则可实现以简驭繁而不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还需处理好另一个问题,即“以义制仪”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变礼的问题。古人以为“礼者,义之定制也;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合,虽先王未有此礼,可酌于义而创为之”。由此可见,作为“礼之权度”的“义”乃是“随时制宜”的伦理原则,它是制礼的依据。相较而言,礼仪则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定制。由于礼义随时制宜,也就自然会不断冲击礼仪之定制,进而引发变礼与制礼的问题。为此就要“明其体而达其用,穷其源而析其流,尽古今之变而备人事之宜”。总之,礼义与礼仪的关系,一方面可谓是无仪无以显义,无义无以定仪;另一方面则是义者随时制宜,仪可以义起。二者的统一既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又体现为动态实践上的相生相成关系。
“通情达礼”的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民族性与民族文化不断转化与创新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围绕转化与创新这一主旨,以民族文化来彰显民族性无疑是一种存在实现方式。它既是民族性的变现,亦是现代性的发展。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此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立乎情理。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德、法并行。礼乐之教显为德治,刑政之治则属法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正所谓刑以弼教,法以济礼,二者相须而成,实质是力求情、理、法的一贯。礼乐之教,得乎情理,化民以德,培善成俗,可谓智深而谋远。法之所罚在于示以威信,止邪归正,正所谓“礼以行义,刑以正邪”。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再者,礼法之用要在中道合义,不可拘泥不化。古人云:“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知有者,可以义起。”无论德治还是法治,皆属政教之一端,所谓道无常道,法无常法,要在审时度势,因势合义,以俾于事,而非固执一端;此外,传统的以德入法乃是就立法的精神原则、理想指向而言,即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惩恶扬善、成就德行,正所谓“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古人论及刑政理想时皆言“为政以德”,但绝非是用道德规范来直接代替刑政之法。为此,古人曾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如果强行理想化地以德入法,则极易导致因道德绑架而轻易构人以罪抑或纵容犯罪。以上思想对当下构建道德文明与法治社会不无裨益。
存敬有畏。中华礼乐文明要在确立人道,其人道实践是在崇天敬祖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古人看来,“崇天”,一则在于“天地者,生之本也”,人道亦本于天,且内在于人,是人的存在规定、价值本原;二则在于“天命无不报”,即天命具有不假人为的至上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古人讲“知天命”“畏天命”,即是在提示行人道的同时,亦要敬畏天命,修身以俟之,正所谓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而“敬祖”则在于“人本乎祖”“无先祖,恶出”,古人提出敬祖意在“重仁袭恩”,不忘先人业绩。以此为基础,古人又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说法,这是将敬祖行为进一步纳入移风易俗的活动之中。崇天敬祖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古人“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人文精神。
在此背景下,人即是一个知止守道、存敬有畏的现实规范性存在。当前社会中涌现出无知无畏、娱乐至死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人心缺少了对于天理道义的敬畏感,以致行为肆无忌惮。结合中华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精神对此做适当反思,当是颇具建设性的。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作者:华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礼关系下的《礼记》礼义学研究”负责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通情达礼”的基本内涵
称情立文。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古人以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故《礼记·曾子问》言:“君子礼以饰情。”正所谓“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不过,古人很重视人情之真,对矫饰之情则持批评态度,故言“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外,古人还言道:“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真情成为善、贵、信等价值评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人对脱离人情的礼表达了质疑,如《礼记·檀弓上》言:“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总体来看,古人以为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所谓“情具于人,先王制礼以顺之,而喜怒哀乐由此而和”;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所谓“好恶正则天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礼的教化作用就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实现“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不逾矩”。概言之,人的好恶之情与礼之间存在顺与节两种关系,其间的分别就在于好恶之情的发动是否合于礼。合则顺行,逆则有节。所谓“克己复礼”,即是“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究其实就是贬抑自身膨胀的欲望,约身合礼以待人行事。古人一则从利生成人的角度讲求“以礼达情”,一则从养生合道的角度强调“以礼节情”。二者可谓一体两面,共同服务于立人成德这一人文化成的目标。
礼者理也。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是情理关系。情理关系可概括为好恶之情与所以然、所当然的关系。所以然可谓是好恶之情得以形成和展开的现实因,是促成好恶之情的现实诸因缘合称,恰如朱熹所言:“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从所以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受制于外物刺激和自我感受,正所谓“感于物而动”。所当然则是指好恶之情的本质规定,亦是所以然中确定不移的部分,对此古人言“有物有则”。从所当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有其内在规定。《论语·卫灵公》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种对好恶之“察”即意味着对于情感发动的所当然之理的发明。对此古人又言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由此可见,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好善而恶恶”的人道原则为思想基础。所谓仁者乃是人道的人格体现,他以行仁为人最本己的存在;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忠恕之道为实践沟通原则。尽己以立身,推己乃成德,忠恕即为立身成德之事。从立身成德之完成上讲,尽己之忠是推己之恕的前提基础,而推己之恕则是尽己之忠的外在展开实现。故忠恕实为立身成德的一体两面。古人内外合一、成己成人的道德内涵即在此中得以一贯。换言之,人自身都有“所欲”和“不欲”,得乎“忠恕”就在于理解人皆有“所欲”与“不欲”而求得彼此一贯的通情;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又以无过犹不及的中和之道为价值实现原则。礼乃称情立文,中礼本质上是得其情实,其外在特征在于“别”,即“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目的在于体现存在之实。但是礼这一目的的实现最终则需落在“和”上,否则就会落入“礼胜则离”的境地。
以礼达理。“理”为事物之条理、秩序,莫非自然,要在于顺。“礼”与“理”的关系是粲然之“文”与内涵之“理”的对应关系。古人言:“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又言:“礼由外作,而合乎万事之理。”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言,特定的事物蕴含着特定的理,事物与理应,如程颢曾言:“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相对于礼而言,则特定的礼与特定的理对应,其目的就在于以文相别。“礼”与“理”的关系建基于具体事物之上,故绝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言“理”与“礼”,正所谓“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对应于具体事物之理的礼文虽然“至繁”,然如能规约于理,则可实现以简驭繁而不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还需处理好另一个问题,即“以义制仪”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变礼的问题。古人以为“礼者,义之定制也;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合,虽先王未有此礼,可酌于义而创为之”。由此可见,作为“礼之权度”的“义”乃是“随时制宜”的伦理原则,它是制礼的依据。相较而言,礼仪则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定制。由于礼义随时制宜,也就自然会不断冲击礼仪之定制,进而引发变礼与制礼的问题。为此就要“明其体而达其用,穷其源而析其流,尽古今之变而备人事之宜”。总之,礼义与礼仪的关系,一方面可谓是无仪无以显义,无义无以定仪;另一方面则是义者随时制宜,仪可以义起。二者的统一既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又体现为动态实践上的相生相成关系。
“通情达礼”的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民族性与民族文化不断转化与创新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围绕转化与创新这一主旨,以民族文化来彰显民族性无疑是一种存在实现方式。它既是民族性的变现,亦是现代性的发展。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此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立乎情理。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德、法并行。礼乐之教显为德治,刑政之治则属法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正所谓刑以弼教,法以济礼,二者相须而成,实质是力求情、理、法的一贯。礼乐之教,得乎情理,化民以德,培善成俗,可谓智深而谋远。法之所罚在于示以威信,止邪归正,正所谓“礼以行义,刑以正邪”。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再者,礼法之用要在中道合义,不可拘泥不化。古人云:“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知有者,可以义起。”无论德治还是法治,皆属政教之一端,所谓道无常道,法无常法,要在审时度势,因势合义,以俾于事,而非固执一端;此外,传统的以德入法乃是就立法的精神原则、理想指向而言,即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惩恶扬善、成就德行,正所谓“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古人论及刑政理想时皆言“为政以德”,但绝非是用道德规范来直接代替刑政之法。为此,古人曾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如果强行理想化地以德入法,则极易导致因道德绑架而轻易构人以罪抑或纵容犯罪。以上思想对当下构建道德文明与法治社会不无裨益。
存敬有畏。中华礼乐文明要在确立人道,其人道实践是在崇天敬祖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古人看来,“崇天”,一则在于“天地者,生之本也”,人道亦本于天,且内在于人,是人的存在规定、价值本原;二则在于“天命无不报”,即天命具有不假人为的至上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古人讲“知天命”“畏天命”,即是在提示行人道的同时,亦要敬畏天命,修身以俟之,正所谓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而“敬祖”则在于“人本乎祖”“无先祖,恶出”,古人提出敬祖意在“重仁袭恩”,不忘先人业绩。以此为基础,古人又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说法,这是将敬祖行为进一步纳入移风易俗的活动之中。崇天敬祖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古人“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人文精神。
在此背景下,人即是一个知止守道、存敬有畏的现实规范性存在。当前社会中涌现出无知无畏、娱乐至死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人心缺少了对于天理道义的敬畏感,以致行为肆无忌惮。结合中华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精神对此做适当反思,当是颇具建设性的。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寓教于礼:中华礼仪的核心意蕴
作者:彭林(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西周是历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治的朝代。在周人看来,人的道德成长优先于一切,“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国家“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殷周制度论》),对官民的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而礼是道德之器械。如何通过礼乐之教提升全民道德水准,是周人竭尽心智研究与运作的重大课题,其中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值得借鉴。
理论探索形成共识
由《尚书》可知,周公、召公等政治精英对“德”与政权兴衰存亡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讨。同时,他们通过制礼作乐,将德治理念转化为制度,导入实操层面。由于最高层的提倡,各国贤达对德与礼的合理性论述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这在《左传》《国语》中随处可见。春秋季世,天下大乱,而孔子与七十子弦歌不辍,在理论层面对礼乐文明作深入探讨,创获巨大,《礼记》则是其结晶。
《礼记》体大思精,讨论的范围无远弗届,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实现大同目标的梯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祭祀天地,旨在“报”,报答它们的化生与养育之恩;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人当按照自然节令,与之共生共荣;人与天地并称“三才”,是万物的灵长,当知自别于禽兽;人人皆应以礼乐内外兼修,勉为君子,希圣希贤,以自身的君子风范,引领民众的道德提升等。这些论述精辟、缜密、深刻、通透,说理多浅近,好用譬喻,生动活泼,回答了人们对自身成长与社会发展最为关切的种种问题,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旨在走向“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运》)的大同境界,故深受历代学者、官员乃至民众喜爱,起到跨越时空统一举国认识的作用,意义深远。
顶层设计全面布局
周代先哲胸襟宽阔,格局宏大,但凡理论的视野所及处,礼的制度建设必随之到达,理念与礼制处处相适应,《周礼》是最好的例证。《周礼》以人法天,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框架,统摄三百六十官,旨在仿效宇宙六合、三百六十度。依据政府管理、社会生产、文化活动、民众生活等事物门类与性质的差异,将家国的礼仪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兵礼、嘉礼等五大类,举凡天文、历法、朝聘、政教、封疆、赋役、祭祀、司法、冠婚、丧葬、贺庆、服饰、宫室、车马、营造、匠作等,一一囊括其中。经精心设计的各种仪式,或庄重,或虔诚,或威武,或喜庆,人们涵泳于仪式之中,感受敬畏自然、崇拜先祖、孝敬父母、友善朋友、哀悼亡者、体恤灾民等的情感,亲历仪式化的生动过程,以及情景式的体验,自然而然地接受正能量的熏陶,身心得以净化、陶冶与提升。
周人从天下大局出发设计的礼制结构,将治国的总体理念有机分布于其中,形成血脉联系,政府日常运作与官民教化自然糅合,浑然一体。无论在哪个位置上,自己都是完整礼制制度下的一员,都在一盘棋局之中,彼此呼应,互相关联。如此成熟的职官体制,与成熟的礼学思想体系为表里,为以德礼治国,奠定了稳固的地基。
童蒙养正培根固本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礼仪教育从他们抓起,不仅时机好,而且效果好,无疑具有战略意义,故《周易》即已提出“童蒙养正”“培根固本”的理念。《礼记》的《曲礼》《内则》,《管子》的《弟子职》,都是当时的儿童礼仪教材。
儿童入世浅,尚未染于陋俗恶习,思想单纯,但模仿能力强,因此,从行为教育切入,在细节上培养品格,最能收到成效。古人将孝顺、谨严、恭敬、谦虚、从容、优雅等德行融入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礼节中。《礼记·内则》载,凡是未成年男女,鸡初鸣之后就要起床,洗漱之后,按照规定的样式韬发、束发,梳理成总角,在领口佩戴香囊,再收拾枕席,洒扫庭院,然后做各自的事情,旨在养成勤奋的人生态度与良好的生活习惯。
《礼记》中的“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长者不及,勿儳言”,“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等语,都是读书人必备的教养,意在培养尊师重道之心。朱熹《童蒙须知》说:“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正”,男子服饰要三紧“头紧、腰紧、脚紧”,将头、腰、脚三处的系带扎紧,人的精气神就起来。凡此,都是在小节处立大节,处处含有道德提示的作用。
童年养成的行为方式,印象最深,对将来立身行事,能产生最深层的影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故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贯之为常。”(《大戴礼记·保傅》)
君子典范引领社会
倡导德治与礼治,善化社会风气,需要君子的“标杆”引领。先秦文献中的“君子”包括两种人,一是有德有位的国君,二是有德无位的社会贤达。
君主居于社会高位,有公权力,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到民众,故但凡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郭店楚简·成之闻之》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
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上苟身服之,民必有甚焉者。君袀冕而立于阼,一宫之人不胜其敬。君衰绖而处位,一宫之人不胜其哀。君冠胄带甲而立于军,一军之人不胜其勇。上苟倡之,则民鲜不从矣。
善政要先体现在自身(身服善),民众才能做到更好(民必有甚者)。国君身穿不同的礼服出现在朝礼、丧礼、军礼场合,神色真诚,下属与民众,都会被深深打动,“鲜不从矣”。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就是此理。
社会贤达不受命于任何人,但笃信周孔之道,以礼修身进德,自奉甚严,自觉将礼的精神贯彻到生命体的所有层面,力求完美。如《礼记·表记》说:“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君子德行的完美从服饰开始,由外及内,扩展到君子之容、辞、德、行,一一相称,如此风范,足以为社会所景仰,成为民众仿效的楷模。
行为规范礼仪教育
社会的和谐与否,取决于人的素质。《孟子·离娄下》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君子有别于常人处甚多,而最重要的则是内心有“仁”与“礼”二字。有强烈的仁爱之心,行为上就一定有礼。仁爱,必然懂得尊重,懂得礼让,并且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坐立行走,举手投足,都能合于规范,不影响旁人。如此之类,都来自教育。
朱自清先生在他的《经典常谈》中谈及大众礼仪教育的必要性时,说了一番浅近而亲切的话:
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规矩。居丧以外,如婚姻、宴会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序和规矩,不能随便马虎过去;这样是表示郑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诚心。至于对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妇、朋友之间,也都自有一番道理。按着尊卑的分际,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朋友互相敬爱,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个人饮食言动,也都该有个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己的份儿,这也是礼的一部分。
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宜居城市,核心指标是人的整体文明水平,而它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出现,而是要经过人们的努力追求与积极争取,真诚付出,才有可能达标。《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与精神必须同步发展,可谓万古不废的至理名言。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是充分吸收历史文化智慧,切切实实谋划全民如何“知礼节”、更好地树立国家形象的时候了。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作者:华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礼关系下的《礼记》礼义学研究”负责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通情达礼”的基本内涵
称情立文。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古人以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故《礼记·曾子问》言:“君子礼以饰情。”正所谓“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不过,古人很重视人情之真,对矫饰之情则持批评态度,故言“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外,古人还言道:“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真情成为善、贵、信等价值评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人对脱离人情的礼表达了质疑,如《礼记·檀弓上》言:“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总体来看,古人以为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所谓“情具于人,先王制礼以顺之,而喜怒哀乐由此而和”;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所谓“好恶正则天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礼的教化作用就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实现“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不逾矩”。概言之,人的好恶之情与礼之间存在顺与节两种关系,其间的分别就在于好恶之情的发动是否合于礼。合则顺行,逆则有节。所谓“克己复礼”,即是“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究其实就是贬抑自身膨胀的欲望,约身合礼以待人行事。古人一则从利生成人的角度讲求“以礼达情”,一则从养生合道的角度强调“以礼节情”。二者可谓一体两面,共同服务于立人成德这一人文化成的目标。
礼者理也。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是情理关系。情理关系可概括为好恶之情与所以然、所当然的关系。所以然可谓是好恶之情得以形成和展开的现实因,是促成好恶之情的现实诸因缘合称,恰如朱熹所言:“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从所以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受制于外物刺激和自我感受,正所谓“感于物而动”。所当然则是指好恶之情的本质规定,亦是所以然中确定不移的部分,对此古人言“有物有则”。从所当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有其内在规定。《论语·卫灵公》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种对好恶之“察”即意味着对于情感发动的所当然之理的发明。对此古人又言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由此可见,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好善而恶恶”的人道原则为思想基础。所谓仁者乃是人道的人格体现,他以行仁为人最本己的存在;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忠恕之道为实践沟通原则。尽己以立身,推己乃成德,忠恕即为立身成德之事。从立身成德之完成上讲,尽己之忠是推己之恕的前提基础,而推己之恕则是尽己之忠的外在展开实现。故忠恕实为立身成德的一体两面。古人内外合一、成己成人的道德内涵即在此中得以一贯。换言之,人自身都有“所欲”和“不欲”,得乎“忠恕”就在于理解人皆有“所欲”与“不欲”而求得彼此一贯的通情;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又以无过犹不及的中和之道为价值实现原则。礼乃称情立文,中礼本质上是得其情实,其外在特征在于“别”,即“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目的在于体现存在之实。但是礼这一目的的实现最终则需落在“和”上,否则就会落入“礼胜则离”的境地。
以礼达理。“理”为事物之条理、秩序,莫非自然,要在于顺。“礼”与“理”的关系是粲然之“文”与内涵之“理”的对应关系。古人言:“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又言:“礼由外作,而合乎万事之理。”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言,特定的事物蕴含着特定的理,事物与理应,如程颢曾言:“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相对于礼而言,则特定的礼与特定的理对应,其目的就在于以文相别。“礼”与“理”的关系建基于具体事物之上,故绝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言“理”与“礼”,正所谓“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对应于具体事物之理的礼文虽然“至繁”,然如能规约于理,则可实现以简驭繁而不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还需处理好另一个问题,即“以义制仪”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变礼的问题。古人以为“礼者,义之定制也;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合,虽先王未有此礼,可酌于义而创为之”。由此可见,作为“礼之权度”的“义”乃是“随时制宜”的伦理原则,它是制礼的依据。相较而言,礼仪则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定制。由于礼义随时制宜,也就自然会不断冲击礼仪之定制,进而引发变礼与制礼的问题。为此就要“明其体而达其用,穷其源而析其流,尽古今之变而备人事之宜”。总之,礼义与礼仪的关系,一方面可谓是无仪无以显义,无义无以定仪;另一方面则是义者随时制宜,仪可以义起。二者的统一既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又体现为动态实践上的相生相成关系。
“通情达礼”的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民族性与民族文化不断转化与创新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围绕转化与创新这一主旨,以民族文化来彰显民族性无疑是一种存在实现方式。它既是民族性的变现,亦是现代性的发展。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此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立乎情理。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德、法并行。礼乐之教显为德治,刑政之治则属法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正所谓刑以弼教,法以济礼,二者相须而成,实质是力求情、理、法的一贯。礼乐之教,得乎情理,化民以德,培善成俗,可谓智深而谋远。法之所罚在于示以威信,止邪归正,正所谓“礼以行义,刑以正邪”。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再者,礼法之用要在中道合义,不可拘泥不化。古人云:“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知有者,可以义起。”无论德治还是法治,皆属政教之一端,所谓道无常道,法无常法,要在审时度势,因势合义,以俾于事,而非固执一端;此外,传统的以德入法乃是就立法的精神原则、理想指向而言,即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惩恶扬善、成就德行,正所谓“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古人论及刑政理想时皆言“为政以德”,但绝非是用道德规范来直接代替刑政之法。为此,古人曾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如果强行理想化地以德入法,则极易导致因道德绑架而轻易构人以罪抑或纵容犯罪。以上思想对当下构建道德文明与法治社会不无裨益。
存敬有畏。中华礼乐文明要在确立人道,其人道实践是在崇天敬祖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古人看来,“崇天”,一则在于“天地者,生之本也”,人道亦本于天,且内在于人,是人的存在规定、价值本原;二则在于“天命无不报”,即天命具有不假人为的至上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古人讲“知天命”“畏天命”,即是在提示行人道的同时,亦要敬畏天命,修身以俟之,正所谓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而“敬祖”则在于“人本乎祖”“无先祖,恶出”,古人提出敬祖意在“重仁袭恩”,不忘先人业绩。以此为基础,古人又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说法,这是将敬祖行为进一步纳入移风易俗的活动之中。崇天敬祖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古人“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人文精神。
在此背景下,人即是一个知止守道、存敬有畏的现实规范性存在。当前社会中涌现出无知无畏、娱乐至死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人心缺少了对于天理道义的敬畏感,以致行为肆无忌惮。结合中华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精神对此做适当反思,当是颇具建设性的。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作者:华军(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情礼关系下的《礼记》礼义学研究”负责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通情达礼”的基本内涵
称情立文。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古人以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故《礼记·曾子问》言:“君子礼以饰情。”正所谓“合声色臭味之欲,喜怒哀乐之情,而人道备”。不过,古人很重视人情之真,对矫饰之情则持批评态度,故言“巧言令色,鲜矣仁”。此外,古人还言道:“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真情成为善、贵、信等价值评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人对脱离人情的礼表达了质疑,如《礼记·檀弓上》言:“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总体来看,古人以为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所谓“情具于人,先王制礼以顺之,而喜怒哀乐由此而和”;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所谓“好恶正则天下之是非瞭然而不惑矣”,礼的教化作用就在于“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实现“发乎情,止乎礼”“从心所欲不逾矩”。概言之,人的好恶之情与礼之间存在顺与节两种关系,其间的分别就在于好恶之情的发动是否合于礼。合则顺行,逆则有节。所谓“克己复礼”,即是“约俭己身,返反于礼中”,究其实就是贬抑自身膨胀的欲望,约身合礼以待人行事。古人一则从利生成人的角度讲求“以礼达情”,一则从养生合道的角度强调“以礼节情”。二者可谓一体两面,共同服务于立人成德这一人文化成的目标。
礼者理也。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是情理关系。情理关系可概括为好恶之情与所以然、所当然的关系。所以然可谓是好恶之情得以形成和展开的现实因,是促成好恶之情的现实诸因缘合称,恰如朱熹所言:“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从所以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受制于外物刺激和自我感受,正所谓“感于物而动”。所当然则是指好恶之情的本质规定,亦是所以然中确定不移的部分,对此古人言“有物有则”。从所当然层面看,好恶之情的发动有其内在规定。《论语·卫灵公》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这种对好恶之“察”即意味着对于情感发动的所当然之理的发明。对此古人又言道:“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由此可见,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好善而恶恶”的人道原则为思想基础。所谓仁者乃是人道的人格体现,他以行仁为人最本己的存在;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乃以忠恕之道为实践沟通原则。尽己以立身,推己乃成德,忠恕即为立身成德之事。从立身成德之完成上讲,尽己之忠是推己之恕的前提基础,而推己之恕则是尽己之忠的外在展开实现。故忠恕实为立身成德的一体两面。古人内外合一、成己成人的道德内涵即在此中得以一贯。换言之,人自身都有“所欲”和“不欲”,得乎“忠恕”就在于理解人皆有“所欲”与“不欲”而求得彼此一贯的通情;好恶之情的当然之理又以无过犹不及的中和之道为价值实现原则。礼乃称情立文,中礼本质上是得其情实,其外在特征在于“别”,即“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目的在于体现存在之实。但是礼这一目的的实现最终则需落在“和”上,否则就会落入“礼胜则离”的境地。
以礼达理。“理”为事物之条理、秩序,莫非自然,要在于顺。“礼”与“理”的关系是粲然之“文”与内涵之“理”的对应关系。古人言:“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也者,理也。……君子无理不动。”又言:“礼由外作,而合乎万事之理。”相对于具体事物而言,特定的事物蕴含着特定的理,事物与理应,如程颢曾言:“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各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哉?”相对于礼而言,则特定的礼与特定的理对应,其目的就在于以文相别。“礼”与“理”的关系建基于具体事物之上,故绝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言“理”与“礼”,正所谓“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以为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对应于具体事物之理的礼文虽然“至繁”,然如能规约于理,则可实现以简驭繁而不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还需处理好另一个问题,即“以义制仪”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变礼的问题。古人以为“礼者,义之定制也;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故协合于义而合,虽先王未有此礼,可酌于义而创为之”。由此可见,作为“礼之权度”的“义”乃是“随时制宜”的伦理原则,它是制礼的依据。相较而言,礼仪则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定制。由于礼义随时制宜,也就自然会不断冲击礼仪之定制,进而引发变礼与制礼的问题。为此就要“明其体而达其用,穷其源而析其流,尽古今之变而备人事之宜”。总之,礼义与礼仪的关系,一方面可谓是无仪无以显义,无义无以定仪;另一方面则是义者随时制宜,仪可以义起。二者的统一既体现为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又体现为动态实践上的相生相成关系。
“通情达礼”的当代启示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民族性与民族文化不断转化与创新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围绕转化与创新这一主旨,以民族文化来彰显民族性无疑是一种存在实现方式。它既是民族性的变现,亦是现代性的发展。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此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立乎情理。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德、法并行。礼乐之教显为德治,刑政之治则属法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正所谓刑以弼教,法以济礼,二者相须而成,实质是力求情、理、法的一贯。礼乐之教,得乎情理,化民以德,培善成俗,可谓智深而谋远。法之所罚在于示以威信,止邪归正,正所谓“礼以行义,刑以正邪”。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再者,礼法之用要在中道合义,不可拘泥不化。古人云:“盖古今之不同,质文之迭变,虽先王未知有者,可以义起。”无论德治还是法治,皆属政教之一端,所谓道无常道,法无常法,要在审时度势,因势合义,以俾于事,而非固执一端;此外,传统的以德入法乃是就立法的精神原则、理想指向而言,即刑罚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惩恶扬善、成就德行,正所谓“以政先示之,则民有所振厉而敛戢矣。其或未能一于从吾政者,则用刑以齐一之。俾强梗者不得以贼善良,而奸慝者不得以败伦理”。故古人论及刑政理想时皆言“为政以德”,但绝非是用道德规范来直接代替刑政之法。为此,古人曾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如果强行理想化地以德入法,则极易导致因道德绑架而轻易构人以罪抑或纵容犯罪。以上思想对当下构建道德文明与法治社会不无裨益。
存敬有畏。中华礼乐文明要在确立人道,其人道实践是在崇天敬祖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古人看来,“崇天”,一则在于“天地者,生之本也”,人道亦本于天,且内在于人,是人的存在规定、价值本原;二则在于“天命无不报”,即天命具有不假人为的至上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古人讲“知天命”“畏天命”,即是在提示行人道的同时,亦要敬畏天命,修身以俟之,正所谓君子“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而“敬祖”则在于“人本乎祖”“无先祖,恶出”,古人提出敬祖意在“重仁袭恩”,不忘先人业绩。以此为基础,古人又提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说法,这是将敬祖行为进一步纳入移风易俗的活动之中。崇天敬祖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古人“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的人文精神。
在此背景下,人即是一个知止守道、存敬有畏的现实规范性存在。当前社会中涌现出无知无畏、娱乐至死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在于人心缺少了对于天理道义的敬畏感,以致行为肆无忌惮。结合中华礼乐文明这一文化精神对此做适当反思,当是颇具建设性的。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12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