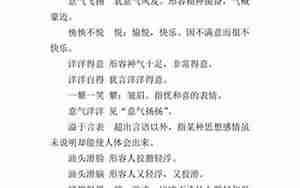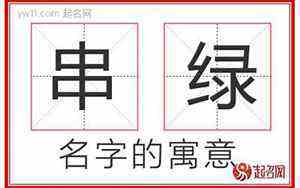
本文目录一览:
叙诡笔记|《汪穰卿笔记》中的1910年东北鼠疫
眼下,全国人民正在团结一心、积极应对,打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科普工作者们不断推出新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普及防控知识,解读疫情趋势,粉碎不实谣言……在这个过程中,1910年发生在东北的特大鼠疫被经常提起,既让读者对某些错误的做法引以为鉴,又从伍连德等医学家对患者的成功救治,让今天的人们认识到惟有科学应对,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性。
关于1910年的东北鼠疫,目前已经出版了不少相关的研究专著,但也许是当时国内的主要学者都集中在京沪和江南一带的缘故,没有多少人涉身疫区,所以在清末民初的笔记中很少见到记载。这其中,清末著名报人、学者和政论家汪康年的《汪穰卿笔记》(汪康年字“穰卿”)算是个例外。汪康年于1910年在北京创办《刍言报》,他从一个非常奇特的角度说明了这场鼠疫的影响——北京城的市民与官员面对汹汹疫情时的各种反应与举措。
汪康年
一、邮传部担心“收入锐减”
1910年是宣统二年,这一年的11月9日清晨,在哈尔滨的秦家岗马家沟附近,一名居住在中东铁路工人住所内的中国工人突患鼠疫死亡,标志着震惊世界的“1910东北鼠疫”拉开了序幕。死神的魔影迅速笼罩在东北大地上,到这一年的年底,已经有无数感染者死于非命。
哈尔滨傅家甸首设消毒所,出自《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撮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年出版
为了防止疾疫传至京师,12月14日,京奉铁路开始停卖京奉二、三等票,邮传部因疫势日盛而下令停止由奉天至山海关的头等车。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只有彻底隔离从奉天到北京的交通,才能阻止携带有鼠疫的旅客进入北京,以确保京城的安全——事实证明,这场鼠疫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被牢牢地“摁”在了东北而没有全国性扩散,这个举措堪称立下了大功。
《汪穰卿笔记》
也正是因为疫情没有进入北京,所以市民们对各种小道消息将信将疑,有的还开起玩笑来。《汪穰卿笔记》记载,有个人初闻鼠疫,不知道是什么病,只听说死人很多,“大惊缩,不敢出”,后来听说就是在欧洲造成大量死亡的黑死病,立刻放下心来,大摇大摆地上街去了。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说:我听说瘟疫这种东西,如果已经感染并幸免于难,就会产生一定的防御力,不会再次感染了,所以我有什么好怕的?大家都愣住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感染过黑死病,他说:“咱们这北洋政府当官的个个黑心,老百姓个个心死,不就是黑死病吗?”引来一片笑声。
此人的这番话虽然笑闹,却也讲出了几番实情,大疫当前,前方医护人员奋不顾身,与鼠疫做殊死搏斗,而北洋政府内的个别官员却只在盘算自己的得失,心中既无国家更无人民,他们照样举办宴席,交杯换盏,而口中议论的则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比如邮传部的官员忧心忡忡地说:如今京奉路或者减少发车,或者干脆切断铁路,路局的收入锐减,如果再这么下去,推广到其他的铁路线路,那可就没钱赚了;外交部的官员则喜气洋洋,因为各国使馆的外交官因为防疫,都很少外出,不是大事也不来部里交涉,所以部务甚少:“外人避事不出,一切要求断然中止,若推广时日,使吾辈耳根永远清净,岂不大妙?”为了自己能偷闲一时,竟盼望着疫情“推广”,也真的是天良丧尽!“内有三五人蹙眉微语,语细不可闻”,后来才知道,他们在担心疫情严重会导致预定的德国王储访华落空,而这种担心也并非全为大清与德国外交关系的好坏,更多的是忧虑“前者所费何以为偿”,说白了就是在筹备王储访华的过程中花费的银两怎么报销——这些花销中到底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公务上,只有天知道!
不过疫情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困顿。汪康年在笔记中这样记录道:“前者东三省之防鼠疫,几半年于兹矣,于是大豆等行销至欧洲颇有为难之势。”当时日本商人在大连、安东等地囤积了大量的大豆,根本卖不出去,“乃亟宣布鼠疫并不及大连等处,遂得畅销无阻”。而英国商人一直将中国的猪肉“销行于英者甚多”,瘟疫一起,立即滞销,“英商乃宣言此猪肉为汉口出口之物,与东三省渺不相接,于是销行如故”。
二、短短时间竟“杀鼠百万”
清末,随着电报的广泛应用,地方上的消息早已不再像以往那样闭塞,是以东北疫区里遍地尸横的可怖新闻像潮水一样迅速传至京城,引发了人们的恐慌。警厅下达命令,民间展开灭鼠行动,“凡捕鼠送警厅者,与铜元二枚”。北京市民积极响应,短短的时间竟“杀鼠巨万”!对此老百姓纷纷称赞:“即使都中并无鼠疫,然假此将都中鼠除尽,避免损毁器物、盗窃食品、搅扰睡魔,亦大佳也。”还有人编出了段子,就事论事,颇有哲理。说是一只狐狸见了一只老鼠,揶揄它说:“汝辈何来此倒运事,自己遭了殃,偶然传染到人身上,便要遭赤族之祸,竟无术自救,岂不可怜?”老鼠说:“此事真太冤,偶然死了几个人,便硬派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不论有疫无疫一概处死,天下哪有此不平事,算来这不叫做人遭鼠疫,真是鼠遭人疫。”有人还写了一首诗,在京城广为流行:“杀鼠令虽苛,无如鼠辈多。蒸成疫世界,拢就鼠山河。鼠岂烧能尽,疫非药可瘥。欲求兹疫净,宝剑要重磨。”
但是警厅接下来的一道命令就让市民们议论纷纷了,那就是突然下令全城杀狗,有人说这是拿老鼠出不了气,就来打落水狗。不过这至少说明市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
这种重视不是没有缘由的。
《北平风俗类徵》
据清末民初的各种史料显示,上个世纪初的京城,公共卫生情况并不乐观。李家瑞编撰的《北京风俗类徵》上记载,北京的家庭垃圾“悉清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沟渠河道的污染特别严重,《晨报》报道:“无论什么脏东西,往(河)里一掷,就可以说了事。”尤其天安门前的御河及南池子一带的水道,“因两岸居民不知爱护河道,任意倾倒秽水及垃圾,以至河身淤垫日高,不独该河本身宣泄不畅,积水易与腐臭,即玉带河亦受它影响。”至于随处便溺更是司空见惯,据《北洋画报》报道,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站是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而就在正阳门一带的城墙根下,屎尿成河,臭不可闻,无人过问——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一旦鼠疫传入,其扩散的速度和程度将是何等惊人!
清末民初的正阳门(前门),当时是京城最繁华的地带
早在1905年,北京改工巡捐局为卫生局,“举凡清洁街道、防疫各法及强迫种痘、考验药品、医术无不司之于卫生局”。这种主要仿自日本的卫生警政模式在当时对北京城市卫生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客观上对1910年鼠疫的预防有了“制度储备”和“人才储备”。疫情不断严重后,京城在转过年来设立了防疫局,给出的薪禄十分丰厚。《汪穰卿笔记》记载,有个人谋得局中工作,沾沾自喜,朋友对他说:“俗话说‘寅吃卯粮’,我倒得出一个对子——‘亥交子运’。”他问此话何解?朋友说:“今年是亥年(1911年是辛亥年),而你得到了这么一份跟鼠疫有关的差事,鼠之生肖为‘子’,岂非‘亥交子运’乎!”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市政府对防疫工作的重视。
三、成功“御疫于城门之外”
虽然鼠疫没有进京,但居住在北京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对于导致鼠疫逞凶东北的原因,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他们看来,“我国人素不重视卫生之道”,实在是亟待改变的问题。汪穰卿笔触沉重地写道:不独老鼠,“居室卑污,衣服垢秽,致滋生种种啮人肌肤、吮人膏血之虫类,若蚊、若虱、若蚤、若蝇、若蜰(臭虫),无南北、无东西何处蔑有(没有)。”如果任由这种境况持续下去,那么就算暂时将鼠疫挡于城门之外,也早晚还会遭到其他疾病的侵袭。
难能可贵的是,在疫情汹汹的情势下,汪康年对另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也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他有一位朋友“游学欧洲殆十年,足迹遍全欧”,曾经告诉他,我国人崇拜外国过甚,就拿臭虫举例,“佥自认为己国特产品而他国无有也”。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位朋友曾经在游览巴黎期间,住宿在一座著名的大旅馆之中,“坐于榻未久,有物啮吾股”。他赶紧找来服务员说:“你们这里有臭虫,麻烦帮我换一个房间。”服务员力白其无,且诅咒发誓旅馆里没有臭虫,他只好回到房间睡下。“睡未交睫,即臭气冲鼻,蜰虫缘榻而来,集喙于吾四体,痒不可忍。”他起了床,点燃了灯,“得一则杀之,涂其血于壁,竟夜杀无数,壁上之血痕缕缕然,然犹未尽诛灭也”。他跟这么多臭虫鏖战了一夜,凌晨时分疲惫不堪,才昏昏睡下。第二天早晨醒来,把服务员叫来,指着墙上的血痕讲述昨晚的遭遇,那服务员目瞪口呆,一边不停地赔礼道歉,一边赶紧给他换了房间——“西俗,如污坏其墙壁乃不规则之举动,例得索赔偿”,而服务员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一争辩则人皆知之,其名誉有损,其营业且立败,故惟有忍之而已”。汪康年讲述这个故事,目的不是为了给旧中国不卫生的习惯找个借口,而是告诉国人,“崇拜外人者,毋乃太过欤”!改变国人卫生观念,树立健康习惯是对国民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好事,但是自强的前提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而不是崇洋媚外。
《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北京向现代化的卫生城市过渡的过程中,各国驻华使馆有意无意地起到了促进作用。各国使节们从自身健康和安全出发,一直督促使馆区洒扫街道、设立茅厕、防病检疫等工作的开展。1910年东北鼠疫事件平息后,他们对此更加重视。历史学者何江丽在《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一书中介绍:1919年华北地区疫情又起,驻京各国医官认为如果不及时协助中国政府开展防疫工作,可能危及各国在华侨民,于是召开联合会议商讨了相关方案,其中要求“业经传染疫症各城镇商埠应实行断绝其与其他处之交通,并实行检疫之方法以杜蔓延”,同时建议“立即取缔交通并于交通机关上施用必要之卫生法,如廊坊为来往必经之地不能断绝交通,应令火车不在该地停站以免传染”。即便今天看来,这些处置方式也是正确和得当的,而中国政府予以采纳,将提议全文照录并令相关各省采纳和实施。此后各国医官联合会又函请中国政府迅速于丰台车站组织设备完全的检疫所,以阻止疫病蔓延至北京……
整整110年前的、针对东北鼠疫的这场“北京保卫战”,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一面自立自强,一面从善如流,一面群策群力,一面科学防控,终于“御疫于城门之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