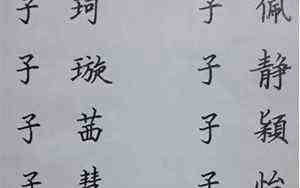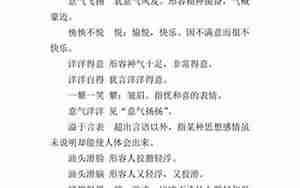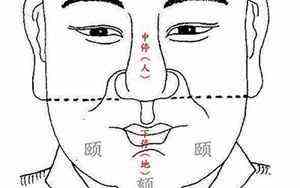
“鬼”怕什么呢?民俗文化中除了钟馗外,这些东西也可以压制鬼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鬼都是由心生的,中国人都说“心里”有鬼,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古人说:“鬼者,畏也,谓虚怯多畏,故名为鬼。”所以我们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是贵鬼的来源于人心的丑陋,所以就奠定了鬼的形象的丑陋,狰狞等等的特点。
鬼的丑陋形象
鬼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民间中有很多关于克制鬼怪的说法,除了那些道士神仙以外,比如钟馗等,还有什么方法去压制鬼怪呢?我们一起看一下。有种说法,鬼怕桃树,相传有神荼、郁櫑两位神仙住在大桃树下,所以鬼对于有关桃树的物件,都有种恐惧,比如桃矢、桃木剑等,还有民间过年时在门口悬挂的桃符,也是用来辟邪驱鬼,甚至连桃木煮出来的汤水泼也在屋顶和墙壁上,也可以驱邪。
桃符
植物中属桃树最为克制鬼怪,动物中则要属鸡了。记载说:“鬼畏金鸡,金鸡飞下,食诸恶鬼。”听到鸡鸣,恶鬼就赶紧逃避。鸡鸣代表着天亮,而鬼一到天亮就要化为鸡鸭羊等禽兽,被人砍杀。除了鸡以外,鬼还怕狗。传说有个人死后变成鬼,总是夜里跟着他儿子回家,每次听到狗叫就胆战心惊,有次被一群狗追咬,立刻逃到树上,再也没有出现,可能是吓死了。在一些古书上,比如《太平广记》,还记载说鬼怕男人的鼻和女人的唾液。
鬼怕光,喜欢黑夜,所以说正午光照 最强时,鬼就会消失不见。另外,例如喧哗热闹的街头,鬼也是不喜欢的,他们喜欢呆在类似坟墓、荒园等一些寂静黑暗的地方,怕听敲锣声音,唱戏,还要爆竹声。这些“雄声大钹”对属阴的鬼有克制作用。鬼是魂魄形成的,有气无形,“鬼性惧风,若无所凭藉,被风一吹,便不知漂泊何处”,所以三种人是鬼最怕的,贞妇、兵勇、醉汉,因为贞妇有正气,兵勇有彪悍之气,醉汉有旺气,这三气都可以冲散鬼气。所以刀枪棍棒对鬼是无效的,还不如以气制之。
王祖贤把小倩“鬼”的虚浮演绎的十分到位
另外鬼还怕一些文字,比如魙,比鬼还凶狠,所以鬼见了这个东西也害怕。唐代就有人在门上写这个字来辟邪。另外,还有水鬼怕“嚣”字,吊死鬼怕“魄”字,传说茅山术士只要伸出手指写个“魄”字,就能将鬼逼到地下。其次还有,朱砂黄纸写得字也能驱赶狐鬼。只有纸也能制服鬼怪,以及大声朗诵子集也能够驱赶鬼怪,其中最为厉害的要数《周易》,相传将《周易》撕开,贴在棺材上,鬼怪就不敢迈开一步。这其中也折射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含义。
《周易》八卦
相传鬼有三计,一迷、二遮、三吓,这三招使用完,鬼基本也就没招了,如何对付呢?还是要归结到人们内心的修炼。比如,对付迷,要心静;对付遮,需淡定;对付吓,要胆子大。所以中国人所说的“鬼”,是内心的“鬼”,还是要靠自己用心解。
钟馗神威图
鬼最怕的5种人,你信吗?
1.木匠:木匠是手工业者的代表,在古代是被看做神明的.尤其鲁班,是供奉的对象,而木匠的墨盒,也就是用来画直线的墨盒,更是鬼所害怕的东西,因为墨盒集中了人类的智能.
2.屠户:屠户因为宰杀牲畜很多,所以身上有恶气和牲畜的怨气,所以鬼不敢近身.屠户的刀也是辟邪之物.
3.泥瓦匠:泥瓦匠也是手工业的代表,泥瓦匠的泥抹子也是辟邪之物
4.恶人:鬼怕恶人,历来在古代小说里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故事,而且大家好象都知道一个说法,就是怕鬼的时候可以大声的骂脏话,于是鬼自然就不敢现身了.
5.孕妇:传说女人怀孕后,头顶会有三层金光护体,这是由于孕妇在人生生世世的循环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她负责把转世投胎的魂魄带到人间,因此,鬼是根本无法威胁到孕妇的.不仅如此,鬼见到孕妇一般都紧张得大喊:哎呀,吓死我啦..屁颠屁颠地跑得无影无踪。
十二生肖最怕什么人?
张旭东︱杨绛的“怕鬼”和“不怕鬼”
约2014、2015年间,我借单位资料室的《顾颉刚日记》翻看,意外被他太太吸引。顾太太张静秋像一列火车一样在后面推着顾先生不断向前,开会、表态、发言,停不下来。顾先生有时赖着停下来不走,顾太太发动全家批斗他,《日记》中甚至有顾太太“批其面”的记载,还不止一次。顾太太永远生活在紧张中,至忘了自己的生日,顾先生还混沌搞不清状况。由此我分析说,在政治方面潜在危险到来时,女人倒比男人敏感。
写完顾太太,一时停不下来,惯性地去看其他人的太太,看她们是不是也能以“变态”的形式救她们的先生。甚至选定了下一个目标,而且顾颉刚日记中也提供了一些线索(顾日记多记友朋结婚、离婚事)。有个朋友冲口说:好啊!你会成为研究这些太太的专家!
“谁要做这个!”我于是止住一切好奇心,不再关心人家太太。
后来才发觉,对着顾太太说的那些话,不是很耳熟吗?“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对,钱先生的《围城》!
那!钱先生的太太呢?好奇心像离离原上草又生长起来。
钱钟书与杨绛,黄维樑摄于1984年
说实话,我对钱太太杨绛先生有点偏见。她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只说钱先生“痴”,好像要包括了一切。笨笨的应该有,体育不太好也是事实,但钱先生洞达人情,EQ很高,我觉得杨先生未免藏了实话。宋淇在写给张爱玲的信中,提到钱先生1979年访美情况,说:“钱抢尽镜头……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大家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志清、水晶都各写长文大捧。我起先有点担心,怕为钱惹祸,但钱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怀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121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
对嘛,这才是我们读者透过《围城》认识的那个钱锺书。“他对人类行为抱有一种心理研究的态度”,“他知得很清楚,愚昧和自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未为意识形态的顾虑所害,仍是目前最博学而敏感的批评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33、338、33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能看透世界,才能做小说家,张爱玲如此,钱锺书也是如此。能写出看透人心、揭开假面的那些句子的人,怎么可能痴痴傻傻?他们虽不生活在最底层,却一定和那些最底层的情感见面认识过。钱先生一定习惯于研究人的心理,有时仔细得令人害怕,如《纪念》里,曼倩偷情后, “为没有换里面的衬衣就出去了,反比方才的事(指与天健偷情)更使她惭愤”。冷血吗?小说家就应该这样,捕捉到这些真实的存在。一个大小说家当以人类的全部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勿止于浅,要进于深。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偏见既然产生,便自然产生了它的效果,就是不肯读杨先生的作品了,认为不真。
直到杨先生以期颐过五之年鹤归,大家写纪念文章,我才觉得这个女人好坚强啊!也慢慢读点家里已有的杨先生的作品,后来也补购了一两册,总之还是不多。但这不多的阅读,已使我足够震惊了。
惊着我的是啥?是杨先生写的“怕鬼”和“不怕鬼”。
“怕鬼”还挺多的。从小就怕,《走到人生边上》回忆:“我早年怕鬼,全家数我最怕鬼,却又爱面子不肯流露。爸爸看透我,笑称我‘活鬼’——即胆小鬼。”(《走到人生边上》,21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我们仨》里也说:“我是最怕鬼的,锺书从小不懂得怕鬼。”(《我们仨》,11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收在《杂忆与杂写》中的《遇“仙”记》其实是“遇鬼记”,是已上了大学的事。有此亲身经历,恐是更怕了。解放后杨先生回到清华,“杨必特地通知保康姐,请他把清华几处众人说鬼的地方瞒着我,免我害怕。我既已迁居城里,杨必就一一告诉我了。我知道了非常惊奇。因为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传说有鬼的地方”(《走到人生边上》,22页)。来回映衬,信而弥坚。
“不怕鬼”来得突然。《干校六记》中第四篇“‘小趋’记情”中说:“小趋陪我巡夜(按“小趋”系小狗名),每使我记起‘三反’时每晚接我回家的小猫‘花花儿’。我本来是个胆小鬼;不问有鬼没鬼,反正就是怕鬼。晚上别说黑地里,便是灯光雪亮的地方,忽然间也会胆怯,不敢从东屋走到西屋。可是‘三反’中整个人彻底变了,忽然不再怕什么鬼。系里每晚开会到十一二点,我独自一人从清华的东北角走回西南角的宿舍。路上有几处我向来特别害怕,白天一人走过,或黄昏时分有人做伴,心上都寒凛凛的。‘三反’时我一点不怕了。那时候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干校六记》,46页,三联书店,2010年)
《我们仨》比《干校六记》出版得晚,说得更详细些,里面说:“‘三反’是旧知识分子第一次受到的改造运动,对我们是‘触及灵魂的’。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色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我有一个明显的变,我从此不怕鬼了。不过我的变,一点不合规格。”(《我们仨》,128页)
世间鬼来了,阴间鬼的威力就差远了。
《围城》末尾,方遯翁送来的那座老掉牙的挂钟全无心肝地敲响,面对诸种人生困局的鸿渐以及同样面对诸种人生困局的读者,都觉得这原本空洞无意味的钟声竟然深于人间的一切啼笑。这个末尾曾打动了无数读者。对《围城》来说,这混沌的钟声,所包含的还只是婚姻、家庭、事业里的一切鸡毛蒜皮,虽均有可能引发人生困局,然终是小事。钱太太在1951年前后,由怕鬼到不怕鬼的转变,才是面对人间恶鬼展开的力量悬殊而生死攸关的恶斗。此处不宜再用是不是深于人间啼笑来做比,因为所描写的分明已不再是人间。
阴间鬼不仅威力不及,即其是否实有也成问题。杨先生身边的杨必、保康姐倒不怕鬼,在我看来,她们根本斗不过世间鬼,惨败!怕鬼的杨绛不是从此不怕阴间鬼,改怕世间鬼,而是要动用一切的谨慎和小心,抖擞起一切精神,她要和世间鬼斗,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救自己,救锺书,救圆圆。这是这女子了不起的地方,真伟大。
杨先生曾经说钱先生随便上什么馆子,他总能点到好菜。这真的是一种本事,你想想看。“选择是一项特殊的本领,一眼看到全部,又从中选出最好的。”(《我们仨》,139页)杨先生耳濡目染,一定也很会选;前面说过,在政治形势下,说不定比钱先生更懂得怎样选。譬如对鬼,她是真怕,又不是假怕。但她又可以马上不怕了,她可以选择。当然需要勇气。
《丙午丁未年纪事》里,淡定从容,我相信,这一定有个过程。从1951年的“三反”算起,已经十五年了;就是算到1957年,也有六年了。从笔墨中,是能找到点线索,在逐渐地转变、应对,但画不出完整的“线路图”。
杨先生自己说:“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锺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我们仨》,108页)“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可是钱先生是不哭的呀!我们这些“成人”,又哭又笑,恐怕只能像圆圆。放进历史的风尘中,只是“年纪”这一点可称成熟。请把你自己放进去,你怕哪个鬼,你斗得过哪个鬼,还是不幸,自己会变成鬼?
1981年,“我们仨”摄于三里河寓所
佳作早成,读者晚到。多少有点扫兴,但我有时庆幸自己是一个晚到的读者。如果来得太早,可能会倏然掠过,不能如现在,这静夜里,一年最冷的几天,读得这样感动,这样惊心。
杨先生晚年,“走到人生边儿上”,又开始信鬼、怕鬼,她说:“有人不信鬼(我爸爸就不信鬼),有人不怕鬼(锺书和钱媛从来不怕鬼)。但是谁也不能证实人世间没有鬼。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走到人生边上》,8、9、22页)但愿一切回到自然,怕鬼的能怕鬼。
补记:
有一个问题总挥之不去,您不觉得杨先生当初抖擞精神,要与世间鬼斗时,表现得很自信吗?我们还得再回去想想。当钱、杨一家下馆子的时候,钱先生总能点到好菜,钱先生点了菜,菜还没上来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观察周围,猜度另一桌儿所坐两位如何,第三桌儿一家几口如何。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分析,钱、杨二先生以此为乐。《我们仨》中所记较详。
关于心理学,钱先生的大学同学饶余威写过一篇《清华的回忆》,说钱锺书“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将饮茶》,124-125页引,三联书店,2013年)。更别忘了,钱先生194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就叫《人·兽·鬼》。当“默存借调在城里工作,阿圆在城里上学,住宿在校”时,杨先生十一二点开完会,往回走,“家里的女佣早已入睡,只花花儿每晚在半路的树丛里等着我回去”。那位女佣是郭妈,《走到人生边上》里有篇《镜中人》,是她的“传”。里面说:“我曾用过一个最丑的老妈,姓郭。钱锺书曾说,对丑人多看一眼是对那丑人的残酷。我却认为对郭妈多看一眼是对自己的残酷。”
文中记述的,是东家和女佣之间“和平的战斗”。故当世间鬼到来时,杨先生多少做过一点“练习题”。她知道,无论时代如何,人类的愚昧和自私始终如一。面对被人摁了按钮的“机器人”变了鬼,其心思无外乎那些。早分析过了,也实战过了。夏志清说钱锺书“对人类有一种理智的鄙视”(《中国现代小说史》,313页),眼光够狠,这种鄙视无疑杨先生也有。惟其如此,面对人鬼转变的恐怖,才保持了冷静,没乱分寸。她当然不想斗,被逼到这一步,只好打起精神来。年轻的父母,生活在好的时代,还在逼着小孩子学奥数、背古诗文吗?不如接触点有趣的心理分析,养成一种思维习惯,也许有一天能帮助他们度过劫波,谁说得准呢!
G
M
T
Text-to-speech function is limited to 200 characters
| Options:History:Feedback:Donate | Clo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