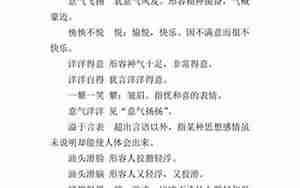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楞严经】讲记
【楞严经】讲记2019最新版
卷一 /d/file/gt/2023-12/pt30hpbvt1g.html /d/file/gt/2023-12/rcpphju4mla.html /d/file/gt/2023-12/5mejxqyrzss.html /d/file/gt/2023-12/fu4sl34cgi3.html /d/file/gt/2023-12/jediv2qz3am.html /d/file/gt/2023-12/trrzxjrgdal.html /d/file/gt/2023-12/xr0wiagpldw.html /d/file/gt/2023-12/cuxv4rlbus0.html /d/file/gt/2023-12/ogva1xve4j2.html /d/file/gt/2023-12/ohogzhsq4sw.html id="《金刚经》的生僻字与多音字怎样读诵">《金刚经》的生僻字与多音字怎样读诵
都知道,今天我们读《金刚经》通行本是後秦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距今有一千五百余年了。译时所采用的是中原古音,而非今之普通话。所以,今天读诵虽以普通话为主,仍有不少生僻字及古音(多音字)在其中。现罗列如下,以就教于尊者:
法会因由分第一
祇树给孤独园中的祇,为多音字qí与zhǐ,读作qí。给,多音字gěi与jǐ,读作jǐ。
祇树给孤独园,亦称胜林给孤独园、祗桓精舍、祗洹精舍、祇园精舍等,位于古印度憍萨罗国都舍卫城南门外五里。其始建于释迦牟尼佛成佛后第六年,是给孤独长者和祇陀太子共同发心建造的,故称。佛世尊在此居住约二十五年,宣讲了许多著名的经典,如《楞严经》、《金刚经》、《阿弥陀经》、《胜鬘经》等。
善现启请分第二
右膝著地中的著,为多音字zhù与zhuó,读zhuó。
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梵文音译,其中的褥字,读nuo(诺)。有些南方寺庙僧人传承念miǎo,也读nòu。都对。梵文阿耨多罗为Anuttara。
藐,读miǎo。梵文Anuttara-samyak-sambodhi,音译为“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後世有将此句意译者,但顺古尊重前师仍为译经原则。
降伏其心,降为多音字jiàng与xiáng,读xiáng。
愿乐欲闻,乐字多音lè、yuè、yào,当读作yào。金刚经中,此字四次出现,均读为yào。乐字读音不同,意义也不同。yuè,指音乐;lè即快乐;yào意即爱好,喜爱。《金刚经》中的乐(yao)字,今多有读le者,亦无不可。
妙行无住分第四
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金刚经》中的不字,三种读法。佛设问,“不″在句尾,读作fǒu(否);须菩提作答,句首的“不″′,读作fú(弗);余均读bù。读fǒu,通否,设问语气助词。读fú,用在对话的句首,示以否定的回答。读bù,当代汉语常态用法,表示否定。今也有不分上述三种读法而全读成bù者。或云整部《金刚经》所有的“不”都读“否”者。
一相无相分第九
乐阿兰那行者 [yào ā lán nuó xíng zhě ] 。梵文Arana‘阿兰那’的译音,汉语译为‘无诤’。那,读音有nǎ、nèi、nà或者nā等,“那”用于地名时,读作nuó。《金刚经》多处“那″字,均读作nuó。很多读者也读今音nà。
行者,修行者的意思。“行″为多音字,“行者″中读xíng。“是谓阿兰那行”中读héng,指阿那兰(无诤)的修行功夫。
庄严净土分第十
庄严佛土者:佛经中的“佛净土、国土、佛土”中的“土”当读为dù,今人多误读为tǔ。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七宝,没有土!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是经名为般若波罗蜜,般若,读bō rě。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不可称量与不可量中的“量",前者读liáng,后者读liàng。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那由他,读作nuó yóu tuō。古印度计量单位,或译为“兆″“沟″。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释迦牟尼。牟读作mó。注意佛教中人物的读音,如摩诃迦叶,读mó hē jiā she
应化非真品第三十二
优婆塞,这里塞字读作sài,不读sè。
读经在心。提倡普通话,亦不妨方言。尊重古音,也不弃今音。尽量正确读音为上。
清代最巨制的佛经译本!一文了解乾隆皇帝御制的《楞严经序》
\r\r\r\r\r \r \r\r\r\r 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及研究[1]\r\r柴冰(注:柴冰,2011级博士生。指导教师:乌云毕力格。)
\r\r《首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具显密圆融之特色。汉文本自唐神龙元年(705)译出后,影响很大,为自北宋《开宝藏》起的各版大藏经所收录,历代多有疏解阐释之作。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曾将其译成藏、满、蒙、汉四体合璧本。本文要探讨的《御制楞严经序》即是乾隆皇帝为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所作序。此序所含版本及历史信息丰富,但探讨者鲜。本文拟对序文的满、汉两种版本加以对勘,以之为切入点, 做一探析。
\r\r 一、《御制楞严经序》的价值及研究背景\r\r《御制楞严经序》是乾隆皇帝为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所作序文。此序文附于四体合璧《首楞严经》之前,亦为四体。各种文字自上而下顺序为藏文、满文、蒙文、汉文。除各语种文本间的语言层面的转译互动及本身的文本价值外,此序内容关涉四体合璧本《首楞严经》译经的缘起、过程、参与人员等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对乾隆时期译制四体《首楞严经》的始末的探讨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清代的翻译史、文化史研究亦可提供一些新的讯息。
\r\r此外,清代各语种之间的互译非常频繁,三体、四体直至五体合璧者亦有之。但是以五种文字翻译佛经似未有之,四体合璧者则即以康熙时翻译、雍正时刊行的《心经》和乾隆时译制的《首楞严经》最为著名。然而《心经》篇幅是大乘经典里最短的,《首楞严经》与之相较篇幅不知大出几何,堪称巨制。可以说,四体《首楞严经》的译制在清代翻译单部经上还是颇具代表性的。
\r\r戴逸先生在《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推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一文中,认为御制诗文在研究乾隆其人以及乾隆时代方面“具有与档案、官书比较毫不逊色的价值”(注:戴逸:《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推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载《清史研究》,1994(2),110页。)。并举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利用诗文写出考证好文为例,倡导对御制诗文的重视。如朱赛虹所说,“清帝敕修的书籍很多,如‘钦定’、‘御批’、‘御纂’之类,唯有‘御制’的文字更能体现帝王的思想、意志、志趣、情感等内心世界”(注: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概析》,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2),88页。)。以乾隆皇帝《御制楞严经序》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或对乾隆皇帝本人对《首楞严经》的认知,乃至其宗教文化政策的探析有一更主观但也更贴切的切入点。
\r\r据《北京地区满文图书目录》,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四体合璧写本、刻本各一。然而四体合璧本深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难得一见。幸运的是,钢和泰先生民国时曾见到藏于雍和宫的一部《首楞严经》的四体文刻本,其形制为:十卷本,刻本,汉、满、蒙、藏四体文,长宽分别为8.5和28英寸。白色厚纸,红字书写。应当就是乾隆二十八年的原刻本。此本不知所终,极有可能就是如今珍藏于北京故宫的刻本。钢和泰先生在自己1936年的论文《乾隆皇帝和大〈首楞严经〉》里附录了序文的17页(注:Baron A. von StalHolstein, “The Emperor ChienLung and the Larger ūramgamasūtr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 No. 1,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936, pp. 136—146.),此17页序文即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r\r关于此序文,寺本婉雅先生、钢和泰先生及沈卫荣先生均有过探讨(注:参见[日]寺本婉雅:《西藏文大佛顶首楞严经に就て》,载《佛教研究》10号 = 3卷3号,1922,73~77页;沈卫荣:《藏译〈首楞严经〉对勘导论》,见《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18辑,81~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但寺本先生的日文译文由藏文版序文译出,钢和泰先生的英文译文译自藏文本,也参考了汉文本。然而两位大学者在此序的翻译方面均错漏不少。沈卫荣先生以汉、藏两种版本的御制序做比照,对寺本、钢和泰两位先生的翻译提出了若干新解,但并非严格细致的对勘。需要指出的是寺本先生所依据的藏文本是一个藏文单行本《首楞严经》的序文,沈卫荣先生所依的藏文本序文出自大谷大学所藏藏文单行本,为当年寺本先生所携归日本。寺本先生所依之藏文本应该也是此本。沈卫荣先生所据的汉文序则是收录于《卫藏通志》。也就是说已有的研究中,只有钢和泰先生是利用了此四体合璧序文的。鉴于目前关于《首楞严经》《御制楞严经序》尚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本文拟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未有人具体研究过的满文版本为新的角度,对《首楞严经》的探讨加以补充。
\r\r注释
\r\r[1]原刊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88~97页。
\r\r 二、《御制楞严经序》满、汉文本对勘\r\r本文以四体合璧《御制楞严经序》的满文、汉文两个版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汉文本参照《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御制文初集》中《翻译四体楞严经序》(注:《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集》第十册,4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及《卫藏通志》所收序文(注:《卫藏通志》卷一,146~147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r\r《御制楞严经序》以下对勘中,分页与断句皆以满文本为准。仿钢和泰先生之例,页码以[1a]、[2a]、[2b]的形式在满文版本每页的结束处标示。(注:1a对应“御制序上一”,因序中无“御制序下一”,故1a之后紧接“御制序上二”,即2a,2b即对应“御制序下二”,依此类推。)第一行为四体序满文版本的拉丁字母转写。第二行为满文字词的逐一汉文释义,主要依据《满和词典》《满汉大辞典》,多义词和语法词根据上下文有所选择和标注。第三行为四体序中的汉文版本。
\r\r满:Haniarahaakdun yabungga nomuni utucin 皇帝 (属)写作的 坚固 行者 经 (属)序
\r\r汉:御制楞严经(注:楞严,此处对应的满文用的词为“akdun yabungga”,akdun、yabungga分别为“坚固的”“有品行的”之意。然而藏文的御制序中对应的词为“dpabargro ba”,意为“勇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 册 No. 0374《大般涅盘经》中解释“首楞严”为:“首楞者一切事竟,严名坚固。一切毕竟而得坚固,名首楞严。”又《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 No. 1509《大智度论》云:“首楞严三昧者,秦言健相。”《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33 册 No. 1706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疏神宝记》云:“首楞严,此翻健相。谓其自性勇健,偏能降魔制敌故也。”可见满文和藏文的译法或有所本,在此之前的著作里即有“勇”和“坚固”两种解读。)序
\r\r满:ilan hacin ganjuri juwan juwe yohingga nomun[1a]
\r\r三 种 甘珠尔(属)十 二 成套 经
\r\rdade gemu tiyan ju baci tucifi ulan ulani
\r\r原本 俱 天竺 处(从)出 辗转,相传
\r\rdulimbai gurun-de hafunjiha
\r\r中国(位)通过来
\r\r汉:三藏十二部(注:三藏十二部,查陈义孝居士编《佛学常见词汇》,三藏指经、律、论,十二部即佛说经分为十二类,亦称十二分教,即长行、重颂、孤起、譬喻、因缘、无问自说、本生、本事、未曾有、方广、论议、授记(75页,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2002)。此处三藏的表达为“ilan hacin ganjur”,译言三种甘珠尔。甘珠尔、丹珠尔为藏文、蒙文大藏经目录分类法,甘珠尔大致对应汉文大藏经里的经、律,丹珠尔则对应论。钢和泰在其所作的英译文中用梵文词汇“Tripit·aka”表达三藏,“Dvdas'ńgapravacana”表达十二部,词义贴合,对应准确。),皆出自天竺(注:天竺,此处对应的满文为“tiyan ju”,为源自汉文的音译。皆出自天竺,此句满文多一“dade”,意为原本、起初,加之句意更为精确。),流通震旦。
\r\r满:tere tuktan wargi baci[2a] dergi baru selgiyenjire de jugūn i
\r\r彼 起初 西 处(从) 东 向 传播(位)路(属)
\r\rdulimba deri alifi ulahangga yargiyani wei dzang(注:此处“wei gdzang”似源于藏文“dbus gdzang”,为西藏的旧称。) bihe
\r\r中(从) 承当传递 确实(属) 乌斯藏是
\r\r汉:其自西达东,为中途承接者,则实乌斯藏。
\r\r满:tiyan ju serengge uthai enetkek inu wei dzang serengge uthai
\r\r天竺 者,是 即 印度 也 乌斯藏 者,是 即
\r\rtubet inu
\r\r土伯特 也
\r\r汉:天竺,即所谓厄纳(注:《御制文初集》《卫藏通志》均写作“讷”。)特克;乌斯藏,即所谓土伯特(注:《御制文初集》中写作“土伯忒”;《卫藏通志》中写作“图伯特”。)也。
\r\r满:tuttu tei ubaliyambuha ele nikan hergen inomun[2b]
\r\r故 今 (属) 翻译了的 所有 汉 字 (属) 经
\r\rdzang ni bade gemu yongkiyam bimbime damu akdun
\r\r藏 (属) 地(位)俱全备在 唯独 坚固
\r\ryabungga nomun akūngge
\r\r行者 经 没有的
\r\r汉:故今所译之汉经,藏地无不有(注:无不有,满文用“gemu yongkiyam”表达,意为“俱全备”。),而独无楞严。
\r\r满:terei turgun ai seci cohome dzang niba i[3a] dulimbai
\r\r其缘故什么若说 也是藏 (属)地(属) 中(属)
\r\rfonde delangdarma han tucifi fucihii tacihiyanbe efuleme
\r\r时候(位)狼达尔吗汗出 佛(属) 教 (宾)毁坏
\r\rmukiyebure nomun suduribe dekjire umbure jakade ineku
\r\r灭经 史 (宾)烧 掩埋以故这个
\r\rfonde ere nomun uthai eden yongkiyarakū ohobi[3b]
\r\r时候 此 经即残缺不全备已这样了
\r\r汉:其故以藏地中叶(注:《卫藏通志》中无“中叶”二字。)有所谓狼达尔吗汗(注:《卫藏通志》写作“浪达尔玛罕”。满文用“langdarma han”表达,应源自藏文“glang dar ma”。关于狼达尔吗汗毁佛之事,可参见《宗教大辞典》“朗达玛”条:“旧译‘达磨’,又称‘达磨赞普’。吐蕃末代赞普。唐开成三年(838)为反佛贵族大臣杰刀热等拥立,下令禁止佛教。(1)封闭和拆毁寺院,据《王统世系明鉴》,大昭寺及桑耶等寺门被堵塞,余下之一切小神殿尽毁。(2)毁佛教经典,据《新红史》载,佛典或被投于河,或被焚,或被埋于沙沟内。(3)僧人受迫害,据《新红史》,著名僧人被杀,次等僧人被流放,低级僧人被驱使为奴。吐蕃的佛教遭到沉重打击。据《佛教史大宝藏论》,卫藏地区的佛教遂全被毁灭。部分僧侣逃往边缘地区。西藏历史将该时期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会昌二年(842)被佛教僧人拉垅贝吉多吉暗杀。死后,吐蕃统治集团分裂,奴隶、属民起义,吐蕃政权灭亡。”(任继愈:《宗教大辞典》,44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者,毁灭佛教,焚瘗经典,时是经已散失不全。
\r\r满:terei sirame udu mangga lamasa niyeceme sirabume banjibume
\r\r其接续虽然能干的喇嘛们 缀补 续编
\r\raracibe jingkini debtelin akū oci gelhun akū balai nonggici
\r\r虽然做正本子没有 则敢妄 添
\r\rojorakū bihebi
\r\r不可来着
\r\r汉:其后虽高僧辈补苴编葺,以无正本,莫敢妄增。(注:钢和泰英译文对此句的理解是:“在此(西藏经典的毁损)之后,学者们意图在文本上重建和修复(此经缺失的部分),但此重建不适于写下来。因为它们基于并未拥有正本的学者们的想象。”)
\r\r满:damu[4a] budondebaksiibiwanggirid tuwabuha
\r\r只 补敦 (与) 巴克什(属) 授记 显示了的
\r\rbade ere nomunbe sunja tanggū aniya oho amala kemuni
\r\r地(位)此经(宾)五 百年 到…了 后头还是
\r\rdulimbai gurunci ubaliyambume tucibufi dzang nibade
\r\r中(属)国 (从)翻译出 藏 (属)地(与)
\r\rdahūme isinjimbi seme henduhe bihe
\r\r复到来(语助)讲说了 有
\r\r汉:独补敦祖师曾授记,“是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
\r\r满:ere gisun cohome guruni baksi janggiya[4b] kūtuktu nomun
\r\r这话才是 国家(属)巴克什 章嘉呼图克图经
\r\rbithebe fuhaame tuwarade bahangga yargiyani akdaci ojoro
\r\r书 (宾)推详阅览(与)得真实(具)凭借为
\r\riletu temgetu obuci ombi
\r\r明显的 证据做为 是
\r\r汉:此语乃章嘉国师(注:《卫藏通志》写作“章嘉呼图克图”。按满文的意思应为“国师章嘉呼图克图”。章嘉系统,依《圣武记》记述,“为黄教第四支,与哲布尊丹巴一支皆住持于蒙古,亚于达赖、班禅二支”。此序所指章嘉呼图克图为三世章嘉。《圣武记》还记载:“逮其第二世呼毕勒罕转生于多伦泊,诏造善因寺居之。高宗朝奉诏来京师,翻定《大藏经咒》,奉言其国五百年前有狼达尔玛汗者,灭法毁教,其后诸高僧补缀未全,《首楞严经》已佚,借此土本四译而归。又佐庄亲王修《同文韵统》。晚年病目,能以手扪经卷而辨其宇,于四十一年趺逝京师。”(魏源:《圣武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217~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据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大辞典》,三世章嘉名为若必多吉(rol bai rdo rje),凉州(今甘肃武威)人。雍正帝令其享受前世章嘉活佛一切尊贵待遇,并供他学习梵文、藏文、蒙文和佛典以及汉、满文化。乾隆命其管理京都各寺庙喇嘛并赐“扎萨克达喇嘛”印,为清廷处理蒙藏宗教事务之主要顾问。乾隆五十一年(1786)钦定驻京喇嘛班次时,被列为左翼班首。(参见任继愈:《佛教大辞典》,112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所诵梵典,炳炳可据。(注:此句依满文解读应为“此语乃国师章嘉呼图克图推详阅览经书,所得之真实,依之可作明显之证据”。与汉文本有所出入。)
\r\r满:bi tumen baita icihiyaha olode[5a] kemuni manju gisuni
\r\r我万 事办理了的 闲暇(位) 每每满洲 语(具)
\r\rnomun bithebe ubaliyamburede ahoaran(注:此处极难辨认,据上下文,应与汉文“爱”对应。) ofi jijungge nomun
\r\r经 书(宾)翻译 (与)做 易经
\r\rdasani nomun irgebuni nomun jai duin bithebe gemu
\r\r书经 诗经又 四书(宾)俱
\r\rubaliyambume anggabuha[5b]
\r\r翻译 使完成
\r\r汉:朕于几政之暇,每爱以国语翻译经书,如易书诗及四子书,无不蒇事。
\r\r满:geli gūnici han mafai forgonde duin hacini hergeni
\r\r又想皇帝 祖(属) 时(位)四种(属) 字(具)
\r\rsureicargi dalinde akūnaha niyaman sere nomun(注:此处“surei cargi dalinde akūnaha niyaman sere nomun”对应《心经》名称,较汉文全面,意为“以智慧到彼岸心经”,对应于梵文“prajpramit”,常被音译为“般若波罗蜜”。)be
\r\r聪明(属) 对岸(与)到对岸了 心 所云经(宾)
\r\rubliyambume tucibufi han amai forgonde folofi genggiyebuhe
\r\r翻译出皇帝 父(属) 时(位) 雕刻使明白了
\r\rbihe akdun yabungga nomunbe[6a] inu nenehe koolibe
\r\r有坚固 行者经(宾) 也 先前例(宾)
\r\rsungkolome(注:此处与汉文相应则为“遵照”之义,但满文中写作“sungkolome”,但据《满和词典》《满汉大辞典》,应写作“songkolome”。) ubaliyambuci ombi seme
\r\r遵照若使翻译 可以 (语助)
\r\r汉:因思皇祖时以(注:《御制文初集》《卫藏通志》均为“曾以”。)四体翻译《心经》(注:此四体文《心经》目前林光明主编的《心经集成》中附有全文(台北嘉丰出版社,2002)。),皇考时锓(注:《卫藏通志》中为“曾锓”。)而行(注:此句汉文中的“行”,满文用了“genggiyebuhe”,是“使明白、使清楚了”之意。两者并不n对应。)之,是《楞严》亦可从其义例也。
\r\r满:guruni baksi janggiya kūtuktude fonjihade uthai juleri
\r\r国(属)巴克什章嘉呼图克图(与)在问了的 即前
\r\rtucibuhe gisuni songkoi jabume wesimbuhe bime
\r\r陈述了 语(具) 依照回话奏存着
\r\r汉:咨之章嘉国师(注:《卫藏通志》写作“章嘉呼图克图国师”。满文为“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则如上所陈。
\r\r满:geli surei cargi dalinde akūnaha niyaman sere nomun
\r\r而且 聪明(具) 对岸(与)到对岸了心说经
\r\roci dzangni[6b] bade dari bihengge akdun yabungga nomun
\r\r是藏(属)地(位)每,各 有坚固 行者经
\r\roci dzangni bade fuhali akūngge aika nikan hergenbe manju
\r\r则 藏(属)地(位)全然 没有的若是汉字 (宾)满洲
\r\rgisuni ubaliyambume manju gisunbe monggo gisuni
\r\r语(具)翻译满洲语(宾)蒙古语(具)
\r\rubaliyambume[7a] monggo gisunbe tubet gisuni
\r\r翻译
\r\r蒙古 语(宾) 土伯特 语(具)
\r\rubaliyambume sohote(注:此处看不清楚,难以辨识。) lak seme budonde baksii biwanggirid
\r\r翻译恰好补敦(位)巴克什(属) 授记
\r\rtuwabuha gisunde acanambi udu adaliame mutenakū bicibe
\r\r显示 语(与)合宜虽然 相似无能然而
\r\rgelhun akū[7b] kicerakūci ojorakū sembi
\r\r敢 不尽力 不可 (语助)
\r\r汉:且曰:“心经本藏地所有,而楞严则藏地所无,若得由汉而译清,由清而译蒙古,由蒙古而译土伯特(注:《御制文初集》写作“土伯忒”,《卫藏通志》写作“图伯特”。),则适合(注:《卫藏通志》写作“合”。)补敦祖师所授记。(注:《卫藏通志》“授记”后多一“也”字。)虽无似也,而实不敢不勉力(注:《卫藏通志》“勉力”为“勉”。)焉。”(注:此句钢和泰先生曾感到颇难理解,后在陈寅恪先生的帮助下,正确地做了翻译。陈寅恪先生认为“虽无似也”不可能为乾隆皇帝自己所称,因而钢和泰先生加了附文,将此句归为章嘉国师所说。观满文则比较明确,句末有“sembi”这个小词,提示引言的结束。也就是说章嘉国师所述至此方告终结,陈寅恪先生的判断无误。)
\r\r满:tereci tob cin wangde ere baitabe nengelekini seme
\r\r于是 端庄 亲 王(注:庄亲王在此处的满文写法“tob cin wang”,tob本为端正之意,常作为封谥用语。“cin wang”为借自汉语发音。据《清史稿》卷二百十九,列传六,此庄亲王应为康熙第十六子,他精数学,通乐律,曾与修数理精蕴。乾隆七年命与三泰、张照管乐部。二十九年,允禄年七十,上赐诗褒之。三十二年,薨,年七十三,谥曰恪。)(与)此 事(宾)支撑(表意愿)(语助)
\r\rhese wasimbufi gurunibaksi janggiya kūtuktu jai funaii
\r\r旨降 国(属)巴克什 章嘉 呼图克图 又 傅鼐(注:《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一, 列传七十八,傅鼐,字阁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高宗即位,命署兵部尚书,寻授刑部尚书,仍兼理兵部。三年,坐违例发俸,发往军台效力。寻卒。然据下文提及的《首楞严经》编纂时间,为乾隆壬申(1752)至乾隆癸未(1763),即乾隆十七年至乾隆二十八年。那么傅鼐在乾隆三年已经去世,如何参与其事。查《清史稿》,有另一名叫傅鼐者,传在列传一百四十八,其字重庵,顺天宛平人,原籍浙江山阴。嘉庆十六年卒于官。依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其生卒年为1758—1811年,也不可能参与《首楞严经》的翻译工程。究竟此种偏差问题出于何处,还需进一步探究。)
\r\rjergi udu niyalmabe isibufi gūninbe akūmbume[8a] acabume
\r\r等 几个人(宾)招致 意(宾)尽心 校对
\r\rubaliyambubufi debtelin aname tuwabume wesimbuhe
\r\r翻译 本子,册依次 使看奏
\r\r汉:因命(注:《卫藏通志》“命”为“请”。据满文,意为“向庄亲王降旨,望其担负起此事”。“nengelekini”为祈愿式,语气不及命令式重,多意愿而非命令意味。)庄亲王董其事,集章嘉国师(注:章嘉国师依满文当译作为“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及傅鼐诸人悉心编校,逐卷进呈。
\r\r满:dari mini beye(注:此处“mini beye”为“躬亲、亲自”之意。) urunakū kimcime tuwafi tuwancihiyame
\r\r每 我的 身体 必定 详察 阅览 纠正
\r\rdasambi kenehujecuke ba bici[8b] uthai guruni baksi
\r\r改正 可疑处 若有 随即 国(属)巴克什
\r\rjanggiya kūtuktude hebdeme yargiyalambi
\r\r章嘉呼图克图(与) 商量核实
\r\r汉:朕必亲加详阅更正;有疑,则质之章嘉国师(注:同注③。)。
\r\r满:ere nomunbe abkai wehiyehe(注:abkai wehiyehe为年号,即“乾隆”。) sahaliyan bonio aniyaci deribume
\r\r此 经(宾)天(属) 扶佑壬 申 年(从)开始
\r\rsahahūn honin aniyade isibume ubaliyambume anggabuha
\r\r癸未 年(位)达到 翻译完成了
\r\r汉:盖始事则(注:“则”字,《御制文初集》用“自”。)乾隆壬申,而译成于癸未。
\r\r满: tobcin wang sa[9a] utucin arafi selgiyereo seme baime
\r\r端庄 亲王等 序写 传谕 (语助) 请求
\r\rwesimbuhe
\r\r奏
\r\r汉:庄亲王等请序(注:《卫藏通志》“序”写作“叙”。)而行之。
\r\r满:manggi mini gūninde akdun yabungga nomun serengge[9b]
\r\r之后 我的 心意(位)坚固行者经者
\r\r汉:朕惟楞严者,
\r\r 三、《御制楞严经序》产生之因由及始末\r\r“朕惟楞严者”之后的内容,钢和泰附文里未曾列入,目前尚无途径得到满文御制序的剩余部分,观《满文大藏经》第54函所收录的《首楞严经》满文本,并无此乾隆帝所作御制序。按照四体序的篇幅,所缺部分为七页。依四体合璧序的汉文版本,其所缺文为:
\r\r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一落言诠,失之远矣。而况译其语,且复序其译哉。然思今之译,乃直译佛语,非若宋明诸僧,义疏会解, 哓哓辩论不已之为。譬诸饥者与之食,渴者与之饮,而非拣(注:《御制文初集》为“拣择”。)其烹调,引导其好嗜(注:《御制文初集》为“嗜好”。)也,则或者不失能仁征心辨见妙谛。俾观者不致五色之迷目,于以阐明象教,嘉惠后学,庶乎少合于皇祖皇考宣扬心经之义例乎。——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r\r钢和泰先生之所以选择附录《御制楞严经序》的前十七页,是认为其属于整个序文的历史部分。此十七页,栏外左侧上方为藏文,下方为满文,栏外右侧上方为蒙文,下方为汉文。内容为《御制楞严经序》的页码,四种文字表达一致。编页自“御制序上一”起,以下依次编号,至“御制序下九”。但缺“下一”,“上一”之后紧接“上二”。
\r\r此序写作时间为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写作缘起则是御制满、蒙、藏、汉四体《首楞严经》的翻译自乾隆壬申(1752)起,至乾隆癸未(1763),即乾隆二十八年告罄,应主要翻译编纂者庄亲王等人的奏请而写。序中提及的翻译工程的负责人是庄亲王允禄,主要参与者则有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和傅鼐。查《清史稿》(注:参看404页注①。),所记载的两个傅鼐的活动时间都与《首楞严经》的翻译始末不符,一个在翻译开始的十几年前已经去世,一个在翻译开始时年仅六岁。是《清史稿》记载有误,还是另有一个傅鼐未被载入其中尚不清楚。
\r\r《御制楞严经序》并未探讨《首楞严经》的真伪问题。然而在乾隆皇帝的另一御制序文里也提及了《首楞严经》,此即他颁布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二十五日的藏文《甘珠尔》的序文。(注:此序名为rgyal pos mdsad pavi gser gyi bkah vgyur rin po che gsar bshengs kyi kha byang,是在深蓝色的纸上金汁书写藏文,钢和泰先生称其现静静地躺在上海银行的贵重物品储藏室里,然而在2011年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的时候,故宫博物院从所藏西藏文物中精选出229件珍品举办“故宫藏传佛教文物特展”,据称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其中就包括了此乾隆金书《甘珠尔》经,磁青纸,泥金书写,总共镶嵌珠宝达14364颗,是清代宫廷佛教经典装饰的极品。目前这部经分藏于北京和台北,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96函(夹)3052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12函(夹)。)这部甘珠尔为金写,装帧精美,首卷封面以珍珠和其他宝物装饰。乾隆三十五年的这篇序文提出,因为汉文本《首楞严经》中包含的经咒,与同一经咒的印度文献完全相同。有印度梵本渊源,因而整部《首楞严经》是真的。(注:参见钢和泰先生前揭文,pp.138—139.)这里提到的另一经咒应指不空所译《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般怛罗大神力都摄一切咒王陀罗尼经》。当然这只是乾隆皇帝或者说及其佛学导师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观点。李翊灼先生即认为正是两部经咒相似,但《首楞严经》中的音写糟糕损害了整部经的真实性。(注:转引自钢和泰先生前揭文,p.139.)以类似经咒的存在来证实或是证伪有待商榷,但至少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三世章嘉的态度,即判定《首楞严经》并非伪经。
\r\r乾隆皇帝为何选择《首楞严经》译成满、蒙、藏、汉四体合璧本,在序中他陈述了若干理由。首先,藏地作为印度佛经流传中土的中间环节,汉译的佛典在藏地也都可找到相应的文本。《首楞严经》却是例外。认为此经应该是在朗达玛统治时期时散失不全,此后的高僧大德由于没有正本,未敢妄加增补。其次,章嘉国师向乾隆陈述了元代佛学大师布顿(bu ston rin chen grub ,1290—1364)所作的授记,即此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自布顿大师往后推算,乾隆时期与“后五百年”时间上也是暗合的。当然,布顿大师的所谓授记,应该是三世章嘉为了劝说乾隆皇帝翻译《首楞严经》所作的附会之辞。再者,乾隆皇帝自述在平时忙于政事的闲暇,喜欢用“国语”翻译经书,《易经》等都是成功的例子。最后,则有追慕皇祖康熙皇帝、皇父雍正皇帝的用意。康熙时曾经以满汉蒙藏四语翻译《心经》,雍正时刊行。《首楞严经》可以效仿这种前例。此外,就《首楞严经》本身的思想内涵来看,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能仁直指心性之宗旨”。乾隆三十六年(1771)御制泥金楷书《首楞严经》汉文写本颇为珍稀,其卷前有泥金龙纹牌记,牌记上方正中是泥金篆书“御制”二字,这一乾隆御制牌记可作为乾隆皇帝对《首楞严经》思想内涵方面解读的一种补充。牌记内写道:“佛顶楞严,是最尊胜。证如来藏,入三摩地。修习圆通,应周十方。五十五位,成就菩提。华幢铃纲,七宝交罗。香海尘界,天人围绕。欢喜书写,聚紫金光。妙陀罗尼,梵音敷奏。恒沙国土,一切众生。悉仗愿力,福德长寿。”(注:向斯:《中国宫廷善本》,2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r\r除过《御制楞严经序》中乾隆皇帝所述的以上理由,笔者以为乾隆皇帝选择《首楞严经》作一四体文的译制,还有一种承自顺治、康熙、雍正各位此前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渊源。《秘殿珠林》记载万善殿钦定刻本中有世祖章皇帝钦定《楞严经会解》十五部(注:张照等:《秘殿珠林》,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823册,7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康熙帝则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定了一部《御选唐诗》,“其注释则命诸臣编录,而取断于睿裁”(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38册,万有文库本,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其中引用《首楞严经》解诗有14处。还曾在内廷刊刻了包括《首楞严经》在内的二十二部经。(注: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272页,扬州,广陵书社,2008。)雍正皇帝共有三部著作被乾隆收入《龙藏》,其中即有一部名为《御录经海一滴》(注:收入《乾隆藏》第164册,编号为1669。)者,雍正帝在序文里自述:“然则大藏经卷,如何可有所拣择耶?乃朕今者万几余暇,随喜教海于《般若》、《华严》、《宝积》、《大集》等经,卷帙浩繁者未及遍阅。但于《圆觉》、《金刚》、《楞严》、《净名》等经,展诵易周者若干部,每部各亲录数十则。”《楞严》被其选入此书,列在卷二。雍正还如此评价将这些经典的选录,“朕今以不拣择拣择,故所采录不独震旦经藏,未尝缺遗一言一句,即西天未来古佛未说者,亦复不增不减,无欠无余焉”,认为完满地收录了佛语之精髓,颇为自得。
\r\r《首楞严经》自唐代神龙元年译出之后,影响极大。而如上所述顺治、康熙、雍正诸帝对《首楞严经》的或印或引或选,体现了他们对《首楞严经》关注及对其价值的肯定。而乾隆帝对《首楞严经》的看重,以至最后组织完成四体合璧本的译制,很可能受到父祖们对《首楞严经》延续性关切的影响。乾隆皇帝本人作诗属文关涉“楞严”者更多,其化用经文娴熟,试举一例。《御制诗集三集》卷十六收录《松严》一首,其诗云:“孤亭四柱俯松岩,岩上松涛了不凡。七处征心八辨见,何如坐此悟楞严。”(注: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7册,2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其中“七处征心”“八辨见”皆是出自《首楞严经》的重要命题。
\r\r谈及《御制楞严经序》四种文字的互动关系,由于前辈学者尚未涉及蒙文本,笔者此文中也未加具体探究,故对蒙文版本不好置评。然而《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亦为乾隆御制,为满、藏、蒙、汉四体序。按照庄吉发先生对该序的判断,认为先有满文,再分别译成藏文、蒙文、汉文。(注:参见庄吉发:《〈清文全藏经〉与满文研究》,见蔡美彪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223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御制楞严经序》是否与之相类,先有满文,再译成藏文、蒙文、汉文,亦很有可能。就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为北京版藏文《甘珠尔》颁赐之《御制番藏经序》的情况而言,有专门校阅序的人员,也有翻译番字序、翻译蒙古字序的人员。而满文、汉文则为誊录官(注:参见李国强:《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4),70页。),似乎并无翻译满文序、汉文序的职责。作为母语,康熙、乾隆诸帝以满文写序份属自然,当然他们亦具备很高的包括汉文在内的以其他文字写作的能力,乾隆即被认为有韩昌黎之风。鉴于乾隆皇帝数量惊人的汉文诗文作品,他自己写作汉文序亦不足为奇。
\r\r 四、乾隆之前是否存有《首楞严经》藏译本?\r\r作为御制的序文,四种文字版本的序文之间应相当符合和翻译严谨。诚如钢和泰先生和沈卫荣先生所言,汉文版本与藏文版本即偶有出入,大部分大同小异。而那些差别之处,却不容忽视,甚至所谓少了汉文版的辅助,可能出现理解的偏差。(注:参见钢和泰先生前揭文,p.142;沈卫荣先生前揭文,5页。)满文版本与汉文版本比照之后,亦可看出两者相当贴切,即使抛却汉文本,依靠满文本理解亦不会如藏文本产生偏差。
\r\r钢和泰先生由藏文序译作英文版,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汉文本的理解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帮助。在他的译文里,在括号中补充了一些信息,以使表意明确。寺本婉雅先生的日文译文依据藏文序译出,由于缺乏汉文版的辅助,加之对此经翻译背景的陌生,产生了不少的理解偏差。沈卫荣先生以汉、藏版本序文对比,对钢和泰、寺本两位先生译文的不妥之处进行了探讨。
\r\r就藏文本与汉文本相较易产生理解偏差的句子,满文里如何解读呢?下面做一对比。
\r\r汉:是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
\r\r藏:lo lnga brgya song bai rjes su yul dbus nyid du bsgyur nas bod kyi yul du mngon par dar barong
\r\r钢和泰英译文:this scripture [the larger s'ūram·ngama], after having been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in China, will reappear in Tibet five hundred years hence
\r\r寺本译文,据沈卫荣先生转译:自[西藏之]乌斯(dbus)国译出,然后一定于西藏传播。
\r\r满:ere nomunbe sunja tanggū aniya oho amala kemuni dulimbai gurunci ubaliyambume tucibufi dzangni bade dahūme isinjimbi
\r\r就以上各版来看,寺本先生的译文相去最远,理解错误。而钢和泰先生的英译文忠实于藏文本,仅表达将从“中国”译至藏地。而满文、汉本则隐含了曾经即从“中国”译往藏地,之后还要再从“中国”译至藏地。此句看似仅是一字之差,却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在乾隆翻译四体《首楞严经》前是否有藏文本,且依据了汉文本而译出?在《御制楞严经序》中除“是经当于后五百年,仍自中国译至藏地”外,还有三句与此话题相关,即:
\r\r1.故今所译之汉经,藏地无不有,而独无《楞严》。
\r\r2.时是经已散失不全,其后虽高僧辈补苴编葺,以无正本,莫敢妄增。
\r\r3.《心经》本藏地所有,而《楞严》则藏地所无。
\r\r就满文本及钢和泰先生的英译文来看,第二句均相符,认为《首楞严经》残缺不全,没有正本。满文本将第一句解为“如今译成的所有汉文佛经,在藏地都是全备的,唯独《楞严经》没有”。 这里的“yongkiyam”意为“完全,完满,完备”,此句似乎更倾向于表达不完备之意。下文朗达玛毁佛佛经散失不全的不全用的也是“yongkiyarakū”,与第一句词源上有所呼应。第三句中满文“藏地所无”以“dzangni bade fuhali akūngge”来翻译,意为“在藏地全然没有”。钢和泰先生的第一句表达法与满文相似,“无不有”用“all …complete”来表达,而“独无《楞严》”更是用了“alone…incomplete”,这里钢和泰先生表达的很明确,是“不全”而“无”。据他所说,藏文本表达“ma thang”也是“不完整”的意思。此句,如果说满文还不够清楚,可做两解的话,藏文、汉文则是两个维度。那么满文最先译出,其他文本转译中有了理解或是语言转换难以规避的偏差较有可能。钢和泰先生第三句的理解再次与满文本高度一致,“is not found”。
\r\r这样一来,文本方面的问题似乎厘清了。然而这几句之间表意的矛盾却显得更加明显。如果说藏文本认为乾隆前存在藏文《首楞严经》译本,只是在朗达玛时期散失不全,汉文本可以理解为没有与汉文本《首楞严经》对应的藏文本,那么第一句话可以成立。第二句则是满、汉、藏版本都认同“散失不全”说。第三句满、汉、藏都一致,即“《楞严》则藏地所无”。此句似与前两句大相抵牾。尤其是且不论第一句如何理解,第三句看上去与第二句“散失不全”相矛盾。这种矛盾或许可结合之前所分析的引起偏差的布顿大师授记的话以及第三句中“《心经》本藏地所有”来理解。可以说第二句、第三句满、汉、藏三个版本达成了理解上的一致。基于第二句“散失不全”的无争议性,满文本第一句解读的两可和解为“不完全”的倾向性,汉文“独无《楞严》”或强调了与汉文本《首楞严经》的对应上,没有匹配的藏文本,即虽有残缺不全的版本,但不“全备”。第三句“《心经》本藏地所有,而《楞严》则藏地所无”中的“本”字值得注意,为“本来,原本”之意,也就是说《心经》在藏地本来就有藏文译本,事实也确实如此,《心经》藏文有十几种版本,在《丹噶目录》《旁塘目录》及《藏文大藏经》中,而且在敦煌也发现了译本。法成即译有藏文本,其藏文注疏本亦有多部。(注:参见旺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藏译文比较》,载《西藏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1),100页。)而《楞严》则本来没有藏文译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满、汉版本的序文中布顿大师的授记会是“仍自中国译至藏地”。
\r\r那么查考藏文资料,可以发现如今的德格版、北京版、那塘版《藏文大藏经》里都收录有两个古藏文译本,在吐蕃时期三大古目里有记载,布顿大师名著《布顿教法源流》里也有着录,并提出其中一个译本《佛顶经九卷之魔品少分译出》译自汉文。(注:参见[日]西冈祖秀:《ブトワン佛教史目录部索引I》,75页。)也就是确实在乾隆时代之前存有藏文译本,且布顿大师认为两部中的一部译自汉文。而《御制楞严经序》中所述授记,即便不是真实,也可说是有所本。两部古藏文译本,经笔者与汉文本比对,发现确为“残本”,大致对应汉文本的第九、第十卷。那么乾隆皇帝在《御制楞严经序》中所述由汉文往其他语种转译,应当可信,毕竟汉文本《首楞严经》是可作为转译基础的“完本”。而此序的解读,也不得不使人感慨乾隆皇帝尤其是其佛学导师三世章嘉学识的广博和译制四体合璧本之功德。两部古藏文译本是否早在朗达玛灭佛前就自汉文译出,有全译本存在,后损毁不少,还是其一源自汉文,另一部另有所本,都将是此序文引出的新的研究议题。
\r\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