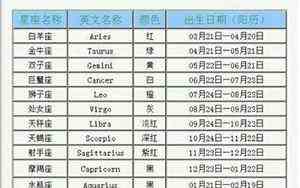何士光:走过人生三条路
写作和人们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根植在你对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追寻里。
“我们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并不清楚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并且后来也一直生活在这个久远的谜里。生命驱使着,乃至追逼着我们,在此后的日子里不断寻觅。这寻觅的道路,朝着生活的、人生的、生命的三条路径延伸,在寻觅之中,内心不断得到满足。”作家何士光如是说。
生活 · 五光十色,匆匆忙忙
1964年夏天,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何士光几经辗转,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贵阳,去往贵州北部的凤冈,准确地说,是凤冈县琊川公社琊川大队东风生产队。后来,他娶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姑娘,住在岳母家里。白天他岳母和妻子到生产队做活,他则去乡村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后,一家人会去种自留地,日子就这样重复着、流逝着。在他住处对面的山上,长着许多梨树,每到春天,雪白的梨花便满了山坡。而琊川就这样成了何先生笔下的“梨花屯乡场”。
在凤冈,何先生一呆就是20年。白天教书、耕地,等到夜晚来临,暮霭残阳亦消落,一切的喧嚣匆忙都变成五光十色的荒凉和熙熙攘攘的索漠。每日的忙碌,让何士光感到“仿佛在行进,其实又一步也没有挪动,就像自己是假装在生活似的,内心深处仍是不安”。
于是,阅读和写作便是他挨过那一个个无助无眠的夜晚最常做的事情。何先生大量读书,“我把那些被没收的书藏了十个麻袋。”何士光回忆说,“‘除四旧’时,所有书都收到文化馆楼上,放在那里准备搞纸浆。因为我的二胡和手风琴拉得好,有一次思想宣传队拉我加入。宣传队就在文化馆,我就瞄准那些书去了,把它们偷偷运回琊川。”
不久,女儿出生了,何士光自然就有了更多的事情。高考恢复后,何先生继续留在琊川任教,要帮助妻子考大学。
人生 ·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也是在琊川的日子里,何老开始了写作。1973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梨花屯客店一夜》诞生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1974年,他写完了中篇小说《草青青》,一年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某城纪事》。只是当时,写过的稿子只能自己藏起来,既不可能出版,也不足以为外人道;非但如此,一经察觉,还会罪在不赦,并且为智者所耻笑。但何老深知,很多事情,需要被记录。
于是,每天在学校上完六节课后,再回来种自留地,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油灯下提笔写作,基本每天要写6小时。何老说:“那时写下了一些文字,说不上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些记录。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也都有切实的依据。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生活,我才敢于把他们写下来,以至于他们具有的文学含义我都来不及考虑。”
直到1977年,何老才开始在《贵州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叫《飞吧,兰雁》。当时,为了避开个人审查,那篇散文还是用妻子的名字署名的。之后,他开始井喷式地发表作品,几乎都是在《人民文学》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上。
“何士光的小说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录。他在对地方的历史,人性的书写,语言的运用,国际的视野,小说的布排上都是有贡献的。”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先生这样评价何先生, “在中国这五六十年期间的小说作家里,何士光毫无疑问是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真实而不粉饰,质朴中又带着时代的忧伤。正是因为对时代的忠实记录,对人性的如实还原,让我们在重新反思那段历史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最有冲击力,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等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重大事件及世态人心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他的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算是极为罕见的。
如何老所说,“一个人要是写下过一点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有过的一点痕迹。”而经历了那些年来的人世沧桑之后,何老却感到生活变好了,心反而更迷惘了。生活对于何老来说已不再是惊诧和期待,写作这件事也开始缺少根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何老几乎不再写文学作品,他不愿再在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圈子里来回重复,而是想要寻找一些更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秘密。
生命 · 你若等待,奥义自来
他研究儒释道三家文化,最推崇道家,他自信地说:“关于生命,全世界没有人能搞清楚,只有中国人知道,而生命的奥义就在《道德经》之中。”他认为,“《道德经》该称得上是科学的著作,它讲天地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道德经》不是主张,不是见解。因为凡是主张、见解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不断更改的,甚至是口是心非的。只有这个是无可更改的、凡此不二的、知行合一的。”
何老举例说,我们的文化语言里,说“走的是道路,讲的是道理,担的是道义,修的是道行,连‘你晓得不晓得’都说你‘知道不知道’,‘道’贯穿我们的一切,只有懂得‘道’的含义,才算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对于生命的体悟,何老认为:求不得,只能等。人生便是各种机缘的总和,时候到了、因缘足了、因果成熟了,也就好比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就会越过原来的樊篱,向前跨出去一步。他关于生命的思考,都记录在《今生》之中了。
生活、人生、生命,感世间、找自己、窥宇宙,在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贵州出版社将何老目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与人生体悟都收录在《何士光文集》(共七卷)当中,走过他人生的三条路,就如同走过了一个时代。
何士光:走过人生三条路
写作和人们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根植在你对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追寻里。
“我们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并不清楚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并且后来也一直生活在这个久远的谜里。生命驱使着,乃至追逼着我们,在此后的日子里不断寻觅。这寻觅的道路,朝着生活的、人生的、生命的三条路径延伸,在寻觅之中,内心不断得到满足。”作家何士光如是说。
生活 · 五光十色,匆匆忙忙
1964年夏天,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何士光几经辗转,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贵阳,去往贵州北部的凤冈,准确地说,是凤冈县琊川公社琊川大队东风生产队。后来,他娶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姑娘,住在岳母家里。白天他岳母和妻子到生产队做活,他则去乡村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后,一家人会去种自留地,日子就这样重复着、流逝着。在他住处对面的山上,长着许多梨树,每到春天,雪白的梨花便满了山坡。而琊川就这样成了何先生笔下的“梨花屯乡场”。
在凤冈,何先生一呆就是20年。白天教书、耕地,等到夜晚来临,暮霭残阳亦消落,一切的喧嚣匆忙都变成五光十色的荒凉和熙熙攘攘的索漠。每日的忙碌,让何士光感到“仿佛在行进,其实又一步也没有挪动,就像自己是假装在生活似的,内心深处仍是不安”。
于是,阅读和写作便是他挨过那一个个无助无眠的夜晚最常做的事情。何先生大量读书,“我把那些被没收的书藏了十个麻袋。”何士光回忆说,“‘除四旧’时,所有书都收到文化馆楼上,放在那里准备搞纸浆。因为我的二胡和手风琴拉得好,有一次思想宣传队拉我加入。宣传队就在文化馆,我就瞄准那些书去了,把它们偷偷运回琊川。”
不久,女儿出生了,何士光自然就有了更多的事情。高考恢复后,何先生继续留在琊川任教,要帮助妻子考大学。
人生 ·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也是在琊川的日子里,何老开始了写作。1973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梨花屯客店一夜》诞生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1974年,他写完了中篇小说《草青青》,一年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某城纪事》。只是当时,写过的稿子只能自己藏起来,既不可能出版,也不足以为外人道;非但如此,一经察觉,还会罪在不赦,并且为智者所耻笑。但何老深知,很多事情,需要被记录。
于是,每天在学校上完六节课后,再回来种自留地,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油灯下提笔写作,基本每天要写6小时。何老说:“那时写下了一些文字,说不上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些记录。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也都有切实的依据。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生活,我才敢于把他们写下来,以至于他们具有的文学含义我都来不及考虑。”
直到1977年,何老才开始在《贵州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叫《飞吧,兰雁》。当时,为了避开个人审查,那篇散文还是用妻子的名字署名的。之后,他开始井喷式地发表作品,几乎都是在《人民文学》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上。
“何士光的小说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录。他在对地方的历史,人性的书写,语言的运用,国际的视野,小说的布排上都是有贡献的。”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先生这样评价何先生, “在中国这五六十年期间的小说作家里,何士光毫无疑问是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真实而不粉饰,质朴中又带着时代的忧伤。正是因为对时代的忠实记录,对人性的如实还原,让我们在重新反思那段历史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最有冲击力,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等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重大事件及世态人心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他的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算是极为罕见的。
如何老所说,“一个人要是写下过一点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有过的一点痕迹。”而经历了那些年来的人世沧桑之后,何老却感到生活变好了,心反而更迷惘了。生活对于何老来说已不再是惊诧和期待,写作这件事也开始缺少根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何老几乎不再写文学作品,他不愿再在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圈子里来回重复,而是想要寻找一些更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秘密。
生命 · 你若等待,奥义自来
他研究儒释道三家文化,最推崇道家,他自信地说:“关于生命,全世界没有人能搞清楚,只有中国人知道,而生命的奥义就在《道德经》之中。”他认为,“《道德经》该称得上是科学的著作,它讲天地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道德经》不是主张,不是见解。因为凡是主张、见解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不断更改的,甚至是口是心非的。只有这个是无可更改的、凡此不二的、知行合一的。”
何老举例说,我们的文化语言里,说“走的是道路,讲的是道理,担的是道义,修的是道行,连‘你晓得不晓得’都说你‘知道不知道’,‘道’贯穿我们的一切,只有懂得‘道’的含义,才算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对于生命的体悟,何老认为:求不得,只能等。人生便是各种机缘的总和,时候到了、因缘足了、因果成熟了,也就好比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就会越过原来的樊篱,向前跨出去一步。他关于生命的思考,都记录在《今生》之中了。
生活、人生、生命,感世间、找自己、窥宇宙,在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贵州出版社将何老目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与人生体悟都收录在《何士光文集》(共七卷)当中,走过他人生的三条路,就如同走过了一个时代。
何士光〡山行偶记
空闲的时候和女儿去黔灵山游玩。这就得顺着曲折的石级上山。知道两旁有人守候着,向你要一些零钱,来到山下的时候,便先换好一些准备着。这不是布施,布施我们还不配。只是觉着漠然地走过去,是很尴尬的。
那么,先是硬币,后来是角票,先是面值小一点的,后来是面值大一点的,一路走过去的时候,也就一一地散出去了。而所谓准备,当然就永远也不会充分,不久也就告罄。这时候却来了一位老人家,看上去不管怎样说,似乎也应该有他的一份,于是又只好搜寻着,找出一张票子来送给他。虽说面值是更大一些了,也算了却了这一路行程。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回首一瞥来路,不知为什么,却忽发奇想:这是乞讨是不是?这是化缘是不是?那么这乞讨或化缘的,又何止是守候在这儿的人们?应该说你也是。难道你没有请求过什么?难道你没有伸手接过什么?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形式。
你来到这人世上的时候,并没有携带着什么,正如人们来到这人世上的时候,也没有携带着什么。我们都不过经由自己的因果,得到和送走自己的一份。
这一份是多少,由什么决定?念头动起来的时候,就不由得想下去。
方式是不是很要紧?但方式却似乎不出于一个人的选择或决定。谁不愿意这方式更简捷、更丰厚呢?但简捷而丰厚的方式,却不属于每一个人。即以同样的方式而论,好比同为一树桃花,却也有零落流水,或者沉香锦被。一路上的人们,不都同样是伸出手乞讨?到底又还是有的多、有的少。要紧的应该是努力?表面地看来是这样的。但又不难看出来,多少与否又不一定同努力成正比。那不仅守候着,而且还追逐的,会不会更多呢?但他追逐了一阵,又还是一无所得。倒不如那始终守候着的,却蒙着更多的机遇。这样一来,也就看不出努力是不是可以指望的。
我们一向不是倚仗因果的分析?那些零钱都对应地落到了不同的人的手上,你能找出来必然的关系?那位后来遇到的老人家,为什么是更多的呢?你和他完全有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相遇,但你们竟然在山路上相遇了,这因果会在哪里?如果要追寻,就不得不伸延开去,差之毫厘的时候,就会失之千里。每一个结果之前都有一串原因,而每一个原因在成为原因之前又首先就是结果,就不得不从他的一生说起,也从你的一生说起。而这又还不过是线索而巳,这样追寻的时候,又不得不对支配着我们的众多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剖析。这样你就会看见原因和结果都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这样你最终面对着的,就不能不是宇宙和生命的奥秘。你都知道一些什么呢?你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你的那一点识心的分别计较又能算什么呢?以至于你对因果的分析,不过是在安慰、欺骗和愚弄自己。照这寺院里供奉着的佛的说法,就不过是“执迷”。而认识存在和我们自己,又正是佛陀在明白了此间的奧秘之后,所期望于我们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始终面对的、愈来愈显得紧迫的课题。
但是当然了,佛陀的言语,是没有多少人在意的。这一点佛陀也十分清楚,说是到了末世时候,人们的染积愈来愈深,也就再难回过头来,好好地审视自己。那么又权且往前走吧,山道走完了,来到这山顶上,又正是熙熙攘攘的。
因果我们认识也罢,不认识也罢,必然是存在的。它就绕行在我们之间,绕行在这山林之中,也绕行在山下的尘世里。这样你也就别希望,所有因果的辗转相成,就一定会使世界,总是更美丽、愈来愈美丽。因为人们固然始终有自己的希望,而因果却又始终有自己的轨迹,以至于“救救地球,救救人类”的呼唤都巳经见诸报端了,虽则和人类的作为相违背,也同样是人们希望的。
写于1994年
本文节选自《田野·瓦檐和雨》
《田野·瓦檐和雨》
何士光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