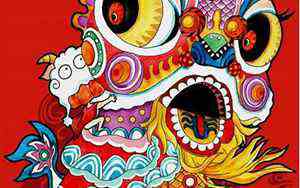潮汕方言外来词琐谈
“薝卜”是“栀子”吗? 1997年出版的《新编潮州音字典》(林伦伦主编)以多字单素词收入“薝卜”一词: 【薝卜】chánbo[siam5bog8檐仆]栀子花。梵语campaka的译音词。唐•卢纶《送静居法师》诗:“~~名花飘不断,醍醐法味洒何浓。” 林伦伦先生将以上结论收进其主编的《潮汕民俗大典》。并在其撰写的该书第九章《潮汕方言与畲语》中指: 栀子花,潮汕话叫“薝卜”siam5bog8,古汉语译为“瞻博”、“占博伽”等,词源是梵语campaka。这也是从西域传进中国的。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云:“陶贞白言栀子翦花六出……相传即西域薝卜花也。”栀子花名已汉化,但“薝卜”却让人一听便知其为音译名词。 该书又在498页对应如下脚注: ①菠菜、木棉、薝卜三个词的词源均来自刘飞琰《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 笔者阅查了《汉语外术词词典》中的“薝蔔”条: 【薝蔔】zhānbò—→瞻蔔伽(本页) 【瞻蔔伽】zhānbòjiā一种开黄色香花的树,树形高大,学名Michelia campaka。又作‘瞻蔔加、瞻蔔、瞻波、瞻波迦、瞻婆、瞻博、瞻博迦、瞻博加、瞻博伽、詹波、蒼蔔、占婆、占博迦、苫婆、赕婆、旃波迦、旃簸迦’源梵campaka。 《汉语外来词词典》并无提及“薝蔔就是栀子”。那么,我们便有必要弄清楚几个问题: 1、从梵语campaka译音过来的植物是否“栀子”? 2、“薝蔔”和“栀子”是否同一植物? 3、潮汕方言中的“薝蔔”是否外来词? 下面,笔者从能翻阅到的部分工具书的释义中分类探讨: 一、未收“薝”、“薝蔔”的《字典》、《词典》: 1、《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1981年12月版。 2、《现代汉语大词典》王重亿主编海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3、《现代汉语实用字典》潘晓龙主编南方出版社2000年9月版。 4、《新潮汕字典》张晓山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 5、《国语潮音大字典》张惠泽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版。 6、《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李新魁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版。 7、《潮州音字典》(普通话对照)吴华重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8、《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92年重排本) 二、收有“薝”、“薝蔔”,但未注明其为“栀子”的《字典》、《词典》: 1、《汉语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薝】zhān《集韵》之廉切,平盐章 字头之下未收录“薝蔔”词。 2、《实用汉字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礼1985年8月版): 【薝卜】(zhān沾)[薝卜]花名。《本草纲目•木部三》“卮子”:“木丹,越桃,鲜支,花名薝卜。” 3、《辞海》(夏征农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缩印本•1989年9月版): 【薝】(zhān沾)见“薝卜” 【薝卜】花名。 4、《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6月版: 【薝蔔】梵语Campaka音译。又译作瞻蔔伽、旃波迦、瞻波等。义译为郁金花。唐卢纶《送静居法师》诗:“薝蔔名花飘不断,醍醐法味洒何浓。”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三•卮子》[集解]引苏颂曰:“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七八尺,叶似李而厚硬。又似樗蒲子,二三月生白花,花皆六出,甚芬香,俗说即西域薝蔔也。夏秋结实如诃子状,生青熟黄,中仁深红,南人竞种以售利。”清赵翼《哈密瓜》诗:“君不见薝蔔分根自大实,茉莉购种从波斯。” 5、《汉语外来词词典》(见上) 而《辞源》在详细解释“薝蔔”一词之后,直接否定了其为“栀子”的说法: 【薝蔔】花名。梵语。又译作旃簸迦、瞻博迦。义译为郁金花。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十八广动植木:“陶贞白(弘景)言,栀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传即西域薝蔔花也。”宋陶谷清异录居室:“杜岐公(衍)别墅建薝蔔馆,室形亦六出,器用之属俱象之。”旧以薝蔔为栀子,非。 三、以上提及的《字典》、《词典》均收录了汉语双音节词“栀子”或“栀”字头: 【栀子】zhizi 1、也叫黄栀子、水横枝。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夏季开白花,很香,供观赏。果实可供药用,也可做黄色染料。 ——《现代汉语实用字典》 2、常绿灌木或小乔木,叶子对生,长椭圆形,有光泽,花大,白色,有强烈的香气,果实倒卵形。花供观赏,果实可做黄色染料。有的地区叫水横枝。 ——《现代汉语词典》 3、[cape jasmine]一种灌木或小乔木。(GowdeniaJasminoides)因其芳香的白花而被长期栽培。 ——《现代汉语大词典》 4、栀子树,常绿灌木,夏季开花,白色,很香。果实叫栀子。叶、花、果、根都可以入药。 ——《新潮汕字典》 5、zhi[哥衣1——枝] 木名。栀子。茜草科,常绿灌木。初夏开白花,稍带黄晕,有香气。果长椭圆形,赤黄色,可入药,又可作黄色染料。《说文新附•木部》:“栀,木,实可染。”《广韵•支韵》:“栀,栀子,木实可染黄。” ——《国语潮音大字典》 6、《说文新附》:“栀,木,实可染。从木,卮声。”木名,栀子,茜草科,常绿灌木。初夏开白花,稍带黄晕,有香气。果长椭圆形,赤黄色,可入药,又可作黄色染料。木黄褐色,质密而坚实,可供雕刻等用。 ——《汉语大字典》 7、木名。常绿灌木,仲春开白花,花甚芳香。夏秋结实如诃子,生青熟黄,可入药,并可作黄色染料。见本草纲目三六木三卮子。 ——《辞源》 通过上述比照,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从梵语campaka译音过来的植物并非“栀子”;“薝蔔”和“栀子”并非同一植物;潮汕方言中的“薝蔔”并非外来词。理由是: 1、《汉语外来词词典》对“薝卜”的释义未提有别名“栀子”,而诸多汉语《字典》、《词典》解释“栀子”时,又不提其音译自“梵语campaka”。 2、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薝卜”是“一种开黄花的树,树形高大”的植物,而在诸多汉语《字典》、《词典》中的“栀子”却是“灌木”,充其量为“小乔木”。大家知道,所谓“灌木”,是“矮小而丛生的木本植物,如荆、玫瑰、茉莉等”(见《现代汉语词典》)。“树形高大”的“薝卜”同“矮小而丛生”的“栀子”不能相提并论。 3、《汉语外来词词典》指:“薝卜”的学名是“Michelia campaka”,而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栀子”的学名是“cape jasmine”。 4、《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薝”的汉语注音是“zhān”,且其不同的17个书写形式,相同字头的“瞻”、“詹”、“簷”、“占”、“旃”,普通话都读“zhān”。而“睒”,普通话读“shǎn”;“苫”,普通话读“shān”。这些读音同《新编潮州音字典》中给“薝”的普通话注音“chán”有相当的差距。 5、“瞻”、“詹”、“占”在潮汕方言中读[ziam1<之淹1>尖](《新潮汕字典》):“睒”读[siam2<思淹2>闪](同上):“苫”读[siam1<思淹1>森](同上);“旃”读[ziang1煎](同上)。同《新编潮州音字典》中“薝”的潮汕话读音[siam5]不相同。 因为通行的《新潮汕字典》、《潮州音字典》、《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以及《国语潮音大字典》均未收“薝”字,我们只能从1937年2月汕头育新书社印行的陈凌千编《潮汕字典》寻求答案:“【薝】占字(平)音尖,亦音瞻,薝蔔,花名”。这与《新编潮州音字典》中“簷”的注音“chán”也绝不相同。 6、事实上,在潮汕,“薝蔔”与“栀子”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①《粤东植物目录》(陈蔚辉编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载:……栀子属Gardenia Ellis 栀子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薝蔔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var.fortuniana 狭叶栀子Gardenia stenophylla Merr ②《潮汕植物志要》(吴修仁编著韩师专学报编辑部1983年1月)更是详细地介绍了《粤东植物目录》所载潮汕地区栀子属的三种植物: 831.栀子(图674)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茜草科] 别名:黄栀子(《植物名实图考》),山枝子、黄枝子(潮汕),水黄枝(普宁、潮阳),水晶花、山婵卜(潮安)。 灌木。生于山坡、灌丛中。果实可作黄色染料。根、叶、果药用,治黄疸型肝炎、蚕豆黄、感冒发热、茵痢、肾炎水肿、鼻衄、口舌生疮、乳腺炎、疮疡肿毒、扭伤。 [附注]同属植物狭叶栀子(G.stenophy lla Merr.),各地也有分布(图675)。 文献:图鉴四册238图5890,汇编上册740,大辞典下册1984,药用图鉴220,潮汕64,陆丰241,南澳336,广志508,海南志三卷325,海南284,中草192,广兽540,惠阳一集88,梅县400。 832.薝蔔(图676) Gardenia jasminoides Ellis var. fortuniana Lindl.[茜草科] 别名:蝉卜、(潮汕),白蝉,白蟾。 常绿灌木。夏季开花,花白色,花大且重瓣,朵朵单生叶腋,芳香扑鼻。本种为潮汕庭园主要观赏花卉之一。性喜温暖湿润,在肥沃的酸性土中生长良好。 《志要》对“栀子”和“薝蔔”的描述,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栀予”是“灌木。生于山坡、灌丛中”。而“薝蔔”却是“潮汕庭园主要观赏花卉之一”。潮汕人所说的“蝉卜”,绝非《汉语外来词词典》介绍的“树形高大”的“薝蔔”。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旧以薝蔔为栀子,非。”斗胆同林伦伦先生商榷。 “斟”是外来词吗? 潮汕人在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普及面较广的一个口语方言是“[zim1<枕1>],相当于普通话的“亲”、“吻”: 勿[zim1]奴囝个面。 伊抱阿细弟青[zim1]白[zim1]。 阿老兄万分激动,对个奖杯[zim1]了又[zim1]。 陈泽泓先生在介绍潮汕方言的演变时,将方言口语表“吻”义的词记录为“斟”,而且归进潮汕方言外来词:“其自马来语,有称警察为‘吗淡’(mata)、铁线为‘亚铅’(ayan)、手杖为‘洞角’(tingkeet)、骑楼下街廊为‘五骹砌’(kaki-lima)、饼子为‘罗的’(roti)、吻为‘斟’、边缘为‘墘’。”(《潮汕文化概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新潮汕字典》(张晓山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收录了潮汕方言“外来词”【斟】:zim1<之音>枕1。①……②潮<外>马来西亚chinm的译音,原义为用鼻子亲热。潮州话表示作嘴唇接触表示亲热,相当于普通话的“亲”、“吻”。 《新潮汕字典》、《潮汕文化概说》在表述马来语表“吻”义的音节时,均使用同音假借字“斟”。而《闽南方言大词典》(周长楫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收录的这个方言“外来词”,又有不同的表述:【唚】[tsim1]亲嘴;接吻。来自马来语tioem的音译。 潮汕方言音节[zim1],用国际音标注音为[tsim1],与闽南方言【唚】的注音一致。同一个“外来词”,相同的发音,用以标记的汉语书写符号不同,这并不奇怪。同一汉语外来词有多种书写形式,哪一个是正体,由各词典的编篡者依据一定的原则确定。本文讨论的问题是:用汉字“斟”或“唚”标记的潮汕方言表“吻”义的音节[tsim1]是方言特有的外来词吗?试比较: 一、除《新潮汕字典》,笔者所能查阅到的潮汕方言《字典》、《词典》均未见用“斟”标记“外来词”的词条或字头: 林伦伦主编《新编潮州字典》 李新魁主编《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 吴华重主编《潮州音字典》 张惠泽主编《国语潮音大字典》 陈凌千主编《潮汕字典》 二、杨扬发编《潮汕十八音字典》(汕头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用与《闽南方言大词典》相同的汉字书写符号“唚”记录了表“亲”、“吻”义的方言词,却未明确其为外来词:“【唚】真音1zim1。<方>接吻,亲嘴:潮汕方言叫‘相唚’,唚嘴。” 三、除了《闽南方言大词典》、《潮汕十八音词典》,其他收录【唚】字的现代汉语《字典》、《词典》,大多将【唚】作为【吣】的异体字注音、释义,且都没有“亲”、“吻”这一义项: (一)【吣(唚)】qìn[cim3深]猫狗呕吐。 采用此释义的有:《新编潮州音字典》、《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潮州音字典》、《新华字典》。 (二)【吣(吢、唚)】qìn①猫、狗呕吐,②<口>谩骂:满嘴胡~。 采用此释义的有:《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实用字典》、《新潮汕字典》。 (三)【唚】(qìn沁)猫狗呕吐。借用以骂人,比胡说更重。 《辞海》、《实用汉语字典》采用此释义。 四、《汉语大字典》第267页上,却清楚地记载了古汉语已使用的“唚”的另一个义项: 【唚】(一)qīn亲吻。清袁于令《西楼记•集艳》:“抱住他唚几个嘴。”今潮州方言还称亲吻叫“唚”。(二)…… 《汉语大词典》第三卷第369页也有同样的释义: 【唚】2[qīn]亲吻,清袁于令《西楼记•集艳》:“抱住他唚几个嘴。” 无论是注音、释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唚】显然有别于其他《字典》、《词典》。 从各种工具书传递出来的不对称的信息,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一、认为潮汕方言表“亲”、“吻”义的单词[tsim1]是外来词,且用同音假借字“斟”作为记录语音的汉字书写形式的,只有《新潮汕字典》和陈泽泓先生在《潮汕文化概说》中的举证,然而陈先生在著述中却末提供作为“外来词”的“斟”的外语词原形。 二、认为方言表“亲”、“吻”义的单词[tsim1]是外来词,且注明其词源的只有《新潮汕字典》和《闽南方言大词典》(潮汕方言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大部分词语无论语音、词义均相同或相近,《闽南方言大词典》对潮汕方言的探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然而《新潮汕字典》、《闽南方言大词典》所提供的[tsim1]的外语原形不一致:《新潮汕字典》称是“马来西亚语chinm的译音”,而《闽南方言大词典》则称其“来自马来语tioem的音译”。在马来语,“chinm”与“tioem”是否同音同义异形,笔者不敢妄言。 三、认为音节[tsim1]表“亲”、“吻”义且用“唚”作为记录语音的汉字书写形式的有《闽南方言大词典》和《潮汕十八音字典》,但两者对词条【唚】的词源分类不同:《闽南方言大词典》将【唚】列为音泽外来词,而《潮汕十八音字典》将【唚】归入方言词。 四、《汉语大字典》收录的古白话词【唚】,其表“亲吻”之义与今潮汕方言同,且该字典也在释义中申明:“今潮州方言还称亲吻叫‘唚’。”据《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载:“袁于令(1592-1674)明末清初戏曲作家……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今存传奇《西楼记》……”“唚”为古白话传奇《西楼记》的用词。换言之,潮汕方言的单音节词【唚】是古白话的遗存。因而,以词源分类而言,将【唚】归为古汉语词也未尝不可。 五、抛开【唚】是外来词、方言词、古语词的争议,既然《汉语大字典》引述了古白话“抱住他唚几个嘴”,学界已有用【唚】表“亲吻”义一说,那么,《闽南方言大词典》和《潮汕十八音字典》用“唚”作为音节[tsim1]的汉语记音符号,应该比用同音假借字“斟”更加科学,更加贴切。今后,其他潮汕方言的字典、词典,是否可以在字头或词条【唚】的释义中,再加上一个义项:“亲”、“吻”。 六、《闽南方言大词典》和《潮汕十八音字典》在为【唚】释义时,似乎也欠妥当: 【唚】亲嘴;接吻。(《闽南方言大词典》) 【唚】接吻;亲嘴:潮汕方言叫“相唚”,唚嘴。(《潮汕十八音字典》) 潮汕方言的[tsim1],相当于普通话的动词“吻”:“用嘴唇接触人或物,表示喜爱。”(《现代汉语词典》)。而“接吻”、“亲嘴”却是:“两个人的嘴唇相接触,表示亲爱。”(《现代汉语词内典》)。 毕竟,“吻”同“接吻”、“亲”同“亲嘴”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相比之下,《新潮汕字典》对潮汕方言词[tsim1]的释义更为准确:潮州话表示用嘴唇接触表示亲热,相当于普通话的“亲”、“吻”。 笔者才疏识浅,祈望以从工具书上抄抄摘摘拼凑而成之拙文就教于方家。 (作者:林庆熙)(作者单位: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发表日期:2013年12月13日)
中国万州有一种美食远销海外声名远扬,最早可追溯至远古
前言
华夏烤鱼,源远流长。自人猿揖别、燧人取火,暗夜中的熠熠火光照亮了人类文明的深远前景。
火的运用让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启了熟食烹饪、文明进化的崭新历程。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及生产力的发展更迭,熟食经历了“火烹、石烹、水烹、汽烹、油烹、”等不同的发展阶段。烤鱼的烹饪方式便是诞生于远古人类的火烹时期。
寻古觅踪话烤鱼——万州烤鱼的前世今生
回溯时光长河,生活在三峡库区长江边上散布聚生的“善舟揖,渔猎为生”的巴人一支的獽人族群,是万州烤鱼发端起源的肇始者。据《华阳国志》载:涪陵和巴郡都分布有獽人群落,大至活动范围在今奉节与涪陵之间。《水经注、江水注》记载:“江水东经壤涂而历和滩”。“壤涂”即今重庆市万州区境内长江上游四十公里的瀼渡镇,因獽人聚居而名;《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下载:“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隋书、地理志》称獽人“其居处、风俗衣冠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
獽人是巴人一分支。学者张勋赕考证:“巴应是南方壮泰语系民族中鱼的读音”,巴就是鱼。在峡江高山大河鱼盐所出的资源条件下,渔猎成为他们攫取生存资料的主要方式和基本来源。在陶器尚未问世前,火烤石炙就是当时唯一的熟食烹饪方式。从峡江地区发掘的夏商至汉代多达三十三处的鱼业遗存(铜鱼钓、鱼叉、鱼镖、石陶网坠、石锚及大量水生物遗骸与火烬灰)中,不难想见远古獽人黄昏时在长江边上,将渔获物抺上盐巴,围坐篝火旁燃木烤鱼的情景。
烤鱼不仅是獽人主要的果腹熟食,同时也彰显出獽人初始的生存智慧和对食物美味的追求向往。更为后世万州烤鱼的开枝散叶播下了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种子。战国后期,随着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的推进,巴人及巴国便从历史版图上永久消失。但发源于万州獽涂獽人的烤鱼烹制方式却被奔波于川江上的纤夫船工传播至峡江两岸的村镇城乡。
如1999年在万州糖坊坪出土的手工打制砾石而成的网坠、2005年在万州中坝子出土的汉初烹鱼陶俑、2016年在巫山出土的汉中期的烹鱼陶俑等文物,便是万州烤鱼流转传播的有力的佐证。时空变幻,食风流转。后世名噪一时的宁河烤鱼、巫山烤鱼均是万州獽人烤鱼延绵不绝的余韵回响。历时几千载,经无数代人的手传心悟、融汇升华,万州烤鱼形成了自已独特的烹制方式和色香味型俱佳的菜品风格。并以几十个不同味型的菜品糸列,征服了不同饮食偏好的中外广大食客。
2018年经考核评审,中国烹饪协会特授予”中国烤鱼之乡——万州烤鱼”的荣誉称号。当下万州烤鱼作为新时期大众餐饮中时尚新品的黑马,在继山城火锅、重庆小面风靡全国之后,闪亮登场,惊艳中外美食老餮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