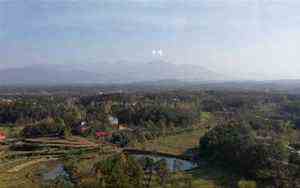为什么从手掌的裂纹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呢?
手相生命线怎么看?生命线是食指与拇指之间,以半圆形包围拇指球的线,任何人的手都刻有此线;最好的生命线,是深刻包围拇指球至底部,忌短及在中部终止或断续的线,又有流向月丘的线,有的紧包围拇指球,也有较宽包围等各种线。
生命线的长短,一般认为是表示寿命的长短,但其实生命线的长短与寿命无关,生命线只是表示:1、个人的体力强与弱。2、个人的家庭环境运气吉凶。3、个人的意外或健康疾厄。4、性能力的衰旺。生命线从起点至末端不间断,更刻著深而又鲜明的线条,此线如稍带红色,表示体力充沛,能做大事业;
相反的线短或断断续续或成为链状或出现十字形等,表示坏的记号,主有病弱或受伤的预兆;生命线多半在起点附近成锁链状,且下部分叉成几条,尤其线的下部,交插(命运线)或(健康线),所以生命线之形状显得不完整,往往很容易成为不规则;下部从生命线之流年来看,等于进入身体衰弱的老年期,所以线无劲而乱,是当然的。
生命线长至手颈中部,深刻又鲜明,表示生命力强,健康长寿,个性开朗坦率,身体健康,精力旺盛。
在生活上,凡事积极主动,勇往直前,但容易独断独行,自以为是,主观意识较强,宜多自我克制,避免过度放纵自我,以免造成身心的伤害。但如果线断断续续或中途出现坏记号,当然不能保持健康长寿;一般人往往只看生命线的长短,其实生命线的长度,虽表示自然的生命力,但是遇自杀,灾祸或战死,则再长的命,也被中断了,因此生命线的长短,并不能决定寿命之长短;生命线的长度,并非永久不变,而存有些微伸缩性的变化;
如仔细的看线尖,会在健康时稍伸出明显一点,长年病痛则稍微呈枯萎而又缩小。生命线短,在中途忽然变细小而消失的,即表示生命力弱,但若以线之长度来决定是否短命是危险的;如左右手的生命线均短,且几乎在同一位置终止的相,即表示在终点的年龄,有生命危险(或仅活到那个年龄),但如果只有一手的生命线较短,则无此顾虑;
即使生命线再短,但大拇指不错或智慧线优秀或辅助线的火星线有劲的话,那就可补救生命线的缺点,短的生命线也有微微伸长的可能性;总之:生命线长的人,如喜欢纵欲或暴饮暴食,亦无法长寿,相反的,即使生命线短的人,如果能多多保重身体,亦能多活几岁。生命线形成大曲线,越过手掌中央的直线,即金星丘之面积显著的变大;金星丘表示精力及活动力和性能力,所以拇指球愈膨大,精力愈旺盛,不会感到疲劳,很容易的能够摆脱生活上的辛苦;
但此精力如错用于性欲,则将会引起色情纠纷;主妇如有此种手相,除非丈夫精力很充沛,否则难免红杏出墙;年轻的女性有此相,即不易控制性欲,可能引起异性间爱欲问题。生命线之弧形少,金星丘的面积小;精力不旺盛或性荷尔蒙分泌少,所以吸引异性的魅力较弱;
生命线或智慧线幼弱,再加上金星丘贫乏,则表示生活力弱,且有虐待狂,因此要开拓命运很难。生命线成为链状,通常都出现在手掌柔软的人,线成此链状的人,体质弱,易于患病,精力不充沛,欠缺耐性,无自信心;如链状涉及于生命线的全体,表示对自己的体力无自信,连想吸引异性的活力,和性爱都没有,生活单调,没什么趣味可言;
假如生命线的上部,和中部成为链状,而其下深刻一条铁线,即表示在中年以前身体软弱,但中年以后,回复健康,可自由自在的活动。生命线由长短不规则的断线成立,即表示生殖力弱或对体力无自信;此手相在左手时,主年轻时呼吸器官或精力较弱,易于生病,初婚之缘份薄;如果中部或下部
成为一条鲜明的线,中年以后可获健康;女性的生命线断断续续,表示不能靠丈夫,自己要找个副业增加收入;生命线的一部份,如消失或细小,主体力弱;
生命线细得几乎看不见,表示气力衰弱,对疾病无抗力,也无恢复力的自信。生命线的中途,出现岛形记号,表示身体虚弱,无法充份工作或不能为对方效力,此相大都出现在无劲的生命线上;
岛形代表疾病和受伤,要看其年龄,看生命线之流年就可知道;假如其流年和命运线之坏的流年一致,表示远离学业,职业或夫妇生活。金星丘附近的折线,横过生命线,称为(烦脑线);此为烦脑线成放射状的伸向手掌之上部,中部或下部的相,心境烦脑、生活的辛劳或喜欢操心;此放射状的线,如果不切生命线,表示在烦脑在内心,私生活很劳累;
如切生命线,表示烦脑由外边因数,社会做事很辛苦,生活情况不好。在生命线呈四角形之记号,最大1.4公分,最小1.5公厘左右;此相有时出现在线之间断处(记号A),有时出现于生命线之侧面(记号B);有此相的人,不管在任何场合,有任何危机,都能死裡逃生,脱离险境,但此记号亦是入狱或失自由的表示。
青眼有加:生命线
文&图/黄敬敬
◐
我是一名急诊科护士。
工作六年来,失落、温暖、感动、无奈、冷静……这些复杂的情绪曾无数次充斥着我的内心。在生命中穿行,也在生命里有了感悟。
医学院读书时,我曾无数次对自己的专业产生过疑惑与排斥,那是一个曾经对生活充满美好想象,决心要过上“诗意”生活的女孩,最后的一份倔强。之后考研失败、转行失败,这才让我决心用不一样的目光与心态来面对我的职业。
生活在真实世界中的我们,与陌生人建立信任,任重道远,或许一个眼神,一句话,便让其产生信任,从而愿意分着他(她)的故事,分担她(他)的无奈与悲痛,当然,他们亦可以选择对我们的关心与关爱置之不理。
每年春末夏初,在绿树成荫的人间世界,各类鲜花争奇斗艳,红粉、白黄,朵朵馥郁芬芳,图得就是凡人俗世的热闹和喜庆。这样的季节,一切都是蓬勃的、向上的,当然,也应该包括心情。
工作在医院,在生命垂危中或治愈康复中,体味到人间的冷暖。
现实是残酷的,它会让一个原本完整美满的家庭毫无准备地接受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所引发的破碎;现实亦是美好的,透过亲情、爱情与友情,能感受到其背后的纯粹与温情,还有看似简单的关爱中,所包含的浓浓爱意。
此时,我坐在窗前,低头可见一排整齐的梧桐,阳光好的时候,总能看到一缕缕光透过绿叶的缝隙投射到地面上。
在同一时刻,医院病床上那些或年轻或年迈的生命,他们竭尽全力,大口大口地呼吸,胸廓的起伏,有力而倔强;万千人流涌进一座城市、离开一座城市,他们要于某个地方紧紧扎根,必须要为此而奔忙于生活的大道上……
在转瞬即逝或永恒之间,而死亡正坐在幽暗处,等待着每一个即将靠近它的人。
我向来不是一个悲观厌世的人,当然,也并不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我只想以一颗最为平静的心,面向每一个生命,也包括面向我自己……
落叶归根
十五年过去了,他回来了,出现在他哥哥面前的是一个颧骨高凸、形体瘦削、疾病袭身的中年人。
虽然只有四十岁,但由于严重的肺结核,长期营养不良,整个人看上去明显憔悴、无神,面容比他近五十岁的长兄苍老许多。
十五年前,他因与父亲争吵,负气出走,壮硕年轻的他,还带有年轻人的傲慢与倔强,十五年里,他的父亲离世,长兄每年都要抽一段时间去寻找他,而他,一无所知。
走了很多地方,想必,也走过了很多情感,很多的期望与失落留在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从他入院时的神志不清中我们也能明白,他短暂而艰辛的一生,再也不会被人所知晓、所铭记。
他急促的呼吸抵抗着呼吸机面罩,双眼紧闭着,卧在凹陷的眼眶里。十几年里,他去了哪里?他是怎么走过来的?又是如何染上严重的肺结核,最后转移至大脑?
这是作为医护人员的我们,浮现在脑海里的疑问。
“我挺气我自己的,去年我在义乌找到他时,当时无论如何都应该把他带回来的……”他的长兄站在病床边,双手猛力擦拭着眼角的泪,声音有些颤抖。
“他为什么不跟您回来?”我忍不住问。
“不知道,反正就是劝不回来,怕拖累我们吧……”职业的敏感,已让我知道不能再深问。
“他肯定是觉得自己快不行了,才打电话给我,十几年了,我号码从未换过。”
我站在对侧,看着心电监护仪上随时可能跳动的数字,也感受到了一种力,那是一种生命的力,脆弱而又顽强。
他的长兄,头一直低垂着,双眼呆滞,身上弥漫着淡淡烟草味,领口泛着黑色的污渍,不时地用黢黑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躺在病床上的弟弟的面庞。
告知书上签署的放弃抢救、要求转院的字迹变得沉重,治疗已没有意义。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他们,当然,也包括我们,在等待他那位七十岁的母亲。
十几年里,她从中年走向暮年,却始终惦记着她的小儿子,她或许也想过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而杨柳依依的初春里,她接到了一个很沉重的消息。
在他母亲未到达之前,我一直在想象着那会是怎样的一位母亲,或者面对着她的恸哭,我该以怎样的职业心态去面对。
她迈着细碎的脚步,走进急诊室,再普通不过,枯燥灰白的头发有些零乱,面容清瘦,躺在病床上的他与她如此相像。
走进抢救室,走近他,她先是短暂的沉默,一句“三儿”未说完,大颗大颗的泪珠便流到了凹陷的双颊。我站在她的身后,听到低低的哭声,那低沉的哭声,传递着一个家庭的即将破碎,也传递一位母亲的心的破碎。
我选择了沉默,或许只有眼泪能解开她心底的愁郁悲痛,而言语,很无力。
呼吸机传来“滴滴哒哒”的报警声,他垂在床边的像根干柴棒一样僵直的手臂晃动了一下。他一定感受到了母亲的气息,昏迷中一定听到了母亲那声召唤。乳名未变,而他与她都变了模样。
“医生,再也治不了吗?”她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再次哀求着进门的医生。
“严重的结核性脑膜炎,要是早点治有希望的,但他拖延太久了。你看他又严重的营养不良,估计这些年生活很苦……”温和憨厚的急诊科医生,话语中不再只是冰冷的医学术语与专业理性,此时,他所秉持的,也是一颗同情心。
我看见,她使尽全力叹了一口气,眼窝里满是泪,额前的皱纹很深,深得炽热的灯光都照不进去。
120的平车转走了他,他的兄长与母亲跟着,而我知道,他奔波辗转的四十年的身体,即将归根。在感知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他耗尽全力想要回来,这都足以说明,他深爱着他的家乡。
我希望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他的记忆里还是一家人围坐桌前、欢声笑语的影像,我希望这样的美好没有被十五年的流浪时光所磨尽,也希望亲情的温暖没有被十五年的现实生活所湮灭。
窗外黄昏的光线投射到万物上,沉稳寂静,把人心中的那份温润、柔软牵出。我们目送着他归根,也期待着他的新生……
爱情的模样
马路旁的粉色茶花芬芳艳丽,即便是凛冽的腊月寒冬,这些可爱的生命也从未缺席过,何况已是暖意浸入,春意荡漾的春天。
初次见她时,我便被她眼里的光打动。即便戴着口罩,使我看不到浮现在她嘴角的笑容,但她的目光里,住着一个春天。
她带着犯有二十余年血友病的丈夫来到了我们科室,“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他这种情况大多数医院都拒绝,我只有来到这里,希望他的痛能缓解一下……”
说话间隙,她拉开身旁丈夫的左侧裤腿,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只青紫肿胀、破溃处不断涌着恶液的的腿,第一直觉便是骨筋膜室综合征。
对于这类疾病,早期立即切开筋膜减压,便能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面对着凝血功能有很大障碍的他而言,切排减压无疑来说是风险很大的。
他蜷卧在灰白条纹的床单上,眼睛低垂,精神萎靡不振,始终沉默着,只有当我们唤他时,他才会无力地抬起头,用那一双黯淡无光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我们,继而又沉重地闭上。
出于护理的需求,我简单地查看了他的病史,血友病、骨筋膜室综合征、抑郁症等,四十岁的身体像一把干枯柴木,每一次疼痛的袭来,都像一把烈火燃烧着他。
“护士,我是真不愿意他遭罪了,家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可我们仍想试试。我把孩子放在老家,带他来杭州,边打工边治病,我相信大城市的医疗……”她说着,拉起被丈夫不小心踢掉的棉被,眼里满是疼惜。
我抬眼望向他,与他呆滞的目光不经意间相撞,立马向他展露一个微笑,他毫无反应,将身体贴近墙壁,沉默地闭上了双眼。
“医生在帮您联系血液科医生会诊,您别着急,都会好起来的。”言语有时很无力,但某一时刻又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给他治病,我上班时三餐缩减为两餐,能省就想省一点钱……”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再次转头看向病床上的他,他仍旧双眼紧闭,不知有没有听到妻子的话语,或者听到后,内心又是怎样的波涛汹涌。
血液科医生到来,将她叫出,说明了大体的治疗方案。“医生,每天大概要花多少钱?”当听到医生的治疗方案能极大缓解丈夫疼痛时,她眼里有了一丝喜悦,但很快意识到了目前对她来说所存在的最大的经济问题。
“每天至少一两万吧。”
我看着她,眼里的那一丝喜悦之光黯淡了下去,中年的她,细纹爬上了额头,由于奔波忙碌,杂乱的头发还未来得及梳理。
她将头稍稍低下,用手掌捂住了双眼,继而又抬起头,深舒一口气,有一种从无尽的黑暗中解救出来的感觉。“医生,我们治,我想办法筹钱……”
她落寞地走到病室门口,又似乎怕自己消极的情绪影响到病房里的丈夫,在门口短暂停留后,才缓缓走进病室。
之后的几天里,我总能看到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忙进忙出,我们的所有治疗与关心,哪怕只是床边的一句简单的问候,她都会满眼笑意地说感谢。
为丈夫翻身、擦身,或者给予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句鼓励的话语,都使我们对她充满了敬意,又时常被她温暖着,看到了爱情最好的模样。
疾病在治疗中慢慢地好转,当疼痛减轻了大半,我们终于从他冷峻沉默的脸庞察觉到了一丝微笑。他开始活跃起来,也渐渐从原来的沉默不语变得会向我们诉说自己的不适或舒适。
有人说是药物的作用,而我却觉得,亲情与爱情的治疗远比药物的治疗来得温和持久。
“只要人活着,就得有希望……”她笑着说,当看到丈夫一天天打起来精神,之前所遭受的所有不堪与挣扎,似乎都变得不值一提。
人世间所留下的那些伤口、疤痕、疼痛,在时光中,被人类的情感治愈、抚慰。我有幸参与了他们的一小部分人生,也有幸看到了对他们目前而言最好的结果。
她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丈夫,满眼笑意地走出了急诊室,脚步很轻松,与她初来时的沉重、无力,明显不同。他们逐渐走出、走远,消失在初春灿烂的阳光里。
路旁的粉色茶花依旧怒放着,杂乱无章的花枝,被粉色温和的单瓣花蕊点缀着,显得错乱而美好。
我短暂地停驻一会儿,抬眼看到初春里的梧桐有新芽从枝端顶出,有一种顽强的生命的力……
阳光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寂静的红光,一步步向下爬,很轻,也很静,在一片寂静中,有一种声响穿过耳旁——只要人活着,就得有希望……
是啊,只要人活着,就得有希望。
归途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但不包括死亡。教育我们的老师讲疾病、讲护理,甚至讲哲理,他们对“死亡”只字不提。
第一学期的解剖课上,我们的学习是手持人体解剖下来的骨骼,一边惊奇地抚摸各个部位的骨骼,一边慌乱的记忆,讲台旁放着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模型,灰白干净的骨头,正庄严地面向我们。
整个过程,既有同学的面红耳赤、心惊胆战,亦有泰然自若。
进入临床工作后,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穿梭,所看到的,既有好转、治愈的喜悦,亦有无奈放弃的沉重,当然,死亡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课程。
他是一位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
这类疾病的患者,靠着脆弱的血管大口大口喝着暗红的血液。疾病一点一点吞噬身体,也一点一点耗尽一家人的耐性。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长期的支持、对症治疗或找寻到合适的骨髓源,进行骨髓移植,生命的长度便可被拉长。但不是每个生命都会如此幸运,在一场不知输赢的赌局中,生命仿佛是筹码。
初见他时,他还是一副活力四射、干净阳光的大男孩的模样。他是我入急诊科后接触的第一位血液病的患者,心想着年轻、阳光的生命,竟因这样的疾病而使生活缺少了很大的精彩,很是可惜。
几年的时光里,他反反复复就诊于急诊科,壮硕有力的身体日复一日地无力消瘦下去。几年里,岁月给我们的身上都增添了或多或少的变化,但我们对他的态度,一直未变,一直将他视为倔强的大孩子。
他是一个沉默的病人,似乎与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完整交流。
最常见的他,便是用整个棉被裹住自己身体,沉默地将自己安放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者在虚拟的游戏网络世界里,争论、发火、大笑不止,这使我常觉得,网络世界里的他才是真实而完整的。
反复就诊的过程中,一直陪伴他的,是他的姐姐——一位带着浓厚东北口音的女人。
他沉默时,她试着打破寂静的氛围,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听得厌了,偶尔会吼出一声,她便立即安静下来,以慈母般的柔情轻抚他的头;他任性发火时,她会默默地选择闭口不言,然后竭尽所能找到他想吃的食物来讨他欢心……
她包容着他的各种小脾气,也以长姐如母般的情怀宠爱着他。在我们所有人眼里,他因着亲情的滋润,活的自在而幸福。
多年里,他始终没有等来骨髓移植的机会。疾病一点一点吞噬着他高大壮硕的身体,也使得他对生活充满了绝望。他变得更加消极、沉默,治疗上的不配合,也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他是在一个深夜,被120车拉到了急诊室,全身的出血点伴着40度的高热,当他被抬至病床上,响亮的咒骂与吼叫从他那混有刺鼻血腥味的口中传来,他不断撕扯着盖在身体上的棉被,裸露出黯沉的上身。
我们询问他各种状况时,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泼口而出大串的脏话,他的姐姐略有些尴尬地站在一旁,一边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温柔地安抚着他。
当他安静熟睡下来,她静静地坐在床旁,我们每一次过去查看,她都小心翼翼地起身,说声感谢,挂着愁绪的脸庞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窗外一片静寂,弦月悬挂在半空中,投射出的清冷的光。
我们都一度以为他撑不过那个春天,可他活了下来,他姐姐的脸庞,又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连日的细雨,将道路两旁的樟树叶洗的干净明亮,撑着伞在雨中行进,也静静地看着雨水落地开花,随后汇成活泼的流,向低洼处聚集。
这个时候,迎面走来一个高个子的男孩,像极了他,我忽然意识到他有近一个月没有前来急诊科,心底一惊,似乎想到了最坏的结果。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不断对自己说,细雨仍旧飘飘洒洒,一阵清冷的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小刘走了,就在前几天,重度感染……”同事的语气很是平静。
他确实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亲爱的姐姐紧紧握着他的双手,我想,在他姐姐布满泪水的笑容里,他一定还看得见这人间的美好;在疾病没有折磨身体之前,他一定是姐姐面前那个蹦蹦跳跳的小男孩。
她陪伴着他走完了短暂的一生,想必,也读懂了他短暂的一生。
写在最后:耳旁听到过辱骂,眼里看到过不屑,甚至思想中也产生过一次又一次无奈、消极的情绪,有人问,“你为何不用犀利的话语或文字表达?”
我沉默,所有能让人产生疼痛的东西,我都不想写,不值得写。我总觉得,人的生命里,只有温暖、柔和的那一部分记忆,才能持久、醇香。
工作在医院,感受的到生的喜悦、死的悲恸,也有对那些轻视自己生命的行为的不解。与患者相处,我从未问过他们对“生命”二字的理解,但从他们在或疼痛或积极治疗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生命的态度。
曾经与九岁的侄女讨论过“死亡”的话题,对她而言,这个话题很沉重,因此,当她想象到以后的世界里没有了亲人或是没有了自己,她表现出来的惧怕与当初的我一模一样。
时隔两年,当她从自己饲养的小动物的死亡中有了些许感触后,再次问她,她倒多了一份坦然。
春末夏初的季节,各类花朵依旧在盛放,浓绿成荫的梧桐、樟树,生机盎然,也昭显着一座城市的生机。
血腥、药物等各种味道混合的地方,也是脆弱的生命顽强扎根的地方,而我,依旧会在穿梭中,以平凡的血肉之躯,感受疼痛、感受温暖、感受爱……
*作者︱黄敬敬:笔名花开无声,浙江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青眼有加qyyjtcq」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