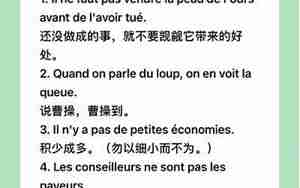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批评家说诸葛亮梦到的是这个人
前言前几天在问答里看到了这个问题: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你也喜欢这几句诗吗?为什么喜欢?
这首小诗是老街读过一遍就再也不会忘掉的诗词作品之一。在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一首小诗或者短短一句话,往往会在不经意之间打动人心。也许当时未必能注意到,但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却会发现,自己能够毫不费力地想起这首诗或者这句话。
至于为什么能够记住,当然是因为喜欢,至于为什么喜欢,有时候却说不出理由。
一、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一首诗这首小诗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至于是罗贯中自己写的,还是如同“滚滚长江东逝水”那样搬运别人的作品就不清楚了。
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 战长江孙氏报仇)中,求贤若渴的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为了表示尊重,宁愿在门外一直等诸葛亮睡醒:
玄德徐步而入,见先生仰卧于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阶下。 半晌,先生未醒。关、张在外立久,不见动静,入见玄德犹然侍立。张飞大怒,谓云长曰:“这先生如何傲慢!见我哥哥侍立阶下,他竟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
云长再三劝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门外等候。望堂上时,见先生翻身将起,忽又朝里壁睡着。【夹批:妙在此时还不便醒。】童子欲报。玄德曰:“且勿惊动。”又立了一个时辰,孔明才醒,口吟诗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孔明翻身,问童子曰:“曾有俗客来否?”《三国演义》
门外三兄弟在苦苦等待,门内的诸葛亮茫然不知,睡了几个时辰后才醒来。睡醒的诸葛亮还没起床,就吟了一首诗: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诗中说:“在这一场大梦中,谁是那个最先醒来的人呢?我自有领悟。”然后按下不表,转而写景,春天里,我在草堂睡开心了,窗外是渐落的夕阳.........不尽之意,却在言外。
这首小诗的诗眼在第一句:大梦谁先觉?这是一场什么梦呢?诸葛亮又梦了什么呢?
二、大梦谁先觉 先生何所梦?苏东坡《西江月》月有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自己的人生如同一场梦,窗外的世间万物、红尘中的纷纷扰扰也是一场大梦,在这场大梦中谁是那个最清醒的人呢?是我诸葛孔明呀。
不过诸葛孔明到底做了个什么梦呢?喜欢解析的人把孔明的梦也分析了一遍。
1、庄子的梦
有人说这是道家对人生的一种看法。在《庄子·齐物论》中说过:\"
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人在梦中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呀,梦中还请人为自己做的梦解梦,在醒来之后,才发觉自己是在做梦。人在了悟大道后才明白自身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的人则自以为清醒,好像什么都知晓。其实....
这一段让老街想起了迪卡普里奥LeonardoDiCaprio主演的电影《盗梦空间》。
诸葛亮是把自己当作庄子吗?
2、孔子的梦
还有人说,这是孔子之梦,《论语·述而篇》中说: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南宋)朱熹说,孔子年轻时,一直想效仿辅佐周武王的周公,所以孔子应该梦见过周公。等到孔子衰老了以后,就没有效仿周公的精力了,所以也就不在作这样的梦了。因此孔子说:“我衰老得很厉害了,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程颐说,孔子即使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了。
孔子盛时,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其老也,则志虑衰而不可以有为矣。盖存道者心,无老少之异;而行道者身,老则衰也。”
诸葛亮是孔子之梦吗?
3、孔明的梦
对于孔明的梦,清朝的毛宗岗品三国时说:
夹批:或问先生何所梦?予曰:仲尼之梦,是梦周公;孔明之梦,必是梦伊尹。
毛氏说,孔明不是庄子之梦,也不是孔子之梦,而是自己的梦,梦到的是伊尹。伊尹协助商汤灭掉了夏朝。
孔明常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但是自己却一直也没有找到可以效力的英主。其实从他和刘备“三分天下”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他自己心目中一定有了选择,所以他听说刘备来了的消息反映还是很开心的。
孔明吟罢,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夹批:妙在童子不即通报,待先生先问。 客曰“俗客”,太难为人。能来此地者,其客亦不俗矣。】童子曰:“刘皇叔在此立候多时。”孔明乃起身曰:“何不早报!尚容更衣。”【夹批:还要更衣,妙。】遂转入后堂。又半晌,【夹批:又是半晌,妙。】方整衣冠出迎。
三、毛宗岗为何说梦到伊尹而不是周公呢?毛宗岗没有说诸葛亮梦到周公,而是说他梦到伊尹,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书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个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人物。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诸葛亮生于出生在琅邪郡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望族。 但是社会地位仍然远远比不上辅佐周武王的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从家庭地位和经历来说,周公天生就具备的条件是诸葛亮无法相比的。
而伊尹出身低微,据说父母都是奴隶,他自己是作为陪嫁奴隶的身份被汤王招致麾下的。虽然诸葛亮没想伊尹那么惨,但都希望被明主求贤,因此毛宗岗说诸葛亮梦到的是伊尹。
四、平生我自知,知道什么?诸葛亮睡起来以后,和刘皇叔畅谈天下大事,就如同今天的ceo面试销售总监一样,来,谈谈市场形势吧,作个市场分析出来。于是诸葛亮侃侃而谈: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计。曹操比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还拿出一张西川的地图来,指点之间,步入天下三强的宏图伟业如在眼前。孔明一席话,说得刘备心花怒放。
后人点评道,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隐士呢?连攻取的目标地图都预备好了。毛宗岗说,真不知道诸葛亮什么时候搜集到的这幅地图,可见他的“高卧”,并不是真正的睡着觉呀。
罗贯中跟上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五律写道:
南阳诸葛亮,高坐论安危。谈笑分三国,英雄镇四夷。
孙权承地利,曹操得天时。独许刘玄德,西川创帝基。
结束语从毛宗岗的品读来说,这首小诗背后隐藏的含义和这一段小说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孔明怀才不遇却颇为自负,所以会有“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说法。
我们不去深文罗织,单单看这一首小诗也颇有情趣。前两句是对于人生的一种看法,显示了对于命运的自信,后两句是一种暂时的满足(小确幸),用写景收尾,意蕴幽长。
三国中的很多诗词是引用了前人的作品,不知道这首小诗是谁写的。也许写这首诗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想法,但是放在这部小说中的语境中,就会生出许多暗喻来。
古人写梦的诗词作品太多了,老街味道比较喜欢苏轼的这首《西江月》,不过这首词相比而言臃肿了一些、也沉重了一些,不如“大梦谁先觉”那么空灵可爱: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诗为心声,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诗。不同的语境,也是不同诗。
@老街味道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坐的意思解释成“因为”对吗?
某些诗词专家讲起诗词滔滔不绝 为何见不到比较有分量的诗词作品
苏轼念奴娇赤壁重韵了吗?爱好诗词的你赞成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呢?
豆蔻梢头二月初 从“豆蔻”2字看出杜牧诗中少女的真实身份
此人被称为孔明转世,镇守蜀地21年,击破吐蕃48万大军,无人能敌
安史之乱,使唐朝由极盛转向衰落。在国内,藩镇割据,各地军阀叛乱不休,朝廷威严扫地;在国外,吐蕃、南诏等国在边境肆虐不止,由于国力虚弱,唐朝不断丧师失地,整个河西走廊都被吐蕃所攻陷,首都长安已然岌岌可危。
吐蕃人攻占河西走廊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富庶的西蜀。在他们看来,只要攻占蜀地,吐蕃便能对唐朝的核心——关中地区实现合围;只要攻占蜀地,灭亡唐朝绝不是空想。因此,吐蕃联合南诏对蜀地展开了夹击,唐军屡战屡败,丢失了不少土地,无数百姓沦为吐蕃、南诏人的奴隶。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叫作韦皋的将领站了出来,他用18年的时间击败了外来入侵者,保证了一方安全。在西蜀百姓眼中,韦皋就是诸葛亮转世。
韦皋本是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出生之时,其父曾找相士给他算命。相士看了他的面相后感叹,这人未来必然是将相之才。韦皋出生后一个月,韦家大摆宴席为他庆生,结果一名相貌丑陋的胡人和尚不请自来,大咧咧地坐在了酒席上。韦家的仆人见胡僧如此无礼,都十分气愤,于是让他坐在院里的破席上。
不久后,奶妈抱着婴儿走了出来。就在这时,原本端坐在破席上的胡僧,霍的一下站了起来,他快步走上台阶,然后向婴儿跪下并痛哭流涕道:“诸葛丞相,我们好久不见,您终于回来拯救西蜀百姓了!”韦皋父亲问胡僧:“你说我儿是汉丞相诸葛亮?”胡僧回答:“正是!此小儿是诸葛亮转世。诸葛亮曾给过蜀人很多恩惠。如今他又降生在世上,将来必为蜀门之统帅。”对于胡僧的话,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于是韦皋父亲专门给儿子取了“武侯”的字号。多年后,胡僧的预言果然应验,韦皋真的成了西蜀的统帅,并在那里镇守了21年。
韦皋长大后,他博览群书,终于考中了秀才。一次,他参加了剑南节度使张延赏举行的酒会。张延赏的妻子苗氏很会看相,一眼便看中了英姿勃发的韦皋。她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待字闺中,于是她立即建议丈夫,将女儿许配给韦皋,并说:“此人相貌不凡,未来必然是将相之才”。张延赏一向看重夫人的识人之能,于是同意了这门婚事。然而两三年过去了,张延赏并没有看出韦皋有什么过人之处,相反此人还自命清高,一身的臭脾气。于是,张延赏从不给韦皋好脸色看。
在张府,韦皋受尽了冷遇,连奴婢都敢欺负他,只有丈母娘苗氏和妻子张氏对他好。受尽欺凌的韦皋决定离开张府,不再受岳父的鸟气。于是,韦皋向张延赏辞行,准备去关中成就一番事业。张延赏早就看韦皋不爽,听说他要走,自然喜不自胜。就这样,韦皋带着妻子一同离开张府,并在外闯荡。
最终,才华卓著的韦皋得到了唐德宗的赏识,他凭借自身的军政才能,不断在对抗吐蕃和国内叛军的战斗中立功,最终步步高升。兴元元年(784年),韦皋升任金吾卫大将军。仅仅一年后,韦皋官拜检校户部尚书,代表朝廷入蜀,接任剑南节度使,正好接替他的岳父张延赏。张延赏见女婿出人头地,感到羞愧难当,无脸再见韦皋。简单交接了职务后,张延赏便立即离开了成都,一刻也不敢多留。韦皋回到府邸,将往日欺负自己的奴婢全部杀死,并丢进蜀江。
韦皋接任剑南节度使时,西蜀的局势很危急,吐蕃和南诏从西、南两面夹击,唐军很难抵抗。韦皋一方面整兵练武,抵御外敌入寇;另一方面,他秘密派出使臣前往南诏,准备瓦解吐蕃与南诏的同盟。南诏本是唐朝的属国,唐玄宗年间无端遭到唐军进攻,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投靠了吐蕃。南诏随吐蕃攻打唐朝,其实是非常不情愿的。韦皋发现吐蕃、南诏一同攻打西蜀时,从来都是南诏人在前,吐蕃人在后,很显然吐蕃是将南诏人当炮灰使。因此韦皋认为,自己必然能将南诏拉到自己一边。
公元787年,韦皋率军大破吐蕃、南诏联军,斩首、俘虏敌军近10万人。吐蕃人认为战争失败,都是南诏人的错,两国盟友关系逐渐破裂。见此机会,韦皋趁虚而入,不断给南诏王异牟寻陈说利害,并终于在788年说服了南诏,使他们重新成为唐朝的属国。公元793年,异牟寻趁吐蕃不备,联合韦皋,突袭其后方,连破十六城,击杀吐蕃十多万兵力,俘获贵族、将领更是不计其数。
从此以后,西蜀战局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以前是吐蕃、南诏夹击唐朝,如今反而变成唐朝和南诏联合攻击吐蕃,由此以后吐蕃在西川的势力一蹶不振。韦皋治理蜀地21年,多次出师击胡,共击破吐蕃军队48万,擒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150人,斩首5万余级,获牛羊25万头,缴获器械630万件,其战绩之辉煌,当代将领无人可比。即使和卫青、霍去病相比,也毫不逊色。最终韦皋被朝廷封为南康郡王,加太尉之职。公元805年,韦皋去世,时年61岁,朝廷追赠太师,辍朝五日,谥号“忠武”,与诸葛亮的谥号一模一样。
那些创下销量数十万册记录的文学期刊,将何去何从?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花城》丛刊第1期封面,图为徐匡木刻作品《草原诗篇》。
在纸质办刊时代,作家与期刊编辑的关系,就像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的作家与图书编辑一样。在该剧中,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
在那时候,文学与文学期刊、作家与文学编辑的命运之紧密也显而易见。比如,在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正是因为一批文学期刊的诞生或复刊,才产生了一群影响深远的作家。他们同样成就了文学期刊的地位。两者共同参与了人们审美、观念的更新进程。
阅读在变革,我们都得革新。而在内容上,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一代作家的先锋性无论是否在减弱,就像朱燕玲所说,文学“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因而,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
现在被人们所热衷谈论的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实际上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中国文坛诞生了此后影响深远的众多文学和文化期刊,包括《十月》
(1978)
《钟山》
(1978)
《花城》
(1979)
《当代》
(1979)
和《读书》
(1979)
等等,由巴金和靳以在50年代创办的老牌文学杂志《收获》也在1979年复刊。
作家往往最早嗅到社会坚冰解冻的气息。在短时间内,文学期刊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兴起,它们为当代文学的萌芽壮大提供了阳光和沃土,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文学期刊被读者所认识和接受,来自西方的实验性写作,也被中国作家们“活学活用”,以“先锋文学”的名义在文学期刊上轮番登场。
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
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格非、毕飞宇、张抗抗、叶兆言、李敬泽、林白、李洱、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
“先锋性”是众人在评价《花城》杂志时重复次数最多的关键词,也是《花城》区别于其他刊物的重要特点。作家们谈到,许多颇具实验性的作品,在其他地方发表不了,但是《花城》勇于冒险尝试。《花城》也敢于力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比如毕飞宇等人的处女作都发表于《花城》,至今,每期仍设有“花城关注”栏目,致力于发掘新生代的写作者。
《花城》的四十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期刊的一个缩影,文学期刊曾牢牢掌握着文学市场的话语权,而今,尽管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但曾经的地位已然被自媒体和网络文学所挑战,那么,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关于《花城》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期刊在未来的命运,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如今,她主持下的《花城》面临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挑战,我们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的共同命运。
朱燕玲,《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
01
“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
新京报:《花城》于1979年创办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作为一本纯文学期刊,它一直带有突出的先锋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而且至今依然致力于发掘优质的新生代作家,这种先锋性或许也是《花城》从众多文学期刊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
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
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她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她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她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她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
1979年,《花城》丛刊第4期封面,林墉画作《春》,秦咢生题字。《庐山恋》发表于这一期。
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然抱有疑惑的时候,《花城》率先刊发了改革开放代表之作《庐山恋》和《“雅马哈”鱼档》。这两部作品随后拍摄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庐山恋》当年的银幕第一吻,可谓惊天动地,成为青年男女的爱情典范,创下连续放映6300多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雅马哈”鱼档》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广东个体户,他们敢想、敢闯、敢干,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从不起眼的“街边仔”,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展现了广州城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缤纷与活力,热播后轰动全国。
《庐山恋》(1980)剧照。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到冷遇、多次被退稿的时候,《花城》力排众议,对其予以充分肯定,在1986年第6期全文刊发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并在刊发后为其举办了一个大型作品研讨会,还将第四届花城文学奖授予路遥。90年代后,《花城》接过先锋文学的旗帜,敢于推陈出新,成为先锋文学的重镇与青年作家的摇篮,以及到今天提出“文学策展”办刊理念,都是《花城》敢于立于潮头的表现。
新京报:《花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与者,时代在变化,文学的主题、叙事方式、审美标准也都在不断变化,你如何描述这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图景的变迁?以及如何评价《花城》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朱燕玲:《花城》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也和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同构,她既是众声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声部。《花城》首发过许多在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地位的作品,如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白银时代》、顾城《英儿》、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王蒙《这边风景》、章以武与黄锦鸿《“雅马哈”鱼档》、残雪《新世纪爱情故事》、莫言《父亲在民伕连里》《我们的七叔》、王安忆《考工记》、韩少功《修改过程》、迟子建《树下》、阿来《行刑人尔依》、阎连科《日光流年》、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欧阳江河《泰姬陵之泪》《凤凰》、王朔《给我顶住》《谁比谁傻多少》、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枕黄记》、刘亮程《捎话》、李洱《花腔》等等。
《花城》杂志1997年第1期刊登池莉、陈染、张承志、史铁生等作家文章。
它们成就了作家个人,也成为了文学史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花城》起的作用,是在作家们刚刚起步的时候,给他们有力的支持,给他们舞台。
比如,当王小波在文学界还籍籍无名的时候,《花城》就连续刊登他的作品,又比如,林白、陈染、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吕新、北村等的成名,皆是从《花城》起步。
同样,《花城》为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新生代、后先锋写作也提供了重要的阵地。优秀的文学期刊往往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风骨,它折射了时代语境的变化,也通过刊选的作品展现出中国作家的文学姿态和思想表达。
1989年,珠海白蕂湖度假村,《花城》编辑部与作家莫言(右四)等人合影。
02
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
新京报:四十年来,《花城》的办刊风格、选文标准是否有作出过调整?你认为,一本文学期刊,哪些东西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哪些东西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朱燕玲:一本刊物的风格既体现着时局和文坛大势,也明显体现着主编个人的审美趣味。《花城》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多任主编,从办刊风格和选文标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丛刊时期
(1979年第1期到1980年第4期)
,丛刊时期的七期本着“解放思想、博采广收、新鲜活泼”的办刊宗旨,奠定了《花城》的发展基础。此时的《花城》无疑秉持了“立场高于名家”的策略,努力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冲破禁区,努力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栏目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开放性。
《花城》丛刊时期第7期封底:何岸,油画。
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达成一致,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借助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设置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等栏目,推介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这在全国刊物中具有开创意义,率先打开了港澳台和外国文学的窗口,具有非常鲜明的“开窗”意识。
进入90年代,杂志开始转型,更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种自觉的文本意识。坚持纯文学,扛起先锋旗帜,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个阶段的《花城》,以“先锋守护者”的角色为90年代文学发现了大量重要作品,深度参与了“90年代文学”的建构与呈现。90年代《花城》小说栏目有一种很强的艺术判断的勇气,乐于发表新人力作。潜质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它考验着编辑的艺术眼光和勇气。同时,90年代以后的《花城》,成为不同代际的作家形式实验的重要文学基地。
新世纪后,应对新媒体时代,拓展思路,提出“文学策展”和多元融合的办刊理念,勇当文学现场的“报信人”。以“文学策展”的思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促使文学期刊成为整个文学生产、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
一个刊物的表现方式可以与时俱进,而内在的精神与编辑立场需要持之以恒。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而对内容的追求,我们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即文学性、艺术性为第一要义。
新京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纯文学热退潮、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类型文学异军突起,文学的读者群体在发生变化。作为文学期刊主编,要如何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花城》未来会刊登科幻小说吗?
朱燕玲:纯文学从走下神坛到今天的小众化,是一个社会从非正常走向正常的历史必然,办刊者既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需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文学现场的动态,研究并且取我所用。
《花城》一直很关注新时代的语境变化,文学的方向就是青年人的方向。所以,必须了解青少年的趣味和爱好。2016年,《花城》与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牵手,推出“域外视角”专栏,分析解读中日韩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东亚地区未来一代的文学表达。同时,又与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
(邵燕君及其博士研究生团队)
携手合作,推出了“特约”栏目,从网络文学、游戏、宅文化、虚拟社会、爱豆文化等文化共性点切入,解读当下青少年的文学语境与精神归属。
从2017年开始,又重点推出“花城关注”栏目,融此前“花城出发”栏目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栏目的实验性为一体,邀请著名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寻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发掘更多文学新生力量。栏目突显前瞻性眼光与国际视野,致力拓展文学的边界,强调关注青年作家与新锐写作,关注跨界写作和跨界文化艺术,同时关注文学文本的各种创新及可能性,三年来好评如潮。
“花城关注”突出问题意识,每期一个主题,三年来做了“影视”“剧本”“故乡书写”“科幻”
(人工智能)
“摇滚”等文学热点。
所以,《花城》在2017年就刊发了科幻小说专辑,已陆续推出过郝景芳、陈楸帆、飞氘、宝树、糖匪等青年科幻作家的新作,还在南京先锋书店开过专门的科幻研讨会,也即将推出因此而生发的“超新星”系列科幻作品单行本。科幻作家们的创作及出版形态,对传统作家有很好的启示。
新京报:随着发表和出版渠道的增加,传统的文学期刊不再拥有文学发表的垄断地位,文学期刊在文学市场中的话语权也在削弱,总体而言,文学期刊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近年来,传统文学杂志的“触网”转型成为大势所趋,《花城》是如何适应阅读和传播方式的转变的?又遇到了哪些挑战?
朱燕玲:近年来,《花城》除了传统媒体的常规化宣传,同时加大了新媒体平台建设和推广力度,比如,实现纸刊的网络销售,上线电子期刊,开设杂志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们还和出版社一起,不断尝试进行数字化转型,包括电子版权的分发、对接影视版权、加强与读者的网络互动等,并打造了“爱花城”文学平台,试图建构一个覆盖文学阅读、社交互动、有声课程、比赛信息、稿件修改等功能的生态闭环。此外,还注重办刊与活动的结合,以“花城雅集”“花城笔会”“花城文学奖”等活动来扩大影响力。
这个过程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经费的可持续性、人员的专业程度,还包括如何将影响转化为人气,将人气转化为效益,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探索。
而仅就传统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版权问题。长久以来,纯文学期刊的版权约定俗成为作者默认授权,即作者投稿默认为授权期刊刊用,并没有像图书出版那样形成合作签署制度,而版权法又明确规定期刊不拥有作品版权。如此,就给纯文学期刊的数字化和版权再利用带来授权不明确的难题。也就是说,期刊的大量投入:办刊经费、稿费开支等等,得到的只是一个作品的首发权。
03
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
电影《天才捕手》(2016)讲述了作家托马斯·沃尔夫被文学编辑麦克斯·珀金斯看中并推出的故事。后者也曾发掘过菲兹杰拉德、海明威等作家。
新京报:你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三十余年,如何看待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编辑被誉为“天才的捕手”,也被嘲讽(或自嘲)为“为他人作嫁衣裳”,你如何看待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收获》主编程永新曾说,“编辑工作与写作是有矛盾的,《收获》编辑部的传统也不鼓励编辑写作”,你是否同意他的“矛盾说”?
朱燕玲:作家和编辑常常是朋友和知音,尤其是发表作家处女作或早期作品的编辑,常被作家认为有知遇之恩,而编辑也会为发现了心仪的作品而倍有成就感。编辑工作的价值就在发现和推广。
我也很认同程主编的说法。他指的显然是全身心投入的编辑,而身兼二职的人也比比皆是。编辑工作有很大的弹性,一本杂志如果只求填满版面,轻而易举;而要精益求精,则是无底深渊。而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上世纪90年代,《花城》杂志编辑部。左起:文能,侯卫红,杜渐坤,刘钦伟,朱燕玲,陈文彬。
新京报:《花城》的作者群有很多知名作家,也有一些文学新人,你挑选作者和作品的标准是什么?三十多年来,你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有过变化吗?
朱燕玲:我挑选作品的标准很朴素,就是单纯看作品,名人和无名者基本一视同仁,比较“铁面无私”,“不太会做人”;同时我不推崇也不排斥什么具体的流派,它可以是现代的,也可以是传统的,我的谱系很宽,能打动我就行。可是,对一个以看稿为职业的人来说,要被打动,谈何容易。它不仅有对技术的要求,还有对“三观”的要求。
新京报:麦克斯·珀金斯曾说,“编辑可能只是让一部作品变得不一样,并不一定会让它更好。”当编辑和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你处理的原则是什么?编辑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
朱燕玲:当编辑与作者的意见发生分歧时,我们首先会提出非常真诚的意见,在最大程度保留作者风格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硬伤部分,或者是情节、人物设置可以更好的处理建议。如果作家无法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也会尊重作家的意见,如果觉得是小瑕疵,也就“文责自负”了,如果觉得有损全局,则只好遗憾不用。但我们遇到更多的情况是作家希望我们给出更多的修改意见,他们也很感谢我们提出的意见。编辑可以说是作家新作的第一读者,有义务跟作家一起,提高作品的完成度。
一个优秀的文学编辑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摆渡人,既要站在作家一边,也要站在读者一边,但更要站在历史一边,筛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这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了解最前沿的创作动态和作品,甄别优劣,预判趋势;编辑还应该有亲和力,有包容心,能团结作家,广集人脉。
04
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
新京报:《花城》经常组织文学笔会和研讨活动,你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今,严肃的文学批评为何式微?
朱燕玲: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当然,说好话容易,说坏话难,严肃文学批评的生存状态,其实就是社会包容性的一个折射。
现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貌似一团和气,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回顾八九十年代,我们还是有过真正的批评,研讨会也曾会争得面红耳赤,一些诗歌会议甚至会争论得打起来。
《花城》部分封面,该刊发表了王蒙、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刘震云、王小波、张承志等人的作品。
我想,一个原因是,现在的研讨会基本是机构组织的,比如出版社。出版社组织的目的是销售。而当年,文学书不愁卖,研讨就真的是为了研讨。此外,当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说话自然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己。双方都有太多的羁绊——在快节奏的社会里疲于奔命的人,再也无力较真了。
新京报:“花城关注”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锋性是否在减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关注?
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用心扶持,严格要求,是我们一惯的态度,我们不愿意因为年轻就对他们降低文学的审美标准。而“先锋性”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文学的潮流是流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如果仅从技术上继承所谓“先锋性”,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20多年来,“先锋性”已经变成寻常元素融入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之中。所以,我们期待青年作家的,是更新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
虽然90后作家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却又是模糊的,也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他们自由而分散。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众声喧哗是必然的结果。
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一个个更有个性的作家脱颖而出,即便是一个“小时代”,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寻找这样的新人。
作者:徐伟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