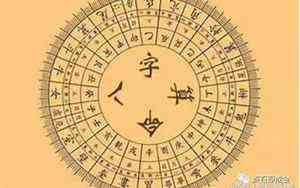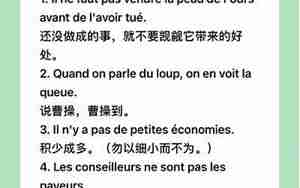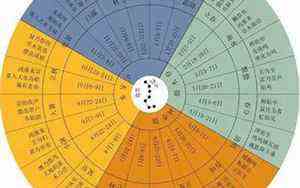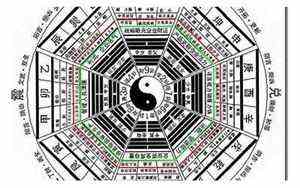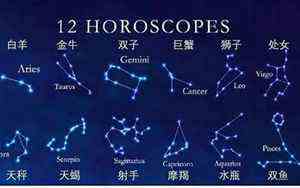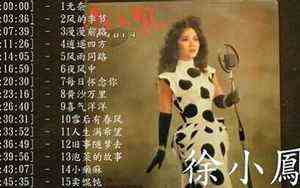
「每日五词」20180103,每天来挑战一下你的认识?
【每日五词】《荀子·大略》:“夫尽小者大,积微成著,德至者色泽洽,行尽而声问远。”
駓駓
敦脄
觺觺
猇声狺语
佐鬭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个人学习,容易掉入坐井观天的坑,欢迎正在学习各类知识的朋友,咱们一起学习,分享经验,哪怕每天分享一个概念、一个知识点、一个经验,咱们都能彼此为对方节省时间,加速进步,毕竟每个人的收获、见解都不一样。欢迎私信,广交学友。
王逸
1、駓駓
[ pī pī ]
详细释义
趋行貌。
《楚辞·招魂》:“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 王逸 注:“駓駓,走貌也。”《后汉书·马融传》“羣鸣胶胶,鄙騃譟讙” 李贤 注引《韩诗》:“駓駓俟俟,或羣或友。”
2、敦脄
[ dūn méi ]
详细释义
厚背。
《楚辞·招魂》:“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 王逸 注:“敦,厚也;脄,背也……言土伯之状,广肩厚背。”
3、觺觺
[ yí yí ]
详细释义
角锐利貌。
《楚辞·宋玉<招魂>》:“土伯九约,其角觺觺兮。” 王逸 注:“觺觺,犹狺狺;角利貌也。” 明 陈子龙 《寄献石斋先生》诗:“蛟龙觺觺黄沙卧,日月冥冥青枫秋。” 清 褚人穫 《和咏戏具》:“润泽耳真同溼溼,峥嶸角亦类觺觺。”
引申为角斗激烈。
唐 王无竞 《北使长城》诗:“六国復嚣嚣,两龙鬭觺觺。”
突出貌。
清 钱谦益 《通奉大夫湖广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公墓碑》:“公方覊贯,头角觺觺。”
4、猇声狺语
[ xiāo shēng yín yǔ ]
详细释义
形容恶言叫骂。
《红楼梦》第八七回:“妹生辰不偶,家运多艰,姊妹伶仃,萱亲衰迈。兼之猇声狺语,旦暮无休。”
5、佐鬭
[ zuǒ dòu ]
基本释义
助人争斗。 《隋书·李德林传》:“佐鬭嫁祸,纷若蝟毛,曝骨履肠,间不容礪。”
你想和我们一起成长么?每天5个词语,已经坚持分享35天,155个词语,一年之后1825个词语,三年之后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共同学习词语的组织,你要早点参与么?
每天更新,每日五词、每日人物。
点滴积累,积微成著;广交学友,相伴成长。
萱草和康乃馨,哪一种花更能代表母亲?
“忘忧之花”萱草和“温馨之花”康乃馨的文化碰撞
文:花木君
母亲节,西方传统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节日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现代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以法律形式命名。
我们国家是最注重孝道的国家,然而并没有固定的母亲节,国内呼吁成立母亲节的声音一直很多,有的提倡女娲,有的建议孟母,有的更是附会一些故事传说,然而不少都带有地域宣传的性质,并非出于公心。有的更是以已经有三八妇女节和五四青年节,再成立母亲节和父亲节似乎节日过多,如果真想成立,可以借鉴美国,不固定日期,而选择在某个礼拜天比较适宜,可以避免放假调整之类的繁琐程序。
没有母亲节这点固然略有遗憾,然而个人认为其实不必搞那么多形式,毕竟,孝敬父母是从内心和行为上的孝敬,而不是非要搞个节日走走形式。当然,有母亲节、父亲节自然是好事,如果能从法律的形式予以颁布,可以说皆大欢喜。
毋庸置言,灿烂的中华文明文化里面,孝道是核心,一直贯穿着中华历史到如今。古人敬爱父母、孝顺父母、侍奉父母的优秀传统一直代代相传,就拿代表父母的花木来说,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尊敬父母,并分别以“椿”、“萱”代表父母,椿指椿树,萱指萱草。在《庄子》的名篇《逍遥游》中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后来就借用此典故,用“椿”比喻父亲,希望和椿树一样长寿。而萱草的记录更为久远,在古代诗歌集《诗经》里边多次提到,其中《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意思是我到那里弄到一支萱草,种在母亲堂前,忘记想念儿子带来的忧愁呢?,后来就用萱草来代表母亲,即可避讳又高雅,更代表了一种尊重敬爱之意,因此,萱草又叫忘忧草。
萱草除了叫忘忧草,还有一个名字叫宜男草。据传说当妇女怀孕时,在胸前插上一枝萱草花就会生男孩,晋代《风土记》云:‘妊妇佩其草则生男’,故称宜男草。
古代关于萱草的诗词俯拾皆是,大多是咏叹母亲和取其“忘忧”之意。比如汉代蔡文姬归汉,母子离别时所做的《胡笳十八拍》有:“我与儿兮各一方,日东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随兮空断肠,对萱草兮忧不忘。”。魏晋“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有“世无萱草,令我哀叹。”诗句。南北朝学者宗懔有“望望无萱草,忘忧竟不忘”。唐代诗人聂夷中的《游子吟》云:“ 萱草生堂偕,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 ”。等等,诸如此类的咏叹萱草的诗词还有很多,不少都是希望母亲欢欣,能够忘记忧愁之意。
而作为西方母亲节的花卉代表,则是康乃馨,在我国被称为石竹花,是一种非常普通也比较常见的花卉品种,名花谱上向来没有它的位置,更别说十大名花了。但是康乃馨在国际上却是久负盛名,作为世界传统四大切花月季、菊花、香石竹(即康乃馨)、唐菖蒲(即剑兰))之一,位居全球花卉交易量的前列。
康乃馨虽然没有被列为名花,但是古人还是对其赞誉有加,比如诗仙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一》里:“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唐朝诗人陆龟蒙的《石竹花咏》:“曾看南朝画国娃,古萝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钱斗,买却春风是此花。”。古人对石竹的欣赏主要在于花色倩丽秀美,常被作为服饰图案印染在服装上。
康乃馨是西方国家赠送母亲的最多见的鲜切花,花语代表着爱、尊敬和真情。并且由于康乃馨是西方名花,销量巨大,几百年来许多园艺工作者不断改良培育选种,如今康乃馨的品种近千种,其中不少母本就源自我国。
而作为国人母亲象征的萱草,由于我们园艺技术相对落后,开展研究晚,再加上国人的习惯并不是送花,而是种花,因此在萱草选种培育方面比康乃馨要少得多。国内萱草原生种有8种,近些年引进了不少新品种,大多为园林公园栽培,很少作为鲜切花推向市场。
萱草花花朵硕大,花色美丽,花期长,文化底蕴深厚,包含着对母亲的敬爱、希冀忘掉忧愁的美好愿望,如果精心培育选种,势必成为另一种风靡市场的鲜切花花卉品种。
忘忧之花萱草,温馨之花康乃馨,不管东方西方,不管国人洋人,都是代表这对母亲的敬爱之心,因而,赠送母亲什么花卉其实到不是特别重要,最主要的是时时刻刻、念念不忘父母的养育恩情,随时尽最大努力回馈给他们真情和孝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方显示人类的伟大。
2019-59易花得木
椿树之心
作者:杜怀超(中国作协会员、江苏作协签约作家)
有些记忆,是哪怕河流也带不走的,像刺隐秘于身体内部。比如门前的那两棵椿树。
在我家的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椿树,另一棵还是椿树。这完全再现了鲁迅笔下“两棵枣树”的意象,不同的是,这两棵都叫椿树的树种,从科学角度辨析,一棵叫臭椿,又叫樗;一棵叫香椿。在独木村人的眼中,它们都叫椿树,就像所有的树木一样,立于大地之上,用抡起锄头的姿势舒展枝叶,野蛮而粗糙地活着。
我清晰记得它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我说的是臭椿。虽然她没有芬芳馥郁的名字,枝叶气味也称得上难闻,可丝毫没有自卑、堕落或者自暴自弃,它用参天耸立、虎背熊腰的形体展现自己积极向上的雄姿。我实在想象不出,一棵树苗如何在与生俱来的缺陷中,忍受孤独寂寞,于绝境里完成自我生长,抵达雍容华盖般的胜境。到底是哪天特意栽下,还是从飞鸟的口中落生?我把疑惑抛向父亲,他用沾满泥土的手,抓了抓脑袋迷茫半天,然后咕噜出一句“我也搞不懂”。父亲对它漠不关心。这也难怪,一个终日在大地上弯腰劳作的人,跟一棵木讷的树有什么分别?谁不是在莫测的天气和不变的四季里勤恳一生?父亲把目光更多的倾注在旁边那棵香椿树上。
香椿,其实也处于难以描述的尴尬境地。它固然没有刺鼻的气味,可是它有鱼鳞般的皮肤。伸手在香椿皲裂的树皮上轻轻摩挲,就会有大片干枯的树皮簌簌脱落,像是揭开一个人愈合不久的伤疤。碎片斑驳脱落,香椿完成某种涅槃与重生。
两棵椿树,声势浩大地矗立在门楣两边,村庄不远处,是守护它的长堤和昼夜不停的流水。
那棵臭椿是父亲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棺木预备的。尚在壮年的父亲,把身后事提前筹划,原以为无限的时间陡然有了清晰的终点。据当地风俗,活着的人备棺木,可以添寿,属于喜事。独木村的成年男人都早早地开始谋划身后事,把生命牵系在一棵树上。我对独木村人的想法产生浓厚的兴趣。确实,生命一旦与树结缘,何止百年?这是对生命长寿的祈祷与祝福,还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的通透注解?父亲选择这样一棵特立独行的臭椿,再苦再累的日子,都有了奔头。
椿树,尤其是那棵臭椿,堵在我的胸口,日日见到它,总要躲着它,绕着它,不敢再以正眼打量它。那股隐匿着神秘的气息,不禁让我想到独木村的社树。
不是所有的树都叫社树。对于独木村而言,社树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以一棵树或一户人家为起点,沿着河流的走向,开枝散叶,葱郁蓬勃,形成密集的树林和村落。以树为巢,以树为生,树木是村庄的保护神。从树叶、树枝、花朵、果实、树干到树根,有的进入灶间,化为生活资料;有的走进锅釜,成为人们口中之粮;有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产中,被制作打磨成农具。农具是连接人类与大地的脐带。人们用扁担承载货物,用大车运输粮食,用连枷脱打稻穗,用水车灌溉农田,用纺车纺线织布……
独木村的社树,一棵古老沧桑、形神磅礴的树,守卫在村子里,仿佛成为对接历史与现实的甬道,追溯着昔日树木成林的哲理。大地承载五谷,树木负载万物。树木是站起来的土地,它在生长一切,比如木屋、木船、农具和无垠的旷野。诗人纪伯伦说,树木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诗行。一棵树苗,努力靠近苍穹,长成参天大树。天空是虚,大地是实,谁不被天空的瑰丽折服?人类固然够不着天穹,却可以以一棵树的形象,立于天地。
独木村有过许多社树,如梓树、柏树、松树、槐树、栗树;而父亲只把家门后的两棵椿树视为社树。我对椿树敬畏的方式之一,就是“抱树”。我个头矮,父亲经常命令我晚上临睡前,必须出门去抱一抱椿树。父亲希望椿树的高大魁梧,成功地嫁接到我身上,或把那道看不见的神灵光亮,植进我的肉身里,以此祈祷我也能像椿树一样出息。昏黄的灯光里,父亲看我抱树回来一身树皮碎末,呵斥道,又抱错了?父亲的意思是我抱了旁边的那棵结满层层疮疤的香椿树。或许父亲是教育我,要像臭椿那样顶天立地地活着,而非如香椿那样,早春一到,它就会在枝头的末端,裸展出一簇簇细嫩的叶子,成为舌尖上的诱惑。
没有人可以阻挡时代的洪流。城市化进程席卷村庄,作为独木村的最后一批搬迁者,父亲母亲即将搬走,独木村也将真正地消失。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收拾家具、农具还有锅碗瓢盆时,父亲却一下子来了脾气,不肯搬了。父亲的意思是,一根木头一根木头垒起来的家,住了几十年突然要走,心里空落落的,像掉了魂。父亲从左厢房跑到右厢房,再从右厢房跑到左厢房,来来回回多少次,凝视着满屋子的农具,满心不舍。他停在椿木棺材板旁,神情落寞,不住地唉声叹气。没有文化的父亲,在椿木棺材与生死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挣扎?后来,我在一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古时把父亲称为“椿”、母亲称为“萱”,“椿萱并茂”常用来形容父母健康长寿。如此,以椿木为棺,生者,从沉重悲痛中走向轻盈;而死者,则在万物轮回里沐浴芬芳。
父亲肯定不知道关于树木的诸多涵义。我猜测他对树木的不舍,或许是人类传承下来的文化里的潜意识?以木为家,“暮栖木上”,城市对他来说,抵不过门前那棵椿树,这是他百年之后的安身之物,也是最后的归处。
午夜梦醒。有风吹过,我隐约看到枝叶在远方婆娑着。
《光明日报》(2023年07月07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