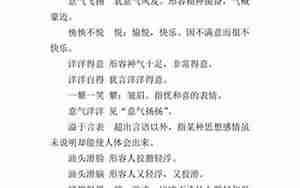若求得。。
1
皇上喜欢我娘亲。
他疯了。
我用茶泼了面前这男人一头一脸。
那男人缓缓站直了身子,水珠仍在滴滴答答往他身上淌。
宫女们都吓了一跳,急急忙忙去拿干帕子擦拭。娘亲牵着我往她身后躲。
「宸妃。」那男人笑了笑,乌沉沉的眸子里含着霜意,「这孩子不懂事,朕可以饶她一次。」
「若还有下次,朕也不介意帮李纳微管一管。」
他说完拂袖去了,只剩下娘亲把我抱在怀里。
我又被送回了府上。
我父亲只是个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与那人比起来,自然可以像只蝼蚁一样任人拿捏。
父亲给我的回应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有什么故事,只知道娘亲过得不好。
娘亲的脖颈手臂上,有淤青和啃咬的痕迹。
在很明显的地方,像是狗皇帝特意展示给众人看的。
他当时蹲到同我一般高,和我说:「你知道吗?朕才是先遇到你娘亲的那个人。」
我恨不能扑上去咬他一口。
可我只是拿茶泼了他。
我嫌他脏,不配被我咬。
狗皇帝从不做个人。
他夺了我娘,恨不能向所有人展示那是他的所有物,全然不顾我娘臣妻的身份和四起的流言。
然后他又要给我爹赐婚。
赐的是宁德郡主。
宁德郡主何曾有德,一嫁丧夫,整日与府中豢养的面首厮混。
他就是故意恶心我爹。
我爹推拒,他就又一旨召令把我召进宫做太子伴读。
他要我爹答应,要他笑着说谢主隆恩。
2
凤栖宫的太子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狗皇帝的儿子,生得与他有四五分像。
却还是个拖着鼻涕的小胖子,总是怯生生想同我搭话。
「若……若姐姐。」
「滚。」
把我召来宫里,却不许我见娘亲,只把我同这么个小子搭在一处,分明是让我做掣肘父亲的棋子。
用父亲和我牵着娘亲,又用娘亲和我来牵着父亲。
真他太后的好笑。
狗皇帝的儿子小我三岁,正没有眼力见地拿着一盘点心讨好我。
「若……若姐姐别……别生气,阿……阿琉请你吃好……好吃的。」
这小狗子还是个结巴。
我接过他手中的盘子,在他要笑起来的那一刻又松开,任糕点在地上滚了个面目全非。
我有些怨毒又开心地看着他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
我不该迁怒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的,可是我忍不住。
我以为他就此走开了,却不想过了一会他又走过来牵我衣角。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推开,就听见他说:「我……我带你去见宸……宸娘娘好不好。」
这次我没有拒绝他。
他带我来到我娘住的地方,那个写着「紫岚宫」三个大字的地方。
门口有人守着。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跟着狗皇帝的太监也在,他还同小狗子和颜悦色地说:「太子还是先回去吧,宸妃现在不方便见客。」
他又同我说:「若姑娘也回去吧。」
这宫里的破房子隔音也不是很好,因为我听见狗皇帝的笑声了。
我扭头往外走。
小狗子也跟上我。
然后我又飞快地转身,趁着所有人不备撞开了那扇门。
我从没有想过男女交媾是这样恶心的场景。
我扑到那男人赤条条的背上又抓又挠。
身后跟着进来的人都吓傻了。狗皇帝反应过来后,一巴掌把我掀到了地上。
他只穿了一条亵裤,上身光溜溜的,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对我说:「李若,要不是这张同朕的宸妃七八分相似的脸,你以为你还能活到今天。」
他又看到了人群里的太子:「阿琉也在啊。」接着说,「再不许让她过来,你可记住了?」
小狗子讷讷点头。
我试图用眼神剜死他。
察觉到我的目光,狗皇帝又笑了:「这样不服气啊。」他用手托起我的脸,「不如……」
「让她走……」我听到床榻上传来带着哭腔的声音,我娘的手还被他用床幔束着,一铺凌乱中显得格外凄楚可怜,「让她走……萧成,我求你了。」
我被众人带出去的时候,都踏过了门槛,却在关门的那一瞬几乎又暴起想折返去杀了狗皇帝。
因为我听见他在说,用那种调笑的语气对着我娘说。
「乖,再叫一个让朕听听。」
那个首领太监攥住了我的腕子。他攥得不疼,手劲却很重,足以治住一个八岁的扑腾的小姑娘。
他对我说:「不想宸妃娘娘难堪,若姑娘还是该学着乖觉些。」
3
我爹还是与宁德郡主成了亲。
狗皇帝说为他们贺新婚,赐了座宅子。
然后把我家先前的府邸拆了个干净。
其实他无须说得这样冠冕堂皇,他想要的,无非是折毁我父亲同娘亲的回忆。
那宅子我娘住过,便留不得了吗?
新宅子里,宁德郡主带来的莺莺燕燕们占了半边院子。我去的时候,也是个男人同我说她多饮了酒,劝我改日再来。
她果然有些醉,眼尾泛红眼神迷离,脚边还滚着酒盅。听到我进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怪不得。你生得就这样好看。」
我其实也不想怎么与她交谈,更别提要我叫她母亲。但我又不可能一辈子不见她。所以我也只是来尽早走个流程看她一眼。
却不想她同我说:「你别担心,我同你父亲不会有什么的。」
「可你娘再也回不来了,你该知道。」
我攥紧了自己的拳头,指尖戳得掌心有些疼。
我不该同一个醉鬼争执。
何况她说的是实话。
狗皇帝没有免了我伴读的身份,我还是要日日进宫去陪小狗子读书。
我其实也想过他应该是不愿见到我的,毕竟他视娘亲为禁脔,连旁人多看一眼都不许。
可他又确实容忍着我的存在。
我也试着在凤栖宫大吵大闹过,闹到把狗皇帝都吵来。他同我说:「李若,你不要耍那些小聪明。」
他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他要留我在宫里,或许是因为他第一次见到娘亲就是这个年纪,又或许,是因为我身上有娘亲先前的影子。
看这个人多搞笑啊。他一面折断她的翅膀,一面却在追慕她未戴镣铐时的模样。
4
六月份的时候。
狗皇帝的大皇子跑到凤栖宫来指着小狗子骂了一顿,说他偷拿了他们宫里的东西。
小狗子委屈巴巴地说没有。
我早就发现,这宫里的人待小狗子都不算好,甚至连宫女太监也是。
小狗子穿的衣服有时都脏了也不给换,鞋子么有时也不怎么合脚。有时候他说什么宫人也不在意,明摆了是敷衍加不上心。
虽然我知道他没了娘。但他好歹也是太子,怎么也不该混到这么惨的地步。
后来我才知道,按照狗皇帝的狗屁逻辑,他故意放任不管,是想让小狗子多吃些苦,想让所有人明里暗里挤兑欺负他,逼得他学会自己崛起反抗。
……用犬类的标准衡量都抬举了他。
我本不该管小狗子的任何事情,平时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日所见太过,哪有这样一直戳着一个五岁的小孩漫骂的。
然后我就上去踹了大皇子一脚。
我本站在他身后,一脚下去差点让他跪下。他反应过来后,一脸恼怒加不可置信地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疯了吧。」
我一脸无所谓地回望他。
他眼睛飞快地转了一下,我猜他是在想我是谁。
果然见他忽然咧嘴笑了:「原来是你啊,那个小野种……」
他话没说完,因为我抄起桌上的砚台开始打他。
那里面还有墨汁,溅得我手上,他衣服上哪哪都是。
我是野种。我父母三书六聘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却成了野种。
宫女太监们吓坏了,先前小打小闹他们不理,现在倒是着急起来了。
因我费了死力追着他打,他也不服气与我绞成一团,小狗子不知怎的也过来挨了一脚,宫人们倒是也费了些力气才把我们分开。
他仍气恼:「你敢打本皇子,活腻了不成。」
「打的就是你。」我咬牙,「你大可跟你皇帝老子去说,有本事叫他弄死我。」
我想将手中的砚台掷出去,因宫人抓着我的手臂只丢到了他脚边。
本来是朝着他额角去的。
他倒是唬了一跳,又不敢真的告诉狗皇帝我们打起来的原因是他推搡了小狗子,又说了我的身世,最后撂下个「今日不跟你计较」的台阶就自己走了。
宫人松开了我。小狗子有些胆怯地递了一方干净的帕子想给我擦手。
我才想起事情的初始起因是因为他,又想起刚刚他过来拉我们的时候被那大皇子踢到了。
难得地朝他缓和了脸色,接了他手里的帕子。
手上的墨渍不好擦,却也染污了帕子。我想着还是要去洗一下,还破天荒地主动和小狗子说了句话。
「别人欺负你,你都不会还手的吗?」
他用那副真的很像小狗崽子的神情摇了摇头。
「那刚刚又为什么跑过来?」
他眼中的无辜天真和示好真的有些戳到了这些天总是对他无端厌恶的我。
他在说:「不……不想若……若姐姐受伤。」
5
我实在受不住他这样的无端好意。
包括后来,每次我见到他挨了欺辱,其实总要替他驳一驳,争一个客观公道的结果。
却不是刻意维护他。只是我见了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总会愤懑。
我娘之前就总说我,天生的疾恶如仇黑白分明未必是好事。
那时我不懂,总是追着问娘亲什么叫这世上不单黑白两色。
现在我也不懂。
可我看到小狗子时又好像有些明白。
我厌恶他。因为他身上流着狗皇帝的血脉。可他又是这样无辜的一个局外人。
我对他的好本与对待街边的流浪猫狗没有半分差别,他却把这份所谓的心意视若瑰宝。
我替他不值,同时无法接受和承担这份好意。
我一面觉得自己不该对他如此,一面又只能对他如此。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拉扯的矛盾感,同时无比希望他应该像我待他一样冷漠。
可他没有,他总是固执地以一个尾巴或者影子的角色跟随,全然不顾我给自己套了层多么冷硬的冰壳子,然后将他的依赖和亲近毫无保留地兜头给我。
……
我应该也是问过他的,为什么。而且应该不止一次地推拒过,不要这样对我。
可他会昂起头笑容灿烂地望着我,同我说:「可是宫里只有若……若姐姐对我好。」
他的结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其实是一日日变好的。
我看着他口齿逐渐清晰,身量逐渐抽长,眉眼长开越来越像那个人。
虽然会在心里叫嚣着这样不对,却还是不能十成十地将他们完全撇清关系。
又或许我是有真的尝试过接纳他,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6
我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我遇见了十一公子。
是中元节的那一天,我拿着小狗子给的珠宝去当铺折换成现银。
我本来不要的,是他说算作我为他斥责了不服管教的宫人的劳谢。他强意坚持了多次,终于我勉为其难地收下。
其实要次次这样也好,划清界限,雇佣关系。我帮他挡灾,他付我酬劳。
只是若他也肯这样想才好。他若想的不是这样,这东西,我是不会再收第二次的。
今日收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打算留存,准备化了银子日后捐给保育堂或者送给那些无处落脚的流民乞丐。
却不想一出了当铺就被人盯上。
人不算多,四五个。我打不过。
我想着甩开,小步快走,左绕右绕却进了死胡同……
十一公子出现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了话本子里为什么总喜欢杜撰英雄救美的情节。
十一公子帮我制服了那些歹人,他说不巧,他不是偶然路过,是见那些人神色异常早早留心一路追过来的。
我谢过他,问他名字,他便说是十一。
十一公子说,他也是才来京城。
说他之前在青州。
车载伤感歌曲《佛前问爱》这首歌是什么意思?爱由心生
[玫瑰]轻点下方欣赏[玫瑰]
跪拜佛前想问个清楚:为什么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入了心的人,动了情,一辈子也忘不掉。刻苦铭心爱也是一生内心的财富,也是一种极致享受。世事难预料,生死难相许,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就不过一场梦的旅行……只能说,没有谁对谁错,这都是老天爷的安排,有时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也不尽然,有时真挣不过天,挣不过命运!!
这首歌唱出了好多的无奈与放下。爱的人受到伤害,自己却无能为力,无所作为,那真是从骨子里,从全身心的痛!!父母,儿女,伴侣,亲近的人,都感受过。所以珍惜当下所拥有的亲情,友情,即使陌生人需要帮助,也要伸出有温度的手,让人与人之间感受到爱的能量!!
每个人都有过往,每个人又有许多不同的经历,有时都怪自己当初太幼稚、太年轻、缺少见识、撕心例肺的痛啊……
你看,有人看海,有人被爱,有人喝酒到现在。或许,不如就这样,收藏起悲伤,陪君醉笑三千场!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坦然接受……只想要平常心来对待每个人,心不要有负担 ,看事做事,无须全够,心安则不乱,凡事开心,你说对吗?
你爱的人,是来为你渡劫的,要么劫后余生,要么在劫难逃。如果你已婚,相信你会认同这句话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哈哈!!!
在看文章听歌曲的你,有没有被触碰到什么?或许有,或许没有吧!
若求得。。
1
皇上喜欢我娘亲。
他疯了。
我用茶泼了面前这男人一头一脸。
那男人缓缓站直了身子,水珠仍在滴滴答答往他身上淌。
宫女们都吓了一跳,急急忙忙去拿干帕子擦拭。娘亲牵着我往她身后躲。
「宸妃。」那男人笑了笑,乌沉沉的眸子里含着霜意,「这孩子不懂事,朕可以饶她一次。」
「若还有下次,朕也不介意帮李纳微管一管。」
他说完拂袖去了,只剩下娘亲把我抱在怀里。
我又被送回了府上。
我父亲只是个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与那人比起来,自然可以像只蝼蚁一样任人拿捏。
父亲给我的回应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他们过去有什么故事,只知道娘亲过得不好。
娘亲的脖颈手臂上,有淤青和啃咬的痕迹。
在很明显的地方,像是狗皇帝特意展示给众人看的。
他当时蹲到同我一般高,和我说:「你知道吗?朕才是先遇到你娘亲的那个人。」
我恨不能扑上去咬他一口。
可我只是拿茶泼了他。
我嫌他脏,不配被我咬。
狗皇帝从不做个人。
他夺了我娘,恨不能向所有人展示那是他的所有物,全然不顾我娘臣妻的身份和四起的流言。
然后他又要给我爹赐婚。
赐的是宁德郡主。
宁德郡主何曾有德,一嫁丧夫,整日与府中豢养的面首厮混。
他就是故意恶心我爹。
我爹推拒,他就又一旨召令把我召进宫做太子伴读。
他要我爹答应,要他笑着说谢主隆恩。
2
凤栖宫的太子是个讨人厌的家伙。
狗皇帝的儿子,生得与他有四五分像。
却还是个拖着鼻涕的小胖子,总是怯生生想同我搭话。
「若……若姐姐。」
「滚。」
把我召来宫里,却不许我见娘亲,只把我同这么个小子搭在一处,分明是让我做掣肘父亲的棋子。
用父亲和我牵着娘亲,又用娘亲和我来牵着父亲。
真他太后的好笑。
狗皇帝的儿子小我三岁,正没有眼力见地拿着一盘点心讨好我。
「若……若姐姐别……别生气,阿……阿琉请你吃好……好吃的。」
这小狗子还是个结巴。
我接过他手中的盘子,在他要笑起来的那一刻又松开,任糕点在地上滚了个面目全非。
我有些怨毒又开心地看着他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
我不该迁怒一个五岁的小孩子的,可是我忍不住。
我以为他就此走开了,却不想过了一会他又走过来牵我衣角。
我还没来得及把他推开,就听见他说:「我……我带你去见宸……宸娘娘好不好。」
这次我没有拒绝他。
他带我来到我娘住的地方,那个写着「紫岚宫」三个大字的地方。
门口有人守着。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跟着狗皇帝的太监也在,他还同小狗子和颜悦色地说:「太子还是先回去吧,宸妃现在不方便见客。」
他又同我说:「若姑娘也回去吧。」
这宫里的破房子隔音也不是很好,因为我听见狗皇帝的笑声了。
我扭头往外走。
小狗子也跟上我。
然后我又飞快地转身,趁着所有人不备撞开了那扇门。
我从没有想过男女交媾是这样恶心的场景。
我扑到那男人赤条条的背上又抓又挠。
身后跟着进来的人都吓傻了。狗皇帝反应过来后,一巴掌把我掀到了地上。
他只穿了一条亵裤,上身光溜溜的,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对我说:「李若,要不是这张同朕的宸妃七八分相似的脸,你以为你还能活到今天。」
他又看到了人群里的太子:「阿琉也在啊。」接着说,「再不许让她过来,你可记住了?」
小狗子讷讷点头。
我试图用眼神剜死他。
察觉到我的目光,狗皇帝又笑了:「这样不服气啊。」他用手托起我的脸,「不如……」
「让她走……」我听到床榻上传来带着哭腔的声音,我娘的手还被他用床幔束着,一铺凌乱中显得格外凄楚可怜,「让她走……萧成,我求你了。」
我被众人带出去的时候,都踏过了门槛,却在关门的那一瞬几乎又暴起想折返去杀了狗皇帝。
因为我听见他在说,用那种调笑的语气对着我娘说。
「乖,再叫一个让朕听听。」
那个首领太监攥住了我的腕子。他攥得不疼,手劲却很重,足以治住一个八岁的扑腾的小姑娘。
他对我说:「不想宸妃娘娘难堪,若姑娘还是该学着乖觉些。」
3
我爹还是与宁德郡主成了亲。
狗皇帝说为他们贺新婚,赐了座宅子。
然后把我家先前的府邸拆了个干净。
其实他无须说得这样冠冕堂皇,他想要的,无非是折毁我父亲同娘亲的回忆。
那宅子我娘住过,便留不得了吗?
新宅子里,宁德郡主带来的莺莺燕燕们占了半边院子。我去的时候,也是个男人同我说她多饮了酒,劝我改日再来。
她果然有些醉,眼尾泛红眼神迷离,脚边还滚着酒盅。听到我进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怪不得。你生得就这样好看。」
我其实也不想怎么与她交谈,更别提要我叫她母亲。但我又不可能一辈子不见她。所以我也只是来尽早走个流程看她一眼。
却不想她同我说:「你别担心,我同你父亲不会有什么的。」
「可你娘再也回不来了,你该知道。」
我攥紧了自己的拳头,指尖戳得掌心有些疼。
我不该同一个醉鬼争执。
何况她说的是实话。
狗皇帝没有免了我伴读的身份,我还是要日日进宫去陪小狗子读书。
我其实也想过他应该是不愿见到我的,毕竟他视娘亲为禁脔,连旁人多看一眼都不许。
可他又确实容忍着我的存在。
我也试着在凤栖宫大吵大闹过,闹到把狗皇帝都吵来。他同我说:「李若,你不要耍那些小聪明。」
他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他要留我在宫里,或许是因为他第一次见到娘亲就是这个年纪,又或许,是因为我身上有娘亲先前的影子。
看这个人多搞笑啊。他一面折断她的翅膀,一面却在追慕她未戴镣铐时的模样。
4
六月份的时候。
狗皇帝的大皇子跑到凤栖宫来指着小狗子骂了一顿,说他偷拿了他们宫里的东西。
小狗子委屈巴巴地说没有。
我早就发现,这宫里的人待小狗子都不算好,甚至连宫女太监也是。
小狗子穿的衣服有时都脏了也不给换,鞋子么有时也不怎么合脚。有时候他说什么宫人也不在意,明摆了是敷衍加不上心。
虽然我知道他没了娘。但他好歹也是太子,怎么也不该混到这么惨的地步。
后来我才知道,按照狗皇帝的狗屁逻辑,他故意放任不管,是想让小狗子多吃些苦,想让所有人明里暗里挤兑欺负他,逼得他学会自己崛起反抗。
……用犬类的标准衡量都抬举了他。
我本不该管小狗子的任何事情,平时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今日所见太过,哪有这样一直戳着一个五岁的小孩漫骂的。
然后我就上去踹了大皇子一脚。
我本站在他身后,一脚下去差点让他跪下。他反应过来后,一脸恼怒加不可置信地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疯了吧。」
我一脸无所谓地回望他。
他眼睛飞快地转了一下,我猜他是在想我是谁。
果然见他忽然咧嘴笑了:「原来是你啊,那个小野种……」
他话没说完,因为我抄起桌上的砚台开始打他。
那里面还有墨汁,溅得我手上,他衣服上哪哪都是。
我是野种。我父母三书六聘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却成了野种。
宫女太监们吓坏了,先前小打小闹他们不理,现在倒是着急起来了。
因我费了死力追着他打,他也不服气与我绞成一团,小狗子不知怎的也过来挨了一脚,宫人们倒是也费了些力气才把我们分开。
他仍气恼:「你敢打本皇子,活腻了不成。」
「打的就是你。」我咬牙,「你大可跟你皇帝老子去说,有本事叫他弄死我。」
我想将手中的砚台掷出去,因宫人抓着我的手臂只丢到了他脚边。
本来是朝着他额角去的。
他倒是唬了一跳,又不敢真的告诉狗皇帝我们打起来的原因是他推搡了小狗子,又说了我的身世,最后撂下个「今日不跟你计较」的台阶就自己走了。
宫人松开了我。小狗子有些胆怯地递了一方干净的帕子想给我擦手。
我才想起事情的初始起因是因为他,又想起刚刚他过来拉我们的时候被那大皇子踢到了。
难得地朝他缓和了脸色,接了他手里的帕子。
手上的墨渍不好擦,却也染污了帕子。我想着还是要去洗一下,还破天荒地主动和小狗子说了句话。
「别人欺负你,你都不会还手的吗?」
他用那副真的很像小狗崽子的神情摇了摇头。
「那刚刚又为什么跑过来?」
他眼中的无辜天真和示好真的有些戳到了这些天总是对他无端厌恶的我。
他在说:「不……不想若……若姐姐受伤。」
5
我实在受不住他这样的无端好意。
包括后来,每次我见到他挨了欺辱,其实总要替他驳一驳,争一个客观公道的结果。
却不是刻意维护他。只是我见了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总会愤懑。
我娘之前就总说我,天生的疾恶如仇黑白分明未必是好事。
那时我不懂,总是追着问娘亲什么叫这世上不单黑白两色。
现在我也不懂。
可我看到小狗子时又好像有些明白。
我厌恶他。因为他身上流着狗皇帝的血脉。可他又是这样无辜的一个局外人。
我对他的好本与对待街边的流浪猫狗没有半分差别,他却把这份所谓的心意视若瑰宝。
我替他不值,同时无法接受和承担这份好意。
我一面觉得自己不该对他如此,一面又只能对他如此。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一种自我拉扯的矛盾感,同时无比希望他应该像我待他一样冷漠。
可他没有,他总是固执地以一个尾巴或者影子的角色跟随,全然不顾我给自己套了层多么冷硬的冰壳子,然后将他的依赖和亲近毫无保留地兜头给我。
……
我应该也是问过他的,为什么。而且应该不止一次地推拒过,不要这样对我。
可他会昂起头笑容灿烂地望着我,同我说:「可是宫里只有若……若姐姐对我好。」
他的结巴,从我认识他那天起,其实是一日日变好的。
我看着他口齿逐渐清晰,身量逐渐抽长,眉眼长开越来越像那个人。
虽然会在心里叫嚣着这样不对,却还是不能十成十地将他们完全撇清关系。
又或许我是有真的尝试过接纳他,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6
我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是我遇见了十一公子。
是中元节的那一天,我拿着小狗子给的珠宝去当铺折换成现银。
我本来不要的,是他说算作我为他斥责了不服管教的宫人的劳谢。他强意坚持了多次,终于我勉为其难地收下。
其实要次次这样也好,划清界限,雇佣关系。我帮他挡灾,他付我酬劳。
只是若他也肯这样想才好。他若想的不是这样,这东西,我是不会再收第二次的。
今日收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打算留存,准备化了银子日后捐给保育堂或者送给那些无处落脚的流民乞丐。
却不想一出了当铺就被人盯上。
人不算多,四五个。我打不过。
我想着甩开,小步快走,左绕右绕却进了死胡同……
十一公子出现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了话本子里为什么总喜欢杜撰英雄救美的情节。
十一公子帮我制服了那些歹人,他说不巧,他不是偶然路过,是见那些人神色异常早早留心一路追过来的。
我谢过他,问他名字,他便说是十一。
十一公子说,他也是才来京城。
说他之前在青州。
《灵魂摆渡2》前世债今生还,因为一个负心汉她痴等几百年
吕哲又做梦了。
自从上次答应了妻子秀秀,帮忙给她无故死去的朋友办一场冥婚相亲之后,他就开始了频繁地做梦。
在梦中,他穿着一身古代的衣服,和衣躺在床上,而躺在他身侧的,是一个身穿古代衣服的女子,那女子面容清秀精致,正在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彼此相握的双手,梦幻泡泡的气氛,俨然是一副甜蜜相恋的情景,可诡异的是,那女子,并非是他的新婚妻子秀秀,反倒更像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他熟悉却又陌生的人。
事情要追溯到几天前,他与秀秀新婚,二人正是如胶似漆蜜里调油的时候,秀秀突然说自己这么幸福,不忍最好的朋友却是孤单一人,她的朋友因病离世,若能求得灵婆给朋友配以冥婚,让朋友在地下也能成双成对,那该多好?【采瑛】
在吕哲看来,冥婚之事纯属瞎扯,他可是社会主义好青年,坚持相信科学,打倒旧社会旧传统的根正苗红的好孩子,怎么可能会去相信这种事情?正所谓,人死如灯灭,鬼魂之说更是无稽之谈,更别说要给鬼相亲配冥婚了,这不是浪费时间瞎折腾吗?
当然,这种话他不好对秀秀说,也不想因此而打击妻子的积极性,不就是配合她走一趟吗,权当是休息打发时间了。吕哲抱着这样的想法与秀秀一起去的,可是当他开车行驶越来越偏僻的时候,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强烈。
秀秀的那个朋友,名叫方祺,是她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好友,方祺妈妈抱着方祺的骨灰盒前来为他相亲,而后交到了吕哲手上帮忙抱着,当他们一起进到那个传说中可通鬼界的灵婆家里,他才发现,这个地方,连空气都是阴冷的,整个家里的气氛诡异又阴森,就好像是从阳光里突然闯入了鬼门关一般,到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采瑛】
吕哲本就不相信这世上有鬼,可那灵婆的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冥婚照片,古式婚礼的黑白照中,新郎或者新娘,总有一个的下半身,是飘着的。
灵婆出来以后,拿出了一张古代女子画像,那画上的女子温柔婉约,眉目间竟有些许熟悉之感,在灵婆的示意下,让他们闭上眼睛不准睁开,她要做法请那死去的女子出来相一相,看看双方是否能够对得上眼,可吕哲实在是好奇,他作为一个相信科学的有为青年,绝对不相信这世上有鬼,尽管灵婆已经千叮万嘱,绝对不能睁开眼睛,他还是在灵婆做法的期间,睁开了眼睛,然后他就看到,他与灵婆中间的空间上方,有一个身着古衣的女子,悬在空中,正直钩钩地望着他。
而怪事,就是从这件事发生之后,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身边。
先是在和朋友聚会的KTV里遇见一个奇怪的女人在唱一首很古老的歌,后是总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监视了似的,一直有人在跟着,当他回头,却又什么都没有,但却又好像能看见,有一袭拖了地的长发在转角处隐去,再是一直都陷入梦里,在梦里,他是他,却又好像不是他,他拥着的女人不是自己的新婚妻子,而是那个在灵婆那里见过的画像上的古代女子。【采瑛】
当人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下,毛孔会本能地张开,感受到这股阴冷,而这股阴冷一直都伴随着他,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被鬼缠上了,随时都会死。
这种不安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他有些埋怨上了秀秀,开着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听音乐的频道总是会发生磁场被干扰的滋滋声,以往从来都没有过这种现象,当他再一次汗毛耸立,不自觉得望向车内的后室镜,他终于看到,那一袭乱糟糟的长发,掩盖着的红衣少女,此刻正坐在他的汽车后座里。
猝然的惊吓,使得他直接撞上了马路边的石墩,将头给磕出了血,晕了过去,当他醒来,他终于确定,自己被一个女鬼给缠上了。
因为他的生病,秀秀本来要在家里照顾他,但是因为要先去公司请假,所以家里只留下他一个人,他看着秀秀走出家门,而后在家里进行翻找,他总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毕竟那个地方是秀秀带自己过去的。
仔细翻找之下,他发现了秀秀隐藏在柜子里的相册,相册里全是她和另一个男人的合影,他们举止亲密,笑容可掬,俨然是一对幸福甜蜜的情侣,而更离谱的是,那上面的男人,就是秀秀所说的那个他早逝的朋友,也是因为他,才去灵婆处进行鬼配冥婚,更是因为他,自己才被一个女鬼给纠缠上了。【采瑛】
他不知道在这件事里,秀秀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但他能肯定的是,他会被女鬼缠住,一定跟秀秀脱不了关系。
疑心生暗鬼,当天夜里他便看到了秀秀穿戴整齐,提着一包东西离开家的身影。
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一路尾随而去,就看见秀秀蹲在马路边上,开始在火盆里烧元宝,烧着烧着,更是拿出了一个纸人扔了进去,而那纸人身上粘着的,竟然是他的照片。
阴谋,这一切都是个阴谋,一定是秀秀和那个男鬼合谋,要害死自己,好让自己为那个男鬼让位,成全他们这对鬼男女,他想要将事情查个清楚,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实在太过离谱,平常人肯定不会相信。
为难之际,他想到了那个学校里的传闻,那时大家都在传,他的大学同学夏冬青,眼睛与寻常人不同,据说他的眼睛,能够看到鬼。
如果冬青的眼睛能够看到鬼这件事是真的,那他就一定会相信自己身上所发生的诡异的一切。【采瑛】
说干就干,他打车去找夏冬青,然后将人带到了一处偏僻之地,将自己最近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秀秀,冬青说这件事还是要跟秀秀问清楚,更重要的是,冬青肯定的告诉他,传闻是真的,冬青真的能看到鬼,而且还能跟鬼进行沟通。
他带着冬青回家,与秀秀摊牌,却没想到,刚一进门,冬青就被那个男鬼附了体,嚣张至极地说要将自己取而代之,没有哪个男人能接受别的男人当众挑衅自己,要抢自己的老婆,即便那个男人是鬼,他也会为了保护自己男人的尊严而战。
他顾不上那是冬青的身体,与那男鬼扭打在了一起,在战事僵持之时,一黑衣男子闯了进来,手持一把枪,逼着那男鬼从冬青身上离开。【采瑛】
那黑衣人,名叫赵吏,看冬青的意思,他应该是个能通阴阳的厉害人物,毕竟连鬼都害怕的人,可不就是个厉害人吗?
赵吏说自己是受人所托,来断一桩冤案,随即拿出一小盒香,将其点燃,口中念道:
生犀不敢烧,燃之有异香,沾衣带,人能与鬼通。。。
上好的犀角香被点燃,异香瞬间在整个房间里环绕,而后现出的是那个面带怒色的男鬼方祺,与长发拖地的红衣女鬼嫣嫣。
方祺去世之后,停留人间太久,就一直待在秀秀身边,看着秀秀结婚幸福,早已是炉火中烧,他无法接受自己最爱的秀秀,移情别恋到了吕哲身上,而后厉化为鬼,被赵吏一枪打散。【采瑛】
那红衣女鬼嫣嫣,也就是一直缠着吕哲的那个女鬼,却是因果相报,本就是吕哲前世所犯下的罪孽。
前世之时,吕哲名唤李哲,是即将参加科举的书生,他与大户人家的女儿嫣嫣相恋,并许下了非卿不娶的誓言,在奔赴京城科考前夕,为了让嫣嫣安心等他归来,特写下婚书,以作证明,嫣嫣满心欢喜,即便家人不许她与李哲相恋,她也誓死维护自己的爱情。
为了守身如玉,等李哲归来,她三番两次拒绝家人为她安排的亲事,终是惹怒了一心为她的家人,家人见她铁了心也要跟李哲私守,便放任不管,任她在绣楼里等她的郎君。
可惜的是,她不仅等来了李哲高中状元的消息,却也等来了李哲被当朝丞相招为贵婿,即将迎娶相府贵女苏绣娘的消息,此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将她的满心欢喜霹成了一个笑话。
为了李哲,她早已与家人决裂,为了李哲,她拿着婚书,枯坐绣楼,思念到天明,可她的坚守,却换来了李哲即将迎娶他人的下场,她的一往情深,终究只是一个自我感动的笑话。【采瑛】
爱情是她的信仰,当信仰破碎,便只剩下一地的绝望,她亲自将自己吊进白绫,而后赴死而去。
她死时的怨念太深,又一心只想找到李哲问个清楚,为此不能转世,只能流连地府,枯等百年,只想找到李哲这个负心人。
而今在一场莫名的冥婚相亲会上,她终于找到了那个负心人,这才从此缠上吕哲,要他偿还自己的一片情深。
凡立下婚书者,已是诏告天地,结为夫妻,李哲负了嫣嫣,与相府贵女琴瑟和鸣,相爱到老,那她嫣嫣,究竟又算什么呢?
李哲与苏绣娘转世之后,再续前缘,可怜嫣嫣因为一个负心汉,沦为孤魂野鬼,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执念之中,一次又一次地枯等。
李哲的罪,当然要吕哲来还,即便已隔了一世,但嫣嫣也只是想要讨个说法,她是因为李哲才会绝望自杀,当然也要他还一条命。【采瑛】
时近午夜,吕哲站在天台之上准备自杀,而后赵吏赶来告诉他,下来吧,嫣嫣原谅你了!
死里逃生的吕哲还以为嫣嫣终于放过他了,可他哪里知道,不是嫣嫣原谅他,而是他的妻子秀秀用死来替他还债,因为他的辜负,先是在前世逼死了深爱他的嫣嫣,更是在现代使得秀秀以命替他还债,吕哲这一生,终究也只能是自己一个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