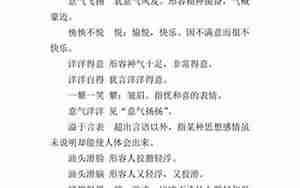五朝所有皇帝生肖整理,明清都是奇葩,唐宋不爱龙马
历朝皇帝属相中,属兔的最多,共34人,其次是龙与马,共28人,紧跟其后的猪、虎各26人,而牛、猴、羊各为24、23、22人,最少的是鸡、蛇、鼠,则各20人。
仔细比较的话,除了兔格外突出之外,其他的其实相差不大。具体到了各个朝代的话,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了。
清朝十二帝属相
清朝皇帝中,属相为龙、马的各三人,生肖为的虎、羊、兔的皆成对。嗯……清朝皇帝真的没有强迫症吗?
明朝十六帝属相
明朝果然是奇葩,集齐了十二个生肖,这是要召唤神龙了吗?
南宋十帝属相
基本上都是草食动物,唯一个蛇也是不走光明路的。似乎给南宋找到了一个弱小的原因。
北宋九帝属相
最容易勤劳苦干的马呢?南宋北宋都没有。
唐朝二十一帝属相
奇怪,唐朝为什么没有属相是龙的呢?
欢颜:夜袭黑当铺!廖凡饰演的老孙为拿回金条,“空手套白狼”?
传奇谍战剧《欢颜》首播上线3集,4小时热度破20000!该剧真的好看!演员、剧情、节奏、画面,都是高水准!
这篇单论老孙带人夜袭黑当铺的情节。
徐天和老孙随身携带的3根金条,被“仙人跳”设计偷走并销赃到当铺。老孙要拿回这3根金条,但是当铺不干。老孙决定夜袭黑当铺,拿回金条。
动这3根金条,就是动了苏区的威信!
老孙一言九鼎,言出必行。
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老友王鹏举,王鹏举又拉来了马天放、胡蛮两个帮手。
夜袭黑当铺行动开始前,老孙同王鹏举他们3个人谈起了行动佣金。
首付的话,每人5块大洋。
老孙手里哪里有现大洋!于是改为后付,每人8块大洋!
也就是说,这8块大洋得王鹏举他们自己到当铺去拿!老孙这不是“空手套白狼”吗?
关于《欢颜》这一段,有观众弹幕评论说,老孙真是商业奇才!
老孙是空手套白狼吗?
不是!
因为老孙还有一段话:前面有个当铺,也做票号生意,黑店!天黑了,把它抢了,不全抢啊,我们不是强盗,你们每个人只拿分内的。
3个人,每人8块。
老孙是以武装突袭的手段拿回苏区的财产,如果没有老孙和苏区做后盾,王鹏举他们3个人,单枪匹马,他们敢抢有武装力量的黑当铺吗?
如果不是老孙知道这是个黑当铺,他们突袭当铺的理由何在?
首先:这3根金条是苏区的财产。
这3根金条,从剧情来看,应该是10两(当时1斤是16两)1根的“大黄鱼”,每根相当于黄金312.5克,如果换算为现大洋(也就是袁大头)的话,1根“大黄鱼”能换400块现大洋。3根“大黄鱼”相当于1200块现大洋。
苏区的财产,被黑当铺拿去,还不归还,老孙代表苏区再拿回来,天经地义。
其次:这里当铺是黑店。
赎回黄金,要拿去5成,最少也要3成。但是他们收的典当品,是“仙人跳”偷来的,这属于非法经营。他们可以被归为土豪劣绅一类。
对于土豪劣绅的非法所得,红军的做法是没收非法所得,还要另外罚款30%左右。
1200现大洋,要罚款,得罚300多元,但是作为参与打土豪行动的战士,也不能把罚款全部拿走吧。
老孙让王鹏举他们每人拿8块作为酬劳,不少了。
最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老孙他们无法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因为这家当铺是黑店,非法经营,按照政策,非法收入应该全部没收,但是老孙他们只有4个人,无法做到全部没收。
只能先拿回属于苏区的金条,同时让王鹏举他们拿走罚款中发酬劳的部分,这就是老孙说的“分内”的意思。其余的事情,红军大部队来了后,会做的。
王鹏举他们3个人跟随老孙夜袭黑当铺,等于已经参加了革命队伍。
老孙做得非常对,根本不是空手套白狼,他们4人对这家黑当铺的罚没和罚款力度还是太少,因为他们和当铺护卫队相比,实力对比太悬殊了。
如果红军大部队过来,这样的黑当铺,这样的土豪劣绅,非法所得肯定会被没收的。
如果从历史史实去推敲细节,大家会发现,《欢颜》剧组真的很用心了,这才是真正对观众负责,对剧组自己负责的好剧。
《欢颜》的演员也都找得太好了!
廖凡的演技非常自然传神,带你分分钟入戏。
老戏骨杨皓宇戏份不多,但前面搞笑,后面感人,让人唏嘘不已。
看似王鹏举是为8块大洋搭上了命,但这其实是王鹏举的自发选择。为了好友老孙,王鹏举甘愿牺牲自己,是条汉子!
#时事热点头条说#
“诸子”概念的古今之辨
作者:冯鹏(河南大学哲学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现存古代典籍中,“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其所表示之意义,约有两端:一指周代封建制度下的众子爵之贵族,见《地官·大司徒》与《秋官·大行人》;二指周代“掌国子之倅”的职官,见《夏官·叙官》《诸子》二篇。西汉成、哀时期,刘向、刘歆奉诏“领校秘书”,并“奏其《七略》”,创立了典籍部类意义上的“诸子”概念,用以指称与“六艺”经传相区别的图书门类。班固《汉书·艺文志》承继其说。这种用法,在后世得到广泛接受。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在界定子部书籍时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仍然延续了刘歆的观念。除图书门类的意义外,“诸子”一词有时也被用来指称学者、思想家。最迟在西汉晚期、与刘歆同时的大儒扬雄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扬雄《法言·吾子》篇谓“委大圣而好乎诸子”,《君子》篇又设“或者”之问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等,便是显证。
近代以后,“诸子”一词的使用逐渐泛化,除过往已有的图书门类、学者二义外,又滋生出学术流派义。在现当代大部分诸子学研究专著中,人们对“诸子”的界定,一般都是同时包括上述三者在内,认为它是指“周秦汉魏,特别是周秦之际、秦汉之际不同的学术流派、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及其著作”(郭齐勇、吴根友《诸子学通论》)。表面上看,这似乎和传统时代所谓“诸子”没有多大的差别;或者说,与之前后相继,且在内涵上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可以断言的是,古今学人虽然共用“诸子”一词,但二者无论是在指称的具体人物、著作,还是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两相对立的。
就指称的具体人物而言,现代学术语境中的“诸子”,包括从孔子或老子开始的、周秦汉魏时期众多以“子”为称的思想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1917)一文有“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之语,《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又谓“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在胡适的观念中,老子、孔子、韩非,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皆属于“诸子”行列。而上引两则论述,很可能就是现代新“诸子”观的创始。自此之后,无论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1935)、陈柱的《子二十六论》(1935)等诸子学研究专著,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1931),除将孔子改列在老子之前外,均继承了胡适的“诸子”观。其与传统“诸子”观之最大不同,在于列孔子为“诸子”之一。从刘歆《七略》开始,一直到清儒章学诚、俞樾,除极个别学者(王充《论衡·本性篇》有“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的说法)外,均未将孔子计入“诸子”的范围!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谓:“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其中,“夫子”与“诸子”的区分十分明显。俞樾《诸子平议》虽对“诸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仍然坚守“孔子”与“诸子”两分的传统意见。即便是俞樾的弟子、民国初期影响极大的章太炎,在所著《诸子学略说》(1906)中也明确表示,“孔子删定六经……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则不然”。
就指称的具体著作来说,传统时代的“诸子”是相对于群经、诸史而言的,且《论语》被列入“六艺略”或“经部”;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则指诸“子”家之著作,而《论语》则为“诸子”书之首。例如,蒋伯潜《诸子通考》(1948)明确说:“诸子之书,多弟子后学纂述其师说以成一家之言者。此风实自孔门纂述《论语》开之。故诸子之书,以《论语》为第一部。”对于《汉书·艺文志》“录《论语》于《六艺略》中,录《孟子》于《诸子略》中”的做法,蒋氏评之为“妄分轩轾,自乱其例”。他当然知道,列《论语》于“六艺略”,是《汉书·艺文志》以来的古老传统,且“后世目录亦皆入‘经’类,未有厕于诸子之列者”;但是,他仍然坚持撰写《论语考》,作为《诸子通考》的首篇,并视之为对其父“考诸子之书,不及《论语》”的必要补充。显然,至迟蒋伯潜撰写《诸子通考》的时代,传统意义的“诸子”概念,在指称对象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且基本定型。
扬雄《法言·君子》篇曾谓:“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如今,我们却将孔子视同“诸子”,且不以为有何不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所秉持的学术观念已经大异于古人。在传统语境中,“诸子”一词是为了建构“道术”体系、辨明“道术”正统而被特意发明的。所谓“道术”,即治理天下之大法。据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孔子删定六经,“以纪帝王之道”,是唐、虞以来“圣帝明王”之“道术”的继承人。“诸子”则“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之际,“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乃“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诸子”之命名,正是为了表明它们不足以代表“帝王之道”的正统,甚至是对圣人之道的偏离和背叛。
至于现代语境中的“诸子”,其背后隐含的观念,与此已大不相同。正如陈柱在《子二十六论·原儒上》所言:“《汉书·艺文志》虽以孔子之六艺别为‘六艺略’,而不列于儒家,其在当时尊崇孔子则然;今就学术而论之,孔子亦当在诸子之列。”这里透显出,将孔子列入“诸子”,是从“学术”的视角论定的。而所谓“学术”,主要是指思想与学说。1902—1904年,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已有“孔、老、墨三分天下”的提法;后著《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1920)一文,则直言“古代学术,老、孔、墨三圣集其大成”。同时及稍后的胡适、冯友兰等人,列孔子于“诸子”,也是就“学术”(哲学)而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即面对异质而强大的西学,必须用新的眼光,对我国传统学术进行整体的审视与省思,重新建构一个系统的、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学术共同体,以与西学相比较,或应对西学的挑战,进而革新中国传统学术。这一点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章总论”部分可谓三致其意。即便是现今致力于创建“新子学”的时贤们,也仍然处于相同或相似的思想氛围之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诸子”概念的古今变化,并指出二者的不同或对立,不是为了反对在现代语境中继续对其进行使用,而是希望研究诸子学或致力于建构新诸子学的学者们,对此一概念的古今之辨保持清醒的认识,明确“诸子”是汉代儒生建构的学术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先秦众“子”的概称,进而避免在论述之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至于汉儒为何选取这样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名词,其中是否别有深意,则俟另文详论。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曲江水满花千树
曲江亭北侧湖边的雕塑名为“怅望江头”,表现的是大中十年,李商隐在长安游赏曲江时写下《暮秋独游曲江》的情景。他独立江头,无限怅惘。
唐长安城示意图。
徐燕孙《明皇并马图》。
曲江池航拍美景。
大唐芙蓉园《大唐追梦》演出。
曲江池畔“元白梦游”雕塑。
大唐芙蓉园“紫云楼”。
韩老夫子有些不高兴!
他一不高兴,写出了描写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
原诗题为《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看题目即知,惹他不高兴的人是“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白居易排行二十二,又曾任中书舍人,故称“白二十二舍人”。
无论如何,在当时官任吏部侍郎且是文坛领袖的韩愈老夫子面前,“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既是下官,又是晚生。可这个晚生下官一点儿都不给韩吏部面子,约好了同游曲江,他竟爽约不至。
这样的相邀,无论放在当年还是现在,多少人都会早早地前去恭候,但轻狂的“白二十二舍人”竟然没来。所以韩吏部很不高兴:你到底因何事不肯来啊?!
其实,白居易就住在曲江附近,唐朝诗人里数他最爱往曲江跑,数他写的曲江诗词最多,达30余首。常常“春傍曲江行”“题于曲江路”,诗中“曲江”二字常直呼出口:曲江相近住、曲江春意多、如到曲江头、还忆曲江春;曲江池畔杏园边、独绕曲江行一匝、曲江西岸又春风、曲江亭畔碧婆娑……
但此次,后起之秀白居易白乐天就是没给文坛领袖韩愈韩昌黎面子。
而韩昌黎也不愧为中唐时之文坛领袖,一首略带责备的七绝居然就写出了盖绝曲江的千古名句“曲江水满花千树”。有此一句,至少在写曲江的诗词竞赛中,韩老夫子就压倒了写曲江数量最多的白乐天,成为现存三百多首唐人曲江诗中影响最大的名句。
不错!迄今流传下来明确写曲江的诗词多达三百余首。而收录进《全唐诗》的500多位著名诗人中,又有一半多曾在曲江留下了足迹。其中包括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高适、王昌龄、贾岛、孟郊、李商隐、岑参、杜牧、刘禹锡等,不一而足。
距今1100多年前那个被称为大唐的时期,那个大唐时叫“曲江”的地方,有太多的诗词、太多的盛雅、太多的故事。
曲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
曲江,从秦汉时起,就和帝王皇室密切相关。
提到曲江,不能不说到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
历史上的曲江区域,位于汉唐长安城东南,地处少陵原和乐游原之间,是一方在原间洼地上因有泉自涌而形成的天然水塘池沼。
2200多年前的秦时,此地名隑洲,直译为河岸曲折的汀州。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咸阳南秦岭北麓之地为游猎享乐的上林苑,并在隑洲修建苑中苑——宜春苑。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仍把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尚武好猎的汉武帝大规模扩大了上林苑操练武备,东南的离宫别馆宜春苑也予以全面整修,并疏凿扩大了涌泉水源。因此地泉涌兴旺,流水屈曲如广陵之曲江,遂改隑洲名为曲江。今天,西安的曲江南湖尚有汉武泉遗迹。
汉武帝在开凿泉源、扩大曲江水面的同时,还在四周广植花草竹木,使宜春苑盛况空前。在上林苑游猎时,常常是先到西端的长杨宫,再回驾至东端的宜春苑休憩宴乐。司马相如随武帝游猎后作《哀秦二世赋》如此描述: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洲兮,望南山之参差。
此后,中兴西汉的宣帝刘询又在曲江池北之高冈处“起乐游苑”,建“乐游庙”,这处地势较高的冈原也因此得名乐游原。
公元581年,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决定在已残破不堪的汉长安城东南另建都城,并将新都的城郭布局、皇宫衙署等悉托城市设计大师宇文恺负责。
宇文恺根据地理形胜,设计并督导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新都。针对东南曲江凹陷地带,他巧妙地将城墙东南作直角向内弯曲,将曲江北半筑于城内,南半更大的凹陷地带隔于城外,并对凹陷进一步开凿加深,建起隋文帝亲自命名的皇家禁苑“芙蓉园”。
大唐初期也多承隋制,在接收隋所营建的新都后,将芙蓉园继续作为皇家禁苑,城内池泊则恢复曲江旧名。曲江从秦之隑洲、汉之宜春、隋之芙蓉,一路走向其最兴盛期的大唐。
唐代的曲江,从文化角度说,是长安城东南隅以曲江池为中心,由附近相邻名胜共组的游览胜地,包括曲江池、芙蓉园以及侧邻的大慈恩寺、大雁塔、杏园、乐游原、青龙寺。有湖池有冈原,有园林有寺院,有皇家登临的紫云楼,有文人登高的大雁塔,是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皇族、百官、进士、商人、僧侣、百姓聚集游览的园林和文化胜地。
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驾临芙蓉园,太子李治在此修建了大慈恩寺,从西域归来的玄奘法师在寺内修建了大雁塔。武则天和唐睿宗时,乐游原成为京城又一游览胜地,原上寺庙也改名青龙寺并成为佛教密宗重要寺院。日本空海和尚来长安即在此研习佛法。
唐中宗、睿宗时,开始了春日游幸芙蓉园,且有宠臣、学士侍宴的活动,并一直延至晚唐。皇帝赐宴臣僚,唐时文人多渴盼之,视为恩宠,并多有诗词记述。李峤曾写“今日陪欢豫,还疑陟紫霄”;宋之问写有“侍宴瑶池夕,归途茄吹繁”;王维有“万乘亲斋祭,千官喜豫游”;李绅有“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
唐中宗神龙年间,形成了新科进士饮于曲江、宴于杏园及雁塔题名等文化习俗,曲江的文化色彩日益浓厚。尤其是到了玄宗的开元天宝年间,皇帝游幸芙蓉苑与百官宴饮曲江池、进士欢醉杏林园、万民曲池皆若狂等,都达到了鼎盛阶段。曲江也一举成为盛唐长安文化荟萃之地,唐诗长安文脉汇集所在。
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
风流天子李隆基携宠妃杨玉环登上了芙蓉园里高高的紫云楼。
携妃立玉楼的他,既喜欢南眺南山秦岭的俊秀俏伟,更喜欢北俯城内曲江池畔的万民乐游。
他不知道,他和他“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贵妃,此后也成了历代文人歌咏的“风景”。他俩“玉楼宴罢醉和春”的大明宫、华清宫、芙蓉园,既是大唐兴盛的象征,也是后人哀怨的对象。
但也正是这个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在他统治期间,将曲江无论是从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推上了历史的巅峰。疏浚了汉武泉,凿修了黄渠引南山义谷水注入芙蓉园和曲江池,使曲江一带水面大增。同时大兴土木,兴建了大批亭台楼阁。李隆基特许中书、门下、尚书等衙署在曲江池营造楼台亭榭,而在芙蓉园内则修建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广厦修廊,连亘屈曲”。
紫云楼高筑于芙蓉园北苑墙上,极大地满足了李隆基喜欢高俯万民的心理。李山甫曾写“南山低对紫云楼,翠影红阴瑞气浮”。为了方便李隆基能随时携嫔带妃到芙蓉园游玩,还专门修建了一道“夹城”:从长安城北的大明宫沿东城墙内侧,向南修了一条和东郭城平行,连通兴庆宫和芙蓉园的复道。夹城的宽度、高度皆与东郭城相同,遇城门处则设置蹬道,逾城楼而过。
对此,唐代诗人多有诗词反映,崇尚和讽喻中,都足见开元之盛及明皇本人对芙蓉园之喜爱。
杜甫曾写:“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李贺曾嘲:“军装宫妓扫蛾浅,摇摇锦旗夹城暖。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李商隐曾思:“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最著名的当属晚唐杜牧的“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南苑草芳眠锦雉,夹城云暖下霓旄”。
当然,李唐皇帝在自己游幸的同时,也很看重百官同娱和万民同乐。尤其是每逢农历二月一日中和节、三月三日上巳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三大节庆,皇帝在游幸时,不仅会赐宴百官,还会给臣僚放假并发放赏钱以供欢娱。《剧谈录》载: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皇室游幸、百官赐宴,推动曲江不断发展成长安最负盛名的游览胜地,三大节日也于此后越来越成为唐人生活中的盛事。春日踏青、夏日赏荷、秋日登高,一年至少三季游人“多绕曲江头”。
这其中,正逢春时的上巳节最为引人入胜。当此之时,长安百姓会蜂拥而至曲江池畔踏青游春,修禊、赏花、插花、折柳、泛舟、乐舞、秋千。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上巳曲江滨,喧于市朝路”“鞍马皆争丽,笙歌尽斗奢”。
生性热闹的唐玄宗此时常携妃游幸芙蓉园,并引领时尚潮流。《开元天宝遗事》曾载玄宗亲手插花宠妃: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把鲜花插在美女头上能助长女性的娇艳和媚姿,一时插花之风盛于长安。
李山甫诗曰:“争攀柳带千千手,间插花枝万万头”。杜牧也有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当时的曲江:桃红柳绿,百花争艳,人流似潮,车马如聚,处处笙歌艳舞,遍地酒宴欢颜,多少王孙公子游逸,多少佳人丽女情长。
唐诗为证:许棠“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刘驾“池边草未干,日照人马来”;赵璜“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章碣“无穷罗绮填花径,大半笙歌占麦畦”;罗隐“江花江草暖相隈,也向江边把酒杯”;薛能“狂遍曲江还醉卧,觉来人静日西斜”……
李唐皇室风流多,大唐百姓也开化。尤其是春日踏青之时,最是男女青年碰撞爱情火花之日。先秦时流行的青年男女仲春会于“桑间濮上”的习俗,在唐代开放的环境下也渗透到上巳春游中。男女青年在此一见钟情,回家禀明父母后纳聘成亲者不在少数。更有一些勇敢女子看到喜爱的男子,“爱把长条恼公子,惹他头上海棠花”,用柳枝敲惹对方,以示爱慕兼表心意。
此类故事,唐人多有记载。最让人心醉又心碎的爱情故事是崔护的“人面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那个大唐啊,那真的是一个很“风流”的时代。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相较韩愈来说,白居易真是少年得志。
不说十九岁时即以“离离原上草”名动京城,单以科举来说,白居易是一举中的,还是“十七人中最少年”。而韩老夫子却是个“老补”,补习多年,先后考了四次,最后才在25岁时登了进士。
此后的宦途,韩愈也多有不顺。唐时,中了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要经过吏部的关试选拔,成功后才授予官职。关试白居易也是一次成功,官授秘书省校书郎。而韩愈就悲催多了,又一连三次不中,只好收拾行装离开长安,转而先去给他人当幕僚谋生。
中进士,对唐代的读书人那可真是“十载寒窗”后的大喜事,后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故事都由此衍生。孟郊的《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读书人登科中进士后的狂喜。
有喜自然要有庆。由此掀起了登科进士曲江游宴活动的高潮,并逐渐演变成:曲江赐宴、杏园探花、雁塔题名、曲江流饮等众多风流雅事,从而赋予了曲江浓厚的风流氛围,曲江在此后不再仅仅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成了一个文化名词。
朝廷于曲江赐宴进士,韦述《两京新记》曰:“唐开元……后以进士每年登科第赐宴曲江。”这种赐宴活动,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到唐末僖宗乾符年间,170余年基本没有中断。
杏园探花,《秦中岁时记》记载:“春时,进士杏花园初会,谓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此时之长安,城中公私园林大都向进士开放,为他们提供遍赏名园、选摘名花的便利。张籍曾有诗赞:“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翁承赞有“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徐夤有“须知红杏园中客,终作金銮殿里臣”。
雁塔题名,《唐摭言》记载:“神龙以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唐国史补》卷下曰:“既捷,列其姓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所题之名“妙有行列,婉若雁阵”。很快,雁塔题名就等同于金榜题名了。
一举及第的白居易曾很得意地题诗记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来,一些举子甚至考试前要在雁塔题名“进士某某”以博取好彩头,待及第后于名前再加一个“前”字。时人曾有诗曰:“曾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此后就进入高潮——“大宴于曲江亭子”的曲江大会。曲江大会也是一个举国盛游的日子,上至皇帝“御紫云楼,垂帘观焉”,下至百官公卿、商人平民,“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此时的曲江,车马填塞,冠盖云集:商人蜂拥而至摆摊设点,兜售商品;长安百姓争相往观,且游且购;公卿贵族携眷观光,乘机挑选东床,物色佳婿。
作为主角的新科进士们,气宇轩昂,风流倜傥,探花题名又酒宴,美馔佳肴歌舞伴。雍裕之《曲江池上》:“殷勤春在曲江头,全籍群仙占胜游。何必三山待鸾鹤,年年此地是瀛洲”;刘沧《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归时不醒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风流人物自风流。宴饮之时,进士们将东晋兴起的“曲水流觞”发扬到极致,成就了新的“曲江流饮”。一些进士甚而“癫饮”。《开元天宝遗事》载:进士郑愚、刘参、王冲等十几人,携妖艳艺伎三五人,于花木繁茂处席草而座,开怀畅饮,且常脱衣除帽,甚至于赤裸、狂笑、斗酒、喧呼,自称作“癫饮”。
曲江大会之盛,屡见于唐人记载及进士们自写诗词。白居易第二年还写诗追记:“去岁欢游何处去,曲江西岸杏园东。花下忘归因美景,尊前劝酒是春风。”
相反,屡试不中的韩愈,在中进士后就几乎没有这样的诗词。可能他不甚喜欢让他屡遭磨难的科举。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曲江的喜爱,否则也就写不出“曲江水满花千树”这样的佳句。
唐朝的文人啊,没有不喜欢曲江的。“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的曲江,是和唐诗同起共兴的文化高地,曲江给了诗人无穷的创作灵感,唐诗则让曲江此后一直都是中国文人心中的文化胜地。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韩愈老夫子一开始是压根就瞧不上白居易的。
最终艰苦奋斗成文坛领袖的韩愈,听说白居易也号称学杜甫,很不以为然。他心里暗想:你那些写给不识字老婆婆的诗也敢说学杜甫?此外,李白也是韩愈推崇的对象,但却遭到了白居易好友元稹的非议,这让韩愈很长时间都对元白二人无好感。
虽然白居易的诗在当时很流行,但在韩愈看来,流行的不一定好,不就是些“老妪能解”的大白话歌谣嘛!于是针对元白二人不客气地写诗讽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让白居易百口难辩。
韩愈和白居易争学杜甫,足以说明杜甫的影响之大。同样的,在唐代众多写曲江的诗词中,杜诗也从一开始就引领了风骚。
长安十年,杜甫常居于曲江南的少陵原畔,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少陵野老”。虽然此时的唐王朝,开元盛世繁华渐谢,天宝危机已露端倪,而他本人也常生计无着、穷困落魄,但他依然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四处奔走。
他常常往来于曲江一带,甚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他的曲江诗,在悲天悯人、忧国忧民、讽刺讥喻的同时,时见绝美佳句,有的甚至字字珠玑。
《曲江对酒》中有个灵动画面:“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二首》中他语出神奇、画感十足、动感万分:“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他在讽刺“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的同时,却又写出脍炙人口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一次行游曲江时,杜甫和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同登大雁塔,因五人都有佳作而成千古佳话。其中岑参写道:“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则落笔时代,感慨时政,意蕴最厚:“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这样的杜甫,让韩愈和白居易都推崇备至。不过二人经历不同、文风不同,对宦海浮沉心态不同,当时的文学主张也有差异。
幸亏诗人张籍!就是曾写出“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张籍。他和韩白二人都是好友,且知道是韩愈错怪了白,于是白居易一有新诗写出,他立马就拿给韩愈看。韩愈后来就越看越欣赏了,也有了缓和矛盾并多交往的念头。
但自己毕竟写诗骂过人家,他又不便屈身,于是就写了一首诗让张籍带给白先试探:“墙下春渠入禁沟,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流到池时更不流。”
白居易一看就明白了,马上提笔写了一首回诗:“渠水暗流春冻解,风吹日炙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二月因何更有冰。”意思是有您韩吏部吹来的春风,咱俩之间还能有什么“冰”啊!两位大文豪在朋友的帮助下最终“冰释前嫌”,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
第二年春天,当岸畔多柳的曲江池又“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时,韩愈通过张籍向白居易发出了同游曲江之邀。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
韩愈把“约会”地点选在曲江是很自然的。
唐代文人有邀约同游曲江池的“文俗”,留下了很多邀游唱和诗。韩愈和张籍之间,张籍和白居易之间都常诗邀诗答。
虽然在科举中屡试不进,但韩愈在长安“复读”时就常和朋友在曲江游吟。此后无论是官居长安还是贬职他乡,曲江都是他常游常忆之所。除了“曲江水满花千树”,他还写有“曲江荷花盖十里”“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等佳句。
至于白居易,那就更是个“曲江通”了,30多首曲江诗词明证了他是多么喜欢曲江,既有“独行独语曲江头”,更有同游同醉同联句。
太和二年,白居易与刘禹锡、崔群、李绛四位诗人分离多年后重聚曲江。他们一时兴起,各吟诗一句,联成一首七律: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崔群)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李绛)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白居易)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刘禹锡)
白居易与“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多是曲江池”的挚友元稹,还有一段佳话:元和四年春,元稹被朝廷派往东川。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诗人李杓直同游曲江。他心里默念着元稹并作诗一首:“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十多天后,梁州信使带来了元稹的信:“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白在曲江想念元并且算他到梁州时,元稹在梁州正梦见和白等同游。
曲江,留下了太多唐人的逸闻趣事。但中唐时的唐朝已经过了顶峰。中唐诗人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之后,唐朝国势日微,曲江和唐诗也一起下滑衰落。
“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来了。终生郁郁不得志的他,经历了晚唐六朝更替,凄美的诗句中更多的是怅惘和哀伤。
他在暮秋独游曲江:“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经常“向晚意不适”的他,常常独自“驱车登古原”:“春梦乱不记,春原登已重”“万树鸣蝉隔岸虹,乐游原上有西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夕阳晚照的晚唐,曲江池盛景逐渐衰落,连池水都逐渐缩小。
公元904年,朱温挟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宫室房屋,木料“浮渭河而下”,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曲江也不例外,当年竟泉水自竭。至北宋时,曲江已全部开垦种植,成为农田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如今的西安,曲江再次迎来了“天文同丽日”。2003年,西安市成立了“曲江新区”,曲江驶上发展快车道。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大唐不夜城等标志性景区相继建成开放。
目前的曲江新区,已是陕西省、西安市确立的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是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承载区,是我国西部重要的文化、旅游集散地,陕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标志性区域。
2020年4月22日傍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江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与市民百姓互动。当晚的曲江,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大唐盛景和现代景致交相辉映。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为什么爽约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下雨了,率性的白居易觉得雨天不好玩,就没有去,但最真实的理由还在他随后的回诗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蹋雨曲江头。
意思是:我家小院子里的红樱树正逢花时,随便绕一圈就是很好的春游啦。您老人家现在正当红,吹捧您的人太多,我可不想在这时候去凑热闹,跟随在您的鞍马后,冲泥又踏雨的。
这个白二十二舍人,可真够率直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