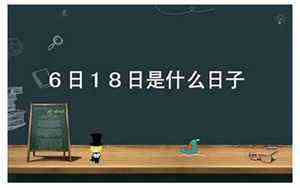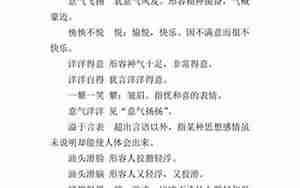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在正确区分“体用”、“道文”
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点难点在区分道文、体用,弄懂道文、体用关系。当前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认知,最大问题就是混淆“体用”、“道文”,错误地把临时性、具体的、多变的“用”、“文”的东西,当成了中国文化本身,甚至当成了中国文化之核心。
中国文化的总体模式,或基本特征,可以用“文以载道”来概括。这里的“文”,并非仅仅指文章,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外在表现。“道”则是指人的内在原则、理念,用来指导外在的行为。
可以把文、道问题,概括为“道文之辩”。就实质内涵而言,“道文之辩”,与“心物之辩”、“义利之辩”、“体用之辩”、“知行之辩”、“意象之辩”等同,谈论是同一个问题,只是侧重不同、视角不同。“道”就是“心”、“义”、“体”、“意”、“知”,“文”就是“物”、“利”、“用”、“象”、“行”。
“道文之辩”有点类似于现代汉语中所说的现象与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文”对应于现象,“道”对应于本质。只是,在实质内涵上,“道”与“本质”之间存在质的不同。“道”有双重含义,既有真理含义,又有心性含义,但是,本质则仅有真理含义,而无心性含义。
“心物之辩”的经典表述是“心物合一”、“心物不二”,这是王阳明的著名观点。“心”是思考主体,“道”是心的思考结果。“物”是做事、事件,人做事是在心的指导下进行的,具体说来就是由通过思考所发出的“意”所指导。或者说,“意”就是心对人所发出的做事指令。
因此,“心物之辩”实际上是把“道文之辩”具体化了。道是由心所发出,做事则形成了文。
这样以来,“道”,就是“心”,就是“意”。“心”是人思考认知主体,其存在是逻辑上的、功能上的、软件上,也是虚拟的,与生理上的心脏、大脑无关。心脏和大脑都是硬件,心则是软件。
作为“道”的意,并非指个人的一般意念、意志,而是自然、本然的“诚意”,也是作为普遍共识的“公意”。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诚意”,与社会的“公意”是等价的。这意味着要或者社会之“公意”,并不需要全体人员去投票,这是向外索求。而只需要向内索求,即通过学习认知自己的本然心性,去“诚意”。
《大学》的“八条目”的学习方法就是基于这已基本原理。《大学》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
“诚意”就是恢复自己的本然心性,然后通过这个本然心性去思考和判断。或者说,“诚意”就是由本然心性所发出的意。何为本然心性,就是排除任何外界干扰的本性,主要是排除当时的不良的社会风俗、风尚的影响。
“意象之辩”的意,就是“诚意”的意,与“道”、“理”、“义”等同。“意象之辩”的直接提出是在易学中,即在对《周易》的研究中。这里的“象”就是卦象,“意”就是“道”。“意象之辩”的核心观点是“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象”。
从狭义的符号学角度,“立象以尽意”与“文以载道”等同,象是文,意是道。“得意忘象”是在强调在意象关系中,意是本体、本质。
但是,“立象以尽意”和“文以载道”,都具有更广泛、更久远的内涵,象可以指代一切的人的外在行为,一切的社会现象,意则是这些行为和现象背后的心性动力。
王阳明之所以把“诚意”看成是《大学》的核心,进一步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这个“诚意”就是道,从而,学习、求道,实际就是一个“诚意”过程,即通过学习来摆脱世俗的影响,来认知、感悟自己的超越时代影响的本然心性。
我本人,也认为中国文化的最核心、最微妙、最难懂的地方就是“意”,因为我将自己的学问概括为“蔡氏意学”。
“格物”就是具体的学习过程,“致知”就是获取知识,获取道。这个“知”就是本然心性,就是“良知”,因此“致知”就是“致良知”。这里的“良”,主要并非善良、好的意思,而是自然、本然的意思,即孟子说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不学”即不受外界的影响。
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知”就是“道”、“意”、“心”、“体”、“义”,“行”就是“文”、“象”、“物”、“用”、“利”。
“义利之辩”是在强调做事中的判断、选择,是实践性的,是行道。“义”就是在做事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利则是有利的具体行为、具体落实。因此说,“义者,宜也”,合宜与否义,是一个判断过程。义是基本原则,利则是考虑就到具体的环境,就是以基本原则为前提,对具体环境最有利的选择。
“义”就是“道”、“心”、“意”、“体”、“知”,“利”就是“文”、“物”、“象”、“用”、“行”。
“体用之辩”,是在强调本体和本体的作用、效用之区别,让大家去识大体。“体”就是“道”、“意”、“义”、“心”、“知”,“用”就是“文”、“象”、“利”、“物”、“行”。
总结一下,“义利”、“道文”、“心物”、“意象”、“知行”、“体用”这些不同的成对的说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在讨论一个问题。说“义利”,一定包含着“道文”、“心物”、“意象”、“知行”、“体用”,对其他任何一项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共同中国文化之内核和轴心,要搞懂中国文化,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彻底搞懂。
进一步,也可以把这些问题概括为“阴阳”问题。“阳”就是“义”、“道”、“心”、“意”、“体”、“知”,“阴”就是“利”、“文”、“物”、“象”、“用”、“行”。
狭义地看,“阴阳”象“意象”一样,也是易学问题,因为研究易经而提出,但是具备更一般的意义。在“阴阳”中,是阴阳合一、阴阳不二的,同时,也是阳体阴用的,阳是根本。
因此,要把握中国文化,关键区分体用,抽象的、超越的、永恒的“道”、“意”、“义”、“心”才是体,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核,而“文”、“象”、“利”、“物”则是用,是具体的、临时的、多变的。
中国哲学:如何理解孔子所讲的“仁”?
在西方哲学史上,“现象”与“本质”是两个重要的范畴,哲学家们认为“本质”是比“现象”更为深刻的东西,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与此不同,中国人更为关注的是“本体”与“效用”的关系,即“体用论”。体用的意思并不难理解,邵雍在《渔樵问对》里就打比方说木柴是体,火便是用;水也是体,而湿则为用。朱熹则说眼睛为体,观看为用;耳朵是体,听觉便是用。
体用论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为“本体”,这个本体无所不在,“百姓日用不知”。由阴阳叠加便成为六十四卦,每一卦也都是“体”,上古之人根据《离卦》发明网罟、根据根据《涣卦》刳木为舟、根据《大壮卦》修筑宫室等等,都是从本体中引申出效用。《老子》也同样将“道”作为体,并且说它“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后世的哲学家大多继承了这种观念,但是他们对本体的解释却各不相同,例如扬雄说本体是“玄”,王充认为是“气”,王弼则说是“无”,而裴頠主张是“有”,佛教盛行后又有许多人认为是“空”。到了宋朝,周敦颐主张本体是“太极”,邵雍则复兴了“道”,张载重申了“气”,司马光则提出了“虚”,在这种背景下,程颢也构建出洛阳学派的本体论,他认为真正的本体应是“天理”,为了说明它,需要先懂得“仁”,这便是《识仁篇》的任务。
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
什么是孔子所说的“仁”?孔子的思想中有两个范畴摆在核心地位,一是“仁”,二是“礼”。他向往西周制度,继承了文王、周公所制定的“礼”,同时又独创出关于“仁”的思想来。
根据《左传》的记载,在孔子之前已经有许多人说到“仁”了。例如五父劝陈候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子鱼辞去王位时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庆郑劝晋候说:“幸灾不仁。”叔向写给子产的信中也说:“守之以信,奉之以仁”等等。可见“仁”自古以来就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类似于善、好的意思。
可以说,孔子是首位把仁视为第一美德的人,《文言》中将仁对应元,认为它是“善之长”,并说“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这样仁便被提升到了首要的地位。而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也非常多,但孔子并没有直接对仁的涵义进行诠释,反而是教导弟子们怎样去达到仁的境界,也就是“求仁之方”。
当颜回向孔子问仁时,他只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这是通过外在之礼来求得仁;
当仲弓问仁时,他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又是通过内在之敬恕来求得仁;
当樊迟问仁时,他直接解释说:“爱人”,这是告诉弟子仁的对象是他人;
在《孔子家语》中对仁的解释以及求仁的方法记载得更为详细,孔子说:
“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乎知贤。”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爱近仁。”
“夫温良者,仁之本也。”
在孔夫子看来,温和善良是仁的基本。善良的人会善待自己也会热爱他人,因此仁的意思与爱相近,但爱的内涵过于宽泛,而且不分亲疏,容易变成无差别的泛爱、兼爱;仁则讲究层级与次序,所爱的对象要从父母亲人开始,然后才到亲戚朋友,进而推及众人与天地,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有若和孟子从近处求仁,才说“孝悌为仁之本”以及“亲亲,仁也。”韩愈则从远处求仁,说“博爱之谓仁”;张载的《西铭》也是沿着韩愈的逻辑来求仁,先讲天地是我的父母,万民是我的同胞,所以我要博爱万物。然后再由大到小,从博爱到亲亲,讲到孝悌。
孔子说“仁”
程颢:“仁”就是与万物为一体程颢的《求仁篇》是在《西铭》的启发下写的,他的逻辑思路跟张载一样,要先论述大体,然后再具体分析。全文仅三百余字,它的核心思想是要确立仁的根本地位,解释仁的含义,并教导儒者们怎么去求仁。
在《定性书》中程颢提出了“天人本无二”的思想,从高度同一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一”,是唯一的一个本体。万物之间只是在同一个本体之中呈现出来的差异,就像手和足之于身体一样,手足形态不一、功能不同,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万物虽然千差万别,品类繁多,但也同归于一个本体之中,程颢认为这个本体就是“理”。所谓的“识仁”实际上就是要懂得这个“理”,并加以运用。
只有先了解了“仁”,我们才能够理解“理”。如果缺乏仁的观念,就容易将万物视为各不相干、彼此孤立,没有共同本体的东西。程颢认为先儒都没有讲清楚仁的意思,他们误把“仁之方”与“仁之体”混为一谈了。例如孝悌是仁的基本功,要从亲亲开始,才能仁民爱物,所以孝悌只是仁之方,而有若却说“孝悌为仁之本”,使人误以为孝悌是仁的基本内核。对此程颢反驳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孝悌只是“仁之方”,是践行仁的基本方法,但并不是仁的本体。那么仁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程颢认为张载的《西铭》已经讲清楚了,即“《订顽》,意极完备,乃仁之本也。”《西铭》早就告诉我们,人是天地所生,与万物同根同源,因此每个人都要仁民爱物,这就是“仁之本”。程颢对此加以发挥,他说: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也。”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
“仁则一,不仁则二。”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是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
所谓的“仁”就是将个人与万物视为一体,将自我与他人视为一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度的同一。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爱我之心推及他人,做到大公无私。如果我们能将万物视为自身,将他人视为自我,那么我们就会像爱护直接的躯体一样去爱护他人,因此“爱”就由“仁”产生了出来,“仁”是“爱”的原因,仁是体,爱是用。拥有这种仁爱的观念,我们才能领悟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的道理,并理解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意思。
如果不能理解“仁”,无法做到“反身未诚”,仍然将人与天地割裂开来,便是“二物有对”,即使“以己合彼”,依然不能得志。
医家常说“麻木不仁”,意指肢体麻痹,失去知觉,神经在手足之间无法传导,所以即使断手去足,患者也无切肤之痛,因为他认为被砍去的这只手不是自己的。对于那些心地不仁、不识义理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不知道天地万物与自己的关系,所以才加以残害,就像一个人挥刀砍向自己麻痹掉的手足一样,害人其实就是害己。所以程颢说:
“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
“天人合一”论者没有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没有认为到“万物皆是一个天理”,依然是将人视为跟物不同的东西,然后再强行去合一,就像把别人的手足接到自己的身上一样,没有达到真正的“仁”。
“万物皆是一个天理”
程颢与其师周敦颐的理论分歧程颢认为儒者所说的圣人就是达到了“至仁”境界的人,这种人把“天地”视为自己的身体,将万物视为我的四肢百骸,从而至公至正地去爱护它们。只要在内心中树立仁的观念,并将仁视为本体,那么其他的美德如义、礼、智、信也就都能够从中生出来,仁是全体,四者是四肢,它们合称“五性”。
学者要想学道,就得先识仁,先领悟“浑然与物同体”的道理,摒弃物我为二或天人合一的观念,然后用诚敬来修持这个新的价值观,不使其发生动摇。“无妄之谓诚”,诚就是诚实的、真实的看待自己,反思自己,不再把个人的私欲杂入其中,不再自欺欺人,能领悟“天人无间断”的道理;敬则是恭敬、敬畏,在这里程颢否定了周敦颐的思想,周敦颐主张的是“静”,而程颢代之以“敬”。周敦颐说“无欲故静”,没有欲望就能不为物所侵扰,对此程颢反驳说:
“才说静,便入于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静字,便是忘也。”
《孟子》曾告诫人们要“心勿忘,勿助长”,要想修行德性、养成浩然之气,就不能揠苗助长,但也不能忘而不管。周敦颐主静,已经偏向放任不管了。程颢则认为需要做涵养的功夫,时刻恭敬待人,并保有敬畏之心。他批判那些主静的人非得追求“身如枯木,心如死灰”的境界,如果人没了欲望,只是一块木头一样,那跟死人还何区别?因此,“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人不如以敬畏之心来整肃自我,以恭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人。如果人的言论和形象不庄不敬,那么鄙诈、怠慢之心就会生成了。因此,弟子谢良佐才说“明道先生......先使学者有知识却从敬入”,在程颢看来,以其做外在的礼节功夫,不如从内在的敬畏之心入门。
“诚敬”是程颢思想的入门,也是修行的基本方法
当我们明白“浑然与物同体”的道理后,就要用诚敬的态度来涵养此观念。不心生懈怠,也不须盲目穷索,一切都会“存久自明。”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困难只在于如何持守。“浑然与物同体”的道理其实就是领悟“万物皆是一个天理”,既然我们将万物视为自己的四肢百骸,那么自然而然的要仁民爱物、博施济众了,这乃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程颢的体系中,“天理”虽然是最高的范畴,是唯一的本体,但他认为“此理至约”,非常简单,不需多说,“惟患不能守”而已。因此,“诚敬存之”反倒是他最想宣扬的原则,他说:
“如天理底意思,诚只是诚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也,非是别有一个诚,更有一个敬也。”
诚敬的对象是天理,天理意味着“浑然与物同体”的道理以及从这个道理中引申出来的诸多义理,至仁之人掌握了天理,也就成为儒者心目中的圣人。对“天理”进行研究,便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