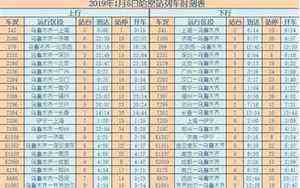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刘群华:北京时间
刘群华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家伙。记忆中好像炫耀一块手表比如今炫耀一辆小车更诱人。
父亲戴的一块上海牌机械表是村里的第一块手表,按邻居最朴素的话说,呱呱叫。父亲呱呱叫的手表一度是他身份显贵的象征,他穿着一条部队里的蓝咔叽裤,还有一件蓝咔叽上衣,手腕上晃动着一块银色的手表,往卖火车票的窗口一伸,窗口的手再挤再乱再多,卖票阿姨总会优先找到戴手表的那只手。
那年头,村里人若碰到父亲,问的第一句是:“子光,几点了?”父亲此时内心无比膨胀和骄傲,十分享受这种被人捧的飘飘然感觉。他徐徐抬起手腕,放在眼前一亮,道:“12点30分。”接着吞了吞口水,喉结滚动几下,补充道:“差几秒就31分了。”
其实那时的表不太准,很少对得上广播里的北京时间。父亲为了让手表准时,便在早上七点、晚上六点各对一次广播里的北京时间。
对时间是父亲每天的必修课。有一回乡里的广播因断电停放,父亲就走路到别的乡听广播对时间。他抽着旱烟默默蹲在广播电线杆子下呆呆地等,听广播听得两耳发闷,昏昏欲睡,突然广播里清脆地嘀嘀嘀三下,一个女音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报时,现在北京时间六时整。”父亲赶快摘下手表,转动小螺母把时间对准六时,这才慢慢起身回村。
本世纪初,我长大了,用打工的钱买回全村第一只手机,这时,村里的机械表感觉到了危机。这种莫名的感觉是窒息的、新鲜的、陌生的。父亲的旧观念此时还颇根深蒂固,盯着我的手机左翻右看,甚是好奇,发现这家伙既可以通电话,还替代了手表的功能,且显示的北京时间相当准。当手机陆续打破故乡人对机械表北京时间的依赖,以父亲为代表的那代人没有优越感了,心里就顿时空落落的,有些许的惊慌,不久就在背后议论,说我手机里的北京时间不太准,准也是一天只准两次。
这些幼稚的心态或者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碰撞的必然的火花。
有一天,村头另一个小伙也带回了一只手机,村里老人依然质疑他手机北京时间的准确性。小伙子觉得老人是羞辱他,便勇敢地与他们比起北京时间来。比赛是在他与一名老人之间进行的,围观的邻居很多,约定以一个收音机上报送的北京时间为准。
那天大雪纷扬,他们围在火炉边静静地等着那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报时,现在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大伙分一拨盯着小伙的手机,分一拨瞅死老人的机械表,兴致勃勃似乎在见证一次伟大的发现。结果老人的手表慢了一分钟,小伙子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与收音机上的北京时间分毫不差,准确极了!那位老人算是输了,因此萎靡不振。老人们很在意80年代上海机械表的兴奋和满足,当年梦寐以求的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他们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上海牌机械表逐渐淡出了故乡人的视线,手机开始充盈大街小巷和村庄。那些过去失落的老人开始释怀,跟着年轻人的脚步玩起了手机。
我一个表兄一直务农,近年靠农作物与城里人做起了电商生意,前年买回了村里第一辆小车奥迪。这么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马上传遍了附近的几个村,几多漂亮妹子一夜之间悄然仰慕起我的表兄。我的一个邻居满脸堆笑地走入我表兄家,不久表兄恭恭敬敬地送她出门,她则说:“放心,包在我身上。”结果,不久我就作为迎亲队伍中的一员,在一个春色迷醉的上午,从山那边迎来了我那漂亮贤惠的表嫂。
那天,作为婚礼主持人的我父亲掐着良辰吉时,不断盯住手机上的北京时间。可有几个老人却看我父亲焦急的样子不顺眼,说:“我们最讨厌子光了,狗爪子拿一只破手机,还在亲戚朋友面前扫来扫去,问现在北京时间多少了,他不是握着一只手机么!”逗大伙笑得前俯后仰。
几年前,村里有个人买了辆较好的小车,车上带有表盘,才买回的那天,此人决定开小车在集市上隆重亮相,风光风光。可当他把小车开到集市上时,熙熙攘攘的邻居们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他及他的小车,于是此人满腹委屈,终于想出一条妙计,掸了掸西服上的尘土,扶了扶领带,快步走到卖蔬菜的邻居面前,问:“现在北京时间多少了?”邻居道:“不知道,没看表。”此人傻傻地笑了笑,说:“哦,那我去看下我小车上的北京时间。”邻居这才恍然大悟,道:“买了小车啊,该庆祝庆祝!”
小车在村里越来越多,村子在愉快的时光中更新长大,村里的人有时在满满的幸福面前竟然不知所措。父亲说:“我真没想到会过上如今美满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出门是小车,生病有报销,时代这么好,人活这一辈子足了。”
父亲的话,是千千万万农民最质朴最善良的心声,让我想起30多年前他的那一块手表,表上的时间指针载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每一小步,所有的进步和变化,都在北京时间里一点一点地描绘着,灿烂地展现出五彩缤纷、磅礴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