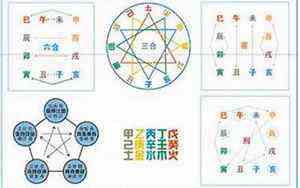从鲁迅兄弟与郁达夫兄弟的矛盾,说说丧父对他们兄弟之情的影响
一
1987年,作家韩石山拜访郁达夫长子郁天民,谈到二三十年代浙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文化名人,郁天民说:“这些人大都是,一,家道中落,二,寡母抚孤,三,个子都很矮。”韩石山对第三项不太明白,问郁天民为什么,郁天民说:“个子矮小的人狠呀!”
我觉得,郁天民说这样的话,是有些玩笑成分的,但也不是随口而说,而是建立在对浙江一带文人了解的基础上,尤其是对近代文学的两位大腕鲁迅和郁达夫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个子矮小的人,气势上、力量上达不到“不怒自威”的效果,便要在“稳、准、狠”上下功夫。当然不是所有“个子矮小”的人都“狠”,我见过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人,也见过个子不矮小肚鸡肠的人。
我觉得“个子矮小的人狠”是以“家道中落”“寡母抚孤”为前提的。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如果鲁迅没有家道中落,是个富家少爷,他所见都是伪装出来的笑脸,虽然虚伪,总是暖的。“家道中落”,别人就没必要伪装,原本是什么面孔就使出什么面孔,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便看得真。“寡母抚孤”是“家道中落”之后的又一打击,父权时代,没了“父”,就像塌了天,未成年的孩子,就要充当起“父”的角色,肩膀小,担子重,心里怎能不悲苦。
有了两个“苦”的大前提,再添上一个“个子很矮”,才是雪上加霜。
哪个人承受着这三重痛苦,也会心中充满郁愤之气,如果他恰巧有文学天赋,这种郁愤之气就会化为笔下文字,倾泄出来,为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
至少从鲁迅和郁达夫的情况来说,郁天民的说法是成立的。
鲁迅与郁达夫都具备“家道中落”“寡母抚孤”“个子很矮”三个要素,他俩的文学成就,也与这三要素有很大关系。
二
鲁迅与郁达夫脾气都不算好,但是他俩特别投缘,对郁达夫来说,鲁迅像大哥一样可敬,对鲁迅来说,郁达夫像小弟一样恭顺,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鲁迅、郁达夫与自己的亲弟或亲兄反而关系不好,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矛盾世人皆知。兄弟两人的决裂过程天崩地裂,周作人修书一封与鲁迅,宣布与鲁迅断绝兄弟之情,鲁迅只好带着母亲和妻子搬离八道湾大院,赁房另居。鲁迅回去取自己的书和物品时,遭到周作人夫妇谩骂殴打。
居住在八道湾外院的章廷谦亲眼目睹了这次风波,他听到周作人的骂声,赶过去劝架,见周作人拿着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正要向鲁迅身上砸过去,章廷谦一把抢了过来。
不管周作人拿着铜香炉是威胁鲁迅也好,还是真的想砸鲁迅也好,兄弟闹到这份上,都是不留情面了。
此次风波过后,鲁迅与周作人再无来往。
直到鲁迅死去,周作人也没有给哥哥奔丧。
郁达夫与大哥郁华也发生过冲突。郁达夫也像周作人那样写信与大哥“绝交”,他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沉沦》中写道:“他恨他的长兄,竟同蛇蝎一样。”
郁达夫兄弟
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的原因,至今没人弄明白,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人把矛头指向鲁迅,与他俩关系不远不近的人把矛头指向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一说与闺房秘事有关,说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与羽太信子有旧情,只是因为已经订婚,于是把羽太信子介绍给弟弟周作人,又说鲁迅曾经偷窥羽太信子洗澡,在羽太信子卧室下“听窗”,羽太信子之弟说他亲眼看见鲁迅与羽太信子在榻榻米上相拥。
另一说与家族琐事有关,诸如:羽太信子生活奢侈,花钱如流水,招致鲁迅不满;鲁迅私拆周作人信件,导致周作人不满。羽太信子性情不好,经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造谣生事,挑拨兄弟两人的关系。
鲁迅兄弟与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
以上之事,皆发生于家庭之内,环境隐秘,外人很难知道原委。只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郁达夫与大哥郁华的矛盾非常清晰,就是因为大哥管教他太严厉,在他看来,大哥是在“欺负”他,“待他苛刻”。
郁达夫初到日本,母亲和大哥都希望他学医,郁家祖上几代行医,学医是继承家族传统,这个职业也容易就业。郁达夫放弃医学,改学文科,大哥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郁达夫心中愤懑,写信与大哥“绝交”。
郁达夫把这些细节写进他的小说《沉沦》之中,这固然是郁达夫向来有自曝隐私的恶习,也是因为他与大哥“绝交”的原因是常见的兄弟矛盾,并非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
郁达夫虽然一时气愤与大哥“绝交”,内心里,他还是依恋大哥,经济上,他也要依靠大哥,很快就跟大哥和解了。
三
探寻鲁迅兄弟与郁达夫兄弟失和的原因以及最终不一样的走向,我觉得应该从他们的原生家庭说起。
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之大,是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承认了的。兄弟之情基于共同血缘与共同的成长环境,更要从他们的原生家庭谈起。
鲁迅与郁达夫都“家道中落”“寡母抚孤”,看似差不多,实际上两家情形还是有很大不同。
鲁迅所说的“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如同一个亿万富翁跌落成了千万富翁,原本开劳斯莱斯,现在只能开旧宝马。郁达夫家是原本开宝马,“陷入困顿”以后,经济适用车都开不上了,只能骑三轮车。
他们两个人的父亲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也不一样。鲁迅家祖业丰厚,阖族之人皆是靠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吃饭,鲁迅祖父做官,维持着鲁迅家的名声和社会地位,鲁迅父亲只考到秀才,对家族经济贡献不大。郁达夫家的生活主要靠他父亲行医和在县衙做小职员的收入,另有一部半“庄书”和十几亩田。父亲去世以后,郁达夫家丧失了大半的经济来源。
两家经济状况的差异,使得两个家庭中“弟”对“兄”的经济依附性不一样。
鲁迅与郁达夫的大哥郁华都是“扶弟魔”,从挣钱那天起,就在经济上扶持弟弟们。但是鲁迅与周作人相差仅四岁,兄弟两人几乎同时上学,同时工作,周作人在经济上对鲁迅依赖不大。
1919年,鲁迅一家搬离绍兴,举家北上,周作人原想就此分家,各过各的日子,由于鲁迅的坚持,他们才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了一座大宅,兄弟三人同居。
这样的同居生活,一定是周作人与周建人受益,他俩有妻子儿女,鲁迅只有他和妻子朱安两人,但对周作人来说,鲁迅的资助仅是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他在北大任教授,收入不少,自己养家没有问题。
郁达夫在经济上是依赖大哥的。郁达夫上中学前,他家经济上已经接近枯竭,幸亏大哥留日归来,有了工作,虽然初入职场,收入不高,总是大大缓解了郁家经济上的困窘。
郁达夫在感情上也依赖大哥。他三岁丧父,几乎不记得父亲模样,年长12岁的大哥代替了父亲的形象,他跟大哥闹的那些矛盾,更像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跟父亲闹的矛盾。
四
鲁迅与周作人的矛盾并非因一时一事而起,而是长久积累的爆发。
他们兄弟的矛盾,我觉得从他们少年时就开始了。
1893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舞弊案下狱,他的父亲愁闷病倒,家境一落千丈。这段经历,在鲁迅笔下愁云惨淡,灰暗无光,而在周作人笔下,云淡风清,仿佛兄弟两人生活在两个不同时空里。
兄弟两人感受上的分歧,除去性格上的原因,跟他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莫大关系。祖父下狱,父亲病倒,十二岁的鲁迅成为一家之“主”,虽有母亲在堂,跑外的工作,比如跑当铺、跑药铺,都要鲁迅去做。看到昔日的翰林府,如今沦落成这模样,很多人是幸灾乐祸的,说话夹枪带棒,明讽暗刺,这对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是很大的打击。
鲁迅故旧新台门正厅
周作人是老二,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变化不大,仍是母亲的儿子和祖父的孙子。鲁迅跑当铺的时候,周作人在杭州陪伴坐牢的祖父,日子说不上富足,却也惬意,每日读读书,习习字,到监牢里陪祖父说说话。他那个坐牢的祖父,日子也相当惬意,在监牢里住着一个独门小院,监房里铺着地板,每天读读书,喝喝茶,与狱卒们聊聊天,一日三餐由自己家雇的厨子送进来,一点苦没吃。
回首少年时光,周作人心里没什么怨恨。
所以“家道中落”,对鲁迅刺激非常大,对周作人的刺激却不大。
鲁迅写过一篇小说《风筝》,写“我”少年时不喜欢玩风筝,认为玩风筝是没出息的事情,有一天看到小弟偷偷做风筝,气得“我”把小弟做的风筝折断,踩烂,扬长而去。
虽然是小说,我总疑心这是写实的,很可能鲁迅年少时,真的特别讨厌弟弟们玩物丧志,希望他们努力,上进,将来有出息,不要再让别人看不起。
鲁迅的这种“紧绷”感,“危机”感,势必会通过一些生活琐事传递到两个弟弟身上,小弟周建人年龄小,无论人格上,还是经济上,很晚才“自立”,他对大哥是依附的,不会反感大哥对他的管束和教诲。周作人才华、见识、经济能力,样样不弱于鲁迅,他的心里住着一个很坚硬的“自我”,这个“自我”给他搭起一方天地,鲁迅传递来的压力感是对他的领地的侵犯,是对他内心里那个“自我”的剥蚀,他心里是不舒服的。
所以他明知与大哥同居,经济上对他有利,仍然希望各过各的日子。
鲁迅“家道中落”以后,经济状况上来说,不像他说的那样差,鲁迅家经济状况最差的时候,家里也雇着烧饭的老妈子,坐牢的祖父雇着厨子,但是社会地位落差特别大,由昔日的翰林府沦落为罪犯之家。这是很羞辱的。
这种羞辱,几乎让鲁迅一个人承受了。
郁达夫家就不存在这样的羞辱。
跟鲁迅相比,郁达夫大哥郁华很明显心态平和。
郁华为官清廉,为人严肃,夫妻举案齐眉,样样堪为楷模,他在郁达夫心中始终是个像父亲一样的高大形象。
鲁迅在周作人心中的形象远不如郁华在郁达夫心中的形象高大,周作人说“我家自昔有妾祸”,这个“妾祸”恐怕也包含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姻,周作人自始至终只认朱安,没承认许广平。
五
周建人说: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愁云惨雾遍被整个家族。姑嫂勃谿, 妯娌争吵 ,婆媳不和 ,夫妻反目;今天这个上吊, 明天那个投河 ,你吞金子,他吃毒药……”
周建人说的这乱糟糟的景象,是周家新台门六房的情景。那时,周家新台门走过一百多年辉煌,即将走向解体。一个家族走向解体的标志,就是家族成员之间三观不合,裂痕越来越大,无法弥合,最后分崩离析。
鲁迅家后来何尝不是如此?
鲁迅母亲与羽太信子婆媳不和,鲁迅与朱安夫妻反目,周建人与羽太芳子夫妻反目,鲁迅与周作人兄弟翻脸,周建人之子周丰三自杀。
我们过滤去名人光环,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去,这何尝不是一个缩小版的新台门?
鲁迅家,最后也是兄弟夫妻母子分崩离析,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赁房另居,后来别母弃妻南下上海,与许广平另组家庭。周建人也抛妻弃子,与王缊如另外组建家庭。
虽然朱安的悲苦处境让鲁迅受到太多指责,但是,这场亲情撕裂的家族悲剧,受害最深的是鲁迅。在父亲去世以后,他为了弥合这个家庭付出了太多努力,承受了太多不应该由他承受的痛苦。兄弟母子的分崩离析,既是他作为“兄”的失败,也是他代行“父”职的失败。
父母,对儿女来说,是润滑剂,是缓冲带,有父母挡在中间,兄弟姐妹可以避免很多直接接触,有矛盾也容易化解。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正面相对,三观相合还好,三观不合,连个居中调停的人都没有。
鲁迅这样早年丧父的孩子,自己还没成年,却要承担起一些父亲的职责。他没有父亲的天然权威,也没有父亲的年龄带来的阅历上的优势。他活得累,弟弟还不领情。
鲁迅的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但是鲁迅兄弟之间的矛盾,母亲无能为力。鲁瑞是个没上过学的家庭妇女,虽然她通过刻苦自学,达到了能读小说看报纸的程度,但是儿子们三观上的差异导致的矛盾,她调和不了,她的见识和文化修养达不到那样的高层次。
鲁迅最终离开北京,移居上海,直到病逝,他没有伸出一只手,与弟弟周作人和解。他也没有在病逝前回北平,看望年迈的母亲,尽管他一生敬爱母亲。
逃离绍兴,让鲁迅逃离了那个让他窒息的家族,逃离北平,让鲁迅逃离了那个让他压抑的家庭,他终于可以轻松地呼吸着空气,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过自己想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