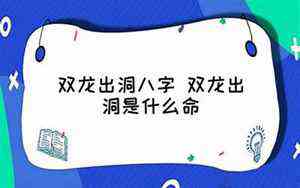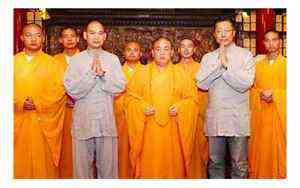约恩·福瑟:书写、声音与差异
约恩·福瑟:书写、声音与差异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文,ChatGPT 译 ,张佳 校
译自Thoughts on One of Norway's Great Writers,
Just in Time for Nobel Season,LITERARY HUB, Sep 30, 2019
标题为小编拟
我最近几天一直在重读约恩·福瑟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1983年到2000年之间写的,也就是说在他多变但奇妙地不断持续的作品体系的前半部分,尽管这些作品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呈现——小说、诗歌、短篇散文和戏剧——但它们始终具有同样明显的特点。从福瑟1983年的首部小说《红与黑》(Raudt, svart)到他十年后写的第一部剧作《我们永远不会分开》(Og aldri skal vi skiljast),再到他2014年发表的最新中篇小说《疲倦》(Weariness),叙述的东西并没有那么不同。
Jon Fosse
这个不可置疑的特质出现在约恩·福瑟所写的一切里,它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它不仅仅是他的风格、重复、曲折、思维层次,也不仅仅是他的主题,那些峡湾、那些划船、那些雨水、那些兄弟姐妹、那些音乐,而更多地体现在所有这些事物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小说《屈服》中,主人公对文学的本质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文学并不难定义。他说,像文学一样,音乐可以用突然的情感淹没我们,绘画可以让我们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但只有文学可以让我们与另一个人的精神接触,包括它的所有弱点和伟大之处,而这种另一个人的存在,他认为,正是文学的本质。他还惊讶地指出,哲学家们竟然对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关注如此之少。
很少有现代作家能像约恩·福瑟和他所代表的文学风格那样,与米歇尔·维勒贝克有如此大的差异。维勒贝克的小说以思想为基础,富有挑衅性,涉及当代问题,充满幻灭感,聪明而厌世,似乎向读者展示一幅面孔。而福瑟的作品几乎没有思想,也没有一丝挑衅,对当代问题进行了淡化处理,或者完全避免,尽管他的作品经常接近死亡并探索一种存在主义的零点,但它从不感到幻灭,绝对不是厌世的,而是充满希望。福瑟的黑暗总是充满光明。此外,他的写作不向读者展示面孔,而是非常开放的。维勒贝克的写作反映了一切,将一切抛还给读者,在其中读者看到了自己和自己的时代,而福瑟的写作吸收了读者,是一种读者融入其中的东西,如黑暗中的风。这些是福瑟作品的基本特征,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维勒贝克作品的基本特征,这两位作家站在了分歧的两端。
Michel Houellebecq
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使他们的作品成为文学的特质,正如维勒贝克在《屈服》中以如此引人注目而简单的方式提出的那样:作品中存在着人的精神。这不是风格或形式、主题或内容的问题,而是特定个体的写作在我们内心共鸣的问题,无论我们是在阅读一部写于19世纪末的俄罗斯小说还是阅读1990年代的瑞典诗歌。作品越贴近作者,越具有作者个人特色和表达作者自己的特质,文学的重要性就越大,因为另一个人的精神存在就是其本质特征。广告的语言,教科书的语言,报纸和媒体的语言,都是通用语言,是被接受的真理和固定习语的表达方式。用这种社会世界的语言写成的书籍充满了其所处时代的精神,而当时间流逝,除了这些已经消逝的过去社会的黑话,几乎没有东西留存下来。
例如,大多数上世纪60年代的书籍只是表达了它们所写的时代,就像一张照片会告诉我们当时的时尚潮流一样。因此,那些能够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是典型的,从来不是用社会的通用语言书写的,而是挑战常规。我们不是因为想了解战后奥地利的社会和文化,也不是因为想了解失去父母意味着什么,才阅读托马斯·伯恩哈德的《灭绝》(Extinction),而是为了沉浸在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文章中,这种文章将我们从自己身上拉出,将我们迅速推向完全不同的东西,某种独特和异常的东西。正是这种独特性和异常性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这种独特性和异常性才是世界和我们现实的真相,而文学的合法性就在于这种悖论。
有人或许会争辩说,声称文学的本质在于作品中存在另一个人是不合理的简化,它剥夺了文学的社会结构(societal)、政治和社会(social)方面,回归到浪漫时代的天才崇拜,那时重要的是独异的个体,同时,这种立场声称文学是作品中存在另一个人,除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书是由托马斯·伯恩哈德写的这一点之外,没有提供任何信息,没有引导我们获得特定的洞见,也没有理解文学作品,这可能会使整个文学研究学科变得多余,或者至少让考试变得更容易通过,因为那时唯一相关的问题可能是:“谁写了托马斯·伯恩哈德的《灭绝》?”或者同样地:“谁写了约恩·福瑟的《船屋》(Boathouse)?”
约恩·福瑟写了《船屋》。这本小说以一句话开篇:“我不再出门了,一种不安已经降临在我身上,我不再出门了。”它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小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小说——并不相似,但很像约恩·福瑟在那之前和之后写的许多作品。读者从第一句话开始感受到的就是约恩·福瑟的存在。但这种存在并不是他生平的存在,唤起他当时的形象(对我来说,这可能相对容易,因为约恩·福瑟曾是我在写作学院学习时的导师,而《船屋》正是在我就读的同一年出版的),对我们阅读这部小说的意义不大,就像我们对写作的时间和社会环境的考虑一样。相反,我们感受到的存在与某种感受性、警觉性、某种气质有关,以及这种存在在文本中为我们打开的东西。写作的奇怪之处在于,自我似乎会被释放,通常在我们自我的构想中维系“我”的东西会被溶解,内在的存在以新的、陌生的方式重新配置。
当我们阅读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了,我们跟随字词往下读,自我随之释放,一时间,我们将自己投入到一个不同的“我”中,全新而开放,却又清晰可见,它有一定的节奏、一定的形式、一定的意愿。在这场相遇中,在无私的作家和无私的读者之间,文学得以塑造。如果这部文学作品很好,它会唤起一种始终存在,但通常在日常世界的噪音中,或在“我”和我们的自我认知的铁腕控制下听不到的情绪和语调中。这些情感和语调唤起了我们对现实的另一种同样真实的体验,因为它们都与情感联系在一起,在小说、诗歌或戏剧中,情感是传达世界的媒介。在文学中,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构想会溶解,就像我们阅读时自己会溶解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接近了他者或世界。
(*约恩·福瑟Boathouse和From Telling via Showing to Writing的引文由May-Brit Akerholm翻译并出版——英译者注)
约恩·福瑟的文章几乎都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它们不涉及文学和艺术的生平、社会学或历史方面的问题,而始终围绕着它们的本质,围绕着什么使文学成为文学,什么使艺术成为艺术。由于这始终存在于独特性之中,在于它们自身的特性,也就是说,使文学成为文学,使艺术成为艺术的东西只存在于文学和艺术自身,以那种独异的方式,约恩·福瑟的文章是关于不可归约的、无法翻译的、神秘的东西。
在他的第一本文章集《从讲述到展示到写作》(Frå telling via showing til writing)中,这些神秘和无法翻译的特质与写作本身联系在一起。福瑟似乎认为,“讲述”(telling)与社会世界、叙事情境本身相连接,而且还包括某种娱乐元素;而“写作”(writing)与其他一些东西连接,与我们语言中只传达自身的部分连接,就像石头或墙上的裂缝。神秘是自主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感觉到福瑟的语言和思想受到1980年代文学理论的塑造。在他十年后出版的下一部文章集《诺斯替派文集》(Gnostiske essays)中,这种神秘的特质仍然是核心,尽管现在与完全不同的东西相连接:神圣。从文学理论中构想的写作和作家,到神圣的宗教概念,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事实未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福瑟在这两种情况下写的都是同样的文学特质,尽管现在是从不同角度切入。他在标题文章中暗示了两者的联系:
叙述者是修辞学家,写作者是反修辞学家。角色,即文学形象,被困在一种或另一种修辞形式中。只有缺乏语言的角色才是自由的。没有语言意味着没有差异。这意味着上帝。在某种意义上,积极的写作必须不断恢复对那些缺乏差异事物的渴望,对上帝的渴望,在优秀的小说中,你或许会注意到类似的东西。
同样,福瑟的散文(essay)和他的虚构作品(fiction)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散文站在艺术之外审视艺术,探索和调查,思考艺术的本质,思考它如何与我、你、我们相关,并由此与社会世界相连接,以这种方式转变,他在1980年代的散文具有1980年代的特点,1990年代的散文具有1990年代的特点。而福瑟的虚构作品却恰恰相反,它不是从外部审视,而是从内部审视世界和读者。无论福瑟写什么,他的声音都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从未缺席,尽管散文的声音是同时代的存在,福瑟虚构作品的声音却是与福瑟的时代无关,而与其他东西相关联的存在,散文试图根据其写作时代以各种方式隔离这种存在。然而,谜团从未改变。没有人比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更能洞察福瑟的文学,特别是主人公安德烈王子在听音乐时感动得流泪并试图理解原因的那一段文字。他在自己内心的无限和世俗物质的局限之间找到了理由。这种我们内在无限与外在局限之间的对比推动着福瑟所写的一切。
——Martin Aitken译自挪威语
封图 Kirsti Stubø I November, regi: Lars Norén. Det Norske Teatret 2001. Foto: Erik Berg©注 释
见文中
《李娃传》中的声景书写
《李娃传》中的声景书写唐传奇《李娃传》充分利用声景书写充当叙事功能,其中有着“过渡礼仪”的体现。
“过渡礼仪”是法国阿诺德·范·热内普 (Arnold Van Gennep)《过渡礼仪》书中的概念,该理论认为:“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从一社会地位到另一地位的过渡被视为现实存在之必然内涵。”
过渡礼仪的基本模式可分为:阈限前礼仪 (分隔礼仪) 、阈限礼仪 (边缘礼仪) 和阈限后礼仪 (聚合礼仪)分离阶段通常以某些象征性行动使个体离开先前在社会结构中的某个定点,被强行送往某处隔离场所(驱逐仪式),完全脱离旧日的角色、人际关系与生活惯例。
经过三阶段完整历程, 社会结构就完成了一次“有序一失序一重回秩序”的调整, 回归社会结构的有序状态中。
从原型看,它是一种个体乃至族群心理成长模式,是自我意识从集体无意识状态分离出来,群体角色脱落,人格自我更新.生命个体和社会身份藉此获得重生,从而回归正常生活。
小说中郑生的社会身份变化,从一社会地位到另一地位的过渡,通过听觉叙事中的声景转换来完成。
声音属于某个人,标志着某个人的身份并印上他的特性。所以声音在塑造人物时,往往可以表现人物身份。
声音作为“阈限”,将小说情节分割,《李娃传》中流落街头的士族子弟郑生歌唱挽歌,挽歌区隔了人物身份,原先恃才自负的士族子弟身份脱离。
郑生被骗病倒后,流落到凶肆寄身。落魄的郑生,不再具有昔日地位,凶肆中的哀歌声能够衬托郑生凄凉、伤感的心境,于是荣阳生开始聆察凶肆中的哀歌声,进而有了吟唱挽歌的兴趣,于是开始独自仿效歌唱,挽歌充当了其转变身份的契机。
此后荣阳生从独自仿唱挽歌到公开学唱挽歌。
唐代社会中挽歌郎,属于底层低贱行业,哀怨的挽歌打动郑生的内心,使得原本自负的富家公子竟不以挽歌郎身份为耻,主动投身挽歌郎行业,完成身份的转变。
郑生为人聪敏,加之心中有真情,以至于成为挽歌郎中的杰出者。之后郑生公开演唱挽歌,参与丧铺之间的挽歌竞赛。郑生在社会中公开展示挽歌,获得听者共鸣,标志着其挽歌郎身份得到了社会认可。
也正因如此,导致其为旧仆发现,以至于旧仆不敢确认其身份。
在唐代,挽歌郎的身份与士人身份是被严格区隔开的。
挽歌郎混杂于民间,他们除歌唱挽歌外,还具有兼卖丧事凶器的商贩身份,在社会中较为低贱。
在门第观念深重的唐代社会,郑生的挽歌郎身份,自然是被看作有辱门第,不能被家族接受,以至于被父责打、抛弃,只能获得同身份阶层者的同情。
从士族转变为挽歌郎,这样的身份转变在唐代是极难为家族所容的,李佐之父,经历安史之乱由士族沦落为挽歌郎,即便后来重归士族,却已然习惯与挽郎群体为伍,难得真正回归往昔身份,以至于儿子李佐无法承受这种身份转变,以“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的结局而终。
同李佐之父一样,郑生也经历身份转变,并因其具备人生转折的情感经验,所以郑生即使在挽歌郎群体中出类拔愁,却也难以为家族所认可。
同时传统儒家思想中少有对死亡的思考,自六朝以来,挽歌体现出的以悲为美的审美,一直并不能被社会主流、世家大族所认同。
郑生歌唱的挽歌中夹杂身世之感,传达出内心的悲伤,在世俗群体中被共鸣,却无奈只能被家族引以为耻,通过听闻郑生挽歌后,父亲与世俗群体差异的表现。
所以听觉叙写在展现人物身份转变的同时,通过收听者不同的表现,可展现出身份转变的背后,不同社会群体的矛盾与区隔。
分隔礼仪是指使个体或群体脱离原先的生活状态,与原有的社会状态进行分隔。
郑生歌唱挽歌作为象征性行动,标志着其从原先社会角色中分隔。
航柯通过分析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材料,发现 “挽歌”总是在代表人生转折点的仪式当中举行的,因此,“挽歌”是最后告别时的诗歌一亲属的去世、女儿的出嫁、儿子的入伍都是表演“挽歌”的恰当的语境。
“挽歌的艺术感染力既来自表演者的强有力的情感经验,也来自表演者对于诗的敏感性。”同时,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妹尾达彦均对郑生唱挽歌这段故事也极为关注,认为郑生于凶肆听、唱挽歌这段情节是小说全篇故事的转折。
故此,小说中的挽歌声引得郑生进入“分隔”阶段,标志着郑生从原先社会角色中分离,体现出其形象的转变。
故事在叙事中沿着“听闻挽歌一学唱挽歌一比唱挽歌”的线索,以声景为串联,表现了郑生从原始身份分离,与新身份建立的过程。
郑生在被父责打赶出家门后,身份由挽歌郎进一步下移,成为以乞食声为标志的乞亏。
李娃所居的鸣珂曲一带,平日里是一处士女往来密集,热闹喧哗的世俗场。
不乏风尘娼妓立于门口主动招揽。如《剧谈录》所言“一旦,与宾朋骤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
歌舞场中人,寻常为了生意,均敞门,主动倾听门外发声。而大雪中的鸣珂曲,因鲜有顾客,外户多不发,唯独李娃宅独启左扉,因此辩得落魄荣阳生的乞食声。
如何对待他人发出的声音,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是:“这种对于他者的关注,对于语言的他者的寻求,作为对他者的一种回应,作为对一种召唤的回应,作为对一种正义的等待,首先就要求着完全敞开自身以倾听他者的声音。”
虽然沦落为乞亏的荣阳生,在社会身份已不如李娃,但李娃却主动聆察、倾听他的发声。
从凶肆中挽歌的影响,到街头乞食声的出现,标志着郑生社会身份不断下移,沦为乞巧的郑生,身份地位已不如李娃,郑生与原来安稳的生活状态彻底分离,原有社会秩序被打破,进入了边缘(阈限) 礼仪阶段。
这一时期,其生活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或底层。
阈限礼仪阶段看似处于失序的状态中,却恰恰是对现实秩序的矫治和调整。
阈限阶段人与人间形成一种平等、简单、同质关系。
李娃对郑生乞食声的主动倾听,接纳,体现着这种平等关系的建立。于是产生了正常社会中不能触犯的禁忌。
其仪式表现为:李娃接受落魄的郑生,“娃前抱其颈,以绣糯拥而归于西厢··....乃与生沐浴,易其衣服,为汤粥通其肠,次以酥乳润其脏”。拥归、沐浴、易服.通肠、润脏。
在这种失序状态下,作为歌妓的李娃甚至能“令生斥弃百虑以志学俾夜作昼,孜孜吃砭。
娃常偶坐,宵分乃寐”。督促其不断努力应试,求取功名。
所谓“聚合”是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相遇和融合,目的是在群体间建立某种约束关系或形成价值认同,尤其是陌生个体、群体间的融合。
新秩序的构建.必须受到人、神认可。所以,李娃与郑生对婚姻不敢自专,只有在得到家族之长父亲的许可后,婚姻才开始。
于是数年后“有灵芝产于倚庐,一穗三秀,本道上闻。又有白燕数十,巢其层。”人间至高的伦理权威(天子) 知道后,特为李郑二人“宠锡加等”、封李娃为沂国夫人。
李娃传故事构建的新秩序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美满。
这样的结局模式又导致“妇道甚修,治家严整”之下,四子“弟兄姻婧皆甲门”家族秩序重新回归于常态。
世俗娼妓与世家子弟的爱恋原本有违社会秩序,但自从挽歌引导郑生进入分离阶段,原有社会身份被破坏,随着乞食声的出现,故事进入阈限礼仪阶段,在该阶段中,家族门第观念等社会秩序被破坏,一系列失序中的犯禁行为,最终促使郑生考取功名,重新获得原有地位,新秩序被建立,最终这段世家子弟与世俗娼妓结合的故事获得了圆满结局。
小说中挽歌、乞食声这些声音不仅可以展现人物形象,还是人物身份变化的重要分隔标志,这些重要声景还引起人物活动,串联人物关联,引导故事进入不同仪式阶段,小说叙事中起了重要的串联作用。
“禤靐龘”102画姓名难哭网友,那你是没见过这些最难汉字!
最近,
有一位同学因被姓名困扰而上了热搜。
他叫禤靐龘,
由于名字太“生僻”,
小学同学叫他“雷雷雷,龙龙龙”,
中学同学更干脆,直接叫他“喂”。
好吧,这三个字的读音,
CD君是百度出来的!
11月27日,香港一名初中生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自己相当羡慕其他同学,名字好写又好读。因为他的父母很迷信,因此在他出生时,请算命师取了“禤靐龘”(xuān bìng dá)这个名字。
他的姓氏“禤”本身就很特别,未料名字更复杂,是由3个雷组成的“靐”,表示雷声,和3个龙组成的“龘”,代表龙飞起的样子。全名粤语近音“圈凭踏”,有着飞黄腾达的寓意。
虽然父母和算命师是出于好意,却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扰。从小学起,同学就取笑他的名字,叫他“雷雷雷龙龙龙”。上了初中之后,虽不像上小学时那样会被嘲笑,但同学时常因为念不出他的名字,叫他“呀”或“喂”。有时候连老师都念错,让他成为全班的笑柄。
此外,有时他参加学校活动,其他班同学还会因为他的名字不想认识他。最令他痛苦的是,每次考试光是写名字就要花很多时间,3个字加起来共102画。“龘”这个字还是一般字典中笔画最多的字,足足有48画!
这名童鞋最后表示,
自己非常想改名
因为连自己都常常会写错名字……
这名童鞋的困扰在微博上传开后,
引发了一干吃瓜群众评论:
▼
还有很多网友表示第一次看见这个3个字:
史上最难认的三叠字,你认得几个?
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字我们从来没见过,更谈不上认识!中国人在看到不认识的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读半边字的情况,然而,碰上这些叠字,你还能淡定吗?
叒
叒(ruò):古同“若”,顺;指“若木”。
畾
畾(lěi):古代一种藤制的筐子。古同“雷”,古同“垒”,田间的土地。
歮
歮(sè):古同“涩”,苦涩,艰涩之意。
孨
孨(zhuǎn):谨慎。 弱,懦弱。 孤儿。
皛
皛(xiǎo):皎洁,明亮:“天皛无云。”
舙
舙(huà):搬弄是非,“舙,谋谮人也。” 古同“话”。
骉
骉(biāo):众马奔腾的样子。
羴
羴(shān):古同“膻”,羊肉的味道,也泛指羊的意思,也是鼻烟品目之一。
赑
赑(bì):赑屃(xì),用力的样子;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像龟。
毳
毳(cuì):毳毛,俗称“寒毛”;鸟兽的细毛。
鱻
鱻(xiān):古同“鲜”。
馫
馫(xīn):古同“馨”。
麤
麤(cū):同“粗”。
飍
飍(xiū):惊跑的样子:“驰谢如惊飍。”
飝
飝(fēi):意义不详。引申之意,指飞的极快,上天之意。
龘
龘(dá):古同“龖”,龙腾飞的样子。
3个以上不认识的,
默默转走吧!
中国日报(微信ID:chinadailywx)综合“观察者网”、新浪微博、新华词典
精彩推荐
部首查字法口诀及要点
部首查字法部首检字法:部首检字法属于按形查字中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汉字的部首去查检的。凡字典正文中的单字是按部首归类进行排列的,都可以运用部首检字。部首检字的基本步骤:⑴确定出部首。先对所要查的字确定出查什么部。⑵查《部首目录》。在《部首目录》中查出该部首在《检字表》中的页码。⑶查《检字表》。按照页码在《检字表》中这个字的余画(即除去部首还余几画)里查出这个字在字典正文中的页码。⑷查字典正文。按正文页码在正文中查出所要查的字。
查字时首先要确定这个字的部首,然后从字典的“部首目录”中查出属于这个部首的字在部首检字表中的页码,就可以按照这个字除部首以外部分的笔画数,从正文中找到它。有些字在检字表中分别放在不同部首下。例如“功”在“工”部和“力”部中都可以查到。凡是要查只知道写法而不知道读音和意义的字,都可以用这种方法,但必须熟悉汉字常见的部首。运用部首查字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①会数笔画数; ②会找部首; ③会笔顺。运用部首查字确定部首是难点,特别是合体字中往往几个部件都是部首,该确定哪个部首呢?可以按以下规律灵活确定。
①查左不查右。左右结构的字,如果左右两部分都是部首,一般查左旁。如:付、默、须、枫、乱、红、拜、江、外。
②查上不查下。上下结构的字,如果上下两部分都是部首,一般查上头。如:类、告、唇、弁、岁、李。
③查外不查内。内外结构的字,如果内外两部分都是部首,一般查外框。如:困、句、司、医、画、夙、庆、这、闷。
④查中坐不查附件。由两个以上部件或零件交叉起来构成的字,中坐和附着在中坐上的部件都是部首,一般查中坐。如:坐(土)、秉(禾)、巫(工)、夷(大)、兆(儿)、臾(人)。⑤查合不查分。构字间架上是“分合式”的字,“分”与“合”都是部首,查合旁。如:影(彡)、皱(皮)、辟(辛),韩(韦),封(寸)、碧(石)、娶(女)、驾(马)、楚(疋)、盐(皿)。
⑥查先不查后。“田”字形间架的字,部首一般在字角,有时几个角的部件都是部首,可以按写字顺序的先后,先写到哪个部首,就查哪个部首。如:鼓(士)、赣(立)、耀(小)、疑(矢)、孵(爫)、够(勹)、孬(女)、舒(人)。
⑦查形不查声。形声字,有时形旁和声旁都是部首,一般查形旁。如:功(力)、赏(贝)、房(户)、载(车)、衷(衣)、点(灬)。
⑧查多不查少。一个笔画多的部首里包含有其它笔画少的部首,一般确定笔画多的部首。如:着(不查丷,查目)、磨(不查广、木,查麻)、解(不查刀,查角)、韵(不查立或日,查音)、欲(不查八、人、口,查谷)。
⑨查复不查单。每个字中都有一个单笔部首(起笔部首),但要尽力分析复笔部首(两画以上的部首),只要含有复笔部首,就确定复笔部首。如:曲(曰)、东(木)、农(冖)、凹(凵)、以(人)。⑩自成部首查本身。有不少字,本身就是一个部首,这叫“自成部首字”。虽然一些自成部首字还可从自身中分析出其它部首,但一般不取其它部首,就查自己本身。如:音(查音)、鼻(查鼻)、麻(查麻)、黑(查黑)、辛(查辛)、骨(查骨)、里(查里)、麦(查麦)、鹿(查鹿)、青(查青)。另外,一个字中分析不出复笔部首时查起笔。有少数独体字,本身不是部首,从本身也分析不出其它复笔部首,就查起笔(单笔部首)。如:万(一部)、中(l部)、九(ノ部)、义(、部)、长(ノ部)。在阅读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可以用部首检字法查出读音和字义。
下面的口诀可以帮助同学们掌握部首检字法:
部首检字并不难,确定部首是关键。
先数部首有几画,部首目录看页码。
检字表里找该部,除去部首查余画。
余画下面找单字,单字右边标页码。
顺着页码翻正文,必有此字不会差。
3数笔检字法数笔画检字法也叫笔画起笔检字法。凡是查读音不知道、部首又不明显的字,宜用这种方法。只要数准字的笔画,就可以在字典的“难查字笔画索引”中查到这个字在正文中的页码。这种检字的方法是以一个字笔画数的多少和前两笔的笔形来查字的。数笔画检字的方法比较简单,只要能正确书写一个字,字的笔画数和前两笔的笔形都不出错,就能找到要查的字。在《新华字典》中,用这种方法可以在《难检字表》中查难检字。用数笔画查字,必须做到三个“准”: ①笔画要数准。 ②笔形要认准。 ③笔顺要写准。
只要做到了这三个“准”,就可以按“笔画总数——起笔笔形——翻阅正文”的步骤查字了。最后送上一首《查字典小儿歌》 小小字典手中拿,看我来把汉字查。
定部首,数几笔,部首目录找到它;
部首外,再数数,检字表中找门牌;
快快快,快快翻,找到正文找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