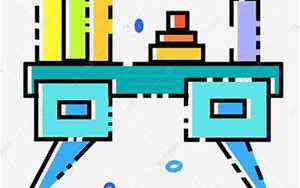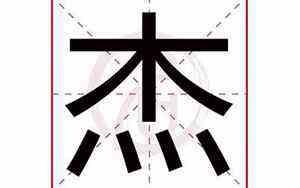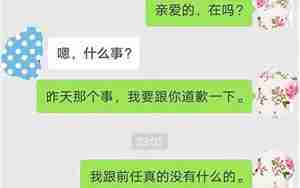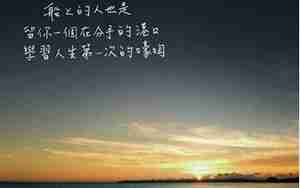朱自清:什么是《春秋》三传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的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明人彩绘圣迹图册页——西狩获麟图 孔子博物馆藏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的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得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的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春秋左传注(修订本)》,杨伯峻译注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阙、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公元前722—前481);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徵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记“赵盾弑其君”,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虽杀身不悔,都为的是徵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拣的这一些。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徵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嚼,这一咬嚼,便不顾上下文穿凿傅会起来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做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做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春秋》,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傅会的办。这正和后世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傅会的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和《穀梁传》,和《毛诗》笺、传,在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穀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战国末期,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穀较晚出的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阙的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穀梁只是家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开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同小异的。《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这部书历来讨论的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做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穀两家。后来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是公、穀不免空谈,《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人的研究,《国语》重在“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三全本《国语》
《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穀》二传早些。《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徵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晋范宁作《穀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人就不少了,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是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工夫,也决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优游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参考资料:洪业《春秋传引得序》
(选自《经典常谈》,中华书局出版,原标题为《〈春秋〉三传第六》分段有调整)邀请汇文中学高级教师导读
附知识点梳理与中考演练题
点书影进入当当购买本书《经典常谈》(全二册)
朱自清 著978-7-101-16110-628.00元《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在1942年为中等以上教育的学生写作的一部普及读物,八十年来广为流传,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在这本书中,朱自清先生以通俗流畅、深入浅出的文字,提纲挈领地解读了《说文解字》、“四书五经”、《战国策》《史记》、“诸子百家”、《楚辞》等国学典籍,客观持平,博采众长,见解精辟。
(统筹:一北;编辑:思岐)
“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
“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是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三部文献记载了春秋时期诸多史事,对研究春秋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同时这三部文献仍有对春秋疾疫的不少记载,是研究春秋疾疫主要的史料来源。春秋三传对疾疫的记载有同有异,其具体表现如下:
“春秋三传”所载疾疫不同之处:首先,比较明显的是在疾疫记载数量上的差异。通观全书可以发现,《左传》一书,与疾疫有关的“疾”字一共出现142 次,与疾疫有关的“病”字出现了 29 次,“疫”字一共出现 1 次,“疾病”连用的情况出现11 次。
《公羊传》一书,与疾疫有关的“疾”字一共出现 16 次,与疾疫有关的“病”字出现了7次,与疾疫有关的“疫”字没有出现。《榖梁传》一书,与疾疫有关的“疾”字一共出现5次,与疾疫有关的“病”字和“疫”字均没有出现。统计发现,《公羊传》、《榖梁传》二者一共记载的疾疫数量才占《左传》数量的 16%,由此可见《左传》所载疾疫数量远比《公羊传》与《榖梁传》丰富得多。
其次,不管是总体上对疾疫的记载还是对单个疾病的描述,《公羊传》与《榖梁传》都没有《左传》记载的详细具体。《左传》记载疾疫活动之多,其中“医和医治晋平公之疾”、“医缓医治晋景公膏肓之疾”以及“齐景公之疟疾”等,都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记载,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对于此类疾疫活动却没有任何记载,这就使得《左传》与另外两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究其原因,虽然《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与《春秋榖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然而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考证,《左传》并非解《春秋》经之书,所以《左传》的内容并不是简单的依据《春秋》经来进行阐释,其记载内容远比《公羊传》和《榖梁传》更加翔实。
另外从“春秋三传”的文体形式来看,《左传》是采用经前传后、互相独立的方式进行补充展开叙事的,而《公羊传》与《榖梁传》却是以问答体的形式进行解经的,这就从形式上限制了《公羊传》与《榖梁传》记载内容的广延性。因为《春秋》经一书对疾疫的涉及其实也非常之少,所以作为解经的《公羊》、《榖梁》二传所载疾疫数量自然要少于《左传》。
“春秋三传”所载疾疫相同之处:首先来说,“春秋三传”所载疾疫在内容上具有互通性。这种互通性源于对《春秋》经的解读,凡是《春秋》经提及的疾疫,三传或多或少都会进行传解,虽然对疾疫的解释各持己见、有所不同,但其结果终究是殊途同归。因此借用这种内容上的互通性可以对春秋时期的疾疫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考证出特定疾疫的属性。
如桓公五年《春秋》经载:“春,正月,甲戌,乙丑,陈侯鲍卒。”这一句交代了陈桓公死亡的年、月、日,可是《春秋》经却说陈侯是在甲戌、乙丑这两日死亡,甲戌日为鲁桓公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乙丑日为鲁桓公五年正月六日,二者相差了十六天,足见陈侯死亡之蹊跷。陈侯的死因从“春秋三传”中便可寻找到答案。
《公羊传》载:“曷为以二日卒之?㤜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榖梁传》云:“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乙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左传》载:“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
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综合三传所言,可知陈桓公患有名为“㤜”的疾病。《广雅·释诂》云:“㤜,怒也” ;《广韵·六术》言:“㤜,狂也”,从其意思来看此病为精神失常所致,是为现在所指精神病。也正如杨伯峻所言:“盖陈桓公患精神病,甲戌之日一人出走,经十六日而后得其尸,不知其气绝之日,故《春秋》经举二日以包之。”其次,在春秋疾疫的写作手法上,三传也有相同之处。“春秋笔法”不仅是《春秋》经写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春秋三传”,其意大致概括为微言大义、暗含褒贬。
由于疾疫带来的痛苦让古人认为其乃不祥,这便使得三传在记载疾疫的时候往往带有贬低的意思,以疾贬人,以疫贬事,给春秋疾疫的历史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左传》一书记载,成公八年,晋景公杀赵同、赵括,成公十年便梦见赵氏先祖索命,醒后身患重病,《左传》记载此疾便是表达对晋景公贬斥之意。
又如《公羊传·庒公二十年》载:“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㾐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此处的大灾,并非指的火灾,当为疫病,《春秋公羊传注疏》云:“欲言大疾疫,而经书灾,故执不知问”,并且“灾”字前面加上“大”字,“知非火灾也” 。
《公羊传》解释大灾为大瘠,大瘠为㾐,㾐者何也,㾐者疠也,“民疾疫也”,故《公羊传》此处的大灾是指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病。公羊传此处所载并非简单的记载灾异,而是另有所指。何休《解诂》云:“㾐者,邪乱之气所生,是时鲁任郑瞻,夫人如莒淫泆,齐侯亦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因此,此处记载大疫是为了讽刺齐国国君的骄奢淫乱以及鲁国任用奸佞小人的昏庸之举。
西周时期的医事分科制度到了春秋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纵观“春秋三传”所载疾疫,不仅涉及内、外科疾病,而且对精神类疾病、妇产科疾病以及流行性传染病也更加重视。因此,现将春秋疾疫划分为内科疾病、外科疾病、精神疾病、妇产科疾病、流行性疫病等五个大类,如下一一进行分析。
春秋时期所载内科疾病主要有心脏病、蛊疾、隐疾等,《左传》中的“六气致病说”表现出春秋时人对内科病因已经开始进行有意识地分析,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疾病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深化和提高了内科疾病的理论认识和治疗水平,对后世内科疾病的治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说文解字》曰:“心,人心,,土藏也。” 心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古人称之为“君主之官”,由此可见心为五脏之首。故因心脏的特殊地位,古人便将心与人的精神活动联系在一起,具有了高度的抽象思维。如《管子·水地》篇曰:“生而心虑。”《礼记》亦言:“总包万虑谓之心。”可见当时人们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亦称之为心。《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③此处所谓“明淫心疾”,是指思虑过多,心神过劳而造成的精神类疾病。
然古人所谓心疾之意并非仅止于此,《左传·襄公三年》记载的子重之心疾便有另外的含义:
春,楚子重伐吴……君子谓子重于是役也,所获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也对周景王心疾有所记载:
春,天王将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乐,天子之职也。夫音,乐之舆也;而钟,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小者不窈,大者不摦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故和声入于耳藏于心,心亿则乐。窈则不咸,摦则不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摦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周景王因心疾死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从,将杀单子、刘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荣锜氏。
子重所患之病为“心疾”,杨伯峻注:“古代所谓心疾非今日之心脏病,而是今日之精神病”,但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之心疾,杨伯峻又言:“盖心脏病急死”,两者前后矛盾,故心疾必有异义。子重因作战失利而遭到国人的责备,内心忧郁成疾,不治而亡,死亡时间较快,周景王也是田猎之时遇心疾而速崩,然精神类疾病并未见急死之症,所以此心疾并非简单的精神类疾病。按照子重以及景王死亡时间长短来看,二人从患病到死亡的时间都是相对较短,那么此心疾为心脏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并且李约瑟先生也认为心疾“可能是由于焦躁而导致的冠心病” 。古人认为心是主管思虑的,那么令心脏致病必然也是思虑过度导致的,因此精神问题或者心理问题则是诱发心疾的重要原因之一。
子重之“心疾”,阮刻十三经注疏写作“心病”,据杜注云:“忧恚故成心疾”,盖此处早先版本是作“心疾”,而非“心病”。另外《易·说卦》有“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的记载,孔颖达曰:“为心病,忧其险难,故心病也”,可见“心病”之因也是精神忧虑所致,心神紊乱、情绪激动而引发心病。所以“心病”与“心疾”的症状相似。
另《左传·庒公四年》载:“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杨伯峻注:“荡,动摇也。心荡犹言心跳、怔忡。”心荡的表现症状为心跳加速、心律不齐,余云岫将其解释为“心悸亢进” ,所以心荡通常为心脏病发作的前兆。楚武王将心荡告于夫人邓曼之后,邓曼说武王的福禄快要到头了,将不久于人世。果然,楚武王很快便死于伐随之途。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期,人们对心脏病非常地重视,此类疾病不易治愈,且死亡率较高。
总的来说,春秋时期的心疾有两种意思,一种指精神类疾病,一种指思虑过多而引发的心脏病。心病与心疾同义,心荡则为心疾(心病)的表现症状。此三者皆以心字命名,既与人们抽象的精神思维有关,又与客观存在的人体心脏器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