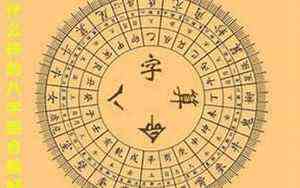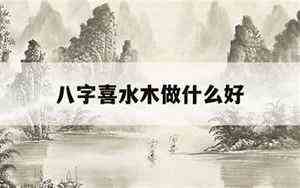百年前先农坛建起两座新建筑,随后为何却沉寂了?
儿时在位于万明路的姥姥家住过很长时间,从那里往南走,不多远就是北京育才学校,我和表妹没事儿就到那里闲逛。那时北京的孩子都知道,育才学校最了不起的就是“先农坛在学校里边儿”,可惜年久失修的先农坛在我们的眼里就是破破烂烂的几座殿宇,观耕台上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坐在庆成宫的台阶上,看着无数的蜻蜓在荒烟蔓草间时飞时驻,心里充满了惆怅……
作为旧京“五坛”之一的先农坛,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虽然曾经被冷落甚至淡忘,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它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都不容抹杀,特别是在民国年间,它曾经以北京第二座平民公园的身份向市民开放,深受大众喜爱,成为这座古城走向开放、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皇帝种的粮食给谁吃?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历朝历代,从皇帝到百姓,对土地和农耕都有着无比的尊崇,而先农坛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农行耕藉礼之所,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02年),比天坛还早18年,最早名叫山川坛,清代改名先农坛。先农坛占地1700亩,共有包括庆成宫、太岁殿、神厨、神仓和俱服殿在内的五组建筑群;另有四座坛台,分别是观耕台、先农坛、天神坛、地祇坛——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观耕台,因为台南边就是大名鼎鼎的“一亩三分地”。
“一亩三分地”的正式名称应该叫藉耕田。是皇帝祭祀先农神之后亲自耕种的田地——这个“规矩”早在明代就有,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曾经详细记载了皇帝躬耕的情况。每年春分前后的一个良辰吉日,皇帝会率众臣驾临先农坛。事先顺天府已经准备好了耕牛和农具,搭好五彩大棚,将耕田整成松软的沃土。皇帝来到后,换上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行躬耕礼时的专用服装),来到耕位,面南而立,在百官吟诵祝禾辞的伴奏下开始扶犁亲耕。顺天府尹执鞭在牛旁,几位老农协助皇帝扶犁牵牛,在一亩三分地上耕犁几个来回(一般是三推三返),然后皇帝登上观耕台,看众大臣和众老农扶着犁继续耕耘播种。清代确立以后,清帝承袭了旧明的祭农之制,清世祖顺治十一年恢复祭农行耕藉礼,而雍正帝对这一礼典极为重视,几乎每年都要驾临先农坛耕种,收获的庄稼可没人敢吃,择吉日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中做祭祀之用。乾隆皇帝曾经对先农坛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改建,并下旨在坛内广植松柏以利圣洁……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虽然贵为天子也不能不事稼穑的以身作则,使得各个阶层对农业都非常重视。由于雍正帝曾经颁诏命全国各地设立先农坛,把对先农的祭祀变成国家祀典,所以各级官员就不必说了,就连百姓在春耕到来之前,也会在庙宇或宗祠中祭祀神农氏的典礼,祈佑五谷丰登。
从十九世纪中末期起,虽然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清王朝自身的统治日趋腐朽没落,先农坛也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丰采,由于皇帝不是以“木兰秋狝”之类的名义逃出京城,就是继位者年龄太小出不得皇城,所以,尽管遣官致祭的过场还能走一走,但祭祀制度日益驰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先农坛被美军占领成为兵营,太岁殿作了军队医院,神仓成为美军司令部,等到美军撤出时,这伙儿强盗将坛内陈设的祭器洗劫一空……从此,这座古老的祭坛就一天天破败下去。
鲁迅“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内务部成立礼俗司,统管清朝移交的皇家坛庙,并把坛庙管理所设置在了先农坛的神仓里。那时的普通百姓对皇家坛庙都有极大的好奇心,所以经常私自闯入游玩,而时论也呼吁对这些地方早做开放,将其变成公园。民国政府开始动议筹办,还派出人员去考察可行性,其中就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鲁迅),他在日记中就曾记录,6月14日这天“午后与梅君光羲、胡君玉措赴天坛及先农坛,审其地可做公园不”。
1912年12月26日,为纪念民国成立一周年,内务部古物保存所宣布将天坛、先农坛开放十天,“是日各处一律开放,不售入场券,望中外男女各界随意观览”,这在当时引起了京城的巨大轰动,民众像潮水一样涌入二坛,先农坛内万头攒动,观者如堵。《正宗爱国报》上记载,一路上“红男绿女,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其一种欢欣鼓舞如痴如狂之态,实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殆所谓如鲫如蚁,车水马龙,不过如是也”!
正是这次为期十天的开放活动,让有关方面看到了市民对公园的渴求和期盼是何等的炽烈。特别是在社稷坛开放为中央公园之后,报章上的呼吁就更多了:“京都市内,面积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仅仅一处中央公园,实在不足供市民之需要。因为中央公园,设在前门里头,仅便于内城一带居民,而于南城外头,有城墙阻隔,终觉不便”。而南城当时是北京市民聚居最密集的地方,平常游玩只能去陶然亭逛逛,实在乏味得紧。而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多位政府工作人员考察后,将目光对准了先农坛:“查南城一带,向以繁盛著称,惜所有名胜处,或辟在郊原,或囿于寺观,既无广大规模,复乏天然风景。详加审度,惟先农坛内,地势宏阔,庙宇崔嵬,老树蓊郁,杂花缤纷。其松柏之最古者,求之欧美各邦,殆不多觏,洵天然景物之大观,改建公园之上选也!”
在京都市政公所主持的选址、规划和修缮之后,1915年6月17日,北京南城的第一座平民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命名为先农坛公园,“入门票收铜元一枚,游览票收铜元五枚”。公园内陆续开设了荷花池和养鱼池,从避暑山庄运来140头驯鹿开辟为鹿苑,在太岁殿中设立了茶社,殿前开辟了秋千圃和抛球场,还有书画社、书报社等休闲娱乐设施,而礼器陈列所则让参观者可以了解古代祭祀的历史,“又于二道坛内,沿路两旁及正殿松林隙地,杂植花草,其东偏桃林一带,约八九亩,均划为陈列花卉之所,红紫纷披,最堪娱目。并于东隅隙地,另辟菜畦,篱豆花开,宛然村落,可以领略田家味。”
这样一个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符合现代公园的规划设计,无疑会大受市民欢迎,而且公园里还不时放映电影和烟花,“先农坛的焰火”很快成为京都一景。不久之后,随着先农坛的外墙被拆除,外坛北部和旧有的内坛合并为一处“城南公园”,溜冰场、图书馆等也都开办了起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务府档案》中的一个统计,可以说明公园的游客量:民国初年的北京,一枚银元能换130枚至140枚铜币,先农坛的门票一共才六个铜元,而北京市政府每年仅靠公园的门票和土地租金两项,就可以获得8000银元的收入。
观耕台上的恶俗照相馆
1919年,先农坛内建起了两座新建筑:一座是以观耕台为底座,上建八角二层的观耕亭,门窗都安装着彩色玻璃;另一座是纯欧式的三层钟塔,俗称“四面钟”,高大的钟塔位于外坛森林中,十分引人注目……但是说来奇怪,大约也就在这之后,就像陈宗藩在《燕都丛考》中所言,城南公园在“极一时车马喧天之盛”以后,突然就“沉寂无声”了,仿佛一夜之间就迅速衰落下去。根据笔者查找的资料,个中原因似乎与管理方贪图经济利益,将公园土地随意租给不良商贩有关。从1925年《晨报》上一则《内务部将拍卖先农坛地亩》的新闻报道上可知,仅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农坛外坛的地亩已经多次易手,而交易的原因是官员“贱价租赁”,将租金助力曹锟贿选,直系战败后内务部将这块地皮收回,又为了“大行添员加薪”而将其再次招商拍卖,“计可得五十余万元”——就好像很多国营老商场,不顾自己的金字招牌,将摊位切割租售给小商贩,搞成了伪劣产品批发市场,最终倒闭一般。
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经多次游览先农坛,他的游记为我们留下了先农坛公园由盛转衰的最后景象。他从先农坛的正门进去:“门上悬挂着用黑体字撰写的‘城南公园’的门匾和侧旁的‘内务部坛庙管理处’的门匾。此外,右侧的小门上有‘京师警察厅巡警教练处’和‘保安警察第二队分驻所’的门匾”。他买票进门后,只见铺满沙石的道路两旁种植着种类繁多的花卉,春夏季里宛若几幅舒展的锦绣般娇艳欲滴。西面用土墙围住的一片区域是鹿苑,这时只剩数十只鹿。太岁殿附近,一群巡警正在学习骑自行车。拜殿的“匾额两侧悬挂着形状几近相同的粗陋的纸额,上面写着‘球房’和‘茶舍’,殿柱上钉着‘每位茶资六枚’的木板”,可见这里已经用作球房和茶馆。拜殿的西侧,“在郁郁苍苍、拔地参天的树间”还开有一个露天的小吃店,年轻的小伙计殷勤地接待着客人,“茶自不必说,此外还有啤酒和汽水,提出特别要求的话,还可以供应中国菜,而且还备着白干酒和绍兴酒”,厨房就设在后面的宰牲亭里。预定的话,可以在这古木参天的地方举行高雅的宴会。中野江汉经常在入夏后来到这里,“独坐在树下,烧酒伴着下酒菜,享受半日清闲”。
不过,这里也有令中野江汉非常厌恶的地方,那就是观耕台上的观耕亭被辟为照相馆,变成了一座“恶俗的镀锌薄铁皮房檐的棚屋式建筑”,四面玻璃上用红笔写着“精巧放大”等文字,北面屋上挂着形似仁丹广告的“容亭照相”的大招牌。中野江汉愤怒地说:“在作为历史遗迹的著名的历代天子观耕台上,将相关建筑改建之后还能心安理得的人,犹如焚琴煮鹤般毫无风雅可言!”至于观耕台前的一亩三分地,已经成了一片任人踩踏的荒芜,跟先农坛内其他破败的建筑一样,令中野江汉“凄恻之情袭扰于心”……
1927年,北平市政府标价变卖先农坛外坛的土地树木,眼看着那些参天古柏、偃地苍松要遭到砍伐的命运,北平市民纷纷出面拦阻,“事始中辍”,但美国学者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在《古都旧景》一书中记载,他三十年代游览先农坛时,这里已经“不再对外开放……院中的大部分古柏被砍,用来做木柴烧了”。
那之后的沧桑岁月中,先农坛成了一道在历史的洪流中时隐时现、若有若无的影子。老北京人都知道它,都敬重它,但除了附近的居民,很少有人再去探望它。一亩三分地成了育才学校的篮球场,后来学校腾退出来,恢复了藉耕田的耕种,不久前还收获了金灿灿的谷穗……我不知道已经在育才学校当老师的表妹路过那片田地时,会不会想起小时候的情景,无论荒芜还是丰收,有迹可循,就好。
六朝古都金陵地名—山川坛
提起南京明山川坛估计知道的人不多,明初朱元璋位于正阳门附近修建山川坛(今石林家居附近)。
网路图片
明代山川坛,为祭祀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钟山、天寿山及京畿山川、都城隍诸神之所。初设祭于南京城南,未有坛壝。洪武三年(1370)建坛于天地坛之西。每年惊蛰、秋分后三日,遣官祭祀诸神。后定正殿七坛:太岁、风云雷雨、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钟山,东西两庑各三坛,东为京畿山川、夏季月将、冬季月将,西为春季月将、秋季月将、京都城隍。渐罢春祭,仅以每年八月仲秋祭祀。永乐迁都北京后,复建于北京正阳门南,增祀天寿山神。嘉靖十一年(1532),改天神地祇坛。
再忆老济南:旧时光中的天地坛街
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四个年头。那年10月,母亲辞去北京三十六中学的工作,带姐姐、我和小弟,从北京西城区达智胡同16号,搬家到济南市历下区天地坛街56号,与在济南的父亲团聚。父亲带大弟在济南已多年,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母亲将全家搬到济南。
天地坛街北首处(1993年)
记得离开北京那天,正好是我10岁生日,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在当时困难的年代,过生日吃两个鸡蛋,已是很奢侈了。那天舅舅送我们到北京站乘火车,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舅舅动情地说:“快看天安门,就要离开北京了!”那时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向往着新的生活,哪懂这句话的份量。多年后回想,离开北京就再回不去了。当时北京户口还未实行管制,以后进京户口就受限了。
从北京来到济南,没有了首都大城市的喧嚣,没有了宽马路,大广场,有的是另外的感觉:城市小小的,马路窄窄的,建筑物低矮,小街巷,小院落,南北兼容的建筑风格,以及浓郁的市井风情。
曲水亭街 (80年代)
天地坛街位于历下区院前大街(现泉城路)中段南侧,南北走向,北通院前大街,直冲珍珠泉;南至南城根街与升官街(现黑虎泉西路)。出天地坛街南口向东不远,就是南门。天地坛街位居济南老城中心,可以说是老城的南北中轴线。据说天地坛街最早得名于明朝。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兵攻陷济南,山川坛和社稷坛被毁。以后在两坛遗址上陆续建起一些商铺和民居,逐渐成为繁华的街巷。天地两坛不复存在,但街名日后得以保留下来。
天地坛街长约300米,宽约3米,青石铺路,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有小饭馆、理发店、榨油坊、裁缝铺,卖烟酒糖茶的杂货铺、加工金银首饰的银匠铺、雕刻石碑的石材铺,还有尹家粥铺、东源盛酱菜园、济生堂药店等老字号。街上的住家,多为四合院,院落不大,门挨门,户挨户。由于天地坛街贯穿老城南北,因此常有马车和地排车拉货经过,马蹄踏在青石板上哒哒作响。拉车人累了,在杂货铺前停车歇脚,在店里打上二两小酒,小酌片刻;有的揣着锅饼,到店里讨口水喝,啃上几口干粮,之后继续拉车上路。那个年代物质虽然匮乏,但百姓的生活却有条不紊,平凡中透着安然自得。
天地坛街北首处(1993年)
天地坛街56号位于街道中段偏南,坐东朝西,厚重的黑漆大门,两边矗立着雕花抱鼓石,威严气派。院中有两个独立的小院,其他是不带院的住房,大约有七八户人家,院中套院的格局。当时住的有张弓弩、邢德林、迟少青、宫叔叔等人家。我家住一单独小院,自成一体。三间北屋,两间西屋,清末民初的老建筑,硬山屋顶,砖木结构。挺大的院落,种的有石榴树、酸枣树等,比在北京达智胡同宽敞多了。
父亲1958年7月调济南军区工作,母亲留在北京,既要教书,又要照料子女,很是辛苦。家搬济南,全家团聚,父亲将奶奶接来一起居住。父亲1938年3月离家,多年来随军南征北战,调动频繁,奶奶一直没在我家住过。在过去动荡的年代,由于爷爷早逝,奶奶携全家颠沛流离,辛辛苦苦将子女带大。今天日子好了,把奶奶接来住,是父亲多年的心愿,尽他的孝心吧。奶奶是福州人,有文化,爱干净,性格开朗。我们小孩在老人面前无拘无束,十分开心。奶奶爱看古书,爱喝花茶,固守着老传统,常跟我们说:“碗里的饭要吃干净,不要掉在地上,掉地上会招老鼠。”我们也深受奶奶的影响。奶奶喜欢热闹,家里天天欢声笑语,洋溢着大家庭的温馨快乐。
家搬济南,我从北京市西城区官房小学转学到济南市南城根小学。所谓南城根,即南城下。那时老城墙已基本拆除,墙基被改造成了渣土路。出天地坛街南口,向西大约200米就到学校了。南城根小学始建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原名山东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小学堂,1914年更名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1938年改名为济南市南城根小学,1964年改称黑虎泉西路小学。学校多次被评为济南市教育先进单位、市爱国卫生先进单位,还被国家教委定为科技教育研究实验学校。南城根小学历史悠久,群星璀璨。据说,季羡林先生、欧阳中石先生都曾是这里的学生,美术大师韩美林先生1953年至1955年在此教过美术。
省立济师附小
学校大门坐北朝南,校园挺大(比北京市官房小学)。进入校门便是操场,操场北边正中,是砖砌的台子和白色影壁墙,上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是学校集会活动的中心,每天同学们要在这里列队做课间操。操场西头是一排粗壮高大的白杨树,半米直径,直冲蓝天,好像是一个个威武的学校卫士。操场北边,是规整的回型校舍,中间为老师办公室,四周是学生教室。我们三年级教室在操场东头。那时的教室,黄土夯的地面,苇子顶棚,原木桌椅,长条课凳,水泥黑板。夏天,教室里热得要命;冬天,靠烧大烟大火的煤炉取暖,有的同学手上生了冻疮,又红又肿。我刚到班里时很不适应,济南土话方言听不懂,同学们听我京腔京调,也挺稀罕,围着我问这问那,甚至有人管我叫“南方蛮子”,真是南北不分了!班主任张老师是女的,高个儿偏胖,圆脸短发,和气可亲。有一次让我朗读课文,描写的是公社社员集体刨红薯的劳动场面。当我念到“一个红薯滚下坡”时,张老师问我:“北京管红薯叫什么?”我回答:“白薯。”大家听了愕然。
班长刘林,男生,个子不高,聪明好动。每天全校课间操,是他站在台子上领操,做的有模有样,神气十足。有天放学后,刘林主动邀请我到他家玩。他家住普利街东头路北,草包包子铺旁边,临街的两层楼房,一楼卖五金土产,二楼住人。那时济南楼房不多,坐落于院前大街的百货大楼也就四层高,住楼房是让人羡慕的。在他家扒着窗户远望,居高临下,共青团路和普利街一带可尽收眼底。
记得班里有个男生叫范建国,圆脸,好和我说话。他有个本事会吹笛子,而且吹得很好。在北京我没见过笛子,很好奇,也想学,就让他到家玩,跟他学吹笛子。这需要父亲的支持,向父亲要了钱,到院前大街乐器店买了一支笛子,天天练习。范建国教得很耐心,还教我怎样贴笛膜,时间不长,我已能吹出简单的歌曲。有天范建国领我到他家,他家在天地坛街和卫巷之间,小院,住两间平房。屋内光线昏暗,摆设简陋,一张大床上靠着一个人,披着衣服,盖着被子,时不时的发出咳嗽声音。范建国说那是他爸爸,有哮喘病,已经很长时间,提出向我家借钱,给爸爸买药治病。那时家家生活都不富裕,但没想到他家这么困难,我很想帮帮他。回家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也很同情,马上拿出钱让我交给范建国,给他爸爸买药。后来怎么样没再问,反正我觉得做了一件好事。
1965年下半年,我家搬到市中区斜马路的崇育里,济南军区政治部宿舍,我则转学到经四路小学。那时活动半径小,没再回过南城根小学。直到我参军后,1971年底探家回济南,才又回南城根小学看看,那时学校已改名黑虎泉西路小学。见到了当时的教导主任,他向我介绍了学校情况。再以后,泉城路、黑虎泉西路经历几次大规模的更新改造。2007年底,黑虎泉西路小学拆迁,让位于济南恒隆广场项目。
新建的黑虎泉西路(1966年)
出天地坛街南口,向东走便到了南门(又称舜田门)。其实,南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被拆除,只保留个地名。如今在南门桥下护城河南岸,还安放着一块镌刻着舜田门三个大字的石碑。当年,桥北两侧各有一面高大的影壁墙,墙上经常张贴着一些通知告示、标语漫画等。在这里,南门桥连接着南门里大街、南门外大街,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护城河,向东可看到解放阁基台(解放阁1986年9月建成),向西便是天下第一泉趵突泉。南门大街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但周边还有数条四通八达的小街巷,东侧有半边街、司里街、所里街,西侧有后营坊、正觉寺街,向南经佛山街可达千佛山。因交通之便,至南门大街一带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百货店、杂货铺、文物古董店、小吃店、照相馆、酱菜园,林林总总。街巷里,拉车赶脚的、挑担赶集的、泉池打水的,车水马龙,非常热闹。记得南门桥东侧有一个很大的空场,自然形成集市,除南北杂货在此交易,还有练武杂耍的、拉洋片的、唱皮影戏的,五花八门,干啥的都有。有年来了个马戏团,支起巨大的帐篷表演马戏、空中飞人等节目,吸引很多人买票观看。我曾在帐篷的缝隙间悄悄逃票钻进去,躲在一边看演出。
护城河(1965年)
在建的解放阁(70年代)
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还属护城河。护城河水源于趵突泉、黑虎泉、五龙潭等几大泉群,水源充足,四季长流,据说是国内唯一全部由泉水汇集而成的河。尤其是南护城河,泉源众多,碧波荡漾,河畔垂柳成荫,芦苇蒲草茂盛,水光山色,为济南这座北方城市增添了浓郁的江南风韵。那时护城河还未人工整治,顺着河堤漫坡下到河边,眼前河面宽阔,河水清澈,缓缓流淌,长长的水草轻轻摇曳,河面泛着点点波光,微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河边有许多青石板,把石板搬开,惊喜地发现,下面藏着许多小虾小鱼,但不好捉,它们逃匿的速度极快。逮不着怎么办?用纱布和铁丝做成网子,捕虾捞鱼,用小玻璃瓶带回家。护城河四时风光不同。清晨或雨后,水面云雾缭绕,周边景致尽在雾霭之中。尤其冬季,泉水与空气温差大,经常出现云雾润蒸的现象,恍若仙境。护城河水质洁净,常有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盆,提着桶,到河边洗衣。她们先把衣物放在河水中浸泡,然后放在石板上,用棒槌反复敲打,敲击的声音还带着节奏。天气晴好,有人将洗净的衣服晾晒在树杈、石板上,傍晚再收回家。河边洗衣,也成当时一种特殊的社交方式,棒槌声,说笑声,交汇成趣,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黑虎泉(1965年)
在天地坛街附近,还有一个好去处,就是位于旧军门巷的新华电影院。旧军门巷靠近西门,是西门大街与南城根街之间一条南北向的老街巷。这条巷子之所以出名,是因明朝时,巷内曾建有巡抚衙门,称为巡抚督察院,后来随着巡抚职责的增加,其衙门改称督抚军门。这也是旧军门巷的来由。当时巷子里还保留着清代山东巡抚丁宝桢的故居,可惜后来被拆除了。新华电影院位于巷子中段路东,建于1924年,据说是解放前老城内唯一的电影院。电影院门面很气派,门口贴满花花绿绿的电影广告,小喇叭不停地播放着电影插曲。影院内是固定的连排座椅,观影条件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影院在寒暑假推出学生专场,售学生票,每场五分钱。新年春节还有通宵电影,可以看连场,对孩子们极具吸引力。《林海雪原》、《红孩子》、《翠岗红旗》、《鸡毛信》等经典影片,我都是在新华影院观看的。
新华电影院服务证及票根
南门桥(80年代)
时代变迁,城市日新月异。记忆中的天地坛街、南城根小学、南门大街、护城河,已被现代化的高楼商厦、宽阔的马路、具有标志性的泉城广场、漂亮的环城公园所代替,仅存的还有浙闽会馆、舜田门遗址石碑等极少的印记。每当来到这里,环顾四周,眼前总会隐隐浮现当年那种纯自然的、未经雕琢的风景,浮现出当年那些人和事……时间一去不复返,但如果在此能有一座博物馆,展现济南老城发展的时空变化,收纳陈列当年的老物件、老照片,辅之以纪念文章、诗词书画,相信一定会吸引众多老济南前来参观怀旧,同时有助于年轻一代了解老城历史,也是市民爱泉城的教育之所。
孙阳
2022年6月1日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齐鲁壹点”,全省6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