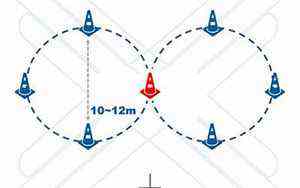现代女性都很少戴花,为什么唐宋时期男子却要戴花
咸淳五年,正是南宋度宗在位时期,当时京城流传一句诗谣:“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这本来是玻璃簪钗的流行,以至于京师之中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头上佩戴琉璃簪钗。然而,这句本还喜气的诗词,却越传越怪异,成为了一句可怕的预言。
原来,“琉璃”与“流离”同音,预示天下大乱,江山易主,百姓流离失所。有识之士认为这是“流离之兆”,果然在度宗驾崩五年之后,宋朝就被蒙古人灭了。
这个故事,往往用来说明在南宋时,男子具有戴花的习俗。即使不戴鲜花,连假花也要佩戴,现代女性都很少戴花了,为什么当时的宋朝男人如此“娘”?这难道就是宋朝积弱的原因,就是外战外行的表现吗?
宋朝人确实喜欢戴花,在小说《水浒传》中可窥一斑。外号“一枝花”蔡庆自不待说,小旋风柴进大官人在进禁苑的时候,就簪花而入。阮小五只是一个渔民,却“鬓边插朵石榴花”。杨雄是个牢头,赞词中却称他“鬓边爱插翠芙蓉”。宋江虽然没有直接戴花,却说道: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
尽管《水浒传》是明朝人写的小说,内容不可尽信,然而艺术是源于生活的,宋朝男人戴花是有根有据,这在数之不尽的名人典故和诗词之中可以看出来。
寇准官至参知政事的时候,还才三十多岁,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宫中赴宴,宋真宗特地赐给他一株罕见的异花,并且向群臣说,你们不要嫉妒,“寇准年少,正是戴花吃酒的年岁”。
宋真宗将鲜花赐给臣下,已经成为了笼络下级,拉近关系的手段。不光寇准有,其他大臣也曾受到过这种恩典。比如在封禅之前,他就任命陈尧叟、马知节为东京留守和大内都巡检使。封官之后,君臣三人饮宴,都带着鲜艳的牡丹。在高兴之余,宋真宗从自己头上摘下最名贵的牡丹,亲自给陈尧叟戴上。
陈尧叟感激涕零,出门之后一阵风吹来,还弄坏了半片花瓣,他连忙让仆人小心收好,还嘱咐道:此乃官家所赐,不可弃之。
宋徽宗自己也爱戴花,史书记载他每次出游“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他的随从都会被赐花佩戴。宋徽宗还规定,御赐的簪花带回家后,不得给仆从佩戴,违者严惩。皇家如此重视戴花,民间百姓更加效仿。当时的男子既可以插一枝花,也可以插满头,陆游在《观梅至花泾高端叔解元见寻》:
春晴闲过野僧家,邂逅诗人共晚茶。归见诸公问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
在韩琦担任扬州太守时,府中的金缠腰花开了。当地早有传说,只要金缠腰一开,就有人要拜相,那次一开就是四朵。为了应景,韩琦邀请了王珪、王安石、陈升之一同赏花。在兴致最高的时候,韩琦摘下金缠腰,给自己和另外三人佩戴。最后,这四人都得以拜相,这也是四相簪花的故事,被沈括写入过《梦溪笔谈》。
有人说送人文弱,才会有男子戴花的习俗。其实,这个风俗就是在民风彪悍的唐朝开始的。有史记载,男子戴花最早出现在唐玄宗时期,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有位叫做苏颋为皇帝作诗,其中一句“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很得皇帝赏识。于是,唐玄宗亲自为他在头上插上了鲜花。这种习俗一直传到了晚唐,杜牧在《九日齐山登高 》赞叹: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所以,宋代男人戴花,也不过是一种文化习惯而已,扯不到什么重文轻武之上,顶多也就是因为宋代更重视文雅之气,让他们对戴花极具浪漫气息的习俗更为热衷而已。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米芾等等文化大家都乐此不疲。到了元代,男子戴花渐渐稀少,但还是有零星的记载,明朝以后就基本绝迹了。
李安拍摄《喜宴》之前,中国台湾电影已打破“禁忌”!
“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恐同?”
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以下简称《鬼家人》)里,存在于2023年的银幕上的女警察,翻着白眼说出这句话时,代表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同志电影,早已从多年的阴霾情绪中走出。
这也体现了中国台湾在同婚合法后,同性关系被普遍接受的集体意识。
除了电影内部对同性关系的理想环境的呈现,电影本身也在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票房成绩。
《鬼家人》上映时票房节节高升,最终收获了3.64亿台币(人民币8270万)的票房,登顶同志议题片票房榜首。
在该类电影并不稀缺的中国台湾,《鬼家人》作为一部现象级影片,在各个维度上准确把握了商业类型片广受欢迎的元素。
它将喜剧梗、高概念、反套路融入其中,再次让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如何在该类电影的赛道上,走在了前列。
然而,也不能忽视,从小众到大众,从悲情叙事到喜剧呈现,中国台湾的该类电影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走出“深柜”POST WAVE FILM
同性恋的历史,与异性恋一样长。
然而文艺作品对同性恋的书写,则要比异性恋晚得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旬,大学毕业的白先勇在长篇小说《孽子》中用大量的笔墨隐喻这一群体的压抑: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
对照那一时期,同性恋者祁家威,因为发表了一篇《同性恋者的恳切声明及呼吁》,被警察署抓去关了半年。
白先勇先生写的这句话,的确暗合了当时这一群体的处境。
作家白先勇
不久后,由小说《孽子》改编的同名电影播出。
但是当时正处于“戒严”时期,受制于审查制度,《孽子》对该群体并没有露骨呈现,甚至在剧中都没有直接提到相关措辞。
《孽子》海报
正如《孽子》一样,当时一些具有同性元素的影视作品(如《孤恋花》《两个油漆匠》),都选择将这一禁忌之爱,淡化为模糊的轮廓,安插在同性话语之中。
在这些作品里,该关系被编码为“反父权”、“反封建”叙事里的隐秘文本。
白先勇(左)与爱人王国祥
1987年,中国台湾正式宣布解严。
社会对该群体的态度逐渐转变,也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态度,该类电影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991年,一部充满女同色彩的电影《双镯》上映。
《双镯》海报
影片虽未直接展现女性之间的爱情,但全篇浓郁的暧昧情愫,刻意模糊了爱情与友情的界限。
在当中,惠花将象征着情谊的镯子交给秀谷,动情地说:“姐妹夫妻永不分离。”
相较只能用“小玻璃”做隐喻的《孽子》,这句台词出现得实属不易。
不过就在次年,中国台湾的电影对该群体的书写,将迎来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
从九十年代起,中国台湾为了让青年导演有机会拍出优质电影,出台了相关方案,并提供一部分辅导金。
获得辅导金的人包括李安、蔡明亮、易智言等人。
而正是这几个人,让该类电影在艺术和商业的双重维度上,走向了一次高峰。
《喜宴》海报
李安的《喜宴》首开先河,打破了中国台湾的电影,不能直接书写该群体情感关系的禁忌。
影片中,伟同对妈妈说:“我是同X恋,Simon是我的爱人。”
这句台词,让伟同完成了身份上的自我确认,对当年中国台湾该群体来说意义重大,也对推动了全社会对相关议题的讨论度。
《喜宴》过后,中国台湾的电影对该群体关系的描述,变得更加直白,讨论的议题也更加深入。
比如,同为蔡明亮的电影,《青少年哪吒》里小康对朋友的爱慕,还只是通过“报复”行为间接地表现。
《青少年哪吒》海报
等到了《爱情万岁》,则变成了一次偷吻。
在1997年的《美丽在唱歌》里,两位女生赤裸相拥而吻的画面,把女性之间的情欲,更加直接地带到了镜头前。
在此之后,该类电影从早期的“深柜”中走出,逐渐进入画面的前景,并在千禧年来临之时,成为商业电影中广受欢迎的类型。
用青春片去探索POST WAVE FILM
进入新世纪,中国台湾向世界展示了对该群体的“开放”态度。
一方面,官方将此类议题写进学生的课本,颁布《性别平等教育实施细则》,规定“任何人不能因其性倾向、性别认同等不同,而受到差别之待遇。”
另一方面,大众媒体看待该群体的角度更加平等,使得此前该类电影里那种愤慨情绪,变成了充满青春朝气的恋爱絮语。
2002年,《蓝色大门》中17岁的孟克柔,因为对好友林月珍的爱慕,陷入了青春期的身份焦虑。
《蓝色大门》海报
在这部电影里,他们的身份不再如往常一样,是让主角被逼至边缘境遇的罪魁祸首。
而是在进入成人大门之前,对自我认同、自我探索感到困惑的诱因。
《蓝色大门》用性向,来讲述青春期的暧昧与躁动,让人们看到了该类电影的另一种可能性。
随后,以此类话题为题材的青春电影,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渺渺》《盛夏光年》《少年不戴花》《17岁的天空》……
此类身份不再是进入主流社会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少男少女成长故事里独特的个人体验。
它们往往轻快、浪漫,具有极强的情感号召力,均有出色的票房成绩。
《盛夏光年》海报
在此之后,电影创作者们又将各式各样的类型元素,与该类题材结合在一起,包括歌舞、悬疑等。
该类电影愈加多元化,也再无不可触碰的“敏感地带”。
但是,这一题材也逐渐显现出在消费主义盛行之下,被“掏干挖净”的疲态。
在类型片变成熟POST WAVE FILM
2017年,司法院宣布受理祁家威提出的释宪申请。
祁家威
不久后,中国台湾地区“大法官”作出「748号解释」,宣布“民法”的婚姻规定,不能保障这一类伴侣的共同生活,属于违宪,需修改相关法案。
他还表示,接下来的两年内,不管立法院有无针对此类婚姻进行修法,两年后,这类恋人只要带着两人的证人签名书,就可以到户政机关办理结婚。
这意味着,中国台湾将有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地区。
此话一出,这一群体纷纷身披彩虹旗涌上街头,相拥而泣。
在等待的这两年里,《谁先爱上他的》作为新历史时期里的该类电影,将焦点对准了“同妻”这一高敏感话题。
《谁先爱上他的》海报
这部电影虽然重诉了这个古老命题,但是又用手绘、儿童视角、喜剧设计等方式,冲淡了影片的苦闷情绪,显露出新的社会环境下的释然和幽默。
当然,也要体现出在该类婚姻正式合法化前,这一类电影应该有的革命力度。
当宋正远决定隔断与高裕杰的恋情时,他说:“让妈妈不难过、不担心,就是我们的责任。”
高裕杰不解,“为什么我爱你,她会难过?”
这个问题抛给了宋正远,也抛给了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体制。
2019年2月21日,以该群体相关的专用法,在中国台湾正式通过。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作为合法后的第一部重量级影片,在上映之前就备受期待。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海报
上映之后,更是多次刷新中国台湾本土的各项票房成绩,带动了中国台湾观众支持该类婚姻的高涨情绪。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将叙述对象定了“旧时”,回顾了在“解严”之初,这一群体的屈辱史。
然而,后面悬浮于现实背景之上的叙事和过多的情感拉扯,让它沦为一出老生常谈的旧戏码。
而到了今年,《鬼家人》选择的路径则是“当下”,一个该类婚姻合法后已有四年的社会。
在这一时期,喜剧片的确是最好的选择,用独具当前社会风格的笑料,对这个耳熟能详的题材进行解构和重构。
在欢声笑语中,让我们暂时忘却这一群体曾经的阴霾,使得这一题材不再特殊。
这是能够表现当下中国台湾该群体生活状态的最典型的电影。
所以,《鬼家人》的出现,的确是意义非凡的。
它代表了该群体已然挣脱了《孽子》中“中央公园”代表的隐性牢笼,走进了裸男的浴室里,开着“叫死gay,还是叫老公”的玩笑。
而这一晃,就是近四十年。
作者丨一只呀
我不是亚当的肋骨。
编辑丨毛头 排版丨凉茶
媒体统筹丨佐爷灵魂贩卖馆
「注:本文部分图片来源于豆瓣及网络,
若有侵权请主动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