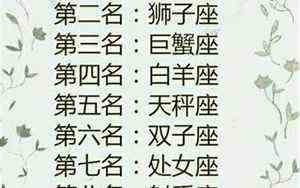
“热肠挂住”与“冷眼看穿”
若论“才情”,庄子之“才”自古至今为天下公认。以古人举例,明末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称《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而将《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以今人举例,郭沫若在《今昔蒲剑》中说庄子“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其为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可见庄子的才学和文章历来备受推崇。但就“情”而论,则自古以来庄子基本被视为对世间无情之人。庄子思想因其深刻性以及入木三分的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历史上曾受到一些误解。后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必己》的注中,说庄子“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这种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庄子便由于“齐万物”、“同死生”、“泯是非”等思想,而被指为崇尚虚无、对世间冷漠无情。
到了清代,庄子终于遇到了知音。一些学者透过庄子看似冷漠无情的处世态度,认识了庄子的真实心境。顺治年间学者林云铭(1628—1697)在《庄子因》中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庭之常,工技屠宰之术,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乾隆年间学者胡文英(1723—1790)的评价则更为深刻、形象。他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他认为庄子对于人世间的态度,是“热肠挂住”与“冷眼看穿”兼而有之。
诚如所言,庄子并非对世间冷漠无情。《庄子·天下》篇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虽然“内圣外王”后来成为儒家关于修身与治国的基本思想,但这个理念毕竟是由庄子首先提出。它反映了庄子对于世间之人、世间之事的态度和情怀。庄子“冷眼”处世,并非出于无情,而是出于冷静清醒。权贵面前,庄子拒绝同流合污。世俗面前,庄子不愿随波逐流。他始终保持一份理智和清醒,而在他看似冷若冰霜的“冷眼”后面,是悲天悯人的热切情怀。
对于世间,庄子既是“热肠挂住”,为何却又“冷眼看穿”?根本原因在于庄子的救世主张与当时的“世之显学”儒家思想不同。儒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君王实行仁政、德治,希图以此救世。而在庄子看来,这样救世无异于“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儒家的救世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庄子·至乐》篇中如下的一则故事,假托孔子之口,批评了儒家试图通过提倡仁政、德治来救世的主张,同时表明了庄子的救世主张:一次,颜渊准备到齐国去宣扬儒家的救世之道,孔子面露忧色,说:“从前,有只海鸟停栖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侯听人说这只鸟是神鸟,就派人把它捉住,亲自把它迎接到祖庙里供养起来,奉上精细的膳食‘太牢’给它吃,演奏美妙的音乐‘九韶’给它听,然而海鸟被折腾得头晕目眩、惶恐不安。它不吃不喝,几天就死了。”
庄子认为,“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儒家的救世主张如同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而不是按照鸟的习性来养鸟,所以结果就是把鸟折腾死。同样道理,救世一定要遵循人的本性。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是由于世人的纯真质朴的本性正在丧失。所以,救世的根本方法在于“救心”,让人们归心“大道”。所谓大道,就是道家所说的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
依庄子之见,让世人归心天地大道、还原纯真本性,才是治世之要义。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安宁。《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以后,鱼儿为了活命,相互之间以口沫来保持对方湿润。这固然是友爱之举,但总不如各自回到浩瀚的大河大湖里去,彼此不相干甚至不认识为好。庄子以鱼喻人,以水喻道,认为人丧失了本性,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因此尽管儒家竭力提倡仁德之治,固然也能够收一时之效,却无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庄子认为,与其号召天下人遵从仁义道德,不如引领天下人恢复本性,归于大道,即“救心”。从庄子对儒家救世主张的多次批评,也可以看出他并非对世事冷漠无情的“出世”之人。倘若庄子真的漠视天下治乱和民间疾苦,又何必如此关注、批评儒家的救世主张?若无“热肠挂住”之情怀,何必谆谆而言之?
为了“救心”,庄子提出了破除“机心”的思想。《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到楚国游历,返回的路上经过汉水一带,看到一老者正在菜园里忙碌。老者抱着水罐给菜地浇水。子贡说:“现在有一种机械,一天不费多少劲就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您老人家想不想试试?”老者问子贡:“什么样的机械呢?”子贡说:“这种机械叫作桔槔。它后重前轻,用它取水非常方便省力,而且取水之快,如同泉涌。”老者说:“这种机械我不愿使用。人有了机械这种东西,就会谋取机巧;有了机巧之物,人就会有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胸怀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的人,他的纯真质朴的本性就会丧失;纯真质朴的本性丧失了,他就会远离天下大道。”可见,庄子的救世,就是要让世人从各种机巧、算计之中解脱出来,回归纯真质朴的本性。他认为,引领天下人的心灵回归本性,才是根本的救世之道。
在庄子看来,人的物质上的贫困,身体的病态甚至死亡,都不值得悲哀。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人的本性的迷失,这就是《庄子·田子方》所说的:“夫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世上能够诱惑心灵的事物太多,且不说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即便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等等,也无不牢牢地束缚住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沉溺于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逐而迷失本性、远离大道。唯其如此,救世就是要“复性”,用天下大道去挽救人心,恢复人的纯真本性。
可见,儒家是试图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实践层面救世,即通过实行仁政、德治而救世;庄子则希图从社会成员内在的精神层面救世,即通过救心、复性而救世。二者都有救世之心,但主张不同。庄子通过“救心”而救世的主张,难免被世人视为十分迂腐而不切实际的。惠施曾经将庄子关于“大道”的看似不着边际的言谈比喻为樗树,说它“立之途,匠者不顾”(樗树长在路旁边,木匠却不屑于看它一眼),原因就在于它“大而无用”。庄子则认为“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其实大道具有为世人所不知晓的大功用。这种“大用”,乃成就事物的本性,包括人的本性。在混乱的浊世,唯有大道可以挽救人心,恢复人的淳善本性。
上述种种,使得清人胡文英认为,漆园吏庄子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比三闾大夫屈原更深切的悲天悯人情怀。他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屈原哀怨,是由于他无力解救当时楚国灭亡的灾难;庄子哀怨,则是由于在他看来,世人纯真本性的丧失可能已经成为万劫不复的惨痛事实。正因为这样,对于人间世,庄子虽然“不能忘情、热肠挂住”,同时却又“终不下手、冷眼看穿”。庄子情怀的这种“复杂性”,似是庄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余秉颐,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热肠挂住”与“冷眼看穿”
若论“才情”,庄子之“才”自古至今为天下公认。以古人举例,明末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称《庄子》、《离骚》、《史记》、《杜工部集》、《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而将《庄子》列为“第一才子书”。以今人举例,郭沫若在《今昔蒲剑》中说庄子“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汪洋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其为文则汪洋捭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可见庄子的才学和文章历来备受推崇。但就“情”而论,则自古以来庄子基本被视为对世间无情之人。庄子思想因其深刻性以及入木三分的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在历史上曾受到一些误解。后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必己》的注中,说庄子“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这种观点被不少人接受。庄子便由于“齐万物”、“同死生”、“泯是非”等思想,而被指为崇尚虚无、对世间冷漠无情。
到了清代,庄子终于遇到了知音。一些学者透过庄子看似冷漠无情的处世态度,认识了庄子的真实心境。顺治年间学者林云铭(1628—1697)在《庄子因》中说:“庄子似个绝不近情的人,任他贤圣帝王,矢口便骂,眼大如许;又似个最近情的人,世间里巷、家庭之常,工技屠宰之术,离合悲欢之态,笔笔写出,心细如许。”乾隆年间学者胡文英(1723—1790)的评价则更为深刻、形象。他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他认为庄子对于人世间的态度,是“热肠挂住”与“冷眼看穿”兼而有之。
诚如所言,庄子并非对世间冷漠无情。《庄子·天下》篇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虽然“内圣外王”后来成为儒家关于修身与治国的基本思想,但这个理念毕竟是由庄子首先提出。它反映了庄子对于世间之人、世间之事的态度和情怀。庄子“冷眼”处世,并非出于无情,而是出于冷静清醒。权贵面前,庄子拒绝同流合污。世俗面前,庄子不愿随波逐流。他始终保持一份理智和清醒,而在他看似冷若冰霜的“冷眼”后面,是悲天悯人的热切情怀。
对于世间,庄子既是“热肠挂住”,为何却又“冷眼看穿”?根本原因在于庄子的救世主张与当时的“世之显学”儒家思想不同。儒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君王实行仁政、德治,希图以此救世。而在庄子看来,这样救世无异于“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儒家的救世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庄子·至乐》篇中如下的一则故事,假托孔子之口,批评了儒家试图通过提倡仁政、德治来救世的主张,同时表明了庄子的救世主张:一次,颜渊准备到齐国去宣扬儒家的救世之道,孔子面露忧色,说:“从前,有只海鸟停栖在鲁国都城的郊外。鲁侯听人说这只鸟是神鸟,就派人把它捉住,亲自把它迎接到祖庙里供养起来,奉上精细的膳食‘太牢’给它吃,演奏美妙的音乐‘九韶’给它听,然而海鸟被折腾得头晕目眩、惶恐不安。它不吃不喝,几天就死了。”
庄子认为,“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庄子·至乐》)儒家的救世主张如同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而不是按照鸟的习性来养鸟,所以结果就是把鸟折腾死。同样道理,救世一定要遵循人的本性。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是由于世人的纯真质朴的本性正在丧失。所以,救世的根本方法在于“救心”,让人们归心“大道”。所谓大道,就是道家所说的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
依庄子之见,让世人归心天地大道、还原纯真本性,才是治世之要义。唯有如此,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安宁。《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涸以后,鱼儿为了活命,相互之间以口沫来保持对方湿润。这固然是友爱之举,但总不如各自回到浩瀚的大河大湖里去,彼此不相干甚至不认识为好。庄子以鱼喻人,以水喻道,认为人丧失了本性,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因此尽管儒家竭力提倡仁德之治,固然也能够收一时之效,却无法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庄子认为,与其号召天下人遵从仁义道德,不如引领天下人恢复本性,归于大道,即“救心”。从庄子对儒家救世主张的多次批评,也可以看出他并非对世事冷漠无情的“出世”之人。倘若庄子真的漠视天下治乱和民间疾苦,又何必如此关注、批评儒家的救世主张?若无“热肠挂住”之情怀,何必谆谆而言之?
为了“救心”,庄子提出了破除“机心”的思想。《庄子·天地》说,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到楚国游历,返回的路上经过汉水一带,看到一老者正在菜园里忙碌。老者抱着水罐给菜地浇水。子贡说:“现在有一种机械,一天不费多少劲就可以浇灌上百个菜畦,您老人家想不想试试?”老者问子贡:“什么样的机械呢?”子贡说:“这种机械叫作桔槔。它后重前轻,用它取水非常方便省力,而且取水之快,如同泉涌。”老者说:“这种机械我不愿使用。人有了机械这种东西,就会谋取机巧;有了机巧之物,人就会有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胸怀投机取巧、算计诈伪之心的人,他的纯真质朴的本性就会丧失;纯真质朴的本性丧失了,他就会远离天下大道。”可见,庄子的救世,就是要让世人从各种机巧、算计之中解脱出来,回归纯真质朴的本性。他认为,引领天下人的心灵回归本性,才是根本的救世之道。
在庄子看来,人的物质上的贫困,身体的病态甚至死亡,都不值得悲哀。真正值得悲哀的是人的本性的迷失,这就是《庄子·田子方》所说的:“夫哀莫大于心死,而身灭亦次之。”世上能够诱惑心灵的事物太多,且不说高官厚禄、金钱美女,即便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等等,也无不牢牢地束缚住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沉溺于对物质享受的无止境追逐而迷失本性、远离大道。唯其如此,救世就是要“复性”,用天下大道去挽救人心,恢复人的纯真本性。
可见,儒家是试图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实践层面救世,即通过实行仁政、德治而救世;庄子则希图从社会成员内在的精神层面救世,即通过救心、复性而救世。二者都有救世之心,但主张不同。庄子通过“救心”而救世的主张,难免被世人视为十分迂腐而不切实际的。惠施曾经将庄子关于“大道”的看似不着边际的言谈比喻为樗树,说它“立之途,匠者不顾”(樗树长在路旁边,木匠却不屑于看它一眼),原因就在于它“大而无用”。庄子则认为“无用之用,乃是大用”,世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其实大道具有为世人所不知晓的大功用。这种“大用”,乃成就事物的本性,包括人的本性。在混乱的浊世,唯有大道可以挽救人心,恢复人的淳善本性。
上述种种,使得清人胡文英认为,漆园吏庄子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比三闾大夫屈原更深切的悲天悯人情怀。他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屈原哀怨,是由于他无力解救当时楚国灭亡的灾难;庄子哀怨,则是由于在他看来,世人纯真本性的丧失可能已经成为万劫不复的惨痛事实。正因为这样,对于人间世,庄子虽然“不能忘情、热肠挂住”,同时却又“终不下手、冷眼看穿”。庄子情怀的这种“复杂性”,似是庄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余秉颐,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世人庸人自扰的讽刺;
曾几何时你我皆是为情而困的情种,亦或者别人眼中的白痴,一往而深的感情,那也只是你自己的一往情深,在现在这个物质和充斥着金钱味道的社会里,有多少人会因为你的一往情深而心甘情愿的双向奔赴!可笑至极,没有这样的人。
情不知所起,是因为你的贪恋,因为你自控欲太差,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无欲无求才会提升自己,价值观的实现完全掌控在你自己的手里,胡乱用情只会使你自己堕落,更或者会一 蹶不振。深渊可以凝视,但是千万不要凝视太久。
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一笑泯恩仇,倚剑走江湖;之所以有恨,除了国仇和家恨,因为付出太多回报的少产生的恨,亦或者因爱生恨,这样的恨根本无药可解,扭曲心理上的爱,其实就是一种虐恋;
你做了99件好事,没人会记得,但是你做了一件坏事,却被人铭记于心。
影响古代朝鲜的辞赋双璧
作者:王进明(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古代朝鲜文人对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苏轼的《赤壁赋》给予高度评价,如李民宬盛赞:“陶渊明《归去来辞》,千古绝唱。”徐居正则说:“赤壁一赋,万古风流。”两文被奉为圭臬,文人争相效仿,成为影响古代朝鲜的“辞赋双璧”。朝鲜朝末期重臣、著名文学家李裕元对汉文学发展作总结时说:“凡仿古者,或于《归去来辞》《赤壁赋》等篇,不换几字,同其法而成之,是亦一段体也。”由此可见其深远影响。辞赋双璧为古代朝鲜文人提供了三重精神寄托:续写赤壁泛游的现实精神寄托,效仿官场归去的理想精神寄托,进行心灵对话的审美精神寄托。
苏轼《赤壁赋》为古代朝鲜文人提供续写赤壁泛游的现实精神寄托。
首先是行为效仿的现实精神寄托。1462年秋七月十六晚,徐居正与好友泛舟出游饮酒分韵赋诗,题写“壬秋七望广津头,拟续前贤赤壁游。”(《四佳集》)开启古代朝鲜文人续写赤壁泛游的范式。赵缵韩在《反赤壁赋》中描述:“今兹岁纪,属于壬戌秋之既望,又值此月,此非苏仙游赤壁之夕欤?是用骚林墨坛好事之徒,莫不提壸挈榼,争泛江湖者。”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7世纪前期文人泛游之繁盛。郑宗鲁在诗序中也说:“每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则思欲泛舟弄月,以办胜游,则必相与泛舟前江而游,用《赤壁赋》分韵赋诗,以写其兴。”(《立斋集》)可见文人效仿月夜泛游雅会盛况空前。
其次,诗歌意象的现实精神寄托。在古代朝鲜文人眼中,苏轼赤壁泛游是文人理想的雅会娱情方式,赋诗中多次用到与赤壁相关意象,如“赤壁秋”“赤壁月”“赤壁舟”“赤壁船”“赤壁游”等,表达效仿苏轼赤壁之游,谋求现实精神寄托。在他们心目中秋天就是苏轼赤壁之秋,如沈喜寿“蜉蝣天地寄悠悠,又直苏仙赤壁秋。”(《铜崔亭晴望》)李昭汉“政值苏仙赤壁秋,问谁文采古人俦。”(《次崔大容有海韵》)李詹宿“烟浓杜子清淮夜,月小坡仙赤壁秋。”(《灭浦院楼》)在文人笔下月变为赤壁之月,如南有容“自古皆言赤壁月,长公豪气凌苍昊。”(《西亭望月作歌》)尹斗寿“珍重此筵须勿负,明宵赤壁月中游。”(《锦城榜会》)孝明世子“画阁夜长玉露晞,千年赤壁月生辉。”(《上林十景》)至于“赤壁舟”“赤壁船”“赤壁游”亦是如此。文人还把本地江河泛游比拟为赤壁,如丁寿岗“欲把汉江为赤壁,吹箫月下共扁舟。”(《七月既望,寄枕流堂》)李荇“拟把汉江当赤壁,何妨壬戌作庚辰。”(《七月既望之夜,泛舟汉江,玩月有作》)
最后,比照苏轼的现实精神寄托。更为重要的是文人喜欢将苏轼作为参照对象,抒发泛游体会,以满足现实心理寄托。如刘希庆“不知此日笙歌兴,争似苏仙赤壁游。”(《沧浪亭泛舟》)南景羲“帆头更得东山月,不让苏仙赤壁游。”(《痴庵集》)宋奎濂“谁知此夕沧江兴,不让当年赤壁游。”(《霁月堂集》)金安国“夜深更击空明去,即是苏仙赤壁游。”(《慕斋集》)赵任道“千载苏仙赤壁游,吾侪此会亦风流。”(《涧松集》)赵冕镐“昨梦苏仙赤壁游,满江明月载扁舟。”(《闰七月既望,步月山庭》)经过文人不断充实,开创了一个续写赤壁泛游范式的海东盛况。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为古代朝鲜文人提供效仿官场归去的理想精神寄托。
第一,进入官场终极目标的理想精神寄托。徐居正提及:“归去来者,晋征士陶潜之辞也。前辈释之曰:‘归其官,去其职,来其家。’盖古人得出处进退之正者莫如潜。后之有志之士,孰不欲幼而学,壮而行,老而退,以全终始者哉。”(《归来亭记》)古代朝鲜文人盛赞陶渊明是官场进退的典范,有志文人皆以其为榜样,遵循年轻入仕、老年归隐的准则,将其作为官场终极目标的理想精神寄托。如李奎报“他日功成便归去,倩人先筑钓鱼台。”(《又次渭津东望诗韵》)蔡之洪“他日功成归可早,季鹰秋思正难禁。”(《别郑季修棹入京》)赵冕镐“功成身退然后事,琴鹤逍遥归涧阿。”(《失题》)郑太和“他日功成归去后,五湖风月在扁舟。”(《阳坡遗稿》)另外,受其影响,古代朝鲜有81位文人选用与“归去来”有关的意象命名字号寓所。
第二,仕途过程“心为形役”的理想精神寄托。陶渊明第一次提出“心为形役”这个命题,认为身在官场束缚自我,要早日迷途知返回归田园,触及文人灵魂深处的主题,给古代朝鲜文人提供了为官仕途中的理想精神寄托。许多文人为官时赋诗表达共鸣,如李詹“未能自克为形役,要向仁山卜结庐。”(《心》)李集“不堪奔走为形役,又见光阴逼岁除。”(《平昌郡楼题咏》)金诚一“胡为形役久不归,两鬓坐受风霜侵。”(《我所思》)李民宬“心为形役奚惆怅,事与时违便乞归。”(《南归》)最典型的是朝鲜朝水陆防备专委守臣李敏求提出“士大夫不可一日不读《归去来辞》。”(《吕子久归去来辞集字律诗三十首跋》)
第三,脱离官场仕隐矛盾的理想精神寄托。仕与隐是古代文人必须直接面对的人生主题。当个人理想与官场现实冲突,或功成名就、或不喜功名,或党派之争等多种因素交织时,文人遂产生归隐想法,自然而然就联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贵独立人格和回归田园的高蹈远举深深影响着古代朝鲜文人。他们结合自身实际,从不同视角赓和“归去来”辞,共有84人写了86篇和辞,其中申钦和李最中各作两篇,构建规模庞大的“归去来”文学群,形成世界文学史的一大奇观。除此之外,许多文人作诗用“归去来”“归去”“归来”“归田”意象表达以陶渊明为楷模辞官归隐田园的美好愿望。正如尹拯所说:“‘归去来’一辞,固骚人墨客之所共咀嚼。或步其韵,效其声响者有之;或集其字,述其意趣者有之。”(《次挹陶堂十咏韵》)经文人不懈地认同、追加、赓和、强化,“归去来”成为文人效仿官场归去的理想范式。
有关辞赋双璧绘画为古代朝鲜文人提供心灵对话的审美精神寄托。古代朝鲜流传许多有关“归去来”和《赤壁赋》的绘画,文人欣赏时将所观所感付诸文字写了很多首题画诗,形成辞赋双璧文、画、诗三融合。如李好闵“元亮扁舟兴,当时岂自知。如今画里见,斗觉壮心违。”(《渊明归去来图》)金应祖:“五柳荫中处士家,石头松老影婆娑。飞鸿数点青冥阔,万古清风载一槎。”(《题归去来图》)徐居“当时行乐绝代无,二赋流传天壤俱。先生气节凌宇宙,先生文章焕星斗。追忆先生四百年,赤壁风月还依然。我今为赋赤壁诗,欲唤先生酹一巵。”(《苏仙赤壁图》)沈希安“十月无边兴,千秋不泯风。苏仙与二客,相对画图中。”(《题赤壁图》)文人面对绘画中的陶渊明、苏轼影像,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进行隔时空对话,产生心理与思想上的共鸣,享受审美体验,得到心灵蕴藉,以诗歌表达向往之情,同时寄托个人情怀。
宋代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说:“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辞赋双璧影响留存于古代朝鲜文人诗文中,超越了时间与空间,跨越了民族与文化,留传千载百世,成为“千古绝唱”“万古风流”,成为他们现实、理想和审美的精神家园,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光明日报》( 2021年04月19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