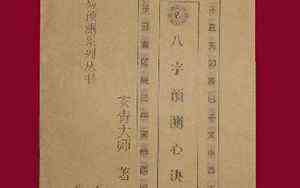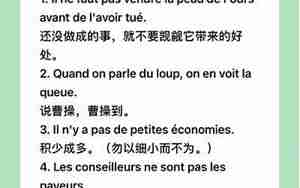《召诰》《洛诰》曆日和周成王元年
《召诰》《洛诰》曆日和周成王元年文/毛天哲周成王像-明人绘
伏生《今文尚书》、孔壁本《古文尚书》皆有<召诰><洛诰>文,二者有记事曆日,涉及成王年间史事。国家学术工程——夏商周断代所设置的据以推求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其中第七个就是"《尚书·召诰》、《毕命》曆日与成王、康王元年"。
断代工程专家定成王元年为前1042年,是基于<召诰><洛诰>曆日为同一年(前1036年)的认识,且以为作于成王七年,由此逆推的结果。客观说,工程定二诰年代没错,但定此年为成王七年实误也。事实上,据哲的研究,<洛诰><召诰>是作于"成王亲政始年",也即"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后一年。
将此二诰年代看作是周公摄政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即成王七年),这个错误观点并不新鲜,已经流传二千多年了,至今还是如此。《汉书律曆志》中刘歆所推三统曆的说法就是如此,尚书正义孔颖达承袭其说。因唐代十三经正义流布天下,故古今学者绝大多数人观点皆囿于此。惟司马迁《史记》所记有异,然基本被忽视。
《史记周本纪》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显然司马迁所述是指周公反政以后,成王令召公、周公先后赴洛邑,为王相宅卜吉,然后召诰、洛诰因事而作。
周公辅成王画像石
《洛诰》末尾史官记事一段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人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孔传云:"王为册书,使史逸诰伯禽封命之书,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鲁公拜后。"据洛诰文义,成王封伯禽正是在"十二月戊辰"之后的烝祭日。此十二月为周正,该年闰,次日为十三月朔日,后一月为周正建子月。
古三正的真义是:夏建寅以立春节为岁首月首;商建丑以大寒节为祀首月首;周建子以冬至节为年首月首。夏商周月建皆以节气而分,而不是以节气所在月朔而分。二十四节气,月初称节,月中称气。故知节必为月首。西周人尚无月首为朔日的概念,文献铜铭从卜用初一十五日之概念。以节气分月,月朔或在节前,也或在节后。惟某年正月朔旦恰逢冬至,月朔年首才正合。
结合<召诰、洛诰>曆日以及<顾命>篇周成王去世日的考证(可以参见哲之《周公摄政暨周成王在位的绝对年代》文章),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此二诰曆日,断代工程已拟推为公元前1036年,此结论基本无误。惟月份的判读和所在王年的裁定上稍有差池。
哲往昔已考定武王克商年日在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夏曆三月初一甲子日),此结论又与以明代天一阁本《竹书纪年》推定的BC.1050辛卯年克商的说法相符。据逸周书明堂解:"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作雒解:"乃岁十二月崩镐",且据武王日名为武丁。依据哲提出的殷商日名死年天干说,拟推武王去世于公元前1045年夏正丙申年十二月(周正丁酉年二月)。
24节气时间
今本《竹书纪年》是将丁酉年定为成王元年。其记:"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以此二诰曆日(己巳年)为周公摄政七年逆推,则成王元年确如断代工程结论为公元前1042年。但距今本《竹书》尚有二年之差。若以此二诰曆日为成王亲政元年逆推,则差距为一年。
哲往昔曾考证了殷商末代五王的在位年、去世年和继位年,确证商代帝王去世后次年皆算丧年,皆归于前王纪年(见《毛天哲:殷周日名死年天干说兼考商代五王在位年》一文)。周武王日名为武丁,去世在丁酉年无疑,则该年是否算作成王元年值得推敲。
有意思的是,以此二诰曆日(己巳年)为周公已反政,是年为成王亲政始年(即成王八年)计,又与今本《竹书》"(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所记之事耦合。而丁酉至己巳则为九年,非八年。两者相较,只能说明今本《竹书》所记成王元年和周公摄政一年并不重迭。
若丁酉年归于武王丧年,以次年戊戌定为成王元年,则周公摄政第七年亦不在己巳年。今本《竹书》记"(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该年正是庚子年(前1041年),符合哲提出的商纣王子禄父日名取自其死年天干假说。
毛氏西周断代年表20200114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今本《竹书》所记和大传说法大同小异,主要是从成王角度记事且更具体。
又《逸周书作雒解》所记亦略同:"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其中"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在今本《竹书》被分记作两年之间事。如"武庚以殷叛。"记在"夏六月,葬武王于毕。秋,王加元服。"文后,又续记"周文公出居于东。"然后记"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综合三家记事分析,"元年夏六月"当指戊戌年夏六月,此年为成王元年。可推成王元年和周公摄政一年为同一年。如是,则<召诰><洛诰>曆日在成王八年无疑,可见司马迁《周本纪》所说此二诰作于周公反政后无疑也是对的。
今本《竹书》将成王元年记在丁酉年也非空穴来风。商人是将前王去世之次年定为丧年,纪元皆归于前王,周人是否有革新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表明。武王继位未改元,无法参考。其他诸王是否有丧年制也不是很确定。
断代工程给出的西周王年皆是次年改元,无丧年之说。更有甚者,断代工程专家为合金文曆谱以弥缝自说,竟然定周龚王是当年改元。西周是否存在丧年制,值得好好研究才是。
师旦鼎铭真伪及周成王元年
惟存世《师旦鼎》铭文曆日有"元年八月丁亥师旦受命"记事文,可惜的是干支日无月相,无法确定是哪一日。前人有武王元年和成王元年二说。哲以师旦受命为八月朔日丁亥推,以周正算,则公元前1044年(丁酉年)最合曆。虽然周武王克商次年(前1049年)七月朔日亦是丁亥,但因月份不符而舍去。
因师旦鼎为周公自铸器,若哲之考证无误,那么可以说明自周武王死后,周公确实有过改制想法。《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不过因各人角度不同,常被误读文意。
引述下: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正常点的学者一般观点是这样的,认为"伯禽以周礼治理鲁国,全用他父亲周公创设的礼乐制度,但是周公认为伯禽未能因地制宜,简化礼制。"哲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更离谱的回答:"这是伯禽回答周公为什么报政来迟的答话,意思就是说他要变革当地的风俗礼仪,为其父服丧三年才脱下丧服,所以来迟了。"我差点喷饭哦。这个回答不光理解古文有障碍,且发言也有障碍。"为其父服丧"听起来倒像是伯禽为周公服丧,周公尚在耶。若是变革民众欲其为父守丧三年,人家没死父亲怎么办,等人家死吗??可见荒谬。
服丧三年本是夏商以来的古制,学者以为是自周公始有?也是错解了文意。哲以为,周公崇尚的是政简平易,伯禽恰恰误会了,他要革除的是服丧三年的古制,而不是推行。反过来可以证明,周公确实有可能将武王去世次年(丁酉年)就作为成王元年。
周公东征
周公这么做当然有政治上的考虑。首先,武王克商后仅六年就崩逝,天下未宁而嗣王幼,早即位能安定人心。其次,武王病重曾有过让周公继位的想法,周公泣涕而拒,坚持辅助成王(见度邑解)。虽如此,流言却不得不防。铸鼎宣布是年为成王元年,也能堵人口实。再者,武王虽灭商得国。但基业是文王创立的。文王嫡庶子众多,夺位之防不得不虑及。
事实上,周公的这些担心后续都发生了。哲以前就考证过,太姒之子唯武王发、周公旦、康叔封、毛叔郑(冉季)四人而已。管蔡成霍曹等皆为文王庶子,非武王母弟。以嫡庶家室而分,周公捍卫的自然是以太姒为母别的家族利益,同时也是考虑到周王室如何守护文王周王传下的基业传承问题。其摄政绝无私心,也绝无取代成王的想法。也正因为周公的坚守,才有了周室传代八百年的传奇。
至于有史传数据指说成王元年在戊戌年(前1043年),很可能出自当时史官的实录。是周王室史官依据惯例,将武王去世次年定为成王元年,也就是周公摄政一年。故哲以为,<召诰><洛诰>曆日为成王亲政始年(即成王八年)是无疑的。
竹书纪年 书影
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出土先秦竹简数十车。后整理出《汲冢书》又称《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为黄帝以来各朝各代史官所记实录。
最初是由卫恒整理考证,不知为何遭忌而遇害。后来是荀勖、和峤接替整理。既然有这么多学者整理考证,故今本《竹书》中成王元年略有差池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今本《竹书》的学术价值并没有被学界重视。王国维更是过分,竟然认为此书无一处不假,是伪书可烧而去之。
今本《竹书》只是整理过程中存在点小瑕疵而已。如果我们将丁酉年(前1044年)定为武王之丧年,则周武王克商后在位确实有6年,和逸周书明堂解合。
以哲考定成王去世于公元前1008年5月1日之结论,以次年为成王丧年,以戊戌年为成王元年,则成王在位也是三十七年。与汉志所载成王在位三十年,合周公摄政七年,共计三十七年的说法也是合榫的。和今本《竹书》所记成王在位年数也是符合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可以发现,今本《竹书》所记成王八年事,被整理者误系到了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正确的应该是:(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作「象舞」。
成王"初莅阼亲政"记在"八年春正月",之后记"春二月"王如丰,再记"春三月"召公如洛度邑(即相宅),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是前后三月连贯之事。
结合《洛诰》所记成王在东都洛邑"蒸祭岁"后返还宗周。接下来大事为"(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庙,初用「勺」",是知凡"春正月"记事皆指夏正立春后。
夏商周皆以节气分月,以子丑寅卯名月,序数为一二三四。夏正建寅,以大雪节为子月始日。周正建子,以冬至节为子月始日。故周王正月与夏正子月刚好差一个节气,在阴曆月序上则差一个半月。
《召诰》的曆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
查张培瑜《中国先秦史曆表》,是年:
冬至日在丙申。冬至月乙亥、二月甲辰、三月甲戌、四月甲辰、五月癸酉、六月壬寅、七月壬申、八月辛丑、九月庚午、十月庚子、十一月己巳、十二月己亥、闰月己巳。
冬至日丙申在冬至月乙亥后廿二日,故周正二月实际在张表的二月和三月之间。朔日在甲戌,既望在十七庚寅,过六天为乙未(前1036年2月27日),成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是日距离立春为十五日,记曆虽在周二月,但已是立春后,故今本《竹书》写作春二月。
周月解有"至于敬授民时,巡守祭享,犹自夏焉,是谓周月,以纪于政。"是知成王"初莅阼亲政"是在夏正月立春日,实际在周正二月,史官写作春正月,是尊王也。可见成王"莅阼亲政"典礼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政事,其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派召公先周公于洛相宅。
《召诰》中"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朏日为金文常见的初吉,在月之二三日。此三月在张表的四月。三月甲辰朔大,胐日在初三,与曆日正合谱。史官在此处记作"来三月"是为了和夏正三月有别。因为夏正寅月和周正寅月,干支月序数皆为三月,只差一个节气。夏称岁,周曰年,来三月是来岁三月的俭省,指立春后的周三月。
营建成周
汉刘歆所作《三统曆谱》(班固汉志中作律曆志,皆班氏所述刘歆之说也)推召诰曆日就犯了古今学者共有的错误。他是以汉代始有的月朔为月节,将该年冬至月(乙亥朔)错推为是召诰所说的周二月。如《汉书律曆志》所云:「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是岁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诰曰:"惟三月丙午朏。"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
自刘歆始肇,后之学者皆囿于其说。故今日学者虽推对了《召诰》曆日的年数,也是步刘歆后尘,将该年的冬至月看做了周二月。所以对召诰为何把他们以为的周正月(冬至月)称作二月而迷惑不解,只能错误地推断为周人当年是建亥。
实际上西周曆法建子是无疑的,是以冬至日为年首月首,该年的冬至月并不完全是周正月,前廿一天归属上年的周正亥月(即周正十二月),自冬至节后才算是周正月之始日。搞清了这些,我们就对洛诰的曆日有了个清晰的认识。
引述下《洛诰》有曆日部分文本:"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关于此段文字的句读注解,尚书洛诰正义中孔颖达已经将古今经师注家的各类见解汇聚并附以己说,繁言不引。哲惟在此要特别点明一点的是:"戊辰,王在新邑。"之事并不在文中的"十有二月"。孔疏亦注意到了这点,他指出,"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认为戊辰日时成王到新邑的日子,并非指烝祭日。
不过孔疏在推曆时,依然然囿于刘歆说,将戊辰日看作了周十二月。将戊辰日次日看作在"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实际上此阴曆月朔日并不在周正建子之月,亦非"夏之仲冬建子之月",而是在夏之孟冬建亥之月。
从前文所推二诰曆日可知,戊辰日越三日方为小雪节气,小雪至冬至为周正建子之亥月(周十二月),故实际在周正十一月。以夏正言,大雪至小寒为夏正仲冬之子月,故戊辰日次日亦非孔疏所说的"夏之仲冬建子之月"。
搞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能明白成王在周正十一月的戊辰日赶到新邑是为了下月即将举行的"烝祭"岁典。周人的"烝祭"一般多选在望日或既望日。我们来看曆日就清楚了。
戊辰为上月晦日,距大雪(夏正建子始日)正是十七日。十二月己巳朔小,既望在十六日甲申。此日距周正年首冬节也是十六日,亦为夏岁建寅子月始日前二日。对周人而言是既祭年又是祭岁,是个盛大的节日。以周人既望日祭祖祭岁推,则十六日甲申(公元前1036年12月13日)为成王在洛邑的元祀"烝祭"日可能性极大。
古之月相真义图释
今本《竹书》记:成王五年,遂营成周。尚书大传亦称,周公摄政五年营成周。是知成周洛邑营建早在成王五年就开始了,是为了完成武王营建洛邑宅中国的心愿。
《作雒解》有周公对建成周洛邑的追忆文字。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考察召洛二诰文义,知召公周公相宅卜吉,是为文武周王建庙,为今王建寝,以备成王在洛邑首次主持祭祀文武周王之元祀,并为之后王宅此洛邑治中国。
《洛诰》是周公反政次年与成王的谈话实录。伪孔序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后至,经营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哲以为,成王先后派召公、周公赴洛邑相宅卜宅后,自己也随之去往洛邑定宅。
召诰有"旅王若公"句,孔疏认为"明此出入是觐王之事,而经文不见王至,故传辩之,王与周公俱至。"召诰乃召公与周公谈话实录,其时王正在赶往洛邑途中,故召公称谓成王为"旅王",明显说明成王随二公之后要来定宅。
出土铜铭中有新邑鼎(柬鼎),铭文记:"癸卯,王来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往〕自新邑于柬。王赏贝十朋。用乍宝彝。"洛诰亦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可见成王自己也是到洛邑卜定宅。
洛诰此次谈话大约是在成王亲自来洛邑定宅,周公携带自己所卜堪舆图吉兆等迎告成王那次会见。洛诰乃周公成王面对面谈话,非伪孔序称周公遣使者以告王。
洛诰说的是洛邑初成,周公告成王居洛之义。居洛治中国,乃继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周公以此故,大审视东土洛邑之居,其始欲成王居之,为民明君之治。成王谢公之定宅之劳,又美其定宅之休。随后,王求教诲之言,公乃诲之居洛之治策(言多不引)。
成王谨遵周公之教诲,答应顺公之言,行天子之政于洛邑。谈话中,周公有反政后退老之意,成王诚恳挽留周公继续留治东都,共安天下。周公拜手稽首,尽礼致敬,许王之留。通观篇义,皆是周公七年归政后言语,是以洛诰作于成王八年无疑。
洛诰中,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说明成王与周公此次对话后,曾返还过镐京,即政于周,命周公子伯禽、太公姜尚之子丁伋用事。今本《竹书》记作:「(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
此处的鲁侯禽父、齐侯伋,皆是史官后记之追称,真正命伯禽为鲁侯应该是在蒸祭岁典上。此处齐侯伋也用事,说明太公姜尚或薨于成王六年,非今本《竹书》所系在康王六年。今本《竹书》所记,在继召公相宅、周公卜宅之事后,又有"王如东都(定宅),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命迁庶殷于鲁事当接续于此后。
洛邑地形图
齐、鲁初封应在成王八年(齐地、鲁地成王五年平叛后才留驻军,成王亲政后才可能封侯。)刘歆《三统曆·世经》云:"鲁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皇甫谧《帝王世纪》亦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此处的成王元年即成王亲政的第一年,实际为成王八年。以上这两条记录证明周公子伯禽于成王八年封侯,与今本《竹书》、《洛诰》所记可互为发明。
"戊辰日"之后举行的蒸祭岁典中,王命有司将上半年与周公的谈话作成策书,乃使史官名逸者在大典上祝读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后为国君也(哲注:其上半年某日已命伯禽用事,此是向文武祭告此事,并明确周公其后封侯)。
其时成王尊异周公,以为宾客。杀牲享祭文王武王诸事,成王皆亲力亲为。王入庙之大室,行祼鬯之礼。所记言其特显成王尊异周公而礼敬深也。于此祭时,王命周公后,令作策书。前一策告书为祭告文武,由大祝告后焚烧献祭。故后作册命书使史逸读此策辞以告伯禽,言封之于鲁,命为周公后也。又总述之,在十有二月蒸祭日。
此段文后"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为一节,特为周公致政成王记时,属特笔。是追记周公摄政年数为七年。召诰、洛诰所记事皆在成王亲政之年,并不能算作周公摄政年数。
综而述之,<召诰><洛诰>二文皆作于周成王八年,非古今经师注家言称在周公摄政七年复子明辟之岁(即成王七年)。考<召诰><洛诰>之曆日,知是年为公元前1036年,为成王亲政之始年。据此逆推,成王元年在戊戌年(前1043年),非今本《竹书》所记在丁酉年(前1044年)。惟据师旦鼎曆日以考,周公自铭成王元年确实在前1044年,盖为周公迫于周初形势欲改古丧制尔。以史官笔法,周武王去世后次年(丁酉年)为丧年,按惯例应归于武王纪年,故周成王元年实在公元前1043戊戌年。以哲考定武王克商年日为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计,得实武王在位年数为六年。以哲考定成王去世在公元前1008年5月11日计,次年为成王丧年,则得实成王在位数依旧是三十七年。皆与古说合榫。断代工程因误读<召诰><洛诰>曆日,而逆推成王元年为公元前1042年,此结论并不正确。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草
作者:毛天哲 简介
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之吐哺握发
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此诗由国画家袁铨君绘制《周公吐哺握发天下归心》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辛卯岁咏周公七律
后启仲尼承往圣,昭彰礼乐建神威。
只愁叛乱谁人定,无惧流言我自岿。
一饭周公三吐哺,百忧天下始攸归。
披肝沥胆尽于命,惊见京师震电飞。
张红星教授注:
仲尼:孔子的字。《史记 孔子世家》:“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昭彰:亦作“昭章”。昭著、显著。亦谓使彰明。《汉书 王莽传上》:“昭章先帝之文功,明著祖宗之令德。”又有光耀之义,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昭章云汉,晖丽日月。”
礼乐:礼节和音乐,《礼记 乐记》:“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史载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大治。《尚书》:“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神威:此谓礼乐文明有神奇的威能。唐李白 《明堂赋》:“崔嵬赫奕,张天地之神威。”金秦略《少室山卓剑峰》诗:“神威洗尽世间雠,电歇雷闲怒气收。”
岿:高峻独立貌。稳如泰山之亦。系“我自岿然不动”之省称。
吐哺:即吐哺握发。《韩诗外传》卷三:“成王 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按:《史记 鲁周公世家》作“一沐三捉发”。后遂以“吐哺握发”形容礼贤下士,求才心切。
百忧:种种忧虑。《诗 王风 兔爰》:“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晋刘琨《答卢谌书》:“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
攸归:攸为助词,无义。攸归即乃归。
披肝沥胆:比喻极尽忠诚。《隋书 李德林传》:“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图谶之文,顺亿兆之请,披肝沥胆,昼夜歌吟。”
尽于命:即尽命。终天年之义。汉荀悦 《申鉴 俗嫌》:“学必至圣,可以尽性;寿必用道,所以尽命。”
京师:《诗 大雅 公刘》:“京师之野,于时处处。”马瑞辰通释:“京为豳国之地名……吴斗南曰:‘京者,地名;师者,都邑之称,如洛邑亦称洛师之类。’其说是也。”“京师”之称始此。后世因以泛称国都。唐韩愈《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一说,陕西凤翔有山曰京,有水曰师,周文、武建都于此,统名之曰“京师”。见清顾炎武《肇域志》。
震电:雷电。电闪雷鸣。《春秋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史记》:“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尚书》:“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毕,示不敢臣也。”
来源:光明网
历史上周公的儿子伯禽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公是周朝君主周武王的弟弟,他这个人非常的仁爱而且一生都忠心于国家。在哥哥周武王当了周朝的国君后,周公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的方面都拼尽全力的协助哥哥周武王治理周朝。周武王去世后,武王的儿子继位,是为周成王,周公又尽心尽力地辅佐成王。
西周初年,周公就帮助周成王出主意,派兵消灭了奄国。周成王为了报答周公对自己的忠心就将奄国一带的土地分封给了周公孩子里年纪最大的伯禽,伯禽于是在那里成立了鲁国。周成王从自己父亲那里接过位置的时候还是个屁点大的孩子,他是在周公的培育和指导下才逐步成长起来的,所以周成王对周公非常感激。为了报答周公对自己的扶持,周成王在周公的儿子伯禽去鲁国受封时,不仅赏赐给了伯禽很多珍贵的典籍和宝物,还赐给伯禽众多的臣民。
周公看到周成王对伯禽如此器重和厚爱,就更加希望伯禽能治理好鲁国,不辜负周成王的一番盛情。伯禽临去鲁国前,与周公告别。周公特意告诫儿子伯禽说:“你从今后就是鲁国的君王了。成王越是厚待你,你越应该要感激他所赐予你的一切。到鲁国后,做事一定要为当地的老百姓着想,治理好鲁国,为周王朝的繁荣和兴盛尽力!”伯禽认真听着父亲的教诲,点头说:“我已谨记于心,定不辜负成王和您对我的期望。”
周公仍不放心,他又叮嘱道:“儿子啊,你去了鲁国之后一定不要摆架子,天下贤人很多,如果你摆架子他们就不会归顺于你的,你要放下身段重用贤才,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我作为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在周朝也算是身居高位了,但我依然不敢有所懈怠。每当有贤士高人来拜访我时,我都唯恐怠慢了他们。有时候正在洗头发,听到有贤人来访,我就会赶紧把头发从水盆中抓起来,停下洗头,立即整理好衣装先去接待来访的客人。有时,我正在吃饭,有士人来访,我会立即吐出口中的食物,放下餐具,起身去迎接士人。我如此谨慎、恭谦,就是因为害怕错失了天下的贤才。你到鲁国后,也一定要像我一样做事人做事都要小心谨慎,要好好的对待那些有贤才得人。不要因为你是鲁国的国君就摆出一副架子给别人看,这样没有人会支持你的”
伯禽牢记周公的叮嘱,一心向父亲周公学习。当他成为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后,可以说是非常的爱戴老百姓,他自己节俭不说,还要求臣子也节俭,所有国家政策都为百姓的利益着想。除此之外他一点也没有着国君的架子,非常的亲民,而且如果他发现一个人有才就会主动找到这个人,向他请求学问。作为周武王的封分诸侯国,他自然也牢牢记着各种周礼,坚持用周礼来治理国家。
伯禽在位四十六年,鲁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还使得原本弱小的鲁国成为被很多大国都尊重、效仿的礼仪之邦。很多诸侯国都派人前往鲁国学习礼乐,效仿鲁国以礼治国的方略。鲁国虽小,却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推崇,成为周朝诸候国中推行周朝礼乐的典范之国。
《诫伯禽书》:中国第一部成文家训
俗话说,“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又称家诫、家范、庭规等,是指家庭或家族中长辈对子孙的垂诫和训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宗族地位,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训很大一部分是为政者教育子孙如何修身做人、立身处世、为官从政的垂诫,从中可以彰显出为政者的官品与官德。《诫伯禽书》就是这样的一部家训。
《诫伯禽书》的作者是周公,周公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既是创建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又是稳定西周王朝、促成“成康之治”的主要决策人。那么,《诫伯禽书》又是缘何而来呢?
周武王灭商后,把周公封在了鲁地,但周公因为辅佐朝政,没有就封,而是让儿子伯禽代为就位。《诫伯禽书》就是在伯禽去封地之前,周公告诫儿子的一段话。《诫伯禽书》把如何从政提到“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开中国古代仕宦家训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成文的家训。
《诫伯禽书》的主要内容: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周公,清人绘。
从这部家训,既能看出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更能体悟出他的为政品德。
第一,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周公曾为见贤人而“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建设国家,恢复生产,制定国家发展规划,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制作礼乐,镇压反周势力,消除周边隐患,安抚商朝遗老等等,可谓政务繁忙、日理万机,就连洗澡都有人打搅。古时候男人头发长,周公握着湿头发从浴室跑出来,接见完了,又回去接着洗,所以一沐三握发。甚至吃饭也在处理政务,吃一口饭,不等嚼完又得吐出来,因为又有客人来求见了,所以一饭三吐哺。后世一些有志向的政治家,也以周公的精神勉励自己。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在《短歌行》中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就是以学习周公吐哺的精神,抒发自己思贤若渴的心情。
第二,谦虚谨慎,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是指言语行动要小心谨慎。作为领导者立言当慎,不仅仅是威严所系,更重要的是关乎社会成本。《礼记·缁衣》记载说:“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说的是,君子用言论来引导人们,用自己的行为来阻止人们的不良行为。所以,君子讲话一定要谨言慎行,行动一定要考虑后果。这样,百姓就能出言谨慎,行动小心。除非时机成熟,势在必行,但凡涉及全局层面的政令都要慎重。朝令夕改,必然会引起社会运行机制和轨道的转换以及黎民百姓行为和心理的调适,而转换和调适的过程,都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
周公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务必要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遇贤才的作风。据《尚书·无逸》记载,周公教导成王勤俭执政时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后来成为诸多帝王教育后代不要贪图安逸奢华生活的名训。周公一再告诫成王要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重蹈殷商失德亡国的覆辙。周公早就意识到国之隐忧不在当前而在后嗣。他对成王的教育,既包括治国安邦才能的培养,也包括个人品格的塑造。在他的教育下,成王终于成长为一代明君。伯禽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了民风淳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