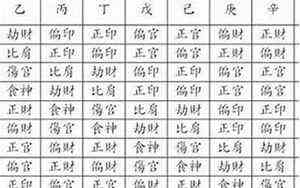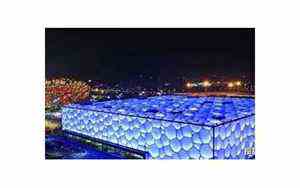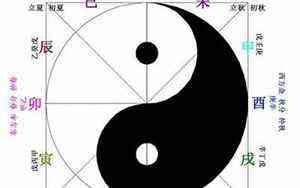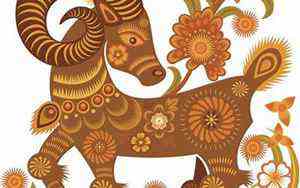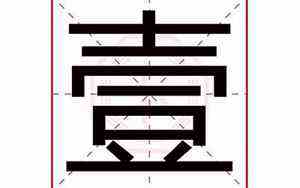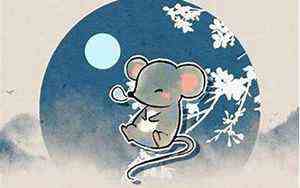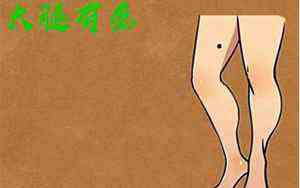00后“国风新青年”:让热爱照进生活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国风爱好者相聚江苏常州茅山东方盐湖城景区,参加2023“国风大典”。
这是“国风大典”活动举办的第四年。每年,00后青年歌手刘宇都会应邀而至,从未缺席。2018年,他因参加国风文化唱演秀节目《国风美少年》被人们熟知,此后就一头扎进“国风圈”。在许多人眼中,刘宇已然成为年轻人玩转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参加这场活动的00后“含量”很高,随便拍张照片,画面中几乎全是年轻面孔。一件衣服、一首歌曲,为他们打开步入传统文化世界的大门。这些年轻人把“锁”在博物馆中的文化“复活”,让国风“吹”进生活。
00后爱上国风的若干理由
“那是一间狭长的舞蹈教室,一位老师在练习古典舞,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转到最远处的窗边,流了很多汗,却一直保持着优雅又挺拔的舞姿。”刘宇回忆,短短几个瞬间,他就被中国传统舞蹈的魅力所打动。
美,是不少人邂逅国风的深刻感受。由数千年文化沉淀而来的美,有着足以穿越时空的感染力。
“一件漂亮的衣裳”是薛薇薇对汉服的最初印象。“2020年,朋友开了一家汉服工作室,邀请我做模特。”薛薇薇说,那一年,20岁的她拍了人生中第一组汉服照。随着接触这个圈子的时间越来越长,这个年轻人逐渐发觉,“不同的服饰穿在身上,似乎能感受到穿越时空的文化”。最近,她爱上了明制汉服的端庄典雅,“让我感觉到宁静,以及一种力量感”。
“国风大典”举办期间,林小曦的摊位前挤满了年轻人,精美华丽的国风饰品和刺绣灯笼吸引着来往游客的目光。
林小曦对国风的热爱始于高中。高中时,社团老师带领同学们参加了国际动漫节“国漫盛典”活动,林小曦被分在道具组,负责所有的服装、化妆、道具,这让她对制作国风饰品产生了兴趣。
在那之后,林小曦跟着师傅学习制作绒花、花丝镶嵌等非遗工艺,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美丽的东西没有人会不喜欢,因为喜欢,我才一直做。”
出生于雕版世家的朱旭从初中开始,就利用寒暑假,跟随祖父和母亲学习雕版印刷技艺。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五代传承人,朱旭从小耳濡目染,“看得多了,也会有感情,就想自己画图、自己雕刻。”在他心里,成为非遗传承人,不仅出于年轻一辈的使命感,更融入了热爱。
“这几年,我们受新式国风的影响比较大。”2002年出生的大二学生张泽钰说,正有越来越多的00后扎进“国风圈”。
张泽钰从7岁起学习古筝,“小时候听周杰伦的《青花瓷》《菊花台》,长大了能听到很多新式古风音乐。这种传统和流行融合的形式更合我的胃口。”在她看来,年轻人爱上国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国风新青年”将爱好发展成事业
如果只停留在“爱好”的层面,或许国风依然距离大众生活比较遥远。如今,更多00后让爱好走进现实生活,他们做出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和传播。
从小学习传统舞蹈,刘宇在日日夜夜的练习中感受到的不是疲倦,而是成长。“国风就是我们自己的风格,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有更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今年8月,刘宇的个人首演会《溯》在上海举办,无论是开场VCR里“风华少年”的概念片,还是融合了多种传统舞蹈元素的表演《夜》,都是他自己对传统文化作出的诠释。于他而言,这是对过往的追溯,也是未来的新起点。
10月4日晚,“国风大典·国风美焕夜”上,薛薇薇作为华服模特,身穿复原战国时期服饰特点的橙色衣袍缓缓走来,举手投足之间,展示出华服之柔美和气派。“成长”对于薛薇薇来说,就是第一次走上“国风大典”走秀的舞台。
尽管此前已经拥有一定的时装走秀经验,她依然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她看来,要具备足够的能力,首先需要对传统服饰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至少能区分不同的服装款式”,其次,还需要了解不同类别的华服文化。
接触华服之前,薛薇薇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现在华服可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陪伴我,这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
林小曦也已经将爱好发展成了事业。2020年,林小曦开了第一家售卖传统手工艺品的实体店,但出现了亏损。后来,她学习互联网营销,在杭州几家直播公司的带领下,做非遗的文化传播项目。
在大凉山宣传当地的描银技艺时,林小曦发现,山里的匠人掌握精美绝伦的技艺,却无法跟上时代脚步,缺少销售渠道。“与其自己去做一个非遗匠人,不如去做一家集合店,把产品带到外面市场上去卖,创造更大的价值。”
2022年底,林小曦转变思路,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合作,由他们生产制作,林小曦去负责销售,同时反馈市场数据,帮助师傅研发新品,从而形成良好的运转机制。林小曦介绍,她现在已经开了4家实体店,“这是我们能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事。”
将传统文化的美传递给更多人
在这些00后眼中,无论是锦衣华裳、非遗技艺,还是热闹熙攘的茶馆市集,在“万物皆可国风”的今天,他们愿意尽力一试,向更多人进行分享。
薛薇薇觉得,如果通过自己小小的力量,能够使更多的人接触和了解华服,会很有成就感。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刘宇给自己的定位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将传统文化的美传递给更多人。今年的“国风大典”特别演出中,他演唱的歌曲《如麟一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龙鳞装的推广曲,流行与戏腔相结合的演唱方式,也是新国风艺术形式的体现。
大学毕业后,朱旭正式加入自家工作室,为雕版印刷这项非遗的传承事业注入年轻血液。传统思维中,雕版印刷制作的通常是线装书,不仅成本高、制作复杂,距离普通人的生活也很遥远。“如果大家都不了解,古老的技艺将难以得到传承。雕版印刷的作品需要更加大众化、年轻化。”朱旭说。
这名年轻人进行了新的尝试。首先,将作品的体量减小,降低成本,让大家都有能力购买。接着,他在雕版中融入现代元素,绘制出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图案,制作出挂件、摆台、扇子等更符合青年审美的文创产品。
这是一项还在起步阶段的“实验”,朱旭收到了“可爱”“有创意”等评价,也遇到过制作成本高导致的“价格偏高”的质疑。在精益求精打磨手艺的同时,朱旭认为更多的拓展仍是必要的,“传统的形式需要保留,也要进行不断创新”,要做一些更现代化的内容,与时代接轨。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才能让非遗的传承人更好地活下去,让非遗更好地活下去。”林小曦希望,所有传统文化中美的东西,都能够以独有的姿态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而不是消散于历史的长河。
“其实我们赚的钱并不多。”林小曦笑着说,“我们尽力分出利润给到真正的非遗传承人,看到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帮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更多人,这真的很有成就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可欣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绝学”不绝 代有新人 让冷门的古文字学不再“蒙尘”
2023-10-09 10:35
来源:中国青年报
链接已复制
字体:小大
今年9月,参加“树人杯”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合影。受访者供图
“博学而笃志”,出自《论语·子张》,也是复旦大学校训中的一句话。在今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中,复旦大学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大四学生彭若枫重新探讨了“笃志”的意思。结合前人研究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铭“博学而孰(熟)记”这一新材料,她认为,相对于“笃定志向”,将其理解为“专注、切实、持续地进行记忆”更加合理。
千百年来,注释《论语》者颇多,往往同一句话的理解就有不少歧义。担任评委的几位古文字学者认为,彭若枫的文章在对旧说做了详细清理的基础上,又根据古文字资料提出了相当可信的新说,殊为不易,值得获评一等奖。
古文字学,是一门识读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并利用古文字材料研究语言、文献、历史等问题的学科。由于门槛高、培养周期长、难出成果等原因,被视为“冷门绝学”。有学者估计,参考两年一度召开的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的参会人数,国内研究古文字学的核心力量有200多人。
一项新的尝试正在带来变革。2020年,“强基计划”将古文字学纳入高校本科招生计划,国内十余所高校每年各招收数名至20多名学生不等,要为国家选拔、培养未来的古文字学家。
当古文字学的“冷板凳”遇上“热需求”
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研究古文字,在发掘文化内涵、赓续文化传统方面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古文字学的地位可比作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意义重大,却距离社会生产十分遥远。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师程浩解释说,古文字研究不光要“认字”,还是一门涉及语言学、音韵学、文献学、历史学,甚至天文术数、医学方剂等交叉学科。与一般文科研究中发散性、阐释性的研究不同,古文字学对文字本体研究的结果是可以得到验证的;在文史哲领域,很多“增长点”都依靠出土文献资料的发现,即先要借助古文字学对新材料进行解读。
近十几年,新材料正在“井喷式”出土。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字学教授王辉以战国楚简为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正在陆续出版,这两批材料的内容十分重要;秦简方面,陆续出版的有湖南里耶秦简、北京大学藏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等;汉简方面,持续出版的有北京大学藏汉简、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等。
随着老一辈学者逐渐退出,古文字学需要新一代学者加入,接续进行解读和研究。然而,古文字学人才培养具有特殊性和高难度,使这门学科必然成为“冷板凳”。
程浩说,从传承学脉的角度来看,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古文字学作为研究经学的工具和附庸,就一直有不少学者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小学”在清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清末甲骨文发现以后,又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西学的传入,古文字学一度成为冷门,甚至要“绝”了。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以研究生为培养起点,在中国语言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属的有关二级学科招收古文字学学生。
有受访教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他们求学时期,本科阶段的课程涉及古文字知识很少,进入古文字学硕士阶段的学生人数不多,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接受调剂,误打误撞来到这个学科的。受限于学科分类培养的方式,要做好古文字学研究,学生必须花很多精力旁听、自学,即使在博士毕业后,还是有一些内容没有掌握,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慢慢补充。
对于古文字学人才培养的困境,王辉直言:“就是学的人少,接不上趟了。聪明的学生,脑子灵光,在各个学科都能够有所斩获,又何必受罪来这儿呢?怎样发现真正有兴趣的同学,如何他们吸收进队伍里来,似乎一直没有解决。”
“学习古文字学是一件很酷的事”
“强基计划”古文字学纳入高校本科招生,改革创新古文字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正是要解决“接不上趟”的问题。据悉,这是古文字学首次招收本科生。包括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十余所高校,根据各自的学科传统和优势,制定了多元化、个性化的古文字学强基计划人才培养方案。
在中国人民大学,“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招收了第一届14名、第二届21名、第三届25名、第四届12名学生。其培养方案强调跨学科属性和“通专”结合,实施“本硕博衔接培养”;汇集了一批来自该校文学院和相关院系的优秀教师,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可以得到专业教师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全面助力。此外,“吴玉章系列讲座”“全球语文学系列讲座”“古文字新青年系列讲座”旨在扩展学生研究视野、锻造学生研究能力;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旨在以赛促训,提升学生科研水平。
在复旦大学,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本科生在大一修习通识教育课程,大二开始修中文的专业培养课程,古文字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在大三、大四展开,低年级学生如果愿意,也可以提前选修或旁听相关课程。“强基计划”为每位学生配备了导师,给予学术和生活上的建议。
清华大学的做法是,将文史哲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纳入日新书院,进行一年通识教育后,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通过双向选择和择优遴选组成“强基计划”古文字班,进行导师制、小班化培养。首届古文字班招收了7位同学,第二届有4位,第三届有3位;目前,首届古文字班已有5位同学“转段”,明确要进入硕士或直博阶段的学习。
经过本科阶段学习,不少学生从不了解到逐渐爱上了古文字。明年将要直博的清华大学大四学生张弋阳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在高中时就对历史尤其是先秦史感兴趣。大一上学期,《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汉字与中国文化》《清华简与中国文明》等课程给了张弋阳很大启发,激发了他对古文字的兴趣。
正式迈入古文字学方向学习后,张弋阳又学习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的通论课和资料选读课,选修了考古学、先秦史、秦汉史、古代汉语等学习古文字时可能需要的交叉科目;今年6月,他参加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开设的暑期专业实践课,课程内容是协助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拍照、整理20世纪70年代末出土的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简。
在张弋阳看来,“学习古文字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在自主阅读其他学者的论著和原始材料的过程中,他会有意识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当自己的想法与学界已有的成果刚好对上的时候,他会获得“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般的惊喜,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进步了。
在这次“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中,张弋阳的研究梳理了包山楚简中所有与“澨”有关的内容,析出了可以确定是地名的材料,并对其地望进行了大致推定,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如何培养未来的古文字学家
作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文化工程,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文旅部等八部委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对深入研究发掘古文字历史思想与文化价值作出了战略部署。
随着社会氛围的改变,近年来对古文字学感兴趣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些都为高校招生、培养和选拔未来的古文字学家提供了土壤。
彭若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在中学时就和同学们参加过浙江省台州市的诗词大会比赛、汉字听写大赛并获得奖项。她说:“认识一个字或词,再去知晓它的来处,会发现汉字的源流演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着深厚的文化意涵,这是我对文字学产生兴趣的原因。”
虽然古文字学难度高、出成效慢,但彭若枫在逐渐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只要多读原始材料,对照释文多摸索,总会熟能生巧。比如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的部分内容基本可以和传世的《诗经》文本对读。如果在熟悉文本的前提下去尝试释读战国文字,对照集释细细理解,便会有解谜般的乐趣和更深入的体会。”
参与“树人杯”未来古文字学者学术征文大赛是彭若枫第一次完整地撰写古文字学方向的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她接受了老师的诸多指导,进行过几次修改,“是一次严谨的学术锻炼”。未来她将进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继续深造。
谈及学术理想,彭若枫引用了《荀子·劝学》中的一句话: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裘锡圭先生用这句话鼓励学生,并说: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赫赫之功,但如想做出一些实在的成绩,没有冥冥之志、惛惛之事也是不行的。这提醒着我们,治学要潜心笃志、戒骄戒躁、求真求实。”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贺军铭在这次征文比赛中以论文“《老子》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语法问题的再讨论”获得二等奖。在学习中他同样感受到,内心浮躁或是有投机心的人,是很难胜任古文字学研究的。
他说:“从第一堂课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古文字学是挑战人类智慧的学问。现在我的目标是踏踏实实地读书学习,打好基础。如果今后有机会继续学习,我愿意刻苦钻研,深入了解古文字材料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探索其中的奥秘。”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马晓稳注意到,“强基计划”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刚开始招生的一两年,确实有一些学生接受调剂进入这个学科,但现在,社会上对古文字学的认知越来越成熟,古文字学专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马晓稳说,“此次‘树人杯’一定程度上能展现各高校培养学生的整体面貌:全国十几所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文字学方向)的‘强基计划’高校几乎都有学生投稿,在研究方向上各有侧重,展现出了古文字学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有不少文章获得了评委们的认可,是相当优秀的。”
不过,古文字学的“强基计划”毕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尝试,如何培养出未来的古文字学家,还需要更多探索。(记者 魏其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