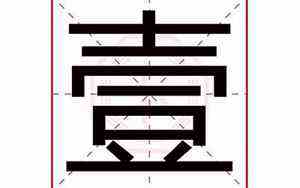63年前,一群渔家妹冲破禁忌闯出北部湾传奇
曾任外沙妇女号副轮机长的黎秀英(左一)在船上洗鱼(资料图翻拍)。记者黄耀滕摄
曾任外沙妇女号船长的黎玉芳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证。记者胡佳丽摄
图为曾任外沙妇女号辅导员的杨明凤年轻时(资料图翻拍)。记者胡佳丽摄
图为外沙妇女号船员在船上拉网(资料图翻拍)。记者黄耀滕摄
破晓时分,天麻麻亮。北海电建渔港内一艘艘渔船回港靠岸,一群群商贩涌向岸边海鲜市场,卸货的号子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里是我国传统四大渔场之一的北部湾渔场。
“今日起网百几担哩,鱼虾蟹鲞满船爬啰。叫声炊事准备好哩,工作完毕食晚饭啰。”84岁的周廷珍唱着疍家咸水歌,也唱着自己和姐妹们的传奇。
63年前,北部湾诞生了一支妇女海洋捕捞船队——北海外沙妇女号,周廷珍是其中一位船长。这些女船员驰骋远洋捕鱼生产,开创了北部湾渔家妇女专业远洋捕捞先河。
她们是海的女儿,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滋养着一代代渔家儿女。
妇女闯出一片海
“我们领着男船队一样的包产任务,从组建到解散,妇女号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63年前,也是这样的清晨,在同一个渔场的外沙港,外沙妇女号扬帆起航。
1958年7月17日,当一对破旧风帆船起锚的那一刻,船上21位妇女无比激动,她们翻开了北部湾渔家妇女专业远洋捕捞的第一页。
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激励下,从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女飞行员到女船长……中国女性的职业潜能得到空前大解放。
外沙妇女号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孕育而生的。“这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男女同工同酬体制下诞生的一支妇女远洋捕捞队。”原外沙公社党委副书记谭大庄说,妇女号的组建冲破了女人不直接从事捕鱼生产的传统禁忌。
“吃死米,坐沉船”,这是形容女人上船不吉利的当地话。船员杨明凤说,即便是以海为生的疍家人,过去女人出海都是做炊事员,是不到甲板上直接从事捕鱼作业的。
一群女人冲破藩篱出海打鱼,不能单凭一腔热情。远洋捕捞不仅要掌握升帆掌舵、拖网起鱼等技能,还要应对恶劣天气、机械故障。航行之初,公社为妇女号挑选了10名男社员,安排在大工、副大工、桅尾工等重要岗位,为妇女号提供技术支撑。
“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我们硬着头皮上船边学边做,后来也有女人担任部分重要岗位。”周廷珍刚登船时21岁,从1958年底开始担任船长,直至1982年妇女号解散。她白天练习上桅杆,夜晚行船时与大工学使舵。
周廷珍说,在苦学技术外,女人出海要过三关:家庭关、晕浪关、讽刺打击关。
生了娃的女人,最难过的是家庭关。不少船员妈妈都有过带孩子上船的经历。周廷珍背着孩子上船作业,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就寄养在亲戚家。
风浪一起就晕船的反应,杨明凤至今还克服不了。“那时一边吐还要一边吃,不吃东西哪有力气干活。”说起这个,杨明凤条件反射地咽了咽口水。尽管她1979年已上岸,她和一群新船员每次吃饭都要将一个提桶放在脚边装呕吐物的画面,时隔42年仍挥之不去。
“女人出深海真是笑话,在岸上缉麻、织网、做家务还差不多。”“妇女出海,我看连菜鱼都捞不到吃。”“大风浪来时她们又要我们去帮助,耽误我们生产时间。”周廷珍坦言,妇女号热闹出航的背后,还伴随不少冷言冷语。
“妇女号的生产证明,女人不能出海的论调已经彻底破产了。”北海市档案馆内,周廷珍的一份发言材料写着:1958年,妇女号诞生的第一个年头,共捕鱼2151担,成为全市产量最高的一对渔船(妇女号两艘一对)。1964年,由于筹建机帆船9月份才投入生产,第四季度生产1497担,完成计划的95%。
“我们领着男船队一样的包产任务,从组建到解散,妇女号的产量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周廷珍非常自豪。
风浪一过,当其他船队还躲在港口望风时,妇女号已经起锚出港。风帆船没有风行不了船时,妇女号的船头船尾排满了人,拿着各种各样的钓具开启钓鱼竞赛,这使得妇女号在无风情况下依旧有产量。
喊着“长摆海,争海工”的妇女号,常为了提高产量而延长海上作业时间。起初的风帆船最长出海半年不回航,由外沙大队派出一条大运输船,运送油盐米等补给过去,再把鱼货运回来。后来的机帆船,一个月航行两次,回港后是第一天休息、第二天取冰、第三天出海。
妇女号的荣誉在《北海市志》(2002年版)可窥见一二:1958年12月,外沙妇女号渔船荣获“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称号;1971年,外沙大队被原国家农林部评为“全国19个渔业先进典型”之一。
妇女号有3名船员产生了4种代表身份:周廷珍是全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黎玉芳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王秀英是全国群英会代表。
“响应号召上船时,哪能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渔家妹,有一天能够到北京参加会议,还获得荣誉。”苍老的双手摩挲着“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72岁的黎玉芳感慨。
劈波斩浪的岁月
两船相隔二三十米,动作不利索容易掉进海里。风浪一来,作为落点的船就随风左右摇摆、随浪高低起伏
风浪不会袒护女人的船。常年海上作业,她们不畏惊涛骇浪,妇女号依旧闯深海、战风浪。
搭载她们乘风破浪的船只,在大风浪中是脆弱的。妇女号使用的第一对风帆船是破旧的儋州船,遇到大风浪,海水不断往船内漫进,船员就要不断往船外戽水。为此,她们自嘲“一日戽水一千几百斗”。
用风帆船打鱼,既常见又危险的动作是“过卡”和“回卡”。两条渔船搞拖网作业,每次起网,下网的“母船”要放几个人到不下网的“公船”里帮忙。抓住桅顶垂下的绳索,从“母船”荡到“公船”是过卡,反之是回卡。
周廷珍介绍,两船相隔的距离在过卡时有20多米,回卡则有30多米远,动作不利索容易掉进海里。当风浪一来,作为落点的船就随风左右摇摆、随浪高低起伏。
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周廷珍,谈起曾经遇到的12级台风仍然心有余悸。那是1961年9月间,台风报告骤然升到12级,原本在北部湾作业的妇女号驶进小港抛锚,没过一会儿绳索和铁锭就被巨浪打掉。
渔船随着巨浪飞出去,在即将被一块大石头撞破、千钧一发之时,掌舵者使尽力气转舵,恰恰躲开。“算是从阎王爷手里讨回了命。”周廷珍说,而这场风暴带来的劫难才刚刚开始。
风力剽悍,渔船不受控制,只好从船头放网,等网张开刮着水,让船不要“飞”得那么快。“当时我们已经换了第二对风帆船,是全大队抗风能力最强的马罗船,在海浪滔天中只能算是大海中漂浮的洗澡盆。”周廷珍说,一波大浪过去,8只小艇就被吞噬了6只。
随风漂流的渔船,遇到近半海里的暗礁,既没有浮标也没有灯光。“突然间,船头有人喊渔船下风角有块颜色不一样的水域。那就是暗礁,快要撞上了!”周廷珍说,后一只渔船船头跟着前一只渔船船尾拼命转舵。就这样又躲过一劫。
船漂到一座小港时,大家又面临生死攸关的选择:是在这个小港抛锚过夜,还是离开去安全的港口?周廷珍说,尽管前行航道很窄,妇女号最终决定继续前行。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同样来自北海的另外两条渔船选择停留在那个小港,在回风时沉没了。而一路经历十几个巨浪的妇女号,被顺势推进港口。“后来我听说,很多渔民在那场台风中失踪,妇女号失联好久,家里人都以为我们……”说到这里,周廷珍陷入沉默。
“每次经历危险后,大家都会问妇女号还敢出海吗。我们当然还敢,以海为生的疍家妇女可是海的女儿。”杨明凤说,不少姐妹即便怀有身孕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直至临近分娩。
也有来不及回港生孩子的。一次航行中,未到预产期的张华凤突然感到肚子阵痛,妇女号立即掉头返航。走了十几海里,新生儿就已娩出。在海上诞生的这名男婴,被他的母亲取名“海生”。
黎玉芳的小儿子杨海韵是回航第四天诞生的。“你知道挺着大肚子在船上摔跤像什么吗?”黎玉芳双手比画着,“像个皮球在甲板上轻弹”,甚至还掉下过桅杆。
“轻伤不下火线”,是船员们的共识。几乎每位船员都受过伤生过病,但没有一位船员提出让缺医少药的渔船提前返航。
5级风浪不回港,6级风浪照撒网,7级风浪勉强生产,8级风浪回港避风。这是妇女号的工作常态。
渐渐地,妇女号开始用“机械武装自己”,去对抗风浪。在载重70吨的机帆船作为第三对船被淘汰后,第四对船是载重84吨的冰鲜船,即带冰出海生产冰鲜的机帆船。“当时整个广西集体渔船里,我们妇女号就是第一对冰鲜船。”黎玉芳经过了专门培训,驾驶机帆船。
岁月更迭,船和人都在更新换代。人与大海的关系也愈加熟悉与和谐。周廷珍说,妇女号出海24年,共使用两对风帆船、两对机帆船,历经200多名船员,没有出现重大事故和人员伤亡,每每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妇女号上岸后,船员们各奔东西,或从事渔业加工,或照顾儿女,共同劈波斩浪的耕海岁月,在平淡的生活中已成为最有滋味的回忆。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子,都有着无比刚强的精神铠甲。当危难来临,总是第一个冲锋,去迎接最前面的风浪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杨明凤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同一天提交的还有上船申请书。申请日期她张口就来——1976年9月11日。
由于一些女船员过不了家庭关,纷纷上岸,妇女号一度人手短缺。为此,时任外沙大队团总支副书记的杨明凤带头申请上船。提交两封申请书的第三天,杨明凤如愿登上妇女号。与她一起递交申请的,还有10名高中毕业生。就这样,妇女号度过了人员难以为继的关口。
在妇女号工作期间,一次杨明凤头部受到重伤,当场不省人事,醒来后只是简单处理伤口,第三天就开始干活。“我怕影响生产不愿意返航,就装作没事的样子。”杨明凤说,15天后返航,她才匆匆去买了两瓶药,以至于留下伴随多年的眩晕症,如今年纪越大症状越重。
妇女号船员们说,共产党员就是这样子,都有着无比刚强的精神铠甲。当危难来临,总是第一个冲锋,去迎接最前面的风浪。
船员黎秀英是一名群众,最佩服的人是黎玉芳。在黎秀英眼里,黎玉芳不仅精通船上工作,还有胆识,有什么困难都冲在前头。一次,渔船机器故障,需要去另一条船上拿零件。风急浪高,黎玉芳乘坐的小艇几次被翻涌的浪头抛起,她硬是凭着过硬的摇艇本领,顺利完成任务。
“船摇一寸,桅摆三尺。”一次,当狂风暴雨把船桅扯帆的绳子打断,黎玉芳二话不说爬上十几米高的桅杆,在令人眩晕的摇晃中把断绳接好,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黎玉芳说:“我是共产党员,在危难时刻就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971年上船前,黎玉芳还是一名女民兵。“党吩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当时我还没有入党,但我们年轻人服从党的领导。”上船后,她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76年还担任了船长。
每一任妇女号船长都是共产党员,她们在船员中开展“一队红”“人人红”比学赶帮活动,掀起学技术新高潮。
杨明凤上船后担任辅导员,指导船员看书读报。黎玉芳上船前并不认得几个字,最先学会的是“中国共产党”。黎玉芳说:“我上妇女号后,有文化的姐妹教读书,才会写自己的名字。”
先进思想潜移默化地润泽船员,吸引亲眷加入妇女号队伍。在船上,有母女,有姐妹。黎秀英就是被大姐黎秀莲吸引而来的,“大姐曾在妇女号上担任轮机员,我非常羡慕,就主动申请上船。”后来黎秀英成为副轮机长。
《北海市渔业志》记载:“继1958年7月17日外沙妇女号扬帆出海后,女人涉足集体海洋渔业长航生产已是常事。”
据介绍,目前北海市有渔业从业人口约21.4万,其中女性6170名。
在以旅游闻名的北海市涠洲岛,64岁的周万娇一直与丈夫结伴出海打鱼,从1984年坚持至今。夫妻主要打捞游客喜欢的海鲜,为一家人带来不错的收入。她所在的滴水村,也有不少像她一样的渔家妇女。“说女人出海不吉利的话,现在听不到了。”(记者胡佳丽、黄耀滕)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原创论文:《让精炼的语言学会跳跃》
作者:陈小宁(醉书香)
让精炼的语言学会跳跃精炼,是诗歌语言的基本质素,是它与散文文体的重要区别。诗歌应该是字字珠玑,应该必求以一语之寡而状世间万态之丰。例如,杜甫的诗句: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这里的“垂”与“涌”,是从一系列相似的字中选择出来的,它们是代表同类字中最准确、最恰切的一个。星星是在空阔的平野之上,仿佛垂落的雨滴,月亮不是自己上升而是被巨大的江流推涌而起。两个动词使天空与平野,明月与江流,在切分中相互对照、映衬,这就构成一幅星月交辉、阔野江流的雄伟壮丽而生动飞腾的夜景图画。由此可见诗歌语言的创造魅力。诗歌语言精炼和概括,必然要求跳跃,跳跃是语言精炼与概括在表现形式上的反映。马拉美说,诗歌是舞蹈,散文是漫步。散文的语言符号多是按部就班地一步步展开:,即使有断层,也有过渡和照应的弥合。但诗歌语言却非如此。它可以省略一般过程的交代,抛去外在的连续,在词与词、行与行、节与节之间进行大跨度的跳跃,又由于词语所负载的时空意识和主客观情况的不同,这种跳跃式的拼接就更可以造成诗歌世界的立体效应。
也可以说,诗歌在语言符号中作生命的旋舞。诗歌语言符号的跳跃性,不仅是诗歌表现技巧的要求,也有它更深层的内在依据。这就是诗人创作的思维特点。正象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抒情的飞跃,从一个观念不经过中介就跳到相距很远的另一个观念上去。这时诗人就象一个断了线的风筝,违反清醒的按部就班的知解力,趁着沉醉状态的灵感在高空飞转,仿佛被一种力量控制住,不由自主地被它的一股热风卷着走。这种热情的动荡和搏斗是某些抒情诗种的一种特色”。可见诗歌的跳跃性,是由诗歌的生命内质决定的。诗歌的跳跃有不同的方式:时空跳跃。诗是时间艺术,也是空间艺术。因此,诗歌不仅可以有时间上的跨跳,也可以有空间上的大幅度转换,更可以有象电影蒙太奇式的时空拼合。例如,张雪杉的《网》: 白天,太阳 向大地洒下一张张金网 夜晚,月亮 向大地洒下一张张银网 金网起网时, 洒落在地上的是汗水 银网起网时, 洒落在地上的是情泪 这首诗是时间上的跳跃,从“白天”到“夜晚”,又由时间上的转换带动了“太阳”和“月亮”,两相拼并,就集中赞颂了人生岁月中的劳动和爱情。又如,美国诗人庞德《诗章》第四十九章有这么几行: 雨,荒江,旅人。 冻云,闪电;豪雨,暮天。 小舟中的孤灯。 芦苇沉重,低垂。 竹林箫箫,似在泣诉。 五行诗中,写了“旅人”、“冻云”、“孤灯”、“芦苇”、“竹林”等十个景物,这些景物在空间中都是孤立的,但诗人跳跃性地把它并置在一起,省略了—切关联词,简洁精炼,但却给我们一种阔大的空间感。这就是空间跳跃所产生的独特效果。虚实跳跃。实是现实生活,虚是诗人情感。写诗不能亦步亦趋地单纯外在地表现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的变动中,激起感情的波澜,这样自然会有从客观到主观,从主观到客观的虚实的跨越,从而使诗歌产生有力的脉动。
例如,李松涛的《上机场,路过新房》: 一眼瞥见,路旁,村庄—— 大红“喜”字映笑一扇方窗。 一个新的家庭昂然出现, 彩色的大地,又一朵鲜花开放。 , 白天,祖国多了一缕炊烟, 夜晚,祖国多了一点灯光。 呵,我的心中又多了一条欢乐的小溪, 淌进我愉快的梦乡。 呵,我的身上又多了一分责任, 伴我云海里日夜巡航。 这是由外在“新家”的客观描绘跳到自己心中欢乐与责任的抒写。主客体交融,焕发了浓郁的诗意。又如,冰心的《繁星》之七: 醒着的, 只有孤愤的人罢! 听声声算命的锣儿, 敲破世人的命运。 人的“孤愤”是主观的,在这种情绪中,却又听到“算命的锣儿”声,这种主客观的拼接,情境相衬,就更增添人的“孤愤”的情怀。对比跳跃。把正相反对的两个事物或两种情感,通过词语的跳跃,结合在一起,相互对比、映照,从而造成巨大的意蕴张力。
例如:曾卓的《我遥望》: 当我年轻的时候 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 遥望六十岁,象遥望 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 遥望我年轻的时候,象遥望 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人在年轻的时候想到老年,到了老年人之后回想青年,两种不同的境遇和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比中抒发了人生的感慨。诗的浯言符号的跳跃功能,是十分独特而巨大的。它可以避免平直,在表达诗意上出奇制胜,从过去到现在,从此岸到彼岸,造成奇峰迭起,千岩竞秀,不仅很好地传导诗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也能为读者留下更多更广阔的思考空间。现代诗多层次、多侧面的建构,也要求诗歌语言符号跨度的丰富多彩。创造更多更好的表达现代意识的流程方式,是诗歌发展的必然吁求。
图片来自网络,欢迎点评,关注,转发!
50年后忆芳华 500位杭州赴黑龙江同江知青再聚首
2019-03-07 07:40 | 钱江晚报
1969年3月6日,18岁的邵凤美和许多年轻人一起坐在车上,车外是熙熙攘攘前来送别的亲属。这一日,前往黑龙江同江的专列启程,1046名杭州知青离开故土,奔赴大东北,将青春留在了那片热土。
50年后的3月6日,杭州赴黑龙江同江知青50周年纪念大会召开。500位当年的杭州知青再聚首,他们站在大会堂前,定格下难忘的大合照。
前进大队金花们再聚首
当年两人一起扛200斤的麻袋
“秋英秋英,这边这边。”拍完集体照,68岁的沈秋英早早地和小姐妹聚在一起了。是的,当年乐业公社前进大队的金花们又聚在一块了。
那一年1000多位杭州知青来到黑龙江同江,大家分散到了各个公社和生产队,才18岁的沈秋英来到乐业公社前进大队。包括沈秋英在内,队里共有11位杭州姑娘。
从杭州到黑龙江同江,沈秋英说,那些年的知青生活,酸甜苦辣都有。
“不管是队里的哥哥姐姐还是同江的乡亲,都特别照顾我们女孩子。不过,我们也不偷懒的。”沈秋英在生产大队织过渔网、干过各种农活,“一麻袋快200斤的粮食,我们姐妹两个一起扛着就走的,你说是不是跟铁娘子一样?”听到沈秋英的话,姐妹们频频点头。
3月6日的聚会,照片里的9朵金花来了8位,还有一位姐妹留在了同江。“她呀,嫁给了一位同江人。这次聚会结束后,我们约好了去同江看她。”金花们说。
跟着渔民在乌苏里江捕大马哈鱼
8天没睡过整觉
现场的大屏幕上,一张张黑白照片慢慢闪过,照片里是杭州知青们在同江工作、生活的一个个片段,每一张照片都难能可贵。
瞧,这张照片拍摄于乌苏里江。江面上两个年轻小伙子坐在一条小木船上,他们正在乌苏里江撒网捕鱼,捕的还是大马哈鱼。
而照片里的主人公,70岁的陈海洋和71岁的潘叶教就在现场。“当年去的时候是毛头小伙,哪里有什么打渔的经验啊,都是当地渔民手把手教的,撒网、划船、起网一个个学。”陈海洋说,那会儿在江面上打渔,最长的时间有8天没睡过整觉,一边划船一边眯一会儿。
今年80岁的龙彼德是杭州知青赴同江联谊会会长,也是当年1000多名知青里年纪最大的一位。1969年,龙彼德30岁,是杭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原本不需要上山下乡,但当时一心想去边疆体验的他主动申请去同江。
“我印象很深啊,当年每天干活十多个小时,每人拿把锄头去庄稼地里除野草。有一种野草叫水红棵,这个野草和庄稼的样子太像了。一开始知青们经常分不清,往往把苗砍掉了,草反而留下了。当地老乡手把手教我们干农活,都是学问。”
在同江的岁月里,龙彼德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同样来自杭州的知青。大儿子也是在同江出生的。1978年龙彼德回到杭州,对于同江,他和很多杭州知青都一直牵挂于心。2013年,同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龙彼德发动在杭州的知青,为同江捐款20余万元。
如今龙彼德已经是一名知名作家,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先后出了两本有关同江的诗集,部分中篇小说也是以知青岁月为基础。他说,知青这10年改变了他的生活,重新塑造了他的人生。
3月6日的这场聚会,每位杭州知青都特别珍惜,因为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沈秋英说,这次聚会之后,大家还要组织一次集体同江游,“人的青春只有一次,而我们的青春是在那里度过的。我们只要一想起青春,就会想起那片黑土地。”
(原标题《500位杭州赴黑龙江同江知青 50年后忆芳华》,记者 王丽。编辑:王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