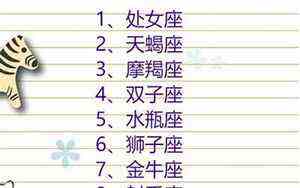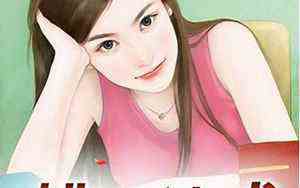“生”字又有什么深意呢?
“生”字甲骨文像草木生出土上,含义是进。《周易·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又“生生之谓易”,“生生”也者,乃生命繁衍,如何生生不息?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音通升,又通圣,只有心存众生,居安思危,把心放到三界以外,以无我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升华生命的价值,才能成贤成圣,获得永生!
“生”字又有什么深意呢?
“生”字甲骨文像草木生出土上,含义是进。《周易·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又“生生之谓易”,“生生”也者,乃生命繁衍,如何生生不息?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音通升,又通圣,只有心存众生,居安思危,把心放到三界以外,以无我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升华生命的价值,才能成贤成圣,获得永生!
人为什么要生孩子?看完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响应国家号召,适...
人为什么要生孩子?人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人为什么要生孩子?人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思考过这个问题,毕竟生育子女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做出生儿育女的决定。
·1.自然与传承。人类和众多动物一样,天生就有一种繁育的本能意为薪火相传,很多时候并没想那么多既然怀孕了就顺其自然,孩子就顺理成章出生了。
就像笔者本人常去一家盲人按摩店,两位按摩师傅是夫妻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几乎全盲的缘故,一度认为他们不会生育后代。可是经过按摩过程的一番闲聊得知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当时我想到的是,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从不把自己看不见视为生命的羁绊,所以也从不认为这是他们不生孩子的理由。
也许在这对乐观的盲人夫妻看来,生孩子只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他们理应薪火相传,理应拥有后代,理应赋予一个人新的生命,幸运的是他们的孩子是健康的,我真心替他们感到安慰,这只是关于自然与传承的一个例子。
·2.为了父母,中国人有句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孩子已经成为了传统意义上的必选项。父母都想看到子女步入生儿育女的阶段,不生育还能被认为是不孝的表现。多少人到了适龄生育的时候被父母问过生孩子的问题,甚至听到不生孩子我们家没后代了之类的抱怨,然而生孩子究竟为了谁?到了今天会有统一答案吗?
·3.为了自己,"养儿防老"成了很多人传统观念中生孩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自己老的时候能有孩子照顾自己、孝敬自己,另外孩子也可以成为人生的支柱,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在想要放弃的时候,他们将是你继续坚持下去的支柱与动力。
自私地说孩子是一份投资,虽然成本高昂但是回报也是十分可观的。
·4.延续希望。很多人到了中年每一天的生活也在不断重复着,对生活的新鲜感也在慢慢淡去,这时候可能需要孩子来打破这一个循环,孩子可以带来很多的快乐。
当你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走路说话或者获得一项成就时,那种自豪和快乐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而且孩子可以带来一份温馨的家庭氛围,让家庭更加的完整和幸福。陪着孩子开展一次崭新的人生,那时人生阅历中一笔无价的财富。
所以呼吁大家响应国家号召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即三孩政策。
人生笔记:婴儿
#秋日生活打卡季#
梁东方很多年没有接触过婴儿了,就好像从来没有接触过一样。多少年前养孩子的时候的记忆随着这多少年来距离婴儿生活状态越来越遥远而竟都忘掉了。已经完全习惯了人在脱离开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之后作为成年人的一切,突然要面对连牙牙学语也还不会的婴儿,时时守在身边,突然就从一向时不我待式的忙碌中抽身出来,在婴儿完全无待的含混朦胧中,望见了生命的本质一般。老子所云“能婴儿乎”,只有你在长时间面对婴儿的时候才会有深入理解的可能。老子所推崇的婴儿的无始无终无往无来的含混朦胧状态,是对人生后续时间越来越进入高效的紧张状态的警示与调节。
婴儿的不计后果、不及未来是以其对一切的浑然不知为基础的,成年人在对一切有知之后,断难恢复到婴儿状,如能偶尔以之为参照,努力修正就已经是至高境界了。说来说去,没有抱过孩子还是不能完全体验孩子之为孩子予人的喜悦的。因为现实的种种困难和理智考量而完全拒绝拥有孩子的状态,一般来说都是以不接触婴儿为条件的。一旦有所接触,便很难不被其实实在在的生命质感所打动。从无从下手到终于学会了不无笨拙的抱法,婴儿在怀中像是一条大鱼。在那种瓷实的沉甸甸的小身坯完全依赖地伏在你的臂弯里、伏在你的胸前的状态中,你顿时就会有一种因为被无限信赖而来的感动。这就是你的基因代代传递之下的最新成果,这就是你的后代,你的亲人的延续。这一团貌似还是无知的血肉的婴孩,将来会变成一个目光明亮、表情丰富的人,会变成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家族传人、社会一分子。这突然被意识到的神奇,就真真切切地正在自己面前发生着,怎么能不叫人由衷地欣喜!婴儿稚嫩的皮肤、圆滚滚的胳膊腿、大大的脑袋和懵懂无知的眼睛都让你猜测其所面对的一定是一个含混的世界。每天都只能躺着,不会坐起来,更不会走路,目光所及仅仅是头顶上的天花板那一小块地方。在一片不能自主的朦胧里,眼前出现的一切都带着一种不可理解的形状和色彩,发出莫名其妙的声音,而自己除了哭,是任何其他声音也发不出来,任何要表达的明确意思都无法明确起来。实际上明确这个词在这一阶段还完全是个奢望,婴儿还在什么也不明确的运转机制里,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再无其他。婴儿几乎重演了人类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由没有意识的低级动物到有丰富精神的高级动物的演化的全过程。以此观之,总被认为太过漫长的十年二十年的成长期也就不嫌其长了。每一个个体都仅仅用了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就已经走过了整个人类多少万年才逐渐达成的进步,岂不是很快!随着时间推移,由刚开始的二十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时间缩短到了十几个小时的时候,婴儿开始有了自己的玩耍。这总是令为人父母者惊喜,因为婴儿的玩耍证明了这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不仅是睡眠,还有舒胳膊踢腿转头之类。这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肢体“锻炼”,可在这样的肢体锻炼中,总是有孩子目光出神的时刻,那样的时刻就是我们感觉其正在建立自己对外在世界的认知的过程。婴儿出神的时候,既像是若有所思,又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地无所事事。婴儿发出嗯嗯啊啊的声音,带给大人的喜悦、发现她在谛听音乐的喜悦,都是发现其具有一般人所应有的功能的喜悦。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还是让父母、让爷爷奶奶、让姥姥姥爷姑姑姨舅都从心底里高兴。一家人倾尽全力呵护的这一团小生命终于一天一天地慢慢有了各种各样的进步,进步成拥有一个人的诸多视听感受与表达能力。只有这样的养育过程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在家庭里建立起牢固的纽带,将可能已经各自独立、各自都有了自己的生活天地的家庭成员重新聚拢起来;也只有这样养育过生命,才会深深懂得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来之不易,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尤其是尊重人的生命权,是多么重要。婴儿无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选择的余地,生在何时何地什么人家都是偶然,也是必然。他们懵懂的眼睛看到的世界大致一样,具体又有不同。从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中看出去,对他们未来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父母、在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中成长也更其关键。这不过是成年人的经验总结,对于婴儿来说一切都在未知之中,理论上始终存在一个一切都不确定的远大前途,父母、祖辈在这样婴儿的前途面前收获的是自己被刷新了的机会,婴儿好像可以完成他们没有可能完成的理想,可以矫正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不足与不甘。其实即使不被这种几乎不能说是幻觉的好感觉鼓舞着,大家对婴儿的凝视也总是由衷地持续着,这来自本能范畴的血脉相连之下的含混而坚定不移的力量。很快,婴儿平静的锻炼结束了,开始浑身“聚连聚连”地抓耳挠腮。长期躺着,越来越胖地躺着,没有长出来的脖子的位置被下巴上的肉覆盖了,起了疹子,自然不知道怎么办,更不知道是长了疹子,就只能还像是饿了困了一样哭。婴儿会笑也更会哭,饿了哭、热了哭、冷了哭、尿了哭、拉了哭、累了哭、困了哭……相比笑的偶然,哭是不需要训练和他人努力就会的本能。哭是一种急切召唤和激烈表达,笑则基本上不具有召唤的意味,只是一种对愉快、有趣、好玩的赞赏的浅淡身体语言。实际上,婴儿不哭也不笑,自顾及自地在那里圆睁着双眼玩一会儿的状态就已经很让人知足了。平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婴儿最高级的品质,孩子平静,大人就已经十足欣慰。婴儿洗澡的时候,稀疏的头发被完全贴到了头皮上,小小的身体和头都像是某种不谙世事的一般哺乳动物一样懵懂而幼稚,带着一种完全可以以弱胜强的单薄渺小,让人于陡生的爱怜之下对其呵护得五体投地。此情此景之下,不爱婴儿、对婴儿不屑一顾都是不可理喻的。我们被婴儿的哭所召唤,被婴儿的笑所鼓励,被其还不会说不会走就能把你调动得团团转的本事而深深折服,在不知不觉中就以其为中心,忘记了自己作为成年人在尘世中一向的习惯,把时间大把大把地给予了这个还只会躺着伸胳膊撂腿的天使。天使就应该是大多数时候对围绕身边的人都没有什么明确的交流状态吧,这时候的婴儿还不大认识每天给自己喂奶的母亲,遑论其他人。只是对母亲父亲的声音有了习惯而已,这种习惯只有在其一天天长大过程中才会演变成一刻也不能分离的情绪和情感。婴儿期就是从一团纯粹的物质逐渐生长出精神来的过程,其全身心的生长,几天、十几天、几十天必然会有一个模样的变化,都是这种生长的外在显现。每个人都不记得了的婴儿期里,每一天居然都是这样含混难熬的。以成年人的角度观察和揣摩之,大量的睡眠之间点缀着的,都是莫名的声音形象和不适,亲人脸对脸的话语和抚摸是一种安慰,安慰之余又因为不可能一直都有安慰而对比出来不安和痛苦。天地造人的妙处就是让婴儿在无知无觉中度过这一段持续时间以年为衡量标准的婴儿期,倘使一开始就让他们拥有成年人的知觉能力,岂不是充满了无法承受的痛苦!这一点完全可以参考那些成年以后因病因灾而只能躺着的人。每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看上去很不容易的婴儿期:柔弱、渺小、低能或者说无能,没有任何防御力……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婴儿状态里一天一天地走过来的,在父母的呵护下一点点长大,着实不易。每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延伸到所有哺乳动物,所有非脊椎动物,所有生命。人类最伟大的宗教和最伟大的哲学,一定都是在对婴儿期的人类有过深刻体验之后才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它们一定都浸透着对每一个人类个体的爱。无我无他、无为而治、仁者爱人、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生而平等……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忙乱,但内心却是异常稳定的。孩子使人心无旁骛,使人进入一种不对其他人和事做任何幻想的超级稳定状态。孩子可以被带到户外活动以后,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突然就变得广阔起来,丰富起来,让大人不由自主地开始向往未来。这大概就是婴儿的伟大,婴儿总是能为日渐疲劳的成年人重新昭示希望。
“被五条人笑死”的网友,能听懂他们在唱什么吗?
▲ 五条人每年春节都要回海丰办一场“五条人回到海丰民谣会”的演出。2012年年初二,仁科(左)、阿茂在歌友会上表演。 (快美林/图)
全文共4674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2009年他们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红色的歌词本设计成老式户口本的样子,写着八个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五条人想以此表达,他们用世界性的音乐和县城外的视角来描述海丰。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终于开播。让人意外的是,率先冲上微博热搜的,却是被淘汰的五条人乐队。仁科和阿茂在问答环节金句频出,很多网友评论称差点“被五条人笑死”,他们也一夜间成了大家的快乐源泉。
临场换歌,人字拖登台,魔性的“yes”……如果你依据这些细节觉得他们是随性的土味民谣组合,甚至以为仁科是走错片场的段子手,那可能就错失了理解他们“音乐野心”的机会。
2012年2月2日,南方周末曾对其进行报道,现摘编于下:
民谣乐队“五条人”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个人:1981年出生的阿茂,1986年出生的仁科。他们每年春节都要回海丰办一场“五条人回到海丰民谣会”的演出,有时候是借用朋友的画室,有时候是在还没装修好的展厅,有时候干脆露天。2012年他们安排了两场,大年初二的歌友见面会和正月十五的演唱会。
在广东,“海陆丰”是一个远比汕尾如雷贯耳的名字。包括海丰、陆丰、陆河在内的“海陆丰地区”,在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为汕尾市,但人们还是习惯延用那个沧桑的老称呼:海陆丰。海丰、陆丰这两座毗邻的小县城,唱着一样的白字、正字、西秦戏,擂着一样的“咸茶”,吃着一样的潮汕丸子,一样跟“农民大王”彭湃闹过革命,有着一样多的香港亲戚……
五条人就从这里走出来。从2006年开始,他们一直用海丰话唱着海丰的那些事儿。2009年他们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红色的歌词本设计成老式户口本的样子,写着八个字:“立足世界,放眼海丰”。这个口号来自海丰县城里四处张贴的标语:“立足海丰,放眼世界”,五条人想以此表达,他们用世界性的音乐和县城外的视角来描述海丰。
2009年,专辑《县城记》还曾获评为南方周末“2009年度原创文化榜”里的年度音乐。评委们认为:“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1“干坏事,小心雷公敲你啊!”
天啊天乌乌 要啊要下雨/我妈在家等我回家吃饭喔/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好呀/我在看守所里面/我妈讲:阿仔啊回家吃饭吧/都怪我那个时候/不成器 老去混/也怪我那个时候呀/老势势
——《道山靓仔》(老势势:海丰话,“跩”的意思)
仁科出生的地方叫捷胜镇,是汕尾东南角的一处半岛,洪武年间有千户侯率民众在这里大败倭寇,所以得名。捷胜人自古就在倭寇和海盗横行中求生存,六十年前,离捷胜不到两公里的龟龄岛,还是“海盗天堂”。捷胜人也因此颇为勇武好斗。
小学四年级之前,仁科一直在这四处漂着鱼腥味的镇子里生活。他自小就听说着村子之间年轻人相斗的故事,有时候因为土地纠纷,有时候“为芝麻绿豆大点事儿”,“他们会拿着西瓜刀互劈”。他也亲眼见过一次,那时他正在外公家坐着,听到楼下有打架的声音,趴到窗边一看,好几个人拿着西瓜刀劈一个人——“那是真劈啊。”仁科说。他自己不擅此道,仅有的一次“战斗”经验,就在对方一木板拍下时瞬间结束,仁科被送进医院。但“西瓜刀劈人”一直留在他脑海里。
仁科和阿茂后来把村民打架写进歌里。那是几个哥们在瞎起哄时想起的一个故事:农村里搭台唱戏,演员在前台演,戏台后就有人在分番薯粥。演曹操的人闻到一股番薯味分了神,后台人对他喊:“曹操,你别怕。番薯粥一人一碗。”曹操立时怒了:“一人一碗,你们把番薯肉分完了,剩下一碗番薯水,那还算一碗吗?”“啊呀呀——”台上台下顿时打骂作一团。曲子开头,五条人用农村最常见的吵架场景作引子:“伶敢行啊瓦阿乡里踏瓦阿田,扑母啊!(你敢来我们村践踏我们的田!找死啊!)”
“天顶雷公,地上海陆丰。”在外地人看来,这句话是对海陆丰民风“剽悍”的最佳印证。但“雷公”的意思并不是野蛮、凶狠。海陆丰人视“雷公”为惩恶扬善的正义之神,看到作恶的人,他们会骂:“小心雷公敲你呀。”“地上海陆丰”说的也正是海陆丰人嫉恶如仇的性格。
遇到不公道的事,海陆丰人一定要讨个说法。“那些时候,海丰人很团结。”仁科说。他对1999年海丰县的一次集体罢市记忆犹新。那时他随父母生活在海城,有天早上一起来,发现“整个县城齐刷刷没有一家店开门”。商人们以此表达他们对超高额罚款的不满。那次罢市持续了三天。
在捷胜,仁科是“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孩子”——爷爷曾在国营食品单位工作,颇有积蓄。父亲是个厨师,掌勺之余,在爷爷的帮助下开餐厅、开酒楼、开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
仁科一家从捷胜搬到海城是在一个晚上。父亲生意赔了,为躲债连夜找了辆车把全家接走。坐在车上,仁科对逃债这件事完全没有意识,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是觉得半夜走“太丢脸了”。他后来知道,这样“丢脸”的事在海丰很常见。
2 牛屎塘已经没有了牛屎
我闲着没事,就去找化工厂那个阿伯聊天/聊了一通,他跟我讲:老板带十多个员工去吃大餐了/就剩我这个老头子在这吃西北风/活该这里生产的蚊香卖不出啊!/但是他又跟我讲/嘿!阿仔!这些话你可千万莫跟我的老板讲呀!
——《梦想化工厂》
陶河镇是“海丰县经济倒着数一数二的”,这多少和陶河的偏僻有关:以前阿茂的父亲和同伴去汕尾挑盐,走路要花上来回一天——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步行。
阿茂的父亲是个泥瓦工,手艺从他爷爷那儿传下来。父亲常常走街串巷招揽生意,阿茂就坐在他的“二八”自行车后面,去周边的镇和村子,去养老院。父亲干活,阿茂就抓麻雀、摘橄榄。那时陶河镇的人多在务农,种些水稻、番薯、花生。到了1990年左右,年幼的阿茂开始看到很多人坐在那里,磨啊,锯啊——镇上开了个宝石加工厂,村里有不少人进厂打工。陶河没什么矿产资源,宝石的原材料都从南美来,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
1994年的时候镇子里有了些变化,经济状况有起色的村民纷纷推掉瓦房,盖起敷着砂砾外墙、“全广东都一样”的小洋楼。起楼不需要什么手续,只要有钱,想建几层就建几层。阿茂的父亲已从泥瓦匠做到了包工头,承建了镇子里不少小洋楼。
建筑生意的走俏让阿茂家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也搬进了两层小楼,以前他们住在一间40平米的瓦房里。父亲赚钱了,说话做事也变得格外有底气。超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父亲就每天开着自家买的三菱越野车,载着阿茂到县城的大超市去采购,吃、喝、穿,样样给足。“人都是这样,风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节制。”现在,阿茂会这样总结那段“有钱的日子”。
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好,1996年他们举家搬到海丰县城。县城没有朋友,阿茂只能每周末骑四十分钟单车回到陶河镇,找小时候的玩伴。后来他进了省城,也还经常回去。2011年阿茂回去的时候,发现小时候经常穿街过巷的一个小村子已经空无一人。那村子叫“牛屎塘”,十几年前很美,现在也还保留着几分姿色:有条小溪(虽然已经长满水葫芦),有座废弃的小鱼池,还生机勃勃地长了不少树。但是已经没了人,更没了牛屎。村子没有人管,“也许有些抢劫犯和吸毒的会经常去。”阿茂猜测。
这样的无人村,在海丰一点儿也不特别。更多的村子里,只住着留守老人和外省人。外省人在1992以后进入海丰,常常是一大车一大车地到来。当地人叫他们“老松仔”(即“北仔”)。东平镇的工厂多,“北仔”们每天上午就在东平的桥头扛着铁锹站成一排,等着工厂来雇工,做一天两块钱。因为穷,他们被人厌恶、瞧不起。本地中学生看多了《古惑仔》,晚上成群结伙,“遇见落单的外省人二话不说就打一顿练手。”直到1997年左右,外省人已在海丰落住了脚,自发组织了“老乡会”,自我保护。
在县城里,阿茂父亲的生意很快被一次赊欠拖垮。1994年父亲靠着关系,承包修建县里某单位的办公楼,垫付了原材料、钢筋、水泥、人工等费用近四十万。楼建好了,工程款却一直拖欠着。拖到1998年,父亲的资金实在周转不过来,债务又追不回,只好破产。直到今天,这笔欠款阿茂家还是一分钱没拿到。
父亲的遭遇,连同阿茂对海丰的其他各种“看不惯”,激发了阿茂的创作欲望。
港纸贩子是海陆丰的特殊行当,他们坐在东门头,低价收购港币,再高价换出。(区区/图)
3“干嘛要把那些女孩关起来呢”
1878年他生于海丰/1933年他死于香港/1935年他葬于惠州。
——《陈先生》
仁科和阿茂相识,是通过“区区五百元先生”,仁科是五百元的朋友,五百元是大茂的同学,大茂是阿茂的哥哥。
五条人的音乐养分,很大程度来自他们卖打口碟的经历。2003年仁科没有工作,五百元就介绍他到广州去找阿茂,跟他一起在暨南大学西门卖打口碟。
此前,两人听过的打口碟都来自阿茂的哥哥大茂。大茂1997年前后在广州上大学,隔三岔五给阿茂和他的同学“区区500元先生”寄些打口碟。
第一次见到打口碟,阿茂打开家里几万块一套的音响,把碟子塞进碟机,他觉得太好玩了:“被锯掉一个缺口居然还能听。”有一张英国独立摇滚乐团Gomez的专辑《bring it on》,阿茂听到后觉得自己要彻底崩溃了,“那时候思维彻底就不一样了。”那年阿茂初三。他还记得和两个喜欢摇滚的朋友站在一起小便,一个朋友问,你们以后想做什么?阿茂提提裤子:“我想做音乐。”
阿茂第一首歌就是写他对海丰的各种看不惯。“听了摇滚乐就觉得自己上了一个层次,总觉得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一个城市搞得乱七八糟,那么多贪官,什么都不好。”阿茂说。
仁科也很认同阿茂的“看不惯”,不过他更愿意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他从小喜欢读故事。四年级从捷胜搬到海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仁科只好天天看书,去县里的旧书店买一块钱两本的过期《故事会》。
刚到海丰的时候,仁科经常看到有人在“海丰的母亲河”龙溪津的源头洗衣服,那时候河水已经污染,现在则几乎“像墨汁一样”。在《踩架单车牵条猪》里,五条人唱道:“龙溪津是一条河,三十年前已经残废了。”
《踩架单车牵条猪》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县城:“唉,朋友/你莫问我/有没搭过海丰的公共汽车/我经常看见它载着空气/从‘联安路口’至‘云岭’/唉,朋友/你莫问我/有没听过海丰汽车、摩托车的噪声/路口那个耳聋的都被震怕了……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海丰公园只开一个门。”
1960、1970年代,许多海陆丰人偷渡到香港去,1980年代末开始回乡投资。这催生了海陆丰的特殊行当:港纸贩子。他们坐在东门头,低价收购港币,再高价换出。五条人为他们写了首歌,叫《倒港纸》:“那一天我经过东门头的时候/我看到古巴的表叔公/他摆张凳子坐在路的旁边浑浑噩噩/他看见我走来便猛然站起来喊:靓仔啊/你有港币无?你有港币无?”
另一首极富海陆丰特色的歌叫《阿炳耀》。海陆丰人的宗族观念很重。一家里的孩子多了,总会牺牲一两个,娶不上老婆。老光棍阿炳耀就每天站在制衣厂的门口,想着女工,骂着老板:“你这个X母的,干嘛要将那些女孩子全部关起来呢?”
五条人把这个故事唱成歌:“炳耀没跟别人那样用钱买个老婆回家睡觉取暖或许他是有这样想过的……他的弟弟炳文一天到晚像只八哥鸟似的总是责问他:‘今天给我喂猪了没有呀?’/锄头、屎桶每天都挂肩上,也从没听他喊过痛。”
五条人唱过海丰的“名片”彭湃。这个大地主的儿子,亲自烧毁自家的田契,鼓动海陆丰农民革命,建立了全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五条人虚构了一个地下革命者撞见宪兵、两人各自谈论彭湃的故事。这几乎是五条人在海丰名气最大的一首歌。有学生在音乐考试的时候唱它,还有个学生告诉区区500元,他们曾在学校里集体唱这首《彭啊湃》。
2012年4月五条人将发行自己的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在那张专辑里他们唱到了陈炯明——从海丰走出去的另一个大人物。和彭湃不同,陈炯明长久以来以“乱臣贼子”面目出现在教科书上。这首叫做《陈先生》的歌只有三句话:“1878年他生于海丰,1933年他死于香港,1935年他葬于惠州。”第一句用海丰话唱,第二句用广东白话唱,第三句用客家话唱。
仁科觉得历史是很难讲清楚的,“你要想了解5000年的历史,就得花5000年的时间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