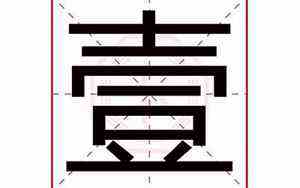学人||金克木,猜谜的人
本文来源:世界古代史研究网转自:世界古代史研究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爱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中有层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谜的兴趣,缺乏好奇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专家”与“杂家” 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跨世纪一代学人中,金克木是难归类的一位。他最显著的公众身份,是北京大学东语系与季羡林并驾齐驱的印度学学者。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金克木还是30年代新诗坛的重要一员,和戴望舒、徐迟等人相契相知,晚年还写作了大量古体诗。此外,他还可算作翻译家,精通梵文、巴利文、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英语、法语等多种外国语言文字,翻译的语种和内容都驳杂,抛开梵语著作、散文小说不谈,甚至译过两部天文学普及著作《通俗天文学》和《流转的星辰》。而金克木真正“成名”,可说是自古稀之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始的,从1979年《读书》创刊到金克木2000年辞世,是他生命的“晚年”,但思考和写作却正处“壮年”,发表随笔杂感100多篇,成为《读书》前20年最高产的作者。 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回忆,1979年《读书》创办时,发现经过10年的中断,青黄不接,能找出来的都是三四十年代就奠定学术根基、时已60多岁的老先生。不但要学问好,还得文笔好,算来算去就那么几位,金克木、张中行、李慎之、费孝通、钱锺书……既然脚下都是禁区,那就从打破“八股”文体开始,不“穿靴戴帽”,不说官话、套话,老先生们成为拓荒者。 “为什么晚年忽然多产?”金克木自问自答,“我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冷和热之间动荡,过了70多年。这恐怕是我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不得不将思想化为文字的内在原因。像蚕吐丝作茧使自己僵化并将自己埋葬一样,我也是倾吐衷曲使自己僵冷。”退休后的金克木抛开“专家”身份的束缚,“70岁老翁在试图解答17岁少年时产生的疑惑”,“对文化猜谜”。这一时期,“不料《读书》杂志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金克木说。 《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回忆,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说不完的话:“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因《读书》与金克木结缘的陈平原15年间常去金克木家拜访,他说:“在他去世10年前,我就听先生说过,脑子不行了,不写了。可‘金盆洗手’之后,报刊上还不时出现他的文章。你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打假’,这个时候,先生会得意地狡辩:天气变暖、不能白吃饭、老花眼突然开恩、电脑很好玩等等,都成了重新写作的理由。”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等一批80年代中后期的毕业生,其后接棒成为《读书》的第二代作者。他认为,就读书心态与文章趣味而言,金克木与现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很不协调,与当代中国散文之注重叙事、抒情也大相径庭。对于纯粹的“文学”或“学术”杂志来说,金文都未免过于“边缘”了些。“幸亏有了这‘不三不四’的《读书》,欣赏他那些‘不伦不类’的文章,这才促使他由功成名就的专家,转而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家。”而《读书》也得益于金克木良多。陈平原曾概括《读书》文体:“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说,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乃标本之一。” 陈平原告诉本刊,金克木去世的第二天,他拿出一大摞金先生的书翻阅。“读他的书就像观赏体操运动员之上下翻腾,表演众多高难动作,给人的感觉是既紧张,又惬意。可一旦落笔为文,却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不是因为书多,而是文体、学问、思想之‘博’与‘杂’,让你一时无从把握。”三联书店学术分社编辑冯金红也有类似的困惑,此时,继《钱锺书集》、《陈寅恪集》之后,著作丰厚又与三联素有渊源的金克木很自然地成为下一个全集编撰对象。在此之前,仅三联出版的金氏著作就有《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书城独白》、《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风烛灰》,再加上其他出版社的自编、他编文集,就更是数不胜数了,如何归类成为难题。最后索性依照金克木的“四重身份”——诗人、随笔杂感大家、印度学专家、翻译家,把他一生著作约400余万字分成8卷。 对应其文的“博”与“杂”,金克木晚年公开拒绝“专家”称号:“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的,零卖一点杂货。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学问的人,我也不是。” 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告诉本刊,父亲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幼时有许多是既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又受过早期西式启蒙学堂教育的。对他们来说,古文经典脱口而出、文言写作随心所欲是很自然的事。那一代学者,还有不少人用毛笔写文言比用钢笔写白话更顺手,旧学根底是幼时基础,中西贯通是后来成果。文史类学人自不必说,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是如此。“我曾听到过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随口背诵《左传》、《史记》;见到过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亲手所记电路图一般工整精确的围棋古谱;至于数学家华罗庚、水利学家黄万里的旧体诗文功力,就更是众所周知了。华罗庚去世后,我父亲曾叹息有些问题再不能和他探讨了,否则一定会有共同兴趣的。” 陈平原对本刊说,金克木早年是诗人,这一“底色”不能忽略,他乐于接受各种挑战,勇于驰骋想象,这点在晚年的文章中仍有很明显的体现。金克木没像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或季羡林晚年完成《糖史》,而是天马行空,自由挥洒,给后人留下无数有趣的“话题”或“谜语”,这两种选择都值得尊敬。陈平原认为,在世人逐步恢复对“专家”崇拜的年代,金克木自称“杂家”,大有深意。传统中国文人,有人专攻文章,有人专攻学问,但是“文”和“学”之间有某种联系。而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成为主流。他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类的文章”。经行 金克木不是科班出身,只在北大当过旁听生,后到印度鹿野苑跟随退隐的老居士乔赏弥读《波你尼经》,好几门外语都是旁听或者自学的,比如他的拉丁语就是在傅斯年的鼓动下,通过翻译恺撒的《高卢战记》而边译边学。这样“不完整”的求学经历,竟然打通多个领域,并在一个冷僻领域成为“专家”,与金家有世交的《群言》杂志主编叶稚珊也不解:“为什么金克木的好动由表及里,按常规的看法,是一个‘坐不住的人’,但他研究的东西又是如此冷僻、沉静,研究的态度是如此沉稳、扎实、灵活、深刻?” 他最初修习梵文的起因是出于偶然。1941年,金克木由朋友介绍到加尔各答一家中文报纸当编辑。“那时印度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我脑中没有离开从罗马帝国上溯希腊追查欧洲人文化的老根的路,还不想另起炉灶攻梵典。”但是,“书中讲的印度各种各样,现实见到的另是一样。于是我又犯了老毛病,由今溯古,追本求源,到附近的帝国图书馆阅览室去借用英文讲解的梵文读本,一两天抄读一课,再听周君天天谈他来印度几年的见闻,觉得‘西天’真是广阔天地而且非常复杂”。其后他到佛教圣地鹿野苑,攻梵典并翻阅那里的汉译佛藏。“因为觉得不能不了解一下中国古人怎么跟印度古人凭语言文字交流思想的遗迹。结果是大吃一惊。双方确是隔着雪山,但有无数羊肠小道通连,有的走通了,有的还隔绝,真是译作五花八门,好像没有条理的迷宫。幸而遇上了来归隐的乔赏弥老人指引梵文和佛学的途径。”他常感念乔赏弥依照古代传统的口语讲说方式:“两人在大炕上盘腿坐着对话。先是我念、我讲、我问,他接下去,随口背诵、讲解、引证,提出疑难,最后互相讨论。这真像是表演印度古书的注疏……就这样,我好像陷入泥潭愈下愈深不能自拔了。” 同在圣地求学的不同国籍的修行者平日在路上相遇都只是合掌为礼,说声“南无”,并不搭话。金克木住在招待香客的“法舍”里,每天太阳西下时,他快步走向“根本香寺”前的大路,在那里与陆续到来的“过午不食”的和尚、居士或零散或结伴奔走,大步流星。这便是古时释迎佛带着弟子罗汉菩萨的“经行”,流传下来,是很多印度人习惯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运动。叶稚珊认为,金克木早年在印度养成的“经行”这一令人敬畏的苦行中,蕴含着对脑力、体力的训练,蕴含着对坚韧、忍耐的考验,蕴含着对自己修行、信念彻与悟的过程。这对于解释“金克木现象”,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金克木印度求学三年后回国,1960年在北大东语系与季羡林共同开设了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招生17人,这是中国系统培养印度学研究人才的开端。曾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黄宝生和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的郭良鋆夫妇是当年17人中的两位,他们对本刊回忆,季、金两位先生交叉授课,各编一套讲义,但风格迥然不同:季先生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照德国学习梵文的模式,繁琐而复杂;而金先生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依照印度传统模式,注重训练学生的口耳反应。他的一大绝活是,在课堂上常常按照印度人的方式,吟唱梵文颂诗,抑扬顿挫,像唱歌一样。及至1984年第二届梵文巴利文班重开,两位老先生已经不再授课,接棒的是1960级毕业生蒋忠新、郭良鋆。那一班学生已经无福听到金克木的梵文吟唱。一次蒋忠新特地将金克木此前录的一盘录音带带到教室放给学生听,当时的学生之一钱文忠回忆说:“带子一放,金先生的梵文吟唱如水银泻地般充满了整个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吟唱后,同学们都垂头丧气。我们平时练习十分困难的梵文发音时,周围的同学都来嘲笑我们,说梵文里有马、牛、狗等等所有动物的声音,还拜托我们不要制造噪音。我们一直认为梵文是世界上最难听的语言,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梵文是圣语,为什么梵文有神的地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啊,‘此音只合天上有’。”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的陆扬也是1984级梵文班上的一名学生,他后来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也受到金克木很大影响。在他看来,金克木的印度学研究,开启了中国梵文巴利文研究的另一条路径。陆扬那时候定期去拜访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沿着东语系的楼向右走,穿过一条隐蔽的小路就是湖边的朗润园,一排房子,左手边是金先生住的地方,右手边则是季先生住的地方,对他来说象征着两个关系密切又截然不同的学术体系。陆扬对本刊说,季先生有一套房子专作书房,进门就是一张长长的书桌,井然有序的书架,说话也严肃严谨,只要是印度学、佛教学方面的问题,问他什么,马上就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而金先生家一开门,杂乱无章,靠墙边一个沙发就是每次谈话的地方,几乎什么书都没有,谈话却天马行空,妙趣横生。这当然只是表象,陆扬认为,其根本不同是季羡林留德10年继承了欧洲研究印度学、东方学的方法,纯客观地从文献出发,强调语法、语言,某种程度上说是把印度作为一个“死文化”来研究,对印度文化的复杂性、多面性没有太多关注。而金克木40年代在印度求学三年,接受的几乎是私塾式的教育,而且当时印度恰恰是从殖民地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转折时期,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真正进入了印度文化的核心,因此他更注重研究文化,尤其注重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钻研,后来形成金克木最为重要的两本学术著作——《印度文化论集》和《比较文化论集》。 让陆扬印象深刻的是,金克木反复讲过一个故事:“你看婆罗门教宣扬牛是神圣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印度亲眼目睹在神庙后面杀牛,鲜血淋漓……”“他在讲述的时候,手举着,眼神就停在那里。在他看到那个场面的那一刻,他心中文化的表层破灭了。”陆扬认为,金克木的一生特别是晚年,始终是在追寻文化底层的东西,从一种无序的文化中去找到背后的符号,因为文化真正要深入,是看到其多变、复杂和不确定的一面。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界限分明的学术评价体系之外,打开了一个新天地。发现的快乐 “思想是风,思想是烛,思想是灰。”不过,纵然风中残烛已成灰,风中的灰仍然传播久远。《风烛灰》是金克木生前亲手编订的最后一部文集,在他最后一次入院前的五六天,他还给编辑寄去刚刚写就的《倒读历史》一文,一个多月后与世长辞。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时任文集的责任编辑,她说:“金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中所写的这些近20篇文章,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博闻强记、思想犀利的鲜明特点。尤为突出的是,他更加超越于一般专业研究之上,意欲打通各种文化,跨越古今中外,去追索人类社会‘是什么’、‘为什么’……读他的这些文字,分明可以感觉到,写作时充盈在他脑际中的真正的‘发现的快乐’。”或许因为这种快乐,他的遗言才那么轻盈而豁达:“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若论学历,金克木充其量只能算小学文凭,驱动他不断去求学的正是无休止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既然处处有谜,就可以处处去试破”。金克木的女儿金木婴告诉本刊:“他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正规考试,没有大学学历,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倒不是考不上,而是没钱考。但他从不承认是自学成材,总是强调他是有老师的,而且老师都是最好的。当然,有明师,能够学‘通’知识,少不了勤学好问的精神与浓厚的兴趣。其实,自己学习专门知识需要有人指点,无师只怕很难自通,受正规教育又何尝不同样需要自学,需要兴趣?” 金克木曾不断提及的30年代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家庭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老师”。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时,巧妙使得“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地,他们指引我门路。” 金克木还特别谈到一位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来的鼎鼎大名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往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第准予借出。借的全是善本、珍本。由于外借需有馆长批准,而馆长那天又刚好不在,这位老先生又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下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 就像金克木喜欢自己打谱下棋一样,晚年几乎足不出户的他也将与人谈天作为一种思维训练。经常去跟金克木谈天的人往往发现,看似漫无边际的谈论,当然更多是他说你听,原来就是不久后某篇金氏新作的“练习版”。“有人说,和我父亲谈天,往往你的专业是什么,他就和你谈什么,如果正好是他熟悉的,自然谈得热闹;如果并非他的专长,那他就更高兴,会说:‘又长知识了。’”金木婴说。 “说我父亲写文章是‘既传统又时髦’,我觉得很恰当。他读书也是这样,兴趣极广泛,看书极杂,可以说是无所不读。”金木婴说,从古老的《十三经》到时新的电脑网络、计算机语言,从高雅的《庄子》与《文选》到通俗的张恨水、金庸、琼瑶,从没几个人懂的梵文、拉丁文经典到浅显的中小学课本,铿锵的拜伦、弥尔顿,难以卒读的乔伊斯、普鲁斯特,大众化的阿瑟·黑利、克里斯蒂、松本清张……什么都看。中外文史哲名著自不必说,自然科学他也有兴趣,围棋、天文、数学更是他的爱好,他一向认为古今中外文法理工本应是相通的。 早年金克木对于天文学有特别的兴趣,不仅翻译过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流转的星辰》,以及《通俗天文学》等著作,还发表过天文学的专业文章。上世纪30年代,因为非常欣赏金克木的文学作品,戴望舒写了一首《赠克木》,让他在星辰天空之外,更多看看人间,算是将金克木从天文学中拉回来。不过金克木颇有遗憾,他曾在一篇随笔中感叹:“离地下越来越近,离天上越来越远。”到了老年,金克木的好奇心一点儿没有泯灭,为了一个微积分的问题,他想方设法借来了英文原版的“数学史”。一看登记卡他乐了,半个多世纪来,他是这本书的第二位借阅者,前一位是大数学家江泽涵。 逝世前不久,金克木还让女儿金木婴借来了霍金的专门谈黑洞的天文学作品,他由此回忆起多年前在徐迟家翻译《通俗天文学》的往事,并在电脑中留下了他的遗作——《黑洞亮了——从译泰戈尔诗赠徐迟谈起》。对与徐迟漫长的友情的开端,金先生说他们成为朋友,“不是由于同而是由于不同,越是不同越是谈得有兴味”。金木婴说,尽管性格爱好有所不同,但在终身都不仅对人文科学,而且对自然科学的新事物、新知识有浓厚兴趣这一点上,父亲与徐迟先生是一致的。“父亲说:‘徐迟永远18岁。’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附录:金克木:一位小学毕业生的65种著作本文来源:《低学历的五大师》,张建安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转自:经史博物馆1. 《蝙蝠集》(新诗库,第1 集之4),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6 年出版。2. 《通俗天文学》(美国西蒙• 纽康著,译本),商务印书馆,1938 年出版;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年再版。3. 《流转的星辰》(译作),中华书局,抗战时期出版。4. 《我的童年》(泰戈尔回忆录,译本),商务印书馆,1945 年出版。5. 《云使》(迦梨陀娑诗歌,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出版。6. 《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年出版。7. 《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年出版;1980 年重印。8. 《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文选》(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出版。9. 《伐致诃利三百咏》(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出版。10. 《印度文化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出版。11. 《比较文化论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出版。12. 《印度古诗选》(译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出版。13. 《旧巢痕》(自传体小说),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出版。14. 《难忘的影子》(自传体小说),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出版。15. 《雨雪集》(诗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出版。16. 《天竺旧事》(回忆录),生活 •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出版。17. 《艺术科学丛谈》,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6 年出版。18. 《燕啄春泥》(百家文丛),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年出版。19. 《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出版。20. 《燕口拾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年出版。21. 《文化的解说》,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出版。22. 《回忆录》(附《我的童年》),泰戈尔著,谢冰心、金克木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出版。23. 《印度文化论集》,台湾淑馨出版社,1990 年出版。24. 《书城独白》,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出版。25. 《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出版。26. 《无文探隐:试破文化之谜》,上海三联书店,1991 年出版。27. 《旧学新知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出版。28. 《金克木小品》(名家小品自选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出版。29. 《摩诃婆罗多• 初篇(一—四)》(与赵国华、席必庄等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30. 《说八股》(与启功、张中行合著),中华书局,1994 年出版,2000 年重印。31. 《蜗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32. 《书外长短》(中国名家随笔精品丛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33. 《梵佛探》(当代学者自选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出版。34. 《路边相》(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35. 《文化卮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36. 《末班车》(读译文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年出版。37. 《槛外人语》(禅趣人生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出版。38. 《咫尺天涯应对难》,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年出版。39. 《金克木散文选集》(百花散文书系),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年出版。40. 《评点旧巢痕》(长篇小说附评),文汇出版社,1997 年出版。41. 《开放社会科学》,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出版。42. 《百年投影》(北大未名文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43. 《异域神游心影》(世纪学人文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出版。44. 《少年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出版。45. 《探古新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出版。46. 《庄谐新集》,东方出版社,1998 年出版。47. 《挂剑空垄》(新旧诗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出版。 48. 《梵竺庐集》(三卷:甲卷《梵语文学史》、乙卷《天竺诗文》、丙卷《梵佛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出版。49. 《译匠天缘》(青年读本丛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年出版。50. 《天竺旧事》(青年读本丛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年出版。51. 《孔乙己外传》(小说集附评),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出版。52. 《华梵灵妙:金克木散文精选》,海天出版社,2001 年出版。253. 《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唐季雍译,金克木校,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年第一次出版,1983 年第二次出版。 54. 《书读完了》(文化随笔),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年7 月出版,到2008 年7 月已是第5 次印刷。55. 《人生与学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56. 《文化三书》,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8 年出版。57. 《倒读历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年出版。58. 《文化八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59. 《大家国学• 金克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年出版。60. 《游学生涯》,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8 年出版。61. 《风烛灰:思想的旋律》,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出版62. 《印度文化余论(〈梵竺庐集〉补编)》,学苑出版社,2002 年出版。63. 《中国新诗库:金克木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 年出版。64. 《金克木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4 月出版。共八卷,400 余万字,收录了迄今能找到的金克木的诗文、学术专著、随笔杂感、译文等全部作品。第一卷为诗文集,包括新旧诗集、自传体小说、回忆录;第二、三卷为印度文化及比较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学术作品;第四、五、六卷为随笔杂感;第七、八两卷为翻译作品。各卷内容如下: 第一卷 挂剑空垄 新旧诗集 旧巢痕 评点本 天竺旧事 孔乙己外传 小说集附评 第二卷 甘地论 中印人民友谊史话 梵语文学史 第三卷 印度文化论集 比较文化论集 艺术科学丛谈 第四卷 旧学新知集 燕啄春泥 燕口拾泥 文化的解说 文化猎疑 书城独白 无文探隐 第五卷 金克木小品 八股新论 蜗角古今谈 末班车 书外长短 第六卷 少年时 庄谐新集 风烛灰 杂著 第七卷(译著) 摩诃婆罗多• 初篇(一—四) 印度古诗选 三百咏 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薄伽梵歌》译本序 我的童年 钻石 控诉 血和地毯 三自性论 第八卷(译著) 高卢日尔曼风俗记 海滨别墅与公墓 炮火中的英帝国 通俗天文学 流转的星辰读书学问于身有亲——金克木的生平片段和读书方法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德海
数年前,忘记读一本谁的通信集了,其中有两段话,意思极好,就抄在了本子上:“学问、逻辑是一障,文字是一障,名词是一障,要能于此斩关而过,始得学问于身亲耳。”“你学圣贤之学,能言语于身亲乎?”当时打动我的,就是这个学问、言语的于身有亲。
写《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的过程中,因为很多事若合符节,我就经常想起上面的话。有意思的是,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这个学问的于身有亲,很多时候并非从容的选择,而是环境导致的不得不然。大概是这样吧,耶稣手上的钉痕,不就是不得不然?
试着看几个金克木的成长片段,能看到些什么呢?
金克木(1912年8月14日-2000年8月5日)
壹
金克木,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生于江西万载县,父亲为清朝最末一代县官。金克木出生不久,父亲即去世,他随嫡母、母亲和大嫂不断搬迁,于动荡中完成了最早的教育。
大概因为记事早,不到两岁的金克木,就在记忆中留下了他们母子随嫡母同往安庆的情景:“A城(按,安庆)是个山城,斜靠在山坡上,裸露在长江中来往的轮船上乘客眼里。城里也几乎到处在高地上都可以望见下面滚滚流动的长江。……他一生中第一件储存在记忆中的材料便是长江中的轮船。两岁时,他一听到远远的汽笛声,便要求大人带他到后花园中去,要大人抱他起来望江中的船。这是有一段时间内他的天天必修的功课。”
金克木与母亲合影
上面的引文出自《旧巢痕》,在金克木自己化名写的评语中,这段话后面的点评是:“漂泊天涯从看江船开始,有象征意味。”不知道金克木这里所谓的象征,是说他婴儿期一家人的不断搬迁,还是包括他少年和青年时期更大范围的居无定所,但每一段漂泊,都跟家庭和时代的剧烈变动有关,其中似乎确实有着命运的影子。人大概就是这样吧,无法择地而生,也无法择时而生,恐怕最终都不得不学着爱自己的命运。
金克木这种旧家庭,人口多,且来自不同地域,故而操持着不同方言。三个哥哥说的是寿县话,大嫂说的大概是一种“官话”,“特点是干净,正确,说的句子都像是写下来的。……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跟早年金克木相处更久的母亲和嫡母,也各说不同的话:“我出生时父亲在江西,我的生母是鄱阳湖边人,本来是一口土音土话,改学淮河流域的话。但她所服侍的人,我的嫡母是安庆人,所以她学的安徽话不地道,直到二十几岁到了淮河南岸一住二十年才改说当地话,但还有几个字音仍然只会用仿佛卷着舌头的发音,一直到七十五岁满了离开世界时还没有改过来。”
在一个天然的复杂语言环境里,金克木完成了早期特殊的听、说训练:“我学说话时当然不明白这些语言的区别,只是耳朵里听惯了种种不同的音调,一点不觉得稀奇,以为是平常事。一个字可以有不止一种音,一个意思可以有不同说法,我以为是当然。”本来,学任何东西都是“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可如果一个人天然置身于杂多的环境,没有因比较而生的分别心,则杂多便可能成为某种特殊的专一。后来金克木学多种外语,都能即用即学,即学即会,或许就跟他成长的特殊语言环境有关。
贰
学前阶段,金克木已经完成了传统的开蒙教育,开始背诵“四书”和部分“五经”,并随三哥读新式国文教材,同时学习英文。1920年,金克木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就读,1925年毕业后,从私塾陈夫子受传统训练两年。
《读书·读人·读物——金克木编年录》黄德海撰作家出版社出版
又是传统的背诵,又是新式教材教法,又是私塾训练,又是学习英语,照现在的说法,金克木所受的,似乎是贯通古今、中西兼备的教育,既能上接传统,又能融入现代。只是,这个新旧之间的教育,恐怕并非如想象那般完美无缺,在深入任何一个领域之前,教育只是对懵懂的简单引导而已。甚至,就连所谓私塾的传统训练,我们的理解或许也没那么牢靠。
两年的私塾,学些什么呢?“他先问我读过什么经书。我报过以后,他决定教我《书经》。每天上一段或一篇,只教读,不讲解,书中有注自己看。放学以前,要捧书到老师座位前,放下书本,背对老师,背出来。背不出,轻则受批评,重则打手心,还得继续念,背。……《书经》背完了,没挨过打骂。于是他教《礼记》。这里有些篇比《书经》更‘诘屈聱牙’。我居然也当作咒语背下来了。剩下《春秋左传》,他估计难不倒我,便叫我自己看一部《左绣》。这是专讲文章的。还有《易经》,他不教了,我自己翻阅。”
看起来顺理成章,我们心目中的硕学大儒就是这样一步步学出来的对吧?只是,不要忘了金克木提到的“传统训练”,这是什么呢?“行业训练从作文开始。这本是几个年纪大的学生的事。他忽然出了一个题目:《孙膑减灶破魏论》,要我也作。这在我毫不费事,因为我早就看过《东周列国志》。一篇文惊动了老师。念洋学堂的会写文言,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奖励之余教我念《东莱博议》,要我自己看《古文笔法百篇》,学‘欲抑先扬’‘欲扬先抑’等等,也让我看报,偶尔还评论几句。……老师从来没有系统讲过什么,可是往往用一两句话点醒读书尤其是作诗作文的实用妙诀。”
快乐的老顽童
理想的读书人,不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吗,私塾老师怎么教的是实用妙诀,这把读书当成噉饭的工具了?某种程度上,或许正是如此:“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做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
这两年的传统训练,给金克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我不明白,后来还看不起这种指点。几十年过去,现在想来,我这靠文字吃饭的一生,在艺业上,顺利时是合上了诀窍,坎坷时是违反了要诀。这就是从前社会中书生的行业秘密吧?可说不得”。或许这段话可以打破我们对读书是高雅之事的刻板印象,回到古代学习的具体情景,也就能够意识到,传统所谓的“耕读传家”,非常可能是两项并列的实用技能。
金克木游学生涯中,有很多长短不一的各类文章,很多人觉得够不上十足的学术,偶尔会出语讽刺。那原因,或许就是忘记了,很长一段时间,写文章是金克木的生存手段,是他身上衣、口中食。衣食尚不能保障的时候,要求一个人出手就是思虑周全的学术杰作,大概有些过于苛刻了。更何况,不管任何外在评价,只对具体一个人的读书和写作来说,这样上手即能完成文章的能力,说不定是一种有效的写作训练。
1991年12月,金克木与邓广铭、端木蕻良
叁
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家人送金克木到乡下躲兵灾,从而得识“警钟”(“井中”),始读《新青年》。1928年,经人推荐至寿县三十铺小学任教,同事背讲《共产主义ABC》。
从前面的分析,其实已经不难看出,无论看起来怎样完善的教育,如果没有跟每个人置身的具体结合起来,其实也可能不过是繁复的装饰,或许能唬人,却实在是于身不亲。除此之外,金克木真正独立读书学习的时候,社会已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双重洗礼,时代的文化重心已然转移,只抱着传统经典摇头晃脑,显然已经不足应付。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金克木结识“警钟”,又叫“井中”,遇到了跟时代同步的契机。
这个相识故事,听起来真像一个传奇。因为躲兵灾避难乡下,金克木遇到在城里读教会中学的警钟,倾盖如故,相与谈笑。“有一天,我把书架上的五大本厚书搬下来看。原来是《新青年》一至五卷的合订本,他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他马上翻出‘王敬轩’的那封抗议信和对他的反驳信给我看。我看了没几行就忍不住笑,于是一本又一本借回去从头到尾翻阅。……我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这五卷书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了,陆续和警钟辩论完了,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
上面的话或许还不够明确,所谓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好像没有具体的说明。《旧学新知集》序里,更为具体地谈论过这件事,让我们对这个转变过程,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因为此前乱读书)我成了一个书摊子,成不了专门‘气候’。我好像苍蝇在玻璃窗上钻,只能碰得昏天黑地。不料终于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洞,竟飞了出来。那是小学毕业后的一九二六年,我看到了两部大书。一是厚厚的五大本《新青年》合订本,一是四本《中山全书》。这照亮了我零星看过的《小说月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随后又看到了创造社的《洪水》和小本子的《中国青年》。我仿佛《孟子》中说的陈良之徒陈相遇见了许行那样‘大悦’,要‘尽弃其所学而学焉’。”
这段话跟上面那段话,时间记忆上有点参差,提到的书也有增减,但过程非常清晰。这个过程,说白了,就是时代的于身有亲。所谓苍蝇在玻璃窗上钻,不就是所读所学没有归处,因而身在时代之外?从窗户洞里飞出去,就是读了《新青年》和《中山全书》之后,此前杂乱的学问奔赴于时代的边际,汹涌的涡流一变而为浩荡的长河,跃跃若新发于硎。
当然,这不是金克木跟时代关系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这只是他不断调整自己与时代关系的一个侧面。重要的是,有了这段经历,金克木打开了此前封闭的信息交换系统,能够随时更新自己与时代的关系。从这一节开头提到的同事背讲《共产主义ABC》,我们大体也能感受到,社会表层之下潜流涌动,更新的时代潮声,已经在大地上响起。
肆
1930年,金克木离家至北平,因无缘得进正规大学,只能勉力游学,徘徊于高等学府之间,进出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在此期间,金克木泛览书刊,自学外语,广交朋友,在切磋琢磨中眼界大开。1935年,经朋友介绍至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得师友指点,获无言之教。
1992年,金克木与启功在北师大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也没有任何一个家庭,会为某个人准备好所有的条件才让他踏上社会。金克木离家去北平,原本打算找个机会上大学,却因为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和家庭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只能不时去高等学府听几节课,然后读所谓“家庭大学”。这个金克木称谓的“家庭大学”,应该来源于他当时读的英文“家庭大学丛书”,当然,包括他进入“私人教授英文”和“私人教授世界语”两处别人的家庭,也包括他逛的旧书店和书摊,最重要的,则是他出入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图书馆。
如果没有身历过同样的困窘,我们大概很难体会交不上房租、穿不上棉袍、吃不上三顿饭的金克木,为什么会觉得图书馆是他最亲切的“家庭大学”。我们不妨设想,在寒冷的冬天,衣着单薄的金克木,偶然进入一家生有火炉的图书馆:“我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馆中书不多,但足够我看的。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金克木与孙女一起
困厄之时,有这样的容留之地可以安心读书,也就怪不得金克木一直觉得,那些普普通通的小图书馆,跟自己的情分算得上“风义兼师友”:“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不是人而是从前的图书馆。那些不为官不为商,只为穷学生服务的公共图书馆,不知道现在还有几所?”后来流徙各地,金克木也是“每到一地,有可能就去找当地图书馆,好像找老朋友”。更重要的是,金克木从图书馆的读书中,养成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我看书如同见活人,读书如听师友谈话”。这个从图书馆习得的奇特读书法,能把已在某种意义上风干的书复活,重新拥有生动的面容,并在深处通向他后来提出的“读书·读人·读物”,有心人或可深思。
除了这些普通的图书馆,金克木跟北京大学图书馆可以说缘分深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足一年的时间里,金克木管借书还书,就此开阔了眼界,结交了朋友,更新了学习方式,可谓收获颇丰:“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更重要的是,这段时间里,金克木领悟到一种读书法,“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
把这方法移用到读书,不妨称为“望气读书法”。学会了这个方法,可以一眼而能知书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并能迅速判断其格局和价值。在当下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这种读书法或许更应该重视。
伍
1938年,金克木到香港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始执教于湖南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和湖南大学,1941年至印度加尔各答中文报纸《印度日报》任编辑,1943年辞职,于佛教圣地鹿野苑随憍赏弥老人钻研印度古典。
1946年7月,在印度加尔各答校梵本《集论》
这段时间的经历,乍看起来非常惊艳,仿佛一个人拥有极大的选择空间,随时随地可以潇洒自如地展现自己的能力。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无论是到香港,还是在湖南,还是去印度,都是因为日本侵华造成的困顿时局,导致金克木不得不辗转求生。拿到香港为例,金克木说那“实在无路可走”,“是‘逃难’去的,是去找饭吃的”,根本没什么潇洒可言。
不过,虽然在如此被动的情形中,金克木却也没有一蹶不振,或者怨天尤人,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势,迅速调整自己的学习和读书策略。就说到香港吧,原来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只是朋友介绍去见萨空了,萨空了见他拿着一本英文书,便让他去报社翻译外电:“那晚上他只对我说了一下美联社的‘原电’的种种简化说法怎么读,路透社的和报上一样就不必讲了。说完便匆匆走了……通讯社陆续来电讯,我陆续译出。快到半夜,他来了,翻看一下,提笔就编,叫我次晚再来。第二天晚上他对我说,他实在忙不过来,又找不到人,要我连译带编这一版国际新闻(约相当于《新民晚报》半版)。桌上有铅字号样本,还有报纸做样子。说完又匆匆走了。”
1946年10月,金克木与沈仲章、崔明奇、吴晓铃在上海虹口公园。
就这样,金克木居然很快就适应了报社的工作节奏,并对这份工作胜任愉快。有意思的是,这段经历不只是能够挣钱养家,还让他锤炼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一年(没有休息日)无形中我受到了严格的训练,练出了功夫,在猛然拥来的材料堆积中怎么争分夺秒迅速一眼望出要点,决定轻重,计算长短,组织编排,而且笔下不停(《立报》要求篇幅小容量大必须重写,规定只用手写稿),不能等排字工人催,不能让总编辑打回来重作。”这种不依赖环境完善,而是在复杂情形中迅速调整,并辨认出重点信息的能力,我觉得是金克木读书甚至做事方法的核心,值得好好思量——世上哪里会有一种情形,是准备好了所有条件才让我们去读书、做事的呢?
体会到这个方法,后面的到湖南教书和钻研印度古典,甚至金克木其他生平片段,就不用一一介绍了,因为都可以看成在不完备条件下迅速做出决断的例子。就像他自己说的,香港报社学会的那套功夫,“后来我在印度鹿野苑读汉译佛教经典时又用上了”,后来也多次用上。
或许,读书和学习就是这么一回事,永远不要期盼有人铺好了全部的阶梯,也永远不要期待此后会有更充分的准备,而是要在每一个条件不完备的环境里,找出适合自己的一条路。这样的方式,因为时时于身有亲,即使走得趔趔趄趄吧,也自有一种特殊的风姿。
(本文图片来源:金木婴)
(责编:孙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