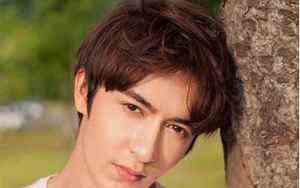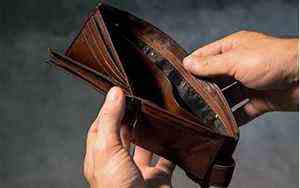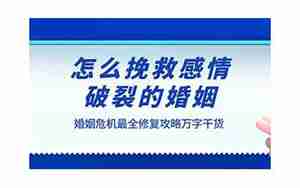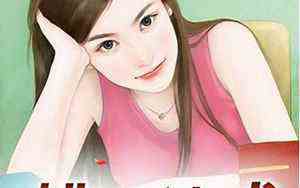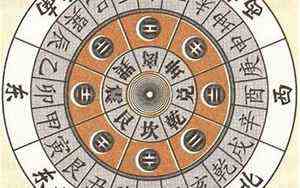“脍炙人口”易伤身:历史上生食淡水鱼而亡的典故
近日,关于虹鳟之于三文鱼,究竟算是同一概念抑或指鹿为马的争论又起。作为淡水鱼的虹鳟到底能不能做成生鱼片生吃,固然现今仍然是众说纷纭;回顾淡水鱼生在中国历史由兴而衰的过程,或可以给今日的我们一个警醒。
致命的诱惑
有个成语叫做“脍炙人口”,意思是说,生切肉与烤肉受众人喜欢。所谓“脍”,按照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的解释,“细切肉也……从肉,会声”。生鱼片在古代中国正是属于“脍”的一种。早在先秦时期,鱼脍就是当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菜肴。《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说,“子胥归吴,吴王闻三师将至,治鱼为鲙(脍)。”这说明吴王阖闾为了迎接攻楚凯旋归来的军队,就是用鱼脍作为犒赏。昔日中国人食脍的盛况,从今天“刺身”在日本大为流行上大约也可见一斑。
三文鱼刺身
不过,与四面环海因而容易获取海鱼作为刺身原料的日本不同,古代中国人所食用的鱼脍,大抵来自内河之中的淡水鱼,一般选肉较厚、刺较少的鱼做原料。譬如汉魏南北朝时重视鲤鱼、鲈鱼,唐代青睐鲫鱼、鲂鱼——这是因为李唐皇室讳“鲤(李)”字。从文献记载看来,即使是深处内陆的关中地区,当时买鱼作脍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官僚士大夫中颇有些人不仅喜食鱼脍,而且还会亲手做,比如初唐太子李建成的部属唐俭、赵元楷等人即曾自夸善于作脍,而太子也不以为奇。
问题在于,虽然《论语》早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说,品尝淡水鱼生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却实在是一种危险的口福——虽不至于如食用河豚一般有立时毙命之虞,却也不见得总能太平无事。
在东汉末年的徐州政治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在《三国演义》里为曹操剿灭吕布出力极多的陈登(字元龙)大概算得上是中国历史第一位因食用生鱼片罹患恶疾的知名人物。担任广陵太守时的陈登突然患上了怪病,觉得胸闷,脸色发红,没有食欲。他找了好多医生治病都无效,后来寻到神医华陀,诊断为“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华佗为其开药,陈登吃下去以后“吐出二升许虫,赤,皆动,半身是生鱼鲙也”。也就是说,陈登正是因为嗜食生鱼而得了肠道传染病及寄生虫一类的重病。病愈之后,华陀叮嘱他不能再吃生鱼,岂料陈登病愈后,嘴巴又馋了起来,终因不遵医嘱贪食生鱼,旧病复发而一命呜呼。
《三国演义》连环画中的陈登与吕布
实际上,对于食用生鱼可能致病这一点,古人并非毫无认识。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就指出,“食脍,饮奶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疟”。几百年之后的南北朝时期,陶弘景也警告食脍可能有害,流行病刚痊愈的人不能吃,否则会引起拉肚子。
不过,很显然,直到隋唐时期,众多吃货并没有将这一告诫放在心上。因为贪食鱼脍导致得病的人实在是史不绝书。宋代《太平广记》记载,唐代永徽年间(公元650-655年),有位叫崔爽的仁兄,吃食生鱼上瘾,每次竟要“三斗乃足”,直到后来口中吐出一状如蛤蟆的怪物,才吓得“不复能食脍矣”。《太平御览》则引用《明皇杂录》记载说,邢州人和璞曾预测房棺会因食鱼脍而死,这个预测后来被证实是准确的(否则也不会记下这个故事)。而另一本宋代笔记《北梦琐言》同样记载了有位少年因食脍太多而致眼花不见的病例。
宋代以后,随着食用生鱼引发的病患越来越多,人们对于脍的看法开始转变。北宋大文豪兼大美食家苏东坡对于生鱼片就抱有一定的警惕。他在《东坡志林》卷一里说,“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可见宋人认为患红眼病时不能吃生鱼片,否则会加重病情。到了南宋,哲学家、养生家真德秀更是呼吁,吃生鱼脍专门招引消化系统疾病,应跟“自死”的牲口一样,划入禁食之列。社会上的这种对于鱼脍的“差评”,想来应该是其晚近之后逐渐式微,淡出中国的主流餐桌的重要原因。
苏东坡
防不胜防
人们不禁要问,古人食用鱼脍容易患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古代的烹饪技术不过关呢?恐怕也不见得。
关于鱼脍的具体做法,古籍中不乏记载。大体言之,古时作脍大概有以下几项技术要求:是作脍的鱼一般要求鲜活,这样做成的脍才味道鲜美;二是刀功要细致,切出的脍要薄而细;三是作脍食脍要调拌蒜、姜、芥末、酱、醋等香辛料和调味品。这与近代黄遵宪在日本看到的制作刺身的景象几无二致——“(日本人)喜食脍,尤善作脍,以生鱼聂而切之,以初出水泼刺者去其皮剑,洗其血鲜,细剑指为片,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姜芥之外,具染而已。”
刺身
不难发现,伴食生鱼片的佐料大多滋味辛香。这除了可以带来口感上的刺激之外,很难说古人没有消毒杀菌的考虑。早在《礼记·内则》里就说,“脍,春用葱,秋用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葱皆能杀鱼肉毒,食品所不可阙也”、芥末“研末泡过为芥酱,以侑肉食,辛香可爱”,兼具有解毒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生鱼有腥味,葱和芥末的味道辛辣,既可遮盖其味,又具杀毒抑菌作用,所以南宋大儒朱熹指出,“如鱼脍不得芥酱……则不食,谓其不备或伤人也。”《后汉书》也记载了方士左慈用法术为曹操钓出淞江鲈鱼的异事,随后鲈鱼就被当场做成鱼脍,曹操却说,“恨无蜀中生姜”。说明东汉古人也用生姜佐食,这自然也是为了去腥杀菌之用。
刺身佐餐的芥末与酱油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辽金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也有吃生鱼的习惯,“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生、獐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与中原人食用鱼脍时用芥酱的习惯类似,女真人吃生鱼时也辅之以“胡荽(香菜)、芜荑酱、卤汁”之类佐料。其目的就是为了消毒杀虫。有金代四大名医之首美誉的张从正在《儒门事亲》记载,“胡荽、芜荑酱、卤汁”“皆能杀九虫”;所以金人所食生鱼虽是“虫之萌”,然而“不生虫”。
到了明代,鱼脍进一步出现了用醋姜生拌的吃法。明初的刘基(刘伯温)在《多能鄙事》里总结当时的鱼脍做法,“鱼不拘大小,以鲜活为上。去头尾、肚皮,薄切摊白纸上。晾片时,细切如丝”,这与过去的工序并无太大区别。但接下来,刘基又说,要用“姜丝拌鱼,入碟杂以生菜、胡荽、芥、辣、醋浇。”除了这种生拌方法,还有用蒜、虀、姜、醋生拌的鱼脍。《本草纲目》就提出要“沃以蒜虀、姜醋,五味食之。”这些佐料都具有杀菌作用,而且姜性辛热,无疑都是古人食脍的经验总结。
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了古人既然小心翼翼地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为何食用鱼脍患病者仍旧是屡见不鲜呢?看起来只有一种解释,寄生在淡水鱼体内的寄生虫实在太过防不胜防,令品尝美食变成了危险的“轮盘赌”游戏。如此一来,合乎理智的选择自然就是敬而远之了。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非常明确地警告国人:“肉未停冷,动性犹存。旋烹不熟,食犹害人。况鱼鲙肉生,损人犹甚。为症瘕,为痼疾,为奇病,不可不知!”这不啻在传统医学(中医)上为淡水鱼制成的生鱼片宣判了“死刑”。
《本草纲目》
岭南的活化石
于是,到清代之后,中国大部分地方的鱼脍不再采用生吃之法。改成熟食之后,经过高温的蒸煮,鱼身上所携带的寄生虫便无处藏身,从而解决了生食鱼脍带来的“安全隐患”。但在少数地方,古老的生鱼脍仍然顽强延续了下来,最明显的就是岭南地区——这从过去广东的一句俗语“夏至狗肉,冬至鱼生”中便可见一斑。所谓“鱼生”,按照民国初期的《清稗类钞》的说法,就是“生鱼脍”。岭南人食用的鱼生,“以嘉鱼,鰽鱼,以黄鱼、以青鲚、以雪魿、以鲥、以鲈、以鲩”,显而易见其中仍然有着大量的淡水鱼类。
近现代的两广地区,堪称古老的“(淡水)鱼脍”如活化石一般存在。明朝的徐霞客在游历到广西地区时,就发现当地“乃取巨鱼细切为脍,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现代广西的汉族、壮族和侗族都延续了食用“鱼生”的习俗。《广西通志·民俗志》记载,“生鱼片,壮、汉、苗、侗等民族的传统菜肴,先用三至五斤重的鲜活草鱼或鲤鱼,刮鱼鳞洗干净,除去内脏,取出骨头,将肉切成片,然后拌上糖、醋、酒、盐、姜、蒜、酱油、花生油等,略为腌制,即可食。其味道鲜嫩香甜。”《上林县志》也说:“上林汉、壮群众遇贵客来临……视‘鱼生’为上品佳肴。”至于今天隶属于广西首府南宁的横县人更是将横县鱼生称作当地的“县菜”。清代《横州志》就记载:“剖活鱼细切,备辛香、蔬、酶下箸拌食,曰‘鱼生’,胜于烹者。”
横县鱼生
只可惜,“鱼生”固然美味,风险依旧巨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很多淡水鱼中有一种非常顽固的寄生虫——肝吸虫,多达30多种淡水鱼可成为肝吸虫幼虫的中间宿主。生食或食用未充分加热的含有肝吸虫的鱼后,其成虫寄生于人的肝脏、胆管内则会导致肝吸虫病。这种虫子可以在人体内生存长达二三十年。而且,被感染后不易察觉。偏偏肝吸虫的发病率与淡水鱼“鱼生”的流行度呈正相关——广西横县正是肝吸虫病的高发区。据广西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广西横县华枝睾吸虫病流行情况调查》统计,仅以一次粪检人群的华枝睾吸虫病(肝吸虫病)的感染率,该县料平村为67.8%、古同村为55.8%,户感染率更是两地都在96%以上,令人不寒而栗。
无独有偶,广东省佛山市的顺德区周边,同样流行蘸着由葱、花生、大蒜、辣椒、胡椒、酱油和醋做成的调味汁,吃着有草鱼等淡水鱼类制成的“鱼生”。虽然当地人认为,制作“鱼生”的鱼肉是顶新鲜的,把肉割下时鱼身还会跳动,鲜鱼就不会腥;而在花生油里泡一泡后据说可以杀菌,再加上点酸辣佐料或喝口烧酒,即使有寄生虫也是“插翅难逃”……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想象的一般美好,在2015年的一次抽样调查中,864位顺德市民肝吸虫的感染率竟高达18.5%。换句话说,几乎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中招”,如此之高的患病率,实在可以称之为“舍命吃‘鱼生’”了。
顺德鱼生
从岭南地区这一“活化石”的情况不难得出结论:淡水生鱼片在历史演进中逐渐被淘汰的命运,实在是与其糟糕的“安全系数”难脱干系的。“脍炙人口”终究只是一句已然凝固在历史中的成语罢了,生食淡水鱼,实在是要三思而后行。
参考文献:
毋燕燕:《关于“脍”的历史文化考察 兼及生鱼片的起源问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9月
王若涵:《脍不厌细:中国古人食脍习俗小考》,《文史杂志》,2010年第6期
在广西吃过酸粥,做梦都在孕育生命
大米是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首选主食,但只有在广西它才被逼出了真本事。
来到崇左扶绥,只要你有一颗求知的心,当地朋友将带你品味一下那些米粒中蕴含的伟力。
能在酸粥洗礼下保持冷静的人,才能稳坐食物链顶端的王座,豆汁儿在它面前,最多就是碗白开水。
当一个人的视线被吸入面前那片白色深渊,就会迷失在孕育生命的轮回中,亚热带骄阳被它完整反射,似乎又积满了岁月的风霜。
第一次见到它开盖时,我短暂的失明了,就像雪盲。
作为发酵界的霸主级选手,酸粥虽然名字还叫粥,但一般的粥跟它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它宛如一件来自远古的法器,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把无数命运封进了坛里。
直到你越靠越近,亲眼目睹粥面波光粼粼,就会明白为什么它总能带来纯粹又崭新的生命体验了。
那是真正有生命的粥,会动。
这片土地显然留存着神话时代的记忆,当地人在炼金术方面的造诣早就达到大师级水准,他们用点石成金的秘法点化了大米。
任何人都能在这里重新发现人类食谱里隐藏的奇迹,平时你能见到的那些最旺盛的生命力,也许就藏在扶绥朋友家里。
有人说这碗粥已经突破了营养学上限,完成从碳水化合物到动物蛋白的深度转化,接触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它。
比起食物,它更像是某位仙人飞升之前留下的遗物。
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劳动人民干不成的事,生活要有进取精神,一切边界都是用来打破的。只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这可能更容易引发一次心灵震荡。
先不考虑入口的问题,面对坛子里从容的舞步,即便是广西其他地方的朋友,也会重新审视“生猛”这个词的具体含义。
此时粥和蛊的区别可能也不是太大
根据懂行的朋友介绍,不存在“做酸粥”这种说法,只能说“养酸粥”,那是种基本的敬意。
他们早已驯化了虫族,在高手心中,有虫的酸粥就是完全体状态。
“事实上不止扶绥,苏圩、宁明、龙洲、凭祥、上思等地都有这种吃法”
只有看透事物本质的老饕才能品鉴超然物外的珍馐,他们知道,要进入食物链中的这种等级,得在抱住想象力的同时解放天性。
没吃过酸粥的人看到它可能会觉得有点头晕,吃过酸粥的人,看到它只会勾起心中最原始的悸动。
如果再出现一盘白切鸭, 基本就算是抵达了人间仙境。
“这是最极品的蘸水,也是最下饭的菜,开盖时会有点酒味,贴近闻才是酸味。”
“酸粥蘸白切鸭是一绝,而酸粥猪肚完全可以再次打开一个新世界。”
如果说辣给一道菜附魔了暴击,那么酸就是增加了穿透力。
有人形容它入口的感觉就像从嘴巴直接给心房开了一道口子,再绝情的人也会被酸爽到灵台失守。
而酸粥是绝对包容的,传说还存在吃薯条也要蘸酸粥的狠人。
酸粥鱼生应该属于双倍冲击
“酸粥下锅加酱油、蚝油、白糖、盐和一点点米酒,然后不停搅拌,出锅香到厨房爆炸。”
“可以用紫苏加辣椒炒,也可以加银米鱼,炒好之后舀到饭里,吃起来酸辣口味很过瘾。”
“你想加什么炒都行,它可以是主菜也可以是配菜,甚至能用来腌制灯笼椒。吃起来不是柠檬那种酸,是种微妙的发酵酸香,炒一次最少下三大碗饭。”
“钦州乡村小孩,奶奶经常用酸粥来炒ong菜(空心菜),很好吃”
很难说清食客对它的赞美,但可以肯定的是,被酸粥加持过的东西,都会变成实际意义上的酸爽炸弹。
从很多社交平台中都可以发现那些溢出屏幕的爱意,在他们心中世间没有比它更值得回味的东西了。
有位南宁苏圩的朋友讲,出门在外想吃一口酸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是在本地,养酸粥也要像养宠物一样细致,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一滩死粥。
“想让粥是活的,就要用心培育,里面可不是普通的虫。”
“它们只吃米饭,还得是冷饭,最好是比较硬的,千万不能粘油盐,不然虫会死。”
在他的描述中,养酸粥的标准很难量化,或者说全凭手感。
发酵时间要随着季节调整,温度变化也会造成口感上的差异,过程中还要专门留一点缝隙让空气流通,过于密封反而会失败。
其中最关键的是需要使用原始菌种,几乎只在本地人之间流传。
也就是说至今养酸粥使用的虫和菌,仍然是过去传承下来的那个族群,好比每一坛新酸粥都继承着相同的遗传基因。
虫界真正的老炮儿家族
“把酸粥种子放进去,接着放新米饭,搅拌一下,再放酸粥种子,再加米饭,如此循环。”
“最后在顶上盖一层酸粥,太稠的话加一点矿泉水,这就算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养粥征程。”
“夏天一周多,冬天一个月,虫和菌就会帮助米完成升华。”
“当然也要注意发酵过程中不能被其他虫污染,不然就真生蛆了。”
“家里长辈说只见蠕动不见虫,才是精品。”
“养好一碗酸粥也是很不容易的”
这就相当于主动给米粥注入了新的生命形式,此时粥里是米,但坛子里的东西又确实需要养活,在养成之后它还是粥。
酸粥虽然是死的,但它永远活着。
很可惜薛定谔当年没吃过这种狠货
也许正是因为多层次的密切传承关系,扶绥酸粥至今仍是当地的家常菜,并且早在多年前就成为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对于外地人来说,单从养育方法上来看,它仍然处于黑暗料理世界的领主地位。
毕竟连传承人本人,在人生第一次看到它时也陷入了一阵思考。
视觉冲击总是抵不过舌尖上的诱惑,之后她都带着酸粥上过电视了
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中记录,酸粥含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双歧菌,其功能与酸醋、酸奶、陈醋相似,可以增进食欲,疏通血管,降低血压。
也有研究表明酸粥中含有维生素C,但大米本身是不含的,其中其他维生素的含量还要超过大米,大概率是由微生物发酵导致。
而酸粥里的虫并不是蛆,其实是一种名为醋鳗的无脊椎动物,也被称为醋线虫,主要在醋里生活,但会使醋产生特别的臭味。
“很多醋的酿造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醋鳗,出厂前会被清理过滤掉。”
一些公开资料显示,醋鳗属于线虫类,寿命长达10个月,繁殖迅速,四十世同堂都属于基础操作,但温度超过44℃以上就会死亡。
同时它还是鱼苗的优质饲料,富含丰富蛋白质。
纪录片《隐形世界》中也有过对醋线虫的介绍
可以说一碗酸粥是由多方势力共同打造而成的,里面有菌群,有线虫,有大米,当地人似乎早已和它们之间产生心照不宣的默契。
它的起源成谜,也许在那些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里,它也完成过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实西北地区也有叫酸粥的食物,以糜米、江米、大米、小米等谷物加水发酵,只需一两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没人知道第一份酸粥是如何产生的,但人们显然延续了一个益生菌帝国,文化和味觉记忆相互依附,“粥种”就像是可以传家的精神寄托。
如今在广西都能吃到一整套的酸粥宴了。
当地人民总是热情好客,客人来了有喝不完的米酒,吃不完的鸡鸭鱼肉。
他们要是拿出酸粥,本身就是对你最热情的欢迎仪式。
就像一位扶绥土著所说,时间是有味道的,那是他心中最好的酸味。
-
资料参考:
《崇左呐莱》之酸粥道——崇左电视台
广西崇左特色美食——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
醋线虫——中国大百科全书
食用鱼生感染肝吸虫风险大 成虫潜伏期可长达二三十年
科普【食用鱼生感染肝吸虫风险大 成虫潜伏期可长达二三十年!】据统计,我国肝吸虫流行区平均感染率为2.4%,而广东地区(尤其番禺、顺德等地)由于饮食习惯,喜欢吃鱼生,感染率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达16.4%。此外,某些地区在鱼塘上盖厕所,也加大了寄生虫进入鱼体内的可能性。感染肝吸虫后,是否发病及严重程度取决于寄生在胆管中的成虫数量,轻者无临床症状,重者表现为急性发热、腹痛、胆道感染,不及时干预,有进展成为肝纤维、肝硬化甚至肝癌的风险。而且,肝吸虫病的潜伏期较长,从食用受污染的食物到出现疾病症状往往间隔时间较长,因此一开始会归因于“急性胃肠炎”。肝吸虫成虫在人体内寄生可达20-30年,等到肝脏出问题了,一检查才发现。(via 健康有约)
来源: 广东1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