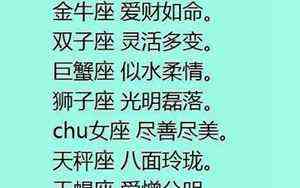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回不去的故乡之:破相
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都留有几块疤痕,或被摔的,或被镰刀割的,或被开水烫的,或被伙伴打的,或长疖子留下的,这是出身的一种标志,女孩也不例外。
我曾经和两个农村女孩谈过恋爱,她们脸上皮肤洁白细嫩,但身上某处都留有疤痕。爱美自尊的她们总在被发现疤痕那刹那花容失色。我就轻轻地抚摸她们的疤痕,轻言细语地说:我爱你,包括你的一切,爱你的缺陷超过爱你的优点。
那一刻,她们感动得眉眼含泪,柔情似水,像巧克力在烈日下慢慢融化。
我身上有很多疤痕,腿上,胳膊上都历历可数。最明显的是脸上也有两块。脸上有疤,俗称破相。这对爱美的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经常在电视里看武侠小说,看到破相女子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找一块黑纱,把脸蒙起来,只露出两只黝黑发亮的美丽眼睛,顿添神秘美感,让人浮想联翩。
我是一个破相之人,脸上的两块疤痕,照镜子的时候,都能清楚地看到。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爱照镜子,又怕照镜子。爱照镜子,是盼望奇迹出现,期待一觉醒来,疤痕突然消失不见了,哪怕变小了;怕照镜子,是因为我知道这种奇迹是不会出现的。照镜子时,第一个闯入眼帘的,不是那对浓眉大眼,不是那张堂堂正正的国字脸,而是脸上那两块疤痕——尽管两块疤痕在脸上占的比例并不大。
脸上的两块疤痕,曾让我饱受打击,痛不欲生,而且老担心前途受到牵连——同村一个女孩,考上了师范大学,体检时,就是因为脸上有一块疤痕,就让学校退档了,我怕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现在,我已经年过不惑,经历了沧桑,对脸上两块疤痕,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这两块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时代在我身上做下的记号,是上帝对我的恩赐。
一块疤痕横在两只眼睛之间的鼻梁凹陷处,是一岁多的时候留下的。
当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劳动,奶奶一个人在照看姐姐,哥哥,我,三个孩子,手忙脚乱的。姐六岁,哥三岁,正是调皮的年纪,到处乱跑,奶奶的主要力都放在他俩身上。
我被放在木制的摇篮车里。一岁多,也是喜欢到处乱动乱爬的年纪。不知道是因为摇篮车禁锢了我的自由,还是摇篮车外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挣扎着从摇篮车里爬了出来,在站在摇篮车上那一刻,车倾覆了,我面朝下,重重地摔了下来,鼻梁正好磕在石头做成的门槛边沿,细嫩的皮肉和骨头抗不过坚硬锐利的石头,我的鼻梁被切成两截,血如泉涌。
母亲闻讯赶回来,帮我把断裂的鼻梁用手捏在一起,也没有去医院——当年穷得也没有那个条件。小命是捡回来了,但疤痕就此留了下来。那道疤痕一直随着我成长而成长。当年鼻子小小的,疤痕是横断面,现在鼻子长大了,疤痕仍是横跨过鼻梁。
现在小孩,是几代人的掌中宝,生怕磕着碰着。我们那时候,两三岁就没人管了。再大一点,父母出工,把你反锁在家,到处乱爬。渴了,没人倒水;饿了,没人管饭;病了,没人送医院;拉屎了,没人擦屁股。感冒之类,能拖则拖,不能拖了,父母找些草药喂你吃下,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看医生。
大舅三个女儿,小时候生病,无钱看医,半年内相继夭折。一个儿子,值钱一点,拖不下去了,抱进医院。病是好了,可落下了耳聋后遗症。比起夭折的那些农村孩子,能够活下来,就算幸运了,一两块疤痕算什么?
另一块疤痕是五岁那年留下的,在左脸中央。
那年秋天特别苦,记忆中永远处于饥饿状态。生产队的甘蔗大丰收,熬出了一块块又大又方的蔗糖。生产队征集劳动力外出卖糖。卖糖的,工分比跟随生产队出工的高。为挣多几个工分,父亲报名要了一担蔗糖。蔗糖有多重,生产队都是称了的,前后重量要对得上。否则,会扣工分。所以,尽管那晚家里有两箩筐蔗糖,但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落,却没有被赏赐一点点。父亲把那担蔗糖放在他们的房子里管理着,我们几个流了一晚上的口水,下巴处的被单被弄得湿漉漉的,好大一片。
第二天清早,哥姐上学去了,我还在吃饭。父亲挑起蔗糖,跨过门槛,准备出去卖蔗糖了。看着父亲要走,我的心都碎了——我确实太想得到一块蔗糖尝尝,哪怕只有指甲那么大小。
在父亲出门那一刻,我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但被脚下的门槛绊倒了。当时我手里端着碗,嘴里含着筷子——仿佛那筷子就是蔗糖。结果一根筷子折断,一根筷子从嘴里刺破脸颊,钻了出来,一半留在嘴里,一半露在脸外。
这件事弄得一个家庭差点分崩离析。母亲很伤心,带着我回了外婆家,半年没有回来,非要和父亲离婚不可——在母亲看来,父亲没有人情,儿子的份量连 一块手指大的蔗 糖都不如。
伤好后,筷子刺破的那边脸留下了一道疤痕。
两块疤痕,尽管不大,可由于生长的地方不对,损害了我的光辉形象,也在心里留下阴影。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情窦初开的中学和大学,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心理障碍。从小到大,我在班上的成绩是很不错的,但那两块疤痕让我非常自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在心仪的女生面前,尽管自己长得并不丑。
我很想和别人一样,有一张光洁的脸蛋,意气风发,洒满青春阳光,不用躲躲闪闪,不用在意别人的目光——甚至有时候,别人看我一眼,我就下意识地以为他是冲着我脸上的疤痕来的。这两块疤痕助长了我的自卑,学生时代,我静静地坐在被人遗忘的角落,不敢抬头,不敢回答问题,不敢看别人一眼,甚至不敢看黑板。课堂内外,我的眼睛始终落在书本上——在书本上花费的功夫多,成绩自然好,也算是没有自暴自弃。
我也想过一些办法来掩饰那两块让我烦恼不堪的疤痕。首先是像女孩子那样买回擦脸用的什么霜,希望借霜来掩盖。霜是白的,脸是黑的,擦霜后,疤痕是不那么明显了,可弄得一张脸黑白分明,比疤痕显现时更难看,只好作罢。后来想到戴眼镜。镜框边沿和连接两个镜框的眼镜鼻梁刚好把两块疤痕遮住了。起初我的眼睛并不近视,家里也没有近视遗传,戴上眼镜,我就慢慢地习惯了它,从假性近视演变成高度近视了。我家兄弟姐妹四个人,除了我,都不是近视眼——为遮掩那两块疤痕,我牲牺了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记得高中,班上有位漂亮女孩喜欢我,有事没事找我。但因为害怕她看到我脸上躲在镜片后的疤痕,我始终不敢抬头看她一眼。我的自卑让她很无奈,吃的闭门羹多了,她就不和我来往了,后来她转学了。
走的那天,她塞给我一封信,大致意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彼此喜欢,但都是自卑的人,在我漂亮的外表前,你自卑脸上的疤痕;在你优异的成绩前,我自卑自己的平庸。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逃离,希望你我都能从作茧自缚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天地,也希望下一个喜欢你的人不要像我,那样辛苦,那样无助。
那封信,对我心理影响很大。晚上躲在被窝里,流了一晚上的泪。那封信,启发了我,也给了我自信。第二天,我摘下眼镜,勇敢地迎着别人的目光,与人对视;勇敢地回答老师的问题。后来由于高中学习用功了,没有眼镜还真不行,不得不重新戴上眼镜。
但那次感情经历,真让我破茧而出,从自我修砌的阴暗房子中走了出来,不再为脸上有疤自卑。
上了大学,换了一个环境。很多同学都是城里人,细皮嫩肉,光洁如玉,且聪明伶俐,见多识广。在他们面前,我还真有些自卑。但这种自卑,已经不是那两块疤痕带来的了,而是知识能力,品格修养。我努力完善,希望出类拔萃,至少不要离他们太远。
四年大学,我确实做到了,成为所在专业的风云人物。再照镜子,读着脸上那两道疤痕,我已经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的珍惜。
后来参加工作,也看到一些广告,说能治愈疤痕,有时候也有点儿心动,毕竟有瑕的玉与无瑕的玉还是有区别。但只是想想,并没付诸行动。
那两块疤痕,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 有它们,我是完整的; 没它们,我才是残缺的。 我已经习惯了,有一天真没有它们了,我还真不习惯了。 没有了,再找回来,就不容易了。 何况现在没人再在意我脸上的疤痕了——记得有段感情,那个女生摘下我的眼镜,轻轻地吻在那疤痕上,那感觉至今还在,让我感动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