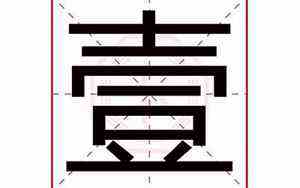阐教十二金仙的杀劫为何物?究竟是自己被杀还是杀别人?
姜子牙在拜在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门下修道。
本来这一切都好好的,可有一天,元始天尊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子牙小徒,你来我昆仑山修道,到如今已经整整四十载,为师观你无缘仙道,而如今周武当兴,为师又有封神任务在身,你与为师代劳封神,辅佐人间明君,享受人间富贵去吧!
这一下把姜子牙惊的神魂颠倒,哀声说,师傅,我不想下山,我就想守在您老身边!
元始又说道,这都是天意,你必须下山!
姜子牙无奈唉声叹气的下山了!
这是封神演义原文第十五回里描述的情节,只不过小刘把他翻译的更白话了一些。
在十五回里,原文又描述了封神大战的起因,其中有一点,看原文中描述,话说昆仑山玉虚宫掌阐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杀罚临身,故此闭宫止讲。
可以说,封神大战的起因有一点便是阐教十二金仙的杀劫,而十二金仙要完成杀劫,必须得天下大乱,如此才好浑水摸鱼,悄无声息的完成自己的杀劫!
在此看来,这十二金仙的杀劫便是杀人,是杀别人,可不是被别人杀!
但很多人都说,十二金仙的杀劫也包括自己被杀,所以,十二金仙便各自收了一些弟子,来代替自己应劫,也即是代替自己去死!
照这么看来,这杀劫是自己被杀!
但太乙真人杀石矶时却是如此表现,且看封神演义里原文。 石矶娘娘大怒,手执宝剑望真人劈面砍来。太乙真人让过,抽身复入洞中,取剑挂在手上,暗袋一物,望昆仑山下拜,“弟子今在此山开了杀戒。”
从太乙真人的表现来看,可见十二金仙的杀劫是杀别人,而不是杀自己!
但看原文里还有描述,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杀罚临身。
这杀罚临身,看起来就是自己被杀,也算是渡过了杀劫,因为他们犯了红尘之厄,有杀罚要降临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这么看来,十二金仙的杀劫,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杀别人,另外一方面还有便是被别人杀,也就是说,杀自己和杀被人一样能渡劫。
但似乎还有一方面,像很多人所说的,十二金仙杀劫也包括找人替自己渡劫。可小刘觉的,找人替自己渡劫不太靠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要知道渡劫,只能靠自己,或者杀别人时引动天数;又或者被别人杀,被别人杀死那就更不用说了,肯定是渡劫了嘛,人都死了,不渡劫还干嘛呢!
但找人替自己渡劫这个,小刘实在想不明白,这不是像替考或者代笔什么的,难道你找人替你渡劫,天还能知道了?
因此,小刘觉的,十二金仙收弟子也绝不是让他们替自己渡劫,因为也替不了!
所以,这杀劫,只能包含两个方面,要么杀别人,要么被别人杀!
小刘侃封神,喜欢的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小刘侃封神
杀破狼
乾坤朗朗,
岂容魍魉定规章?
众生平等,
何须双标论短长?
文明得来殊不易,
而今豺狼明里抢,
恃强欺弱小,
利益我为上。
是可忍,
天理能昭彰?
东方有巨龙,
无欲也刚。
历经百年辛酸泪,
终得奋发图强!
肃纲纪,
驱魔障,
一声霹雳响东方!
今有青钢剑,
势必杀破狼,
横刀立马雄威起,
敢教群狼休再狂!
强强推文54《杀破狼》作者:priest
主角:顾昀,长庚
内容标签:强强 年下 古代权谋 江湖 机甲
简介:
一直生活在边陲小镇的长庚,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身世竟然这样的离奇。
寡母不是亲娘,耳聋眼瞎的小义父摇身一变成了威震四方的安定候,而自己竟然是流落民间的四皇子。
一夕之间,长庚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小义父“沈十六”亦或顾昀是否能一直守护在他的身边……
小说节选:
顾昀可能是头疼,双手紧紧地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眉头皱得死紧,竟没有察觉有人进来。
长庚在离着几步远的地方干咳一声,轻轻地叫了他一声:“侯……”他刚一出声,床上的顾昀瞬间翻身而起,一探手从被子里抽出了一把佩剑,脱鞘三寸,长庚连眼都没来得及眨,雪亮的剑刃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寒意顺着他的脖颈攀爬而上,持剑人就像一条被惊醒的恶龙。
长庚被他杀意所震,脱口道:“十六!”顾昀幅度极小地微微侧了侧头,好一会,他才眯起眼睛,似乎认出了长庚,含糊地说了一声:“对不住。”
他将佩剑重新塞进被子里,在长庚的脖颈上轻轻地摸索了片刻:“我没伤到你吧?”长庚惊魂初定,一个隐约的疑惑却忽然冒出来,他心想:“他不会真的看不清吧?”可随即又觉得不可能——安定侯怎么会是个半瞎?
顾昀摸到了一件外衣,胡乱披在身上:“你怎么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想要站起来,不料一下起猛了,身形微晃,又坐了回去。顾昀深吸一口气,一手抵住额头,一手按着床沿。
“别动。”长庚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他。他迟疑了一下,弯下腰将顾昀的腿扶起来,重新放回床上,又替他拉过被子,避过一把乱铺在床头的长发,扳着他的肩膀扶他躺下,做完这一系列的事,长庚尴尬地在旁边傻站了一会,搜肠刮肚不知该说什么,只好僵硬地问候道:“你怎么了?”顾昀身上的药正发作,没料到正跟自己“闹脾气”的长庚会突然来访,当下也只好勉强忍下头疼和耳边忽震耳忽模糊的声音。
他打算先把长庚打发走,便若无其事地笑道:“让一个翻脸不认人的小白眼狼气的——劳烦殿下给我拿壶酒来。”依照他的经验,这种时候,喝一口酒好像能好一点。长庚皱着眉,狐疑地端详着他。
顾昀头痛欲裂,便顺口扯谎道:“沈易配的药酒,治偏头疼的。”听闻古时候那挟天子令诸侯之人也时常犯偏头疼,人皆有类比联想之心,他这么一说,长庚果然被糊弄住了,将他挂在轻甲旁边的一把小壶取来。顾昀一口气灌下去半瓶,眼看要干瓶,长庚忙握住他的手腕,强行将酒壶夺了下来:“够了,药酒也不能这么喝。”烈酒入腹如火,全身的血都沸腾了起来,顾昀吐出口气,果然觉得眼前清明了些,只是可能酒喝得太急了,他觉得有点上头。
两人一时没话说,大眼瞪小眼了一会,顾昀有点撑不下去了,便靠在床头,轻轻合上了眼。他这分明是送客之意,长庚也知道自己该走了,可是脚下却如同生了根。
长庚一边在心里唾弃自己:“你操心也是白操心,还不识相快走。”一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替顾昀按起穴位来。边按边觉得自己贱,可手却停不下来。顾昀额头冰凉,除去一开始皱了一下眉以外,便没发表别的意见,乖顺地任他摆弄。直到长庚的手有一点酸了,低声问道:“好些了吗?”
顾昀才睁开眼,沉默地看着长庚。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亦有一得”,顾昀这辈子借着酒意,竟偶尔也会说句人话。
他忽然开口道:“就算到了京城,也有义父护着你,不用害怕。”长庚狠狠地一震,在灯光晦暗处几乎是打了个哆嗦。他在这样一个微妙又早熟的年龄段里,当他心里知道自己无可倚仗的时候,就能咬着牙让自己变成一个冷静克制的成年人,可是这一点逼出来的强大很快就会在他所渴望的一点微末温暖面前分崩离析,露出内里一团柔软的孩子气来。
顾昀冲他伸出一只手:“义父错了,好不好?”他并不知道这一句话是怎么穿透那少年冻裂的心魂的,本意想来也不怎么真诚,因为顾昀大部分时间并不认为自己有错,即便偶尔良心发现,也不见得能知道自己错在哪。
他只是借着酒意带来的温柔和纵容,给了长庚一个台阶下。长庚紧紧地扣住他的手掌,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僵硬了多日的肩膀突然就垮了下来,差点哭了。
他发现原来自己一直以来等的不过就是那么两句话,只要那个人当面跟他说一句“义父错了,没有不要你”,让他能感觉到这世上没有了虐待他的秀娘,没有了来不及见最后一面的徐百户后,还给他留了一点温暖的念想……那么他就可以原谅小义父的一切。从来的和以后的。不管他是叫沈十六还是叫顾昀。
顾昀觉得眼皮越来越重,便靠在床头闭目养神,几不可闻地说道:“长庚,很多东西都会变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归宿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不要想太多。”长庚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的脸,目光中不知不觉中带上些许小心翼翼的贪婪,心里悲哀地承认顾昀说得对——很多东西会变,活人会死,好时光会消散,亲朋故旧会分离,山高海深的情义会随水流到天涯海角……唯有他自己的归宿既定且已知,他会变成一个疯子。
顾昀往床榻里面挪了挪,伸开手臂,拍拍自己身边:“上来,明天还要赶路,在我这凑合一觉吧。”后半夜,长庚在顾昀帐子里睡着了,乌尔骨照常不肯放过他,噩梦依然一个接一个,可是他鼻尖上总是萦绕着一股淡淡的药味,潜意识里就知道自己很安全,甚至隐约明白这是在做梦,那些恐惧与怨恨便似乎和他隔了一层。
这对于长庚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安眠了。当然,要是他醒来的时候,没发现自己压麻了安定侯的一条胳膊,还没完没了地往人家怀里钻就更好了。
尤其顾昀那混账永远也不会体谅少年人敏感多变的心,别人越是局促,他就越要雪上加霜。顾大帅自以为同床共枕一宿,长庚就已经算跟他和好了,于是故态重萌地可恶起来,他不但揉着胳膊拿人家取了一早晨的乐,还大有以后要时常挂在嘴边拎出来鞭尸的意味。
小小杏子林匪窝转瞬便被甲戈填了个水泄不通。沈易不明白顾昀为什么还在装怂看热闹,被震天喊杀声所激,差点要掉头下阁楼,一转身,却看见长庚面不改色,箭尖指向始终不离顾昀周遭,谁胆大包天敢靠近,就要把谁穿成串。
“沈将军放心,义父心里有谱,我也盯着呢。”长庚说话的时候有种不显山不露水的笃定和不容置疑。
一瞬间,沈易心里忽然生出一个想法——顾昀刚刚刻意激化傅志诚与蒯兰图的矛盾,是想借刀杀人么?长庚:“今天如果傅志诚被拿下,南疆统帅空缺,皇上虽然一意孤行,但也知道轻重,边疆重地,必要大将来守,放眼朝野,没有人比沈将军更有资历了——何况说到底,皇上打压我义父的兵权,不过是疑心病太重而已,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在,大梁的安危也还架在我义父肩上。
击鼓令一出,玄铁虎符形同虚设,南疆统帅任谁当,都是有统辖权却无实际兵权,义父既然已经表明态度,皇上难道不应该打一棒子给一颗甜枣,为沈将军行个方便?”说到这,长庚顿了顿,笑道:“沈将军你看,皇上虽然不怎么待见我这个便宜弟弟,逢年过节该给的赏却一分也没少过,加起来比义父的俸禄还高些呢。”
沈易忽略了“府到底是谁在养家”这个复杂的问题,他震惊地看着长庚,神色几变,良久才感叹道:“殿下真是不一样了。”当年他们从雁回小镇领出来的少年那么单纯倔强,喜怒哀乐全都一目了然,沈易暗地里钦佩过很多次他心志坚定——换个普通孩子,一夜间从小镇少年变成当朝皇子,早被繁华帝都迷了眼了,而长庚那时候还是个从来不知荣华富贵为何物的孩子,却居然毅然离开侯府,宁可天高海阔浪迹江湖,也不肯回去做他井底之蛙的贵人殿下。
此时在剑拔弩张中与他侃侃而谈天下大势的年轻人,周身已经褪尽稚气,面目全非得让他心惊胆战。
长庚没应声,四年来,他从身到心都不敢有一天懈怠,不是为了想要建功立业,而是想尽快强大起来,有一天强大到能与乌尔骨谈笑风生……能保护一个人。“我朝眼下最大的问题是缺钱,”长庚道,“海运虽开,但中原人却很少出海,海防也就那么回事,靠洋人们往来穿梭带来贸易,说到底,大笔的利润还是这些跑船的洋商人赚去的,那点流进来的银子不够皇上私下里和西洋人买紫流金的。”
沈易:“这只是一时,并不是没有出路。”长庚似乎笑了一下:“不错,我今年春天去古丝路看过,见楼兰入口繁华得难以置信,一想起这是我义父一手扶植的,心里便不禁与有荣焉——最多三年,古丝路就能彻底打通,真正贯穿大梁全境,等百姓真能从中获利时,必有足够的金银流入国库,到时候灵枢院再不必为银钱发愁,各地守军军饷充足,兵强马壮,何人还胆敢进犯?那么是兵部说了算,还是我义父说了算,在他眼里,可能并无分别。”
沈易默然,他不知道为什么分别五年,长庚反而更了解顾昀。但他说得一个字都不错。前些年,顾昀还时常念着要揍这个揍那个,自从他接管古丝路,却越来越少提起这些了。一方面是随着他年龄渐长,思虑渐多,激愤渐消,另一方面……是顾昀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抓着兵权不放逞什么威风。
他毕生所求,不过家国安定而已。若可战,便披甲上马,若需守,他也愿意做一个丝路上清贫的商道守卫。
他说完,幽幽地叹了口气,两人各自沉默片刻,顾昀忽然道:“明天将钟将军的折子拿给我看看,倘若时机合适,早朝时候呈上去,真是听他们吵够了。”
沈易一愣,安定侯的态度全权代表军方,这么多年没在内政上表过态,这回是要站在军机处……雁亲王背后了吗?
正这时候,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的长庚插话道:“不必,义父,些许小事,哪就需要你亲自出面了?”沈易见他来,忙撤下方才坐没坐相的姿态,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道:“王爷为苍生社稷殚精竭虑,我们这些只会花不会赚的败家丘八也是想略尽绵薄之力。”
长庚笑道:“沈将军哪里话,众将士浴血在前,才有我们喘息倒手的余地,运河沿岸设厂一事牵涉众多,你们牵涉其中反而容易恒生枝节,我还摆得平,放心吧,保证在天寒地冻前安顿好。”
如今的雁亲王早已经不是雁回镇上的懵懂少年了,国家危亡必有挑梁之人,他年纪虽轻,手掌军机处的一身沉稳威仪却已经尽在周身,三言两语宛如闲聊,经他嘴里说出来,却仿佛掷地有声。
沈易恍然想起来,自从雁王接手军机处,他们要钱来钱,要粮来粮,一批一批的火机钢甲一点也不犹豫地往前线送,倘若不是他们自京城来,知道朝廷是怎么一个千疮八孔的熊样,大概还得纳闷,怎么日子比战前还要宽裕些?沈易正色抱拳拱手道:“无论如何,末将要替边疆数万将士谢谢王爷。”
长庚笑道:“沈将军说得哪里话,都是应当应分的……再说义父都已经谢过了,是不是?”
顾昀:“……”这小王八蛋!长庚从他手中抽出油纸包,柔声道:“零嘴解解馋吃两口就算了,多少节制点,待会还有正餐。”沈易这万年老光棍简直不好意思在此地坐下去了,这回不用顾昀赶,也想吃完饭赶紧溜,安定侯家的饭吃起来真牙碜。
晚间送走了身心遭到重创的沈将军,长庚抽走顾昀拿着不放的酒杯。顾昀懒洋洋地笑道:“没酒了,就一个杯底,我闻闻味。”长庚丢给他一包安神散:“爱闻闻这个。”
顾昀无奈地摇摇头——他放纵是放纵,但只要是自己想节制,也绝不含糊,多日滴酒不沾,沈易来了,也才喝了三两杯,基本就是沾沾嘴唇润润喉的量,知道长庚要管他,才不主动放杯子。长庚实在太爱管他,事事照顾到,并且绝不假手他人,好像这样能让他心里踏实似的。
都是小事,顾昀也乐得不动声色地惯着他。两人洗漱干净回房,却并没有什么旖旎,顾昀拍拍床头,对长庚道:“银针拿过来。”长庚那日先是大惊大悲,几乎陷入幻觉,随后又是多年夙愿一朝成真,心里欢喜太过,整个人都魔怔了,顾昀当时按捺住没表示什么,隔两天沈易等人抵京,他便去找了陈姑娘。
陈姑娘过来看了一次,当时就动手将重瞳时不时冒出来的雁王扎成了一只刺猬,意味深长地说道:“自古就有乐极生悲,极乐至失心疯的事屡见不鲜,常人尚且如此,王爷这个情况,还是节制点吧。”说完她还隐晦地看了顾昀一眼,字里行间仿佛也闪过了“禽兽”二字,远远地糊在了安定侯头上,下了一打禁酒禁辛辣禁吵闹禁欲的禁令,嘱咐雁王每天睡前以银针安神固心,有些他自己够不着的地方便只能让顾昀代劳,顾昀跟着陈姑娘学了好几天,所幸他自幼习武,穴位都还找得准。
长庚安然趴在床头,解了顾昀的发髻,将他一缕披散的发梢抓在手中把玩,将后背交给顾昀那二把刀,一点也不怕他扎错了。
每天无论怎么心力交瘁,这一会工夫都是他心里最放松的时候,恨不能一直这样到地老天荒。顾昀对针灸之术一窍不通,完全照着陈姑娘教他的死记硬背,他以前时常听民间说些一针扎不对,能把人扎瘫了之类耸人听闻的传言,因此一点神也不敢走,深浅一分也不敢错,也真难为他那双瞎眼。
直到最后一根针放好,顾昀才微微松了口气,身上出了一层薄汗,随手拿起旁边的汗巾擦了擦手,一回头,却见长庚侧着脸,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看,他眼睛里的血色与重瞳尽去,眼神安静而悠远,映着汽灯一点微光,像是含着古佛下、青灯中的一双人间烟火。
顾昀:“看什么?”长庚的嘴角僵硬地挑了挑,然而银针在身,他又被封成了一个面瘫,笑不出来。顾昀的目光匆匆从他那线条流畅的后背上掠过,虽然很想“报仇雪恨”,却不敢违背医命,在这种时候碰他,便干咳一声道:“好了,别笑了,赶紧休息,明天不是还要早起?”
“子熹,”长庚面部能调用的肌肉不多,话也只能轻轻地说,越发像撒娇,“亲我一下好不好?”顾昀警告地瞥了他一眼:“找事是吧,都成刺猬了,还勾引我。”
长庚早把他看透了,一声“义父”就能让某人束手就擒,这种流氓里的正人君子才不会趁他身上扎满针的时候动他一根手指头,因此有恃无恐地看着顾昀,只是笑——嘴角挑不上去,眼睛里却盈满了笑意。
顾昀心道:“爬到我头上来了。”然而他毕竟不是个老和尚,看着那青年人裸露的宽肩窄腰,头发披散如缎,黑是黑白是白,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便只好端坐在一边闭目养神。没过多大一会,就听见旁边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顾昀一睁眼,见长庚僵尸似的爬了起来,凑到他面前,先在他嘴唇上碰了一下,随后轻柔地含住他的嘴唇,来回琢磨,浓密的眼睫微颤着,与他那一脸被针扎出来的木然成了鲜明的对比。
顾昀本想推开他,可长庚那一身的针,他压根没地方下手,手尚未张开,便被长庚扑到了床榻上。
心上人乌发披散,半裸着扑到自己身上,顾昀的喉头明显动了一下,感觉自己快要百忍成钢了,当即气得在雁王殿下的尊臀上拍了一下:“针还在身上呢,又疯!”长庚伏在他身上,下巴垫在顾昀脖颈间,喃喃道:“我没事,就是那天一想到你在我怀里,就总觉得自己是梦醒不过来,我没做过什么好梦,总怕是开头欢喜,一会又出个什么魑魅魍魉捅我一刀,有点自己吓唬自己,魇住了。”
顾昀抬眼望着床帐,想了想,问道:“噩梦都会梦见些什么?”长庚也不知听进去没有,只看着他,也不答话,在他侧脸上一下一下地啄着。顾昀伸手一挡:“别起腻,点了火你又不管灭。”
长庚叹了口气,头一次一点也不想听医嘱,老实下来,小声道:“你穿朝服真好看。”顾昀挑了个没针的地方,懒洋洋地搂住他:“我穿什么不好看?”他已经有点困了,因为长庚睡不安稳,屋里一直点着安神散,安不安得了长庚的神不好说,反正被殃及池鱼的顾昀是困得越来越早了。
他被西域人暗算,旧伤一度反复,小半年了,伤虽然见好,但他自己感觉得到,精气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人在前线的时候心里尚且有根弦绷着,眼下回朝,每日不必枕戈待旦,心里的弦稍稍一松,身上就时常有种缭绕不去的倦意,此时话说了没两句,已经迷迷糊糊地闭上眼。
长庚爱极了他这股理直气壮的厚颜劲,低低地笑了几声:“要是只穿给我一个人看就好了,穿朝服我一个人看,穿盔甲我一个人看,穿便装也是我一个人的,谁也不准觊觎……”
他这话里真假参半,已经合上眼的顾昀却只当是说着玩的床笫私语,坏笑了一下回道:“那恐怕是不行,不过什么都不穿倒是可以只给你一个人看。”
长庚的眼神顿时就变了,从手背到手腕上几根银针竖着,也没耽误他的手缓缓上移,动起手脚来,活活把顾昀摸醒了。
#耽美##耽美小说推文##耽美小说##小说安利##杀破狼##顾昀##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