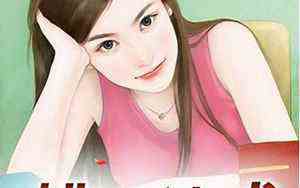清朝正黄旗人都有通天纹,通天纹是啥,为何古籍说通天纹开不得?
你或许听说过前不久发生的一则新闻,北京某公交上一位大妈与乘客发生争执。
这位大妈不仅言语不堪,大骂对方是来北京要饭的外地人,同时还特别自豪地说自己的身份十分尊贵,是额头有通天纹的正黄旗满人。
这一幕也被一旁的路人录制下来发到了网上,而网友们纷纷表示大妈的话语真的是啼笑皆非。
不仅在公共场合大闹撒泼不说,还在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宣扬封建社会的那一套,着实令人哭笑不得。
不过也有人好奇大妈口中的“通天纹”到底是什么?难道真的如她所说,这通天问是八旗满人独有的吗?
通天纹的解读大妈口中的通天纹长在她的额头上,实际上这是对通天纹的一种错误认知。
实际上通天纹是一种“手相”,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穿钱线”,一个良好的通天纹是从手腕处穿过整个手掌,一直延伸到中指上面。
在上古时期,人们认为拥有这样的手相的人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是神力的化身。
到了后来,拥有通天纹的人也被认为是不俗之相,古籍中记载,如果左手有通天纹,那么这人一生都会富贵安康、无灾无难,若是右手有通天纹,那么这人会先贫后富、老有所成。
若是双手都有这种通天纹的手相,那么定然能成就一番事业、是青史留名之人。
这样看来通天纹确实是不俗的“宝相”,那么大妈口中长在脑袋上的通天纹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就要来源于一个诞生在清朝的误区,清朝是满洲人建立,满洲人对于南方的汉人而言本身就是外来民族,而他们创立的清朝也经常被人诟病“得国不正”。
所以为了树立自己“承天顺道”的正统性,满清的统治者开始神化自己。
而为了让满人旗人的地位凌驾于汉人之上,清朝统治者开始将一些满人身上比较明显的特征加以突出,并宣称这是不俗的迹象。
而通天纹的概念也开始扭曲了起来,满洲人的面貌特征同汉人在细微之处有很大差别,满人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多半为通古斯人种。
这样的人种往往个子比较矮小,而且面部脂肪多、颧骨高、眼睛小且细,并且因为肌肉的分布,眉头常常出现深刻的皱纹。
许多清朝皇帝的画像上便有这一点特征,于是眉头上的皱纹也开始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
统治者声称眉头上的纹路是一种“王者之气”,是可以与天地沟通的“通天纹路”,所以眉头上的眉间纹也成了富贵的象征。
这也不得不感叹,有的时候大家坚信不疑的说法实际上可能是祖辈的别有用心,如今流传下来的习俗也都有历史的因素在其中,并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满洲八旗虽然满人的眉间纹或许会更加明显,但是其他民族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会出现眉间纹。
所以单单依靠这所谓的“通天纹”来断定眼前的人是否尊贵,的确是一个荒诞的说法。
因此视频中大妈口中“正黄旗”独有通天纹也是一个谬论,不过许多对历史不了解的人可能也会好奇,这正黄旗究竟是什么。
正黄旗最初来源于满洲特有的编制制度,满人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渔猎民族。
和同时期汉人已经发展出城郭不同,满人还处在部落阶段,不同的部落之间不仅凝聚力强大,而且还有属于自己的图腾。
努尔哈赤起兵也正是因为背后有多个强大部落的支持,为了便于将手下的兵士进行统计编制,它便按照征服的先后顺序、地理位置以及不论大小把它们以“旗”归类。
分别是正白旗、正黄旗、镶黄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等8旗。
其中以正白旗、镶黄旗、正黄旗为上三旗,是努尔哈赤家族最亲近的部族,其他5旗是下五旗,为后来归顺的部落,下五旗的人地位比上三旗底,要定期为他们做差役。
而随着发展,努尔哈赤还把这8旗还分为满蒙汉三种大类,其中满蒙为尊、汉为卑。
但是地位都比非旗人要高,可以圈地圈奴,可以做官,借此来提升满人的地位、吸引南方的汉人投降。
视频中的大妈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正黄旗,只是若是在满清或许真能被高看一眼,可是生活在21世纪的新中国,我们早已废除帝制,不再讲究封建社会那一套了。
所以大妈这种活在过去的行为着实不提倡。
开不得的通天纹一些熟悉手相或者面相的人或典籍都会说通天纹不可轻易打通,一旦打通,祸患无穷。
实际上这种说法也是一种迷信,如果是额头上的“通天纹”,那么这不过是满清留下的历史因素,通天纹只是最普通的皱纹而已。
如果是指手掌上的通天纹,虽然谁也不敢说手相玄学到底存不存在,不过对于这种模糊的话语说法大可一笑置之。
首先中国拥有书籍文字的历史悠久,正经的史记典籍是古籍,话本小说也是古籍。
对于从古代留下的说法也要以辩证的态度去面对,毕竟古人同现代人一样,也有那种戏说鬼本在市面上流传,而这种书本也不过是古人编造的戏言罢了,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
而且不仅打通通天纹的记载模棱两可,甚至都没有具体的书籍说明如何打开通天纹。
是需要修炼功法还是冥想静心,谁都不知道,21世纪也没有谁会清闲到去尝试打开通天纹这种行为。
所以以后对于此类的说法,大家大可一笑置之,不予理会。
结语通天纹这东西大家不要因为拥有而自豪,也不要因为没有就觉得可惜。
毕竟通天纹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谁也不能确定它的真实性。
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应该做到“活在当下”,毕竟富贵与幸福是要靠着后天的努力才能获得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有不同之处,有的人出生在富贵人家,有些人出生在工薪阶层。
不论你出生在哪个环境,都要心怀对未来而憧憬,以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去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看左手——书法家戴泽
这个标题非我所创,偷来的。穆涛送给贾平凹的。穆涛说贾平凹一生成就了两个事业:主业和副业。主业是编辑和写作,副业是画画和书法。都干的出了彩。就好比左手和右手,主业用右手----人们惯常用的那个,因此主业都能做得很好,但能用左手做副业却不同,别扭的很,稍不留意便会影响到右手,能左右开弓的人不多,可一旦得心再应了手,事情就不一般了。
戴泽的事业也是分出了主业和副业。主业是在人大做个好秘书,副业书法。两样都叫得响,“笔笔见其韵,画画有其神。有名的‘戴一笔’”,早在七、八年前就听说了。正应了穆涛所说的“搂草时打来了兔子”。右手打球已经是简洁漂亮,不料左手竟也是大气撩人。
书法穿越古今。在今天,很多古人说的话,我们都是从一些书法作品里看到的。于古人,是必须;于今人,却是装饰。古人从饮食起居到精神创造都离不开书法,而今天,机械化让世界变了样:墙壁是铅直的,车道也是整齐划一……与生活相关的大都有了专门的机器、专门的设备。农民不想站在稻田里风吹日晒,有收割机;作家不愿伏在桌上一个个地爬格子,有计算机……剩下书法。画线条,不为吃喝,也不为实用,是用来审美的。机器不懂得人的精神,那就留下吧。
书法,这个线条,实用已经不需要了,一旦用起来就是精神的。
书法家戴泽,与《西部》编辑部关系很好,《西部》杂志中很多文章的片头都是由他题写。所以结识戴泽也是和《西部》有关的一些场合,首次相遇是今年的四月份。记得是个饭局,戴泽因事耽误了些时候,先到的人围坐在桌前,一边等候一边寒暄着,话题大多和那个被称为“老戴”的人有关,便以为他真是“老”戴,不由在心里感慨:难怪字写的飘洒俊逸。“老”戴究竟有多老呢?即便不是八十高龄的耄耋老者,也应该是“耳顺”或“知天命”年龄的人。
我错了,错的一塌糊涂。当我看到戴泽迈着那种唯他所特有的沉稳步子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错了。戴泽一点也不老,身上有的是壮士枭雄、河山万丈的豪情。酒桌上,属于那种敬的率性、喝的率性,亲和力很强的领导型人物。我不善酒,那天还是喝了不少,一晚上都晕乎乎的。第二天,徐主席打来电话,一边致歉,一边反复申明:昨夜的喝酒,完全是个人意愿,没有半点强迫的意思。
再见到戴泽是两个月后的今天。因为采访需要,坐在了他办公桌前。看得出:他很忙。不停地有人进来,送文件、签字……我们的谈话一次次被打断,本打算两小时就结束的采访一直到下班都没有结束的意思。午饭时间到了,戴泽干脆向家里请了假,我也不客气,正愁没地方吃午饭,“宰”了他一顿。
不知是不是那顿饭的故,反正戴泽的面相清晰了。书法练的是“童子功”。虽然父母无甚文化,但外公、舅舅却了得,不管你喜不喜欢,遭遇书法没商量。放假了,跟着舅舅出去玩,不留神,舅舅露了两招,不怕你不喜欢。舅舅的两招还真管用,小学一年级就敢给人写春联。那年月,毛主席语录是必读之物。小学一年级的戴泽,刚才认识了毛主席、共产党、祖国等简单的几个字,硬是把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祖国万岁”组成的上联、下联和横批,写到了庄户人家的门楣上。乡亲们说要得,戴泽也说要得。不然怎会有年三十带着一群顽童,揭了人家门上的春联,而后满不在乎地说:“等我会写字了,还你”
“等我会写字了,还你”,也许只是当时的无意识,今天看来却是性灵、神思这样的东西。古希腊人将其视为感受神的灵气、代神立言的工具,决定着一个人才华的高度,更决定着心灵的厚度。也许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说辞,正是戴泽日后能够成为书法家的偈语。
戴泽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是行草,着实让我意外了一把——主要是见了人以后。“行”是快步行走,而“草”则是电光火石般的大气盘旋,相信书者在书写时也一定如电闪雷鸣般迅捷。但,面前的戴泽,无论是坐、立、行,还是他的谈话,怎么看都像是和楷书一样的方正有型之人。尤其是听他讲麻将经,思辨的气息在不大的空间里弥散的四处都是。虽然有发自内心的吆喝和铮铮跺脚的声音,但也只是温柔敦厚里飘洒着一缕清风。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这样纵横捭阖、恢弘舒畅的人呢?
事物都是辩证发展的,能意识到不明白就已经是明白的开始。人这个理性与感性的综合体,既遵从着理性教给人的正确,又向往着感性带来的快乐。只知道理性做事,从来不懂得情感抒发的人,只能是神,戴泽也不例外。但理性与感性却永远是一对冤家,没有几个人能处理的好,戴泽充满矛盾的面象已经告诉我:他处理的很好。他把这些分别交给了左手和右手,左右手可以同时干活,却有着明确的分工:右手掌管理性的事、左手负责抒情。该右手出手时,左手绝不越位;同样,遇左手工作时,右手只会隔岸听着音乐。通常人们看右手比看左手时候多,只看到表象,没有看到本质,不奇怪。
戴泽的行草很有一些特别之处,字字都飘逸着,既像一朵朵浮云袅袅地飞向天际,又像是舞蹈家摇曳着腰肢,轻歌曼舞。时而顿挫,时而修长,如果再配以音乐,我一定会误以为是一群舞者在舞台上翩跹的身影。
舞蹈与书法具有相同的艺术抒情特征。舞蹈是利用舞台空间塑造出不同的时空运动线;而书法则是在平面的宣纸上,“系于点画,显于间架结构,成于章法布白”,从而构成各种线条样式。如果说前者是对空间线条的造型,后者则是对平面线条的勾勒。“舞蹈者在舞台上舞动的身影,恰似书法家手中飞舞的笔墨。”古人比我们更谙此理,不然怎么会造出 “龙飞凤舞”、“舞文弄墨”、“笔飞墨舞”……这样的经典。
既然是相通的,那么,舞蹈家观看书法家挥墨,书法家坐在剧院里赏剧,实则是一个相互切磋的过程。听说林怀民为编辑舞剧《行草》曾跑到台北故宫博物馆长时间地观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不知道戴泽的舞蹈精神是不是也与研究舞蹈有关。但我确实知道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草书水平立刻大长的故事。据说有人欣赏张旭草书时还浮想联翩来着:看到的舞影也许就是当年公孙大娘优美的舞姿。
有人说:书法是一种文化的书写,同时也是文化的过滤器。通过书写,一方面与先哲对话,一方面过滤掉文化中一些滥俗的东西。所以,书法家只能是一些文化人,写出的每一个字都包涵着浓厚的文化意象,也折射出书者个人的文化底蕴。戴泽的作品无疑是有厚度的,将自己从生活中积淀的生命感、生命形体意识以及个人情感的依托通过书写引发出来,使人产生感受、联想,甚至判断等。但我发现:无论是应试的,还是留给自己看的,都有一种偏向,偏向于庭院深深、飞红落英的温情和婉约。如:李商隐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徐俯 “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有一种江南烟雨中从宋词里笑吟吟走出来,浅言轻笑,弹一曲渔舟晚唱的柔美气息。
既然是偏向,就一定是他个人的东西。我一直在想,他在情感上一定是个既丰富又细腻至极的人。有那么多温婉的情愫,装载于昨夜的那缕晚风里,寄托在南飞燕子的呢喃里……,总是需要一个可以释放的载体。书法帮了他,行草帮了他。一横、一竖、一撇、一捺……每一笔中都饱蘸着他恣意的想象,于飞舞的笔墨中淋漓尽致地流淌。
一遇有空闲,戴泽就会进到那个被他称之为工作室的储藏室里,看书、挥毫、思考……没觉得咋样,已是夜深人静。我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不觉累,反觉兴致盎然。从开始练字始就是这样:“临帖,总结分析,再写自己的……几十年来,尽管因为各种原因,中间曾经有所中断,但只要一有条件,就会着魔般地写下去。作品示人,一定要先过了自己的关。姜老师的《和谐赋》书写出来长达四米,硬是写了三遍……”
坚持!本是件辛苦很的事情,到了戴泽这里却变成了惬意的享受。用他的话说,是触到了庙门,门开了,发现里面盛满了快乐,久了就不想出来了,愈来愈贪婪。姜老师曾就此赠诗与他:临池学书志坚韧……挥洒自如人称善……
这些饱含着情感的书写在我看来已是优美至极,书者的技能、才识、精神品格、文化修养等全部收纳其中,这哪里是书写,分明是在挥毫嘛!面对我的夸赞戴泽表现出不以为然,指着那幅已被收录于《德阳墨韵》的“春风之在园西畔,荠菜花繁蝴蝶乱……”说:“确是飘逸着,但大多是向上飞,缺少变化。”接着又拿出刚写的“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那些向上走的线条果然改道了……“旌城书画院每月都有一次小聚,参加的人带着自己近期的作品,互相点评。”说此话时戴泽显得很兴奋,显然,他很喜欢这样的聚会,那个“飘逸”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发现的。喜欢临摹古人的碑帖,也经常参加一些书法大赛,只为提高和检验自己当前的水平。
两只手,戴泽也许更偏爱左手,这只手掌控着他的心跳,承载着他情感和哲思。从这只手送出去的各种信息,绘制出来,就是他的心电图。他的热情、他的激动、他的愤怒、甚至他的安静和他对世界的感悟,全在其中。
每到左手上工时,相信戴泽都是满怀着欣喜。翻出王铎的、欧阳询的……再拿出自己的,用手中的笔与千百年前的魂魄对话,和自己对话……这时的戴泽,一定是蜕去了社会的外衣,迈着轻盈的舞步。当手中的笔在宣纸上游龙戏凤般翩跹着的时候,一定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活脱一天生的左撇子。没有因此影响右手,反而成为了右手疲劳时的稍事休息。我更愿意相信他就是史飞翔说的活在第三境界的人,“香风细细,鸟语花香”。戴泽就在这个世界里,时而挥毫,时而游弋。
老戴,如何能老?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