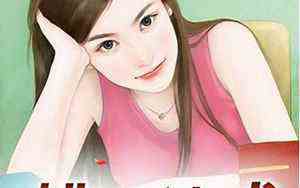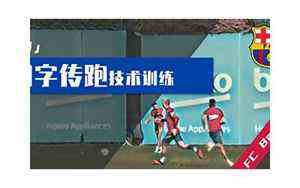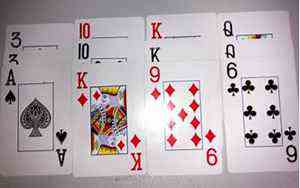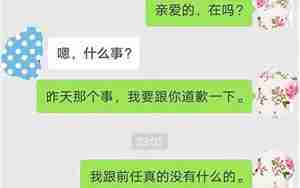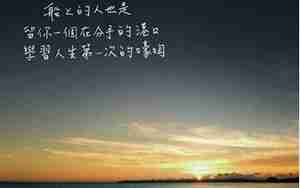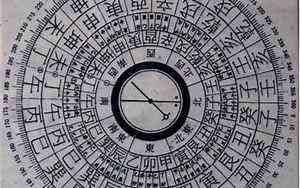
追念:钱耕森先生为何提出“大道和生学”
钱耕森先生
惊悉钱耕森先生过世
陈寒鸣
哲人竟逝令人悲
往事历历涌心田
卅余年前初相识
自此而结忘年谊
春秋转换二十度
和生之学力倡矣
承邀赴皖参盛会
畅论斯学会贤侪
哪知竟成诀别晤
繇今思来泪涕涟
钱耕森,1933年10月,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位大师。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国际知名学者。
历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道家道教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常务理事,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委员,冯友兰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冯学论坛讲座教授,张岱年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宗教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顾问、研究员。兼任东日本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韩国东亚人文学会顾问,马来西亚孔学研究总会顾问、导师,加拿大中华学院客座教授,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学术委员、荣誉研究员。
钱耕森先生提出“大道和生学”的意义
陈寒鸣
【内容摘要】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究竟何在?长期以来,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观点,而钱耕森先生积其六十余年学术积累,潜心研究,会通儒道,从中国先贤那里体贴出“大道和生”四字,用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并试图据之重新建构中国哲学史。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大道和生学”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应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文化;哲学智慧;精神价值;“大道和生”;钱耕森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延续5000余年的伟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如何评估这精神?有论者谓:“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内在特质的基本风貌。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又有沉滞抑郁、激人图变的一面。优异的一面中蕴含着消极的因素,令人愤激的一面中包孕着值得宽慰、可以向另一面转化的潜在质素。”
学者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作了种种归纳,如以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以“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人文主义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等等。
钱耕森先生积其六十余年学术积累,潜心研究,会通儒道,从中国先贤那里拈出“道”、“和”、“生”三个概念,用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他在新著《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指出:“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和”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与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最根本的特点。紧紧扣住最基本的原动力、核心与精髓、最根本的特点,用“道”、“和”、“生”三个概念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周易》有“一阴一阳为之道”之说,又称天、地、人“三才之道也”;老子把“道”视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同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 四十二章》)孔子则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名言。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认为,正是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故“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亦有论者说:“道无古今,但道生生不已,蕴含着时间上的历程,即有古今;道所生者,有古今、有旧生、有新生。对生生不已的道可以论,是为道论。……离开道论,便不可能言道生;离开道生,何以言道?……在道论中,与道符合、一以贯之而又深入人心、甚至为人喜闻乐见,在历史上一脉相承的道论,可谓道统。道统散见于各学科中,有学统,道统、学统运用并实践于政治活动中,有政统。道统、学统、政统,都是道或道论的展现。无论为学还是为政,不入统绪,不得其门而入,不足以为真学问、真政治。因为‘统’非其他,就是人类文明长期延续下来的优秀传统。”
其次,自黄帝提出“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尧帝提出“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理念以来,《周礼••天官冢宰•礼典》又提出“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思想,由此而形成十分重要的中华文化精神传统;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涵化、融合发展成民族大家庭而成为世界史上的典范,无疑与此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一精神和传统不仅在历史上发展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处理世界各国的邦交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且它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崭新的人权理念有彼此呼应的关系”。
最后,《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这奠定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哲学基础,使得中华文化始终讲求如何使人及由人构成的共同体的生命生生不息,永续发展。并且,“生”与“和”紧密相连,“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生’是‘和’的目的、归宿点、最大价值、最高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最高理想,‘和’的本质与最大价值在于‘生’”。
因此,钱耕森先生以“道” 、“和”、“生”三个概念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颇为令人信服。
不过,在我看来,当以“大道和生” 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时,尚需对“大”一概念予以足够重视。孟子从“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矣”(《孟子•尽心上》)的思想出发,明揭“先立乎其大”(《孟子•告子上》)之旨,强调道德主体意识,提倡“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确立尊道乐义的独立、自由、自尊、自主的人格。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如南宋陆九渊本孟子此论而力倡“发明本心”,自作主宰。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犹如孟子,陆氏此处所说的“此心”,乃是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来指示本体。他将这本体又称为“本心”,谓其为内在的,本来就有的,是道德智慧的不竭泉源、纯善意识的无尽宝藏,而诸如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公正心等都不过是“本心”的表现。“本心”遇到相应的事物就会自然表现出来,如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见丘墓则生悲哀之心,见宗庙则起钦敬之心;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是知其多是,非知其为非……凡此种种,皆“本心”之发用。一切道德义理皆自“本心”流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即仁义之心、此理即仁义之理,故而“心即理”。在陆九渊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此良善“本心”,人应于此深思痛省,理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故其强调学者须先立志,自作主宰。他启发学者首先要认识自己,自觉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天之所以与我者,凡、圣之间原未有异,因此不应该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不必把圣人当作偶像顶礼膜拜。若能发明此心,涵养此心,凡者即圣人。他告诉学者,本心自有明德,学者应先明己德,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而不必旁骛外索,作无益之求。自立者亦须自重,不能随人脚后,学人模样,“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懈怠流浪,患不觉耳,觉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如此”(《陆九渊集》卷四《书·与诸葛诚之三》)。自立又要培养宽宏力量,要认识弃发掘自身内在的力量,自作主宰,不能因外在习俗影响而夺己志。他说:“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陆九渊集》卷四《书·与曾宅之》)“请尊先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事皆备于我,有何欠阙?”(《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后世的王阳明及其后学均受象山这思想的影响,力倡“自作主宰”,如阳明尽脱“乡愿”之意而坦呈“狂者胸次”;王艮自尊自信,赤身承当,磊磊落落,毫无媕婀媚世之态;颜钧则赋诗道:“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与古人盟。”我认为,这样一种“大”的思想与实践、这样一种“大”的人格和气节,同“道”、“和”、“生”一样,也生动展现了十分珍贵的中华文化精神。千万年来,中华民族所以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有关。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而特别重视“道”、“和”、“生”三个概念,而是从此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试图对中国哲学史作出新的描述、解释,这是钱耕森先生近二十多年所作的重要学术工作,是他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如一部中国哲学史究竟应从何处开篇?上世纪初叶,陈黼宸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首开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三皇五帝讲起,由伏羲而商朝讲了整整一年,给学生们提供了无数材料;稍后,改由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以《诗经》作时代的证明而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在学生中引起轰动性反响。顾颉刚对此忆述道:“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傅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的。……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惊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上卷)始于老子,冯友兰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则始于孔子,这两种主张流行至今近百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有很大影响。而钱耕森先生毅然对胡、冯二氏的主张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哲学史应始于史伯,其理由是:
第一,史伯是一位哲学家,他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所构建的“和生”哲学,有背景、有理论、有论题、有论据、有论证、有践行、有影响。其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三个命题:“夫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同之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其中“以他平他谓之和”,是史伯对“和”下的一个定义。这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和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定义,又是历久弥新的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史伯提出的“和生”哲学,以及“和异禆同”精湛的辩证法观点,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远。
第2, 史伯是西周末年人,约早于老子和孔子200年。他的“和生”哲学,直接影响了老子和孔子,是他俩的先驱,因此可以说史伯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大哲学家。这就“使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顺理成章的从前5世纪的老子、孔子提前到前七八世纪的史伯,完全可以也应该大大地提前二三百年”。他并进而认为:“史伯比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早约200年。所以,他也可称为中西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哲学家。”钱先生的这一研究发现,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在钱耕森先生之前,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已有专节“伯阳父论‘和’、‘同’”,对伯阳父即史伯的“和同”论有所论析:什么是“和”与“同”呢?“和”就是“以他平他”。所谓“以他平他”,是指各种不同事物的配合与协调。伯阳父认为事物是由“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的。事物相杂,协调配合,用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足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悦耳,正七体(七窍)以役心……”(《国语·郑语》)。由此进而讲到政治。政治上也应提倡“和”,君臣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所谓“同”,指的是事物的单一性。单一的东西不能长久,“同则不继”,“以同禆同,尽乃弃矣”。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根据“和”、“同”的理论,王应顺“和”弃“同”。“和”最关重要的是“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君主必须纳谏,对事情进行比较,才可能巩固政权。可是幽王却与此相反,幽王弃和“而与剸同”,拒谏饰非,拒“明德”之臣,听阿谀奉承之词,重用“谗匿”之人。根据“同则不继”的道理,断言幽王不会长久。这里当然也注意到了史伯“和同”论的哲学思想性,但主要是从政治思想史处所作的论述,且并无高度评价,如指出:“史伯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互相补充的道理引出君主应该纳谏。然而应该不等于现实。幽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这就说明个人专制同纳谏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纳谏虽是一种美德,由于没有制度的保证,常常流于空谈。事实上,在专制主义条件下,纳谏只能是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
而钱耕森先生对史伯的研究,与刘氏有诸多重大不同。
第1, 刘氏以为伯阳父(甫)即史伯,钱耕森先生则经考论断言“史伯与伯阳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史伯与伯阳父同为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代的大臣。周幽王在位的时间很短,从公元前781年至771年,连头带尾仅有11年。这两位大臣的主要事迹都记录在文献《国语》里”。“ 史伯与伯阳父二人虽然同时都是周幽王的大臣,都功勋卓著,且思想深邃,富于创新,都预言用幽王的西周必将灭亡,但是他们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活动以及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都是不相同的”。
第2, 刘氏所论及言及史伯的“和同”,而钱耕森先生则注意到“史伯既用了‘和合’,又用了‘和生’,还用了‘和同’”,指出:“在史伯那里,‘和合’具有方法的意思,‘和生’是哲学上本体论与生成论的范畴。‘和’是生成万物的本质,万物是由‘和’而生的。‘和同’,补充了史伯对‘同’的肯定看法,体现了他对‘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
第3, 刘氏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论史伯的“和同”,并无太高评价,而钱耕森先生则从哲学史角度对史伯予以高估,称其为“中西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哲学家”。
钱耕森先生不仅将史伯的“和实生物”新诠为“和生”学,将“以他平他为之和”说新
诠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经典性的哲学命题,而且将老子的“道生”说新诠为“和生”说,并将之与史伯的“和生”相打通,认为:“老子的‘道生’说其实也就是‘和生’说。老子直接继承了先驱史伯的‘和实生物’的理念,又在自己的‘道生万物’的立场上,极大地改造发展了史伯的‘和生学’。”“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建立了‘和生学’,史伯与老子共创‘和生学’。”他又进而打通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庄子的“气生”说以及《周易》的“太和”说,还将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新建为“生物之用,和为贵”,揭示了“和”的本质与最大价值在于“生”。经过这样创新性地构寻,钱耕森先生构建了一个“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
回视中国哲学史,所谓“轴心时、时代”原创性大师姑置不论,后世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大家,每每从前辈、尤其是“轴心时代”原创性宗师及其留下来的经典中汲取智慧,并从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社会需求出发,开掘传统智慧,进而据之提出自己的新思想。这样的新思想,必然以传统为依据,以当下为出发点,而以引领未来为旨归。
如宋代二程及其后继者朱熹以《礼记·乐记》中“天理”二字为据而提出的以“天理”为核心观念的理学思想体系;明代王阳明以《孟子》中的“良知”二字为据而提出“良知”论的心学思想体系;如此等等。
而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和生学”新哲学体系,也是这样一种以传统为依据、以当下为出发点而以引领未来为旨归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钱耕森先生在《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说他创立“大道和生学”是受到其两位恩师金岳霖和冯友兰的教诲与启迪,“金先生对‘道’情有独钟,对‘分析哲学’造诣精深,以其名著《论道》构建‘道’的新哲学体系;冯友兰高度评价为‘论超白马,道高青牛’。冯先生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十分重视‘和的哲学’,他早年提出‘大和’说,认为‘各种好皆包在内’是‘唯一的好’,晚年提出了‘和解’说,认为张载所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在我看来,钱耕森先生虽其学有所授受,而“大道和生”四字乃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在为《大道和生学研究》所作“序”中赞之曰:“‘大道和生学’,创于史伯,立于老子,而先生继以倡之,文化一线命脉,虽时缀时续,终得以大明于今世。”苏州大学的蒋国保教授在提交给“2018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大道和生学”之我见》中,提出如果只就学说架构形式来看,区分学说类型不外乎一种划分,就是看其是“创作”之学还是“述作”之学。所谓“创作”之学(简称为“作学”)是从作者自身的哲学理念出发来剪裁哲学史史料,将哲学史史料化为构是自己哲学体系的有机元素;而“述作”之学(简称为“述学”)则是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对哲学史史料加以梳理与解释,但这种梳理与解释却未必建立在作者自己的哲学理念之上。
“作学”与“述学”,二者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是“述学”的光辉典范。当孔子说他在学术上“述而不作”(《论语·述而》)时,他是要突显自己的学说在思想上与周代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联系,并非否认其“仁”体“礼”用学说对周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后孔子二千多年的清代学者汪中,之所以将其考据、释文、证义、辨伪等文章汇集命名为“述学”,显然不是为了强调其学只“述”不“作”,而是为了方便对自己的学问作全面的表述。这样的“述学”,既“述”且“作”,又“作”又“述”,“述”与“作”有机一体,“作”寓于“述”之中。在国保教授看来,“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虽不自命‘述学’,却正可谓名副其实的‘述学’”。
钱耕森先生在《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自谓:“大道和生学”是我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生”思想,进行挖掘、梳理、研究与创新,所形成的“和生学”的新哲学体系。它所回答的是宇宙万物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大道和生学”主张“万物产生于大道之和气”。“大道和生学”这一哲学体系,理论渊源于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庄子的“气生”说和《周易》的“太和”说与“生生”说。这一哲学体系的研究特点是即哲学史讲哲学,将传统哲学中4个重要的核心理念,“道”“和”“气”“生”相结合,作为理论命题,并以大道立论,将“和生学”提升到“大道”的本质与规律的高度,形成为“大道和生学”。所谓“即哲学史讲哲学”,实际就是既“述”且“作”,寓“作”于“述”的“述学”。这种“述学”,是他对孔子“述而不作”文化精神的继承。
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反映了当下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社会需求。他在《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大道和生学”充分反映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大道和生学”在理论上发展了“和”文化,创新了“和生”学。“和生”即“和谐共生”,是生命共同体的相融共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生学”的五大核心要素: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息。“大道和生学”是以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万物生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促进人的个体生命、人类生命和社会生命、自然界生命健康成长、幸福成长,皆大欢喜!
当代社会,弊端丛生。如从文化角度以西方为例而论析之,则可看到西方人以科学的方法看物质,固然引发出许多抽象精密的科学理论和发明创造,使工业社会创造了人所兴知的辉煌成就。但因之而忘乎所以,对大自然索取无度,永不餍足;又奉行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主义,肆无忌惮地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须知,人类仅仅掌握和运用与物质享受有关的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寻求与精神生活有关的高层次的知识与境界。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西方就全然没有这种知识与境界,但从总体上看,西方精神文化中居于主流的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思想,它是在所谓自由主义权利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而且更是一种全面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和目的而以社会为手段和形式的思想理论,早已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各种制度之中,不仅与资本主义制度血肉相联、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等。不可否认,自由主义的功利学说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上及现实社会中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社会早期,它对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培育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挥个人的潜能,推动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建立资本主义文明等无疑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推演,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表现出的贪婪攫取性和享乐主义正在严重地销蚀着资本主义社会,使之陷入越来越深重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当中。由于个人主义的泛滥,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联系之间的平衡已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了“现代性的病症”。由于人人都只关注自己,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感,社会分裂成无数自我封闭的原子,相互碰撞而缺乏理解和沟通,社会也就成为没有凝聚力的“沙砾场”,呈露出濒临崩溃的危机。所以,经济、科技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强盛,给人一种资本主义还有无限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假象,而实际上,透过表像深入到文化层面来分析便不难发现,内在危机早已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与发展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当今中国,问题不少。随着改革和开放,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来各种各样的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陆,这对促进近40年来社会经济进步和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现代产业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瘟疫”也迅速蔓延了开来,造成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异化,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正常轨道而走向极端。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公与私等等之间失去了平衡,导致了多种关系的不和谐。这主要表现在几方面:
(1) 在个人身心之间,由于身处商业化社会的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加之人际疏离、亲情淡漠、竞争激烈、生活紧迫等,导致许多人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裂,并由此而引起的焦虑、孤独等,使酗酒、吸毒、赌博、凶杀、自杀、精神失常等现象不断上升,不仅毁灭了精神失衡者个人及其家庭,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
(2) 在家庭之间,仅就婚姻问题而言,由于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性解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而由家庭解体所导致的老人失养、子女失教、人们精神失所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已在我们这个东方伦理大国呈日趋严重之势。
(3) 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个人主义极端发展,为了一己私利和享乐,一些人惟利是图,毫无信义,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甚至杀人越货,不择手段,无所不为,连亲人之间也相互算计、欺诈伤害,什么良知人性、天理人情全遭践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猜忌和仇视造成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4) 个人与社会之间,本是同生兴荣、共同发展的关系,但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高度膨胀,一些人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要权利、不履行责任和义务,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思道义、不讲廉耻、不顾人格和国格。
(5) 人与自然之间,本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但为了满足人的自我欲望,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财富,只讲征服自然而不思保护自然,以致使科学成了毁灭自然的武器,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等等无不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
(6) 在公与私关系方面,由于把“人都是自私的”观念推向极端,一时间“盗窃无害有益”论竟成为“主流”话语,甚至还有“著名”学者在提倡“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于是导致腐败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权势者中饱私囊之时,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受到极为严重的侵害。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我们应当到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求智慧,应当依据对时代精神的把悟并从现实社会需求出发去对传统作出现代性的创新。而钱耕森先生构建的“大道和生学”,“在实践上有益于解当今社会存在的四大危机:人的身与心的危机、人与人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人与自然界的危机;有益于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绿色中国,有益于我国的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示范,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能给人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启迪。
综上所述,钱耕森先生提出的“大道和生学”实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极有价值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不仅仅是钱先生个人的,不仅仅是安徽大学的,而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是人类的!
【作者简介】
陈寒鸣教授,江苏镇江人,在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兼任南京大学泰州学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专著:《中国企业文化简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上下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其先师黄宣民先生共同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卷本,2009年出版),参著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罗汝芳学谱》(阳明文库之一)等。另有200余篇学术论文散见于《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国际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历史教学》《中华文化论坛》等刊物,有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文化研究》及《新华文摘》等转载。
追念:钱耕森先生为何提出“大道和生学”
钱耕森先生
惊悉钱耕森先生过世
陈寒鸣
哲人竟逝令人悲
往事历历涌心田
卅余年前初相识
自此而结忘年谊
春秋转换二十度
和生之学力倡矣
承邀赴皖参盛会
畅论斯学会贤侪
哪知竟成诀别晤
繇今思来泪涕涟
钱耕森,1933年10月,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和张岱年两位大师。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国际知名学者。
历任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道家道教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学会常务理事,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委员,冯友兰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冯学论坛讲座教授,张岱年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宗教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顾问、研究员。兼任东日本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韩国东亚人文学会顾问,马来西亚孔学研究总会顾问、导师,加拿大中华学院客座教授,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学术委员、荣誉研究员。
钱耕森先生提出“大道和生学”的意义
陈寒鸣
【内容摘要】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究竟何在?长期以来,学者们见仁见智,提出了很多观点,而钱耕森先生积其六十余年学术积累,潜心研究,会通儒道,从中国先贤那里体贴出“大道和生”四字,用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并试图据之重新建构中国哲学史。这是很有意义的尝试。“大道和生学”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有现实应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文化;哲学智慧;精神价值;“大道和生”;钱耕森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延续5000余年的伟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如何评估这精神?有论者谓:“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特定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内在特质的基本风貌。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又有沉滞抑郁、激人图变的一面。优异的一面中蕴含着消极的因素,令人愤激的一面中包孕着值得宽慰、可以向另一面转化的潜在质素。”
学者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作了种种归纳,如以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以“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人文主义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等等。
钱耕森先生积其六十余年学术积累,潜心研究,会通儒道,从中国先贤那里拈出“道”、“和”、“生”三个概念,用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他在新著《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指出:“道”,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和”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与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精髓。……“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最根本的特点。紧紧扣住最基本的原动力、核心与精髓、最根本的特点,用“道”、“和”、“生”三个概念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周易》有“一阴一阳为之道”之说,又称天、地、人“三才之道也”;老子把“道”视为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同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 四十二章》)孔子则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名言。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认为,正是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故“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亦有论者说:“道无古今,但道生生不已,蕴含着时间上的历程,即有古今;道所生者,有古今、有旧生、有新生。对生生不已的道可以论,是为道论。……离开道论,便不可能言道生;离开道生,何以言道?……在道论中,与道符合、一以贯之而又深入人心、甚至为人喜闻乐见,在历史上一脉相承的道论,可谓道统。道统散见于各学科中,有学统,道统、学统运用并实践于政治活动中,有政统。道统、学统、政统,都是道或道论的展现。无论为学还是为政,不入统绪,不得其门而入,不足以为真学问、真政治。因为‘统’非其他,就是人类文明长期延续下来的优秀传统。”
其次,自黄帝提出“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尧帝提出“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理念以来,《周礼••天官冢宰•礼典》又提出“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思想,由此而形成十分重要的中华文化精神传统;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断涵化、融合发展成民族大家庭而成为世界史上的典范,无疑与此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一精神和传统不仅在历史上发展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我们处理世界各国的邦交关系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并且它与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的崭新的人权理念有彼此呼应的关系”。
最后,《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这奠定了中华文化精神的哲学基础,使得中华文化始终讲求如何使人及由人构成的共同体的生命生生不息,永续发展。并且,“生”与“和”紧密相连,“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生’是‘和’的目的、归宿点、最大价值、最高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最高理想,‘和’的本质与最大价值在于‘生’”。
因此,钱耕森先生以“道” 、“和”、“生”三个概念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颇为令人信服。
不过,在我看来,当以“大道和生” 来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时,尚需对“大”一概念予以足够重视。孟子从“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矣”(《孟子•尽心上》)的思想出发,明揭“先立乎其大”(《孟子•告子上》)之旨,强调道德主体意识,提倡“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确立尊道乐义的独立、自由、自尊、自主的人格。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如南宋陆九渊本孟子此论而力倡“发明本心”,自作主宰。他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犹如孟子,陆氏此处所说的“此心”,乃是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来指示本体。他将这本体又称为“本心”,谓其为内在的,本来就有的,是道德智慧的不竭泉源、纯善意识的无尽宝藏,而诸如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公正心等都不过是“本心”的表现。“本心”遇到相应的事物就会自然表现出来,如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见丘墓则生悲哀之心,见宗庙则起钦敬之心;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是知其多是,非知其为非……凡此种种,皆“本心”之发用。一切道德义理皆自“本心”流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即仁义之心、此理即仁义之理,故而“心即理”。在陆九渊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此良善“本心”,人应于此深思痛省,理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故其强调学者须先立志,自作主宰。他启发学者首先要认识自己,自觉意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天之所以与我者,凡、圣之间原未有异,因此不应该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不必把圣人当作偶像顶礼膜拜。若能发明此心,涵养此心,凡者即圣人。他告诉学者,本心自有明德,学者应先明己德,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而不必旁骛外索,作无益之求。自立者亦须自重,不能随人脚后,学人模样,“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懈怠流浪,患不觉耳,觉即改之,何暇懊惜?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如此”(《陆九渊集》卷四《书·与诸葛诚之三》)。自立又要培养宽宏力量,要认识弃发掘自身内在的力量,自作主宰,不能因外在习俗影响而夺己志。他说:“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陆九渊集》卷四《书·与曾宅之》)“请尊先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事皆备于我,有何欠阙?”(《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后世的王阳明及其后学均受象山这思想的影响,力倡“自作主宰”,如阳明尽脱“乡愿”之意而坦呈“狂者胸次”;王艮自尊自信,赤身承当,磊磊落落,毫无媕婀媚世之态;颜钧则赋诗道:“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与古人盟。”我认为,这样一种“大”的思想与实践、这样一种“大”的人格和气节,同“道”、“和”、“生”一样,也生动展现了十分珍贵的中华文化精神。千万年来,中华民族所以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此有关。
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揭扬中国文化传统精神而特别重视“道”、“和”、“生”三个概念,而是从此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哲学史,试图对中国哲学史作出新的描述、解释,这是钱耕森先生近二十多年所作的重要学术工作,是他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如一部中国哲学史究竟应从何处开篇?上世纪初叶,陈黼宸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首开中国哲学史课程,从三皇五帝讲起,由伏羲而商朝讲了整整一年,给学生们提供了无数材料;稍后,改由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他以《诗经》作时代的证明而从周宣王以后讲起,在学生中引起轰动性反响。顾颉刚对此忆述道:“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傅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的。……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惊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后来,胡适写《中国哲学史》(上卷)始于老子,冯友兰的二卷本《中国哲学史》则始于孔子,这两种主张流行至今近百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有很大影响。而钱耕森先生毅然对胡、冯二氏的主张提出异议,认为中国哲学史应始于史伯,其理由是:
第一,史伯是一位哲学家,他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他所构建的“和生”哲学,有背景、有理论、有论题、有论据、有论证、有践行、有影响。其体系最核心的内容是三个命题:“夫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同之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其中“以他平他谓之和”,是史伯对“和”下的一个定义。这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和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定义,又是历久弥新的一个经典性的定义。史伯提出的“和生”哲学,以及“和异禆同”精湛的辩证法观点,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极其深远。
第2, 史伯是西周末年人,约早于老子和孔子200年。他的“和生”哲学,直接影响了老子和孔子,是他俩的先驱,因此可以说史伯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大哲学家。这就“使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顺理成章的从前5世纪的老子、孔子提前到前七八世纪的史伯,完全可以也应该大大地提前二三百年”。他并进而认为:“史伯比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早约200年。所以,他也可称为中西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哲学家。”钱先生的这一研究发现,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在钱耕森先生之前,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已有专节“伯阳父论‘和’、‘同’”,对伯阳父即史伯的“和同”论有所论析:什么是“和”与“同”呢?“和”就是“以他平他”。所谓“以他平他”,是指各种不同事物的配合与协调。伯阳父认为事物是由“土与金、木、水、火杂”而生的。事物相杂,协调配合,用长补短,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足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悦耳,正七体(七窍)以役心……”(《国语·郑语》)。由此进而讲到政治。政治上也应提倡“和”,君臣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所谓“同”,指的是事物的单一性。单一的东西不能长久,“同则不继”,“以同禆同,尽乃弃矣”。又说:“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无讲。”……根据“和”、“同”的理论,王应顺“和”弃“同”。“和”最关重要的是“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君主必须纳谏,对事情进行比较,才可能巩固政权。可是幽王却与此相反,幽王弃和“而与剸同”,拒谏饰非,拒“明德”之臣,听阿谀奉承之词,重用“谗匿”之人。根据“同则不继”的道理,断言幽王不会长久。这里当然也注意到了史伯“和同”论的哲学思想性,但主要是从政治思想史处所作的论述,且并无高度评价,如指出:“史伯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互相补充的道理引出君主应该纳谏。然而应该不等于现实。幽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这就说明个人专制同纳谏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的联系。纳谏虽是一种美德,由于没有制度的保证,常常流于空谈。事实上,在专制主义条件下,纳谏只能是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
而钱耕森先生对史伯的研究,与刘氏有诸多重大不同。
第1, 刘氏以为伯阳父(甫)即史伯,钱耕森先生则经考论断言“史伯与伯阳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史伯与伯阳父同为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代的大臣。周幽王在位的时间很短,从公元前781年至771年,连头带尾仅有11年。这两位大臣的主要事迹都记录在文献《国语》里”。“ 史伯与伯阳父二人虽然同时都是周幽王的大臣,都功勋卓著,且思想深邃,富于创新,都预言用幽王的西周必将灭亡,但是他们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具体活动以及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都是不相同的”。
第2, 刘氏所论及言及史伯的“和同”,而钱耕森先生则注意到“史伯既用了‘和合’,又用了‘和生’,还用了‘和同’”,指出:“在史伯那里,‘和合’具有方法的意思,‘和生’是哲学上本体论与生成论的范畴。‘和’是生成万物的本质,万物是由‘和’而生的。‘和同’,补充了史伯对‘同’的肯定看法,体现了他对‘同’的视阈具有全面性。”
第3, 刘氏从政治思想史角度论史伯的“和同”,并无太高评价,而钱耕森先生则从哲学史角度对史伯予以高估,称其为“中西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哲学家”。
钱耕森先生不仅将史伯的“和实生物”新诠为“和生”学,将“以他平他为之和”说新
诠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经典性的哲学命题,而且将老子的“道生”说新诠为“和生”说,并将之与史伯的“和生”相打通,认为:“老子的‘道生’说其实也就是‘和生’说。老子直接继承了先驱史伯的‘和实生物’的理念,又在自己的‘道生万物’的立场上,极大地改造发展了史伯的‘和生学’。”“史伯开创了‘和生学’,老子建立了‘和生学’,史伯与老子共创‘和生学’。”他又进而打通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庄子的“气生”说以及《周易》的“太和”说,还将有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新建为“生物之用,和为贵”,揭示了“和”的本质与最大价值在于“生”。经过这样创新性地构寻,钱耕森先生构建了一个“大道和生学”新哲学体系。
回视中国哲学史,所谓“轴心时、时代”原创性大师姑置不论,后世有创造精神的思想大家,每每从前辈、尤其是“轴心时代”原创性宗师及其留下来的经典中汲取智慧,并从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社会需求出发,开掘传统智慧,进而据之提出自己的新思想。这样的新思想,必然以传统为依据,以当下为出发点,而以引领未来为旨归。
如宋代二程及其后继者朱熹以《礼记·乐记》中“天理”二字为据而提出的以“天理”为核心观念的理学思想体系;明代王阳明以《孟子》中的“良知”二字为据而提出“良知”论的心学思想体系;如此等等。
而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和生学”新哲学体系,也是这样一种以传统为依据、以当下为出发点而以引领未来为旨归的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钱耕森先生在《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说他创立“大道和生学”是受到其两位恩师金岳霖和冯友兰的教诲与启迪,“金先生对‘道’情有独钟,对‘分析哲学’造诣精深,以其名著《论道》构建‘道’的新哲学体系;冯友兰高度评价为‘论超白马,道高青牛’。冯先生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十分重视‘和的哲学’,他早年提出‘大和’说,认为‘各种好皆包在内’是‘唯一的好’,晚年提出了‘和解’说,认为张载所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在我看来,钱耕森先生虽其学有所授受,而“大道和生”四字乃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在为《大道和生学研究》所作“序”中赞之曰:“‘大道和生学’,创于史伯,立于老子,而先生继以倡之,文化一线命脉,虽时缀时续,终得以大明于今世。”苏州大学的蒋国保教授在提交给“2018全国‘大道和生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大道和生学”之我见》中,提出如果只就学说架构形式来看,区分学说类型不外乎一种划分,就是看其是“创作”之学还是“述作”之学。所谓“创作”之学(简称为“作学”)是从作者自身的哲学理念出发来剪裁哲学史史料,将哲学史史料化为构是自己哲学体系的有机元素;而“述作”之学(简称为“述学”)则是作者以客观的态度对哲学史史料加以梳理与解释,但这种梳理与解释却未必建立在作者自己的哲学理念之上。
“作学”与“述学”,二者并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低之分,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就是“述学”的光辉典范。当孔子说他在学术上“述而不作”(《论语·述而》)时,他是要突显自己的学说在思想上与周代文化精神的内在本质联系,并非否认其“仁”体“礼”用学说对周代思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后孔子二千多年的清代学者汪中,之所以将其考据、释文、证义、辨伪等文章汇集命名为“述学”,显然不是为了强调其学只“述”不“作”,而是为了方便对自己的学问作全面的表述。这样的“述学”,既“述”且“作”,又“作”又“述”,“述”与“作”有机一体,“作”寓于“述”之中。在国保教授看来,“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虽不自命‘述学’,却正可谓名副其实的‘述学’”。
钱耕森先生在《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自谓:“大道和生学”是我多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生”思想,进行挖掘、梳理、研究与创新,所形成的“和生学”的新哲学体系。它所回答的是宇宙万物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大道和生学”主张“万物产生于大道之和气”。“大道和生学”这一哲学体系,理论渊源于史伯的“和生”说、老子的“道生”说、庄子的“气生”说和《周易》的“太和”说与“生生”说。这一哲学体系的研究特点是即哲学史讲哲学,将传统哲学中4个重要的核心理念,“道”“和”“气”“生”相结合,作为理论命题,并以大道立论,将“和生学”提升到“大道”的本质与规律的高度,形成为“大道和生学”。所谓“即哲学史讲哲学”,实际就是既“述”且“作”,寓“作”于“述”的“述学”。这种“述学”,是他对孔子“述而不作”文化精神的继承。
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反映了当下的时代精神和现实社会需求。他在《大道和生学研究•前言》中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大道和生学”充分反映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大道和生学”在理论上发展了“和”文化,创新了“和生”学。“和生”即“和谐共生”,是生命共同体的相融共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和生学”的五大核心要素:多元、平衡、和谐、共生、生生不息。“大道和生学”是以人的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万物生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促进人的个体生命、人类生命和社会生命、自然界生命健康成长、幸福成长,皆大欢喜!
当代社会,弊端丛生。如从文化角度以西方为例而论析之,则可看到西方人以科学的方法看物质,固然引发出许多抽象精密的科学理论和发明创造,使工业社会创造了人所兴知的辉煌成就。但因之而忘乎所以,对大自然索取无度,永不餍足;又奉行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主义,肆无忌惮地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须知,人类仅仅掌握和运用与物质享受有关的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寻求与精神生活有关的高层次的知识与境界。当然,也不能绝对地说西方就全然没有这种知识与境界,但从总体上看,西方精神文化中居于主流的个人主义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思想,它是在所谓自由主义权利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这种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道德原则,而且更是一种全面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强调以个人为本位和目的而以社会为手段和形式的思想理论,早已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各种制度之中,不仅与资本主义制度血肉相联、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等。不可否认,自由主义的功利学说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历史上及现实社会中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社会早期,它对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大胆追求个人幸福,培育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发挥个人的潜能,推动商品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建立资本主义文明等无疑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推演,发展到今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表现出的贪婪攫取性和享乐主义正在严重地销蚀着资本主义社会,使之陷入越来越深重的文化和精神危机当中。由于个人主义的泛滥,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个人自由与社会联系之间的平衡已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了“现代性的病症”。由于人人都只关注自己,失去了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感,社会分裂成无数自我封闭的原子,相互碰撞而缺乏理解和沟通,社会也就成为没有凝聚力的“沙砾场”,呈露出濒临崩溃的危机。所以,经济、科技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强盛,给人一种资本主义还有无限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假象,而实际上,透过表像深入到文化层面来分析便不难发现,内在危机早已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生存与发展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当今中国,问题不少。随着改革和开放,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来各种各样的现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被引进到中国大陆,这对促进近40年来社会经济进步和人们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现代产业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瘟疫”也迅速蔓延了开来,造成人与社会不同程度的扭曲和异化,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正常轨道而走向极端。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公与私等等之间失去了平衡,导致了多种关系的不和谐。这主要表现在几方面:
(1) 在个人身心之间,由于身处商业化社会的人们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加之人际疏离、亲情淡漠、竞争激烈、生活紧迫等,导致许多人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裂,并由此而引起的焦虑、孤独等,使酗酒、吸毒、赌博、凶杀、自杀、精神失常等现象不断上升,不仅毁灭了精神失衡者个人及其家庭,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
(2) 在家庭之间,仅就婚姻问题而言,由于强调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性解放,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单身家庭、单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而由家庭解体所导致的老人失养、子女失教、人们精神失所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已在我们这个东方伦理大国呈日趋严重之势。
(3) 在人际关系方面,由于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害关系;个人主义极端发展,为了一己私利和享乐,一些人惟利是图,毫无信义,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甚至杀人越货,不择手段,无所不为,连亲人之间也相互算计、欺诈伤害,什么良知人性、天理人情全遭践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猜忌和仇视造成了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4) 个人与社会之间,本是同生兴荣、共同发展的关系,但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高度膨胀,一些人置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利益于不顾,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要权利、不履行责任和义务,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思道义、不讲廉耻、不顾人格和国格。
(5) 人与自然之间,本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但为了满足人的自我欲望,无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财富,只讲征服自然而不思保护自然,以致使科学成了毁灭自然的武器,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等等无不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
(6) 在公与私关系方面,由于把“人都是自私的”观念推向极端,一时间“盗窃无害有益”论竟成为“主流”话语,甚至还有“著名”学者在提倡“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于是导致腐败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权势者中饱私囊之时,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受到极为严重的侵害。如何切实有效地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着的种种问题?我们应当到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求智慧,应当依据对时代精神的把悟并从现实社会需求出发去对传统作出现代性的创新。而钱耕森先生构建的“大道和生学”,“在实践上有益于解当今社会存在的四大危机:人的身与心的危机、人与人的危机、人与社会的危机、人与自然界的危机;有益于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绿色中国,有益于我国的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示范,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能给人们提供诸多有益的启迪。
综上所述,钱耕森先生提出的“大道和生学”实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极有价值的思想。这样的思想,不仅仅是钱先生个人的,不仅仅是安徽大学的,而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是人类的!
【作者简介】
陈寒鸣教授,江苏镇江人,在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任教,兼任南京大学泰州学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专著:《中国企业文化简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上下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与其先师黄宣民先生共同主编《中国儒学发展史》(三卷本,2009年出版),参著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罗汝芳学谱》(阳明文库之一)等。另有200余篇学术论文散见于《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国际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历史教学》《中华文化论坛》等刊物,有多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文化研究》及《新华文摘》等转载。
《大学》第60课 君子有大道
在讲平天下的过程中《大学》有三次都谈到了得与失。
第一次是在道得重则得国,失重则失国,告诉我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第二次是在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教诲我们天命无常,但也有常。一个人心善行善则天命护佑;心恶行恶则天命被欺。
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句原文:
事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君子有一条大道忠信立身就能和大道相应,而骄傲自满就会和大道相悖。我们知道这里说的君子不是指那些外在地位很高的人,而是指内在品质高尚的人。就是我们从百日成长第一天就在讲的大人。
所谓大道也是《大学》在一开篇就给我们揭示的大学之道,本质上就是大人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有中性这样的品质就能够得到大人之道;那如果是骄傲自满了,就会失去大人之道。
我们看这前后三次提到的得失,是先从得人心谈到了得天命,最后又谈到得大人之道是一种层层深入的递进,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学》全篇的一以贯之和首尾的呼应。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一看,今天原文当中这四个特别关键的字,我们总结为忠性骄泰这四个字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第一个字忠就是忠诚的忠。从字形上来看,忠这个字上面是中间的中,下面是心,这里就有两重寓意了。
第一、由心而发真实不欺。
第二是在心上不偏不倚很中正。什么意思呢?在《传习录》当中,有一位弟子就曾经问到阳明先生心上不偏不倚,究竟是何等现象呢?
阳明先生回答说,没有染浊才能不偏不倚。一颗没有染浊的心就体现为我们的清澈良知。良知清澈,自然就能知善知恶,知善知恶自然就能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所以古人就把这个忠字解释为内尽其心,而不欺也,可见忠的本质就是诚意。有了这份纯粹的诚意,才能够达至清澈的良知。
第二个字是信,我们今天常常讲相信,就是指在内心深处坚定的认为某个人事物,它是正确的,真实的,这就叫做信。可是信也有迷信和正信之分了。如果是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而完全没有甄别呢,这就叫做迷信。相反,如果是用清澈的良知去感应这个世界,在洞察了它的真相和本质之后,再审慎的做出选择,那这就叫正信。
比如阳明先生在龙场悟道之后,就对心中拥有无尽宝藏有了极其深刻的明白和体证,所以才教诲我们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也是阳明先生的信。由此可见,信的本质是明,它的根源就是对心中拥有无尽宝藏的明白和体证。我们简单来说,所谓忠讲的就是诚意。
因为诚意而达至了清澈的良知,也所谓至诚如神。信归根结底说的是对心中拥有无尽宝藏的相信、明白和体证。
骄说的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而泰说的就是一个人从内心深处轻视他人。但凡是有一丝一毫认为自己了不起,轻视他人这样的起心动念不管我们有多大的功劳,多大的本事,本质上已经把自己和这个世界割裂开了,是把自己推到了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故骄泰以失之。
相反,一个至忠至信的人明白和体证到的是天地万物都是自己的心中宝藏,所以才不敢有一丝一毫的不好的起心动念。生怕这些不好的起心动念遮蔽了自己的心中宝藏。这样的人就能和大学之道,大人之道同频共振,故忠信以得之。
忠与信这两个字看似简单,却是分量千斤。忠和信,它既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护身符,也是我们洞察他人、发现人才的两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