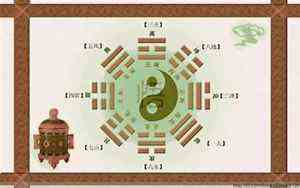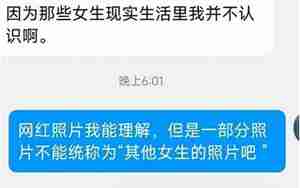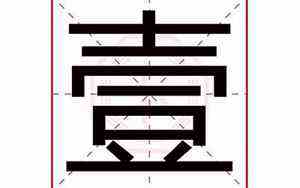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是学科基础也是学科方法:史学史学科地位解析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向燕南
摘要:作为对学科的反思,史学史在历史学的整个学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史学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第一,从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上看,作为历史学统摄下的首个二级学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体现了学科设置者对其在历史学中基础性地位的理解;第二,从历史知识(认识)论看,作为真实历史替代品的历史文本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中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具有史学史的性质;第三,研究历史有必要事先对赖以认识客观事实的历史文本进行史学史研究,这意味着史学史还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自觉有助于推进对历史的求真。
作为一门具有学科自我认识、自我反思性质的学科,史学史具有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虽然史学史被教育部规定为历史学科的必修课程,但在很多院校包括一些顶尖院校的历史教学中,它并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一些大牌的专家教授,在诸如学科评议、职称评定乃至相关的学位论文答辩时,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些许的不屑。个中原因,固然与相关成果不够深入,明显带有程式化、教条化等不足有关,然究其根本,亦可能与史学界未能真正理解史学史的学科价值有关。本文试从学科设置、历史知识(认识)论及方法三个方面,解读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地位的问题。
一、从学科设置看一般观念中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地位
知识在簿录分类结构中的位置,也可看作是人们一般观念中对于知识层级秩序的理解。当然,知识秩序的安排会受权力的影响,如传统文献中经史子集的顺序,传统史部目录下的正史、编年、别史、杂史等,诸如此类,其背后都可以寻绎到权力的影子。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像今天图书分类中位列第一的A类,它基本属于我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撰述的经典著作,以及对这些经典的解读著作。除了权力对知识统摄关系的影响外,知识系统自身的统摄层级关系也是在知识关系理解下的对知识统属进行顺序排列的依据。例如,传统类书中天、地、人的顺序安排等,也是决定知识簿录分类结构的基本因素。应该说,这种知识层级的统摄关系,也是现代学科设置背后所体现的对于学科内在关系的一般理解。
关于知识系统主干与分支之间的统摄层级关系,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有着很鲜明的体现。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各个学科门类之下,皆设有若干一级学科,并在一级学科的基础上,再设置若干二级学科。其中,一级学科的划分,是根据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需要;其属性则表现为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至于二级学科,则是根据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在一级学科内再进一步划分若干种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这些相对独立的学科或专业,共同属于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这样,通过学科一二级关系的设置,人们也就对某一门类知识的每一学科总、分之间的统属关系,表达了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历史学及史学史在学科目录中的设置情形。
中国由国家发布的学科培养目录始于1983年。1983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个草案中,我们看到,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属分列的第一个二级学科,就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此后,1990年10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以1983年《学科专业目录》为基础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获得批准。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再次联合发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包括历史学等12大学科门类,72个一级学科,249个专业即二级学科。从上述国务院三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看,历史学作为一级学科,其下统属的二级学科首列学科始终是“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这样的学科体系直到最近才发生变化。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将“历史学”分为“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分列其下并大体上仍然保持首重地位。例如,“考古学”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考古学史和考古学理论”,“世界史”下的首个二级学科是“世界史学理论与世界史学史”;只有一级学科“中国史”下的二级学科,将“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的“史学史”前,冠上了“中国”属性,称“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置于“历史地理学”和“历史文献学”之后。虽然如此,1983年以来国家多次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与史学史的统属关系及其位置,不管是否出于自觉,仍然能够反映历史学界对于自身学术体系认识的一般观念。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在历史学之下所处的位置,充分体现了该学科在历史学中被视为基础性地位的认知。
除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外,学科、专业设置的具体名目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史学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史学史”,是被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设置的。尽管在2011年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历史学设考古学、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但在总的方面依然大体保持了旧的二级学科的分科精神,如世界史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考古学下属的二级学科首列“考古理论与考古学史”。而在其他学科如文学学科中,作为学科理论的“文艺学”或“文艺理论”,与作为学科发展史的“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等,则属于分立的不同的二级学科;在法学学科中,其下属的二级学科“法学理论”与“法律史”同样是两个分开的学科。总之,在各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中,可能只有历史学,是将学科理论和学科发展的历史放在一起作为一个学科来设置。
为什么历史学科会这样设置?应该说,这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有关。按照现在一般的理解,史学理论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史学理论包含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史学理论仅指史学理论。这种分别,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区分的翻版。这个分法,最初要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沃尔什。当然,这样的划分也存在争议。【1】这里且不说任何历史理论本质上也是一定的史学理论支配下的产物,即在实际认识中,历史和史学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纠缠、难以截然划分的;因为仅就史学史学科而言,其所探讨的内容,不外是有关人们如何认识客观历史,以及人们在这认识的实践中如何认识这种认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史学史事实上是将对本体的认识、对主体的认识及对学科的认识三方面融汇在一起的反思。这样的事实,既体现了史学史在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统合为一个二级学科在知识构成上的依据。即,这一个二级学科的背后,既是知识(认识)论层面上人们对这两个学科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史学史学科与整个历史学之关系有别于其他学科中学科理论和学科史之关系的体现。当然,若要更深入地认识这中间涉及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从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层面详加讨论和说明。
二、从知识论的层面理解史学史学科的基础性
要想真正认识史学史学科对于历史学学科的基础性,或真正理解历史学学科设置背后的理论依据,就有必要循着康德“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简单梳理一下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作为现代的一个常识,作为“经验”的而非“超验”的存在,历史本体之“在”【2】无疑属于客观性的“定在”,也就是有规定性的存在,即“在者”。但是,历史本体之“在”的规定性(事物的规定性同时也是事物的限定性),使之与其他经验之“在”,存在明显的不同。即,时间的一度性规定了历史本体之“在”,虽为经验的、确实存在的客观,却无法直观地获得。也就是说,客观的历史从存在论讲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即“不存在”的存在。尽管可能会有像“弹洞前村壁”之类的遗迹传递着曾经有事发生的信息,但是事件的完整经过及缘起,则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时空中再现。当然我们可以说,从连续性来讲,作为曾经的存在,不在场的过去始终规定着后面的来者;但是,就认识来说,我们怎么认识、辨识、触摸这已经消逝在时空中不再存在的客体呢?或者说,作为认知主体的“我”(历史研究者),如何超越“主体自身”,去确切地直观把握那个(消逝于时空中的)“客体”呢?抑或说,“我”怎么知道“我”所获得的关于历史的知识是确切的、可信的、毋庸置疑的呢?对于历史的认识者来说,这的确是个令人“讨厌”的问题。于是,这个问题也就自然指向了有关历史的知识(认识)论这个如何理解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关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可说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在历史认识上的体现。只是,相较于其他具体的物理性的“在者”,如何认识历史之“在”的问题,更加令人困惑而已。
关于思维与存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考对后人影响巨大。康德一反古典哲学的提问方式,不再追问认识(知识)的客观性,而是反过来追问人的“认识(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不首先探讨认识的能力和性质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是完全不可能的。即,“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康德的追问最终导致了哲学认识论(知识论)的转向,人们开始对认识什么、如何认识以及认识何以可能等问题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为了解决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对立,寻求认识中主客体二者的统一,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路径展开探求。其中,现象学将认识主体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及其反思作为连接主体与客体的中介;哲学语言学者从语言的本质出发,将语言视为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卡尔·马克思则对旧唯物论与唯心论固执于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所造成的认识上的截然对立,提出尖锐的批评。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正是在扬弃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局限,在坚持外部客观世界对人的思维的“优先地位”的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马克思完成了以人的实践为中介联结主、客观世界的认识论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的认识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知识(认识)论,克服学界一些老派学人对于唯物主义的误解,进而认识史学史学科的特点及其价值是有帮助的。事实上,针对“历史是什么”的追问,也正是在认识论转向之后,才被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触及历史知识(认识)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在整个古典时期,尽管一些零星论述曾经提出过某些模糊的猜测,但就学术整体来说,要到19世纪末知识(认识)论拓及历史学领域以后,人们才认真地思考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认识的特点和局限的问题。
经过历史知识(认识)论转向的洗礼之后,人们对历史这个“在者”,作为认识对象所具有的不在场性而无法理性直观的特质,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即对于完全意义上的客观的历史本体,人类无论如何不能直观获得。这在决定历史学知识形态之本质特征的同时,决定了史学在获取历史知识(认识)的实践当中,马克思所谓“人在与世界关系中之能动因素”,较之其他“在者”的知识获取,占据更为关键的地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认识),几乎无一不是经过主体在完成对材料的理解和解释性选择之后形成的“一家之言”,即我们知道的历史,是被主体叙述并赋义之后才形成的有意义的、文本化了的历史。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按照解释哲学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包含了前人对历史理解和解释成分的“效果历史”(Effective history),是客观历史及主体对其理解的统一体。也就是说,在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解释中,主体的“偏见”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也是后人赖以对客观历史进行理解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从知识(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重新思考、定位文本的历史,或经过主体理解的历史与历史本体之关系的问题,便很自然地凸显了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柯林武德正是从历史知识(认识)及其表现的层面,提出了“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史学史”的命题。【4】从其相关论述看,这一命题实质上也从属于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说的命题,或者说是他的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体两面。但是,若从如何获得历史知识的事实上看,柯林武德认为,作为历史主观反思意义的史学史,应该较之直观的客观历史,更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这样一来,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研究对象的观念性与对它认识的现实性之间,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应该说,柯林武德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史学史的学科意义具有直接的理论启发。历史研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我们只能通过史学才能认识历史,这也是史学史在历史认识上较之直观的历史更具有逻辑优先性的体现。因为我们得到的有关过去的历史信息,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镜像反映出的直观的历史之真,而是史学家有选择地传达给我们的信息。例如,司马迁《史记》所预设的问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荀悦《汉纪》所预设的问题是“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司马光《资治通鉴》所预设的问题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杜佑《通典》所预设的问题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当然,就事实而言,一切遗存下来的文本,甚至包括当事者回溯性的复述,也同样存在特定语境和情感影响下对于事实的选择性组织的问题。正所谓“研究任何历史问题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second-order)历史。所谓次级的历史是指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想的历史”,即史学史的问题。【5】
我们不想对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同时也是史学史”与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两命题之间的关系进行辨析,也不想执着于主客二分的反映论的立场批判柯林武德“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只想从现代历史知识(认识)论的立场,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立场,强调这样的事实:人们只能通过史学来认识历史。因为作为经验后设性的存在,历史的书写只能间接地通过前人的文字及文物孑遗等,假以史家的思想推理和想象、赋义才能“完型”。这也就是说,对于后世来说,根本不存在主观与客观、观念性与现实性完全对立意义上的历史知识(认识)。而历史知识(认识)的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对于历史的“求真”,必须在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统一中思考。简单地说,“史学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史学就其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就其表述而言是主观的;史书的首要要求是如实,是符合客观历史,而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条件却在于史学家的治史能力和限度”。【6】这也就意味着,在探求历史本体之真前,我们首先要研究史学史,即有关客观历史之“真”是怎样因史学而呈现的。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研究,就不仅仅要研究前人提供给我们的结果,更要研究这些结果产生的过程,即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从史学工作的性质及特点看,我们所看到的,作为解读历史的文本,不过是一个结果。那么,文本形成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或文本是在怎样的情形中形成的?作为对历史本体反思的史学史,其在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史学史的学科价值,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在追问历史事实之前追问一下:这些史实产生于怎样的语境?又是怎样流传至今的?这些史实经过史家哪些筛选后进入他的叙事之中?为什么作出这样的筛选?这些史实的筛选和安排服从哪些叙事策略?背后有哪些政治、意识形态等权力因素,以及史家自我情感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而自己又是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些过去的事实的?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者在与历史进行对话之前,即在关心客观的历史是什么之前,有必要追问我们得到的信息为什么是这样。只有将史学史的追问,即历史知识(认识)的追问,置于对历史本体论的追问之前,我们才能保证所得到的历史本体的认识更接近于历史之真。由此,史学史学科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就不仅仅是对学科历史的反思,而且也具有了历史学的研究实践赖以展开的基础性。
三、从史学实践看史学史研究的方法意义
上述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历史研究者,其所面临的研究对象,不过是客观历史的文本替代物,而不是真实的历史,犹如画家的写生或画像,其所呈现给观众的作品,不过是画家对世界理解下的符码编辑产物。事实上,在历史认识中,人们也总是通过文字符码将其对于历史世界的经验转化成对客观历史世界的表现。也就是说,人们赖以认识历史的,实际上是历史文本的作者以其经验及其理解所转达的信息符码。这就是史学史学科之于历史学的基础性。
有如绘画,这些据以表达画家思想的信息符码,可以是印象派,可以是表现派,也可以是抽象派。同理,史家在文本中采取什么方式组织这些信息符码,同样取决于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而这些又无不受着史家自身及其时代的制约。诚如钱钟书所言:“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7】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总是解释者的历史;任何历史文本的背后总有史家及其社会的影子。历史文本的这种历史性,也就是史学史的学科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这句常被批评的名言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尽管客观历史这个“小姑娘”不会变,但是她会被人穿上不同的服饰,梳上不同的发型,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如此一来,讨论客观历史之前,就有必要先以史学史的方式同情地理解历史文本符码背后的史家及其是如何编码的。剥去那个“小姑娘”的种种外饰,才能显现出“小姑娘”的本真面目。一句话:只有经过了史学史反思的历史,才是更接近事实之真的历史。这也正是史学史对于历史学来说具有的方法上的意义。
其实,古代中国早就注意到史家对于史学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史家推崇的史学最高境界是“信史”。而所谓“信”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信,诚也,从人、言。”对此,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解释是:“言必由衷之意。”【8】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性,是要以传达历史事实的主体的品质,即史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为保证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中的所谓“知人论世”的认识,同样是强调理解文本作者对于理解文本的重要性。这在事实上也间接地反映出,古人亦意识到,文本与历史真实之间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古代一些史学批评的论著,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刘知幾《史通》及章学诚《文史通义》等,都有从历史文本撰述者的心态、品格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讨论历史文本这样的内容。其他一些学者也留下很多有价值的论述。例如宋代的叶适即指出:“载事必有书法,有书法必有是非。”【9】所反映的正是历史的书写中作者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的纠结。明代的王世贞所谓“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的“三史”之说,指出的同样是不同作者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问题。【10】
如果说中国古代史家的理论还不足以清楚说明史学史研究对于历史研究实践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如果再看看现代一些史学大家的学术实践,就会对史学史学科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方法价值和意义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言及现代史学史中成就最突出的史家,王国维外又有史学“二陈”即陈垣先生和陈寅恪先生,这可以说是没有人不同意的公论。两位陈先生之所以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文献史料注意本着“知人论世”原则进行史学史的分析。
先以陈垣老为例。陈垣老在研究实践中十分注意对文本的史学史理解。他不仅自己重视目录之学(史学史的一种形式),而且“金针度人”,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在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高校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和“史源学”等史学史性质的课程。在当时所写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教学札记中,陈垣老明确地注明该课程的目的,是要告知学生了解历史文本自身的重要性。其中,所需了解的要点是:“每一书到手,须先观其:出于何时,地位;出于何人,性情、道德、学问,各各不同。又须观其为官书,抑为私书。官书患其慑于势力,多所忌讳;私书患其惑于感情,多所恩怨。”【11】20世纪30年代,陈垣老在新的课程中又一次详细地说明,该课“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著者之生平,本书之体例,以及史料来源、编纂方法,板本异同等等,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12】20世纪40年代,当陈垣老再开此课之时,其课程说明除了依旧强调“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每书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板本之异同”,又增加了有关“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而其目的,依然是要以这些史学史的介绍,作为“学者读史之先导”。【13】唯因注意到历史文本的历史性,陈垣老除了对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史事”进行讨论外,亦注意对该书中有关“史法”即历史编纂方法的讨论。
当然,陈垣老学术实践中的史学史意识,也有一个随着对史学认识不断深入而增强的过程。被认为是陈垣老“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通鉴胡注表微》,【14】之所以被陈垣老自称“学识的记里碑”,【15】个中原因,就是陈垣老这部撰述于抗战时期的史著,以自觉的史学史意识,对胡三省隐藏在《通鉴音注》注文中的思想和情怀进行细腻的发覆和表微。书中,陈垣老指出:“不谙身之身世,不能读身之书也。”【16】“不谙身之当时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17】该书二十篇,前十篇讲史法,后十篇讲史事。其中,无论是言史法还是言史事,其旨都是在分析胡三省《通鉴音注》的“说什么”和“怎么说”,完全属于史学史的问题。经过陈垣老的发覆,不仅使沉埋于历史中的胡三省事迹昭揭于世,而且使胡三省的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得到更为准确的解读。
与陈垣老的史学史意识相类,但在方法上更具自觉性的,是陈寅恪先生。其中最具方法论价值的,是先生区分“今典”和“古典”,进而形成对历史文本作者“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这两点亦皆属于史学史认识的范畴。
陈寅恪先生论及“今典”和“古典”的问题,最早是在他1939年发表的《读哀江南赋》一文中。陈寅恪先生在文中说:“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18】此后,陈寅恪先生亦常常提及“古典”与“今典”的问题。例如他晚年“为示方法例”撰述的《柳如是别传》,即多处提及以“今典”发覆史事的方法。在首章“缘起”中,陈寅恪先生即着意指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19】其中古、今典之间,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古典”易解,因为“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于检索中可得;而于“今典”,其义则相对难以显明,“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20】也就是说,要理解“今典”,就必须将文本置于文本产生的语境之中,切身体会文本作者当时所经历的历史,以及作者因之而持据的特定的立场与情感,方能同情地体会文本的意蕴。因而,作为历史的研究者,需要“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21】通过对作品中古典、今典的双重释证,才能达到对文本的通解。也就是说,当依据历史上的文本材料说明历史事实时,有必要先行明了文本作者所欲说或所不欲说的原因及语境,即我们欲研究客观的历史,必须先行对所引文本进行史学史的分析,进而才能据以推求历史的本真。史学史的研究于此也就彰显出了它的方法论的意义。
现代史学史中,史学“二陈”之外,钱穆先生也是位有着明确史学史意识的大家。与史学“二陈”不同,钱穆先生常常针对历史知识(认识)的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而他的史学史意识,也正是建立在他有关历史知识(认识)论的认识之上的。因此,分析钱穆先生历史研究中的史学史意识,就有必要扼要介绍一下他的知识(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钱穆先生的历史知识(认识)论,概括有三点:第一,按照佛教“能所不二”的理论,提出“知是所知、能知相接而成”的知识(认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主客相统一的历史知识(认识)论。即,在承认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同时指出,历史文本实质上是主体情感和价值判断介入而再现的结果。他说:“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22】第二,在主客统一的历史知识(认识)论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的生命性,即认为历史是融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一体的文化生命,指出“研究历史者,实即研究此一有宽度之现在事件也”。第三,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的当代性或时代性、民族性。钱穆先生曾说:“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历史研究两要点。历史的记载,好像是一成不变,而历史知识,却常常随时代而变。”【23】
上述认识表明,在钱穆先生看来,历史文本中,作者的情感等主体因素的介入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因此,对于研究中所使用的文本史料的理解,也必须要具备对其历史的考量,就是阅读文本“当懂得上窥古人用心,”【24】“透过吟咏古人文章,逐步进入古人的心境的,理解古人的心灵与境界”,【25】才有可能达到对于文本更准确更真切的解读。如此一来,钱穆先生对于历史文本而理解的态度,也就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今典”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在具体历史的研究中,钱穆先生也是这样带着史学史的意识去认识和使用文本材料的。例如他的《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就是通过明代不同时代文本材料的分析,探究其“时代内蕴心情”的作品。
应该看到,目前除了一些年龄较大的史学工作者仍受马克思所批评的“旧唯物论”影响,表示对建立在主客体融通的认识论下的新的历史理论难以接受,视之为“唯心主义”外,大多数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已逐渐意识到历史中主体因素的影响,史学史在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的意义也逐渐获得一些学者的认同。这里且不说作为研究起点的学术史回顾本身就具有的史学史属性,仅就近来出现的一些成果看,在后现代主义文本分析理论的影响下,原本被研究者视作客观的历史记载背后之具体语境的影响,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形成了一股使用“史料批判”探讨历史问题的方法热潮。这里所谓“史料批判”,究其实质,无疑是建立在新的历史知识(认识)论基础上的、属于史学史的方法范畴。这些通过历史文本的史学史考察的成果,将历史文本置于文本产生的语境之中加以理解,显然增加了历史追问的深度和对历史事实认识的厚度,使历史研究更接近历史之真——尽管一些学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作的这一层追问实质上就是史学史的工作。因此我认为,假若每一位史学工作者,都明了我们只有通过史学才能认识历史和理解历史的事实,在反思历史之前,自觉地先建立一个对于史学反思的自觉。(当然还要建立对自我的反思,因为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其自身也同样具有历史性、局限性。)这种研究的程序方法,也就是E.H.卡尔在其《历史是什么?》所说的:“在研究历史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26】我想,这些史学史方法自觉的建立,庶几对于史学的求真实践,肯定会有不小的推进。
注释
【1】按,沃尔什的相关论述主要在《历史哲学——导论》第一章第二节中。按照沃尔什所说,他这样区分,是参考了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其中所谓“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研究自然时间的实际过程,着眼于构造一种宇宙论或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明自然界”。所谓“科学哲学”,“其任务则是对科学思维的过程进行反思、检查科学家们所使用基本概念以及这类的问题”。对于历史哲学这样的划分,虽然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实际上应该说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因为与自然界和科学相比较,历史学具有的主体性更为突出,即历史学是主体自觉不自觉地依从某种理论、从其现实立场前溯式叙述的产物,所谓“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他自己的观点在‘观看’过去的”。也就是说,在历史学中,“是”和“应该”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谓对历史自身的认识与对历史学的认识,或者说所谓历史理论与所谓史学理论,两者在事实上往往是紧密纠缠为一体,“历史真实性与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实际上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彻底明晰地划分出此疆彼界。唯因如此,对于这样的划分,不仅学术界一直有所争议,即使是沃尔什本人,也认为“它们并不总是以严格的准确性在使用着”。参见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这里使用的“本体”,乃中文意义的“本体”,即指事物的原样或自身,而非哲学意义的“本体”(being)。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页。
【4】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第三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关于柯林武德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的相关论述,分别见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柯林武德著《历史的观念》(其中有关论述见于该译本对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增补的“历史哲学讲稿”及“历史哲学纲要”部分);大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柯林武德的历史思想》(第三辑)“历史哲学”之三“历史哲学纲要”;以及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柯林武德自传》的第十一章。国内对此的相关论述,有学林出版社2013出版的张小忠著《思想的力量: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王利红、王丰收《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5】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124页。
【6】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7】钱钟书:《模糊的铜镜》,摘引自姜德明主编《七月寒雪:随笔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83页。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92页。
【9】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第9《春秋》,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本,第117页。
【10】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魏连科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11】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陈智超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1页。
【12】《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第1页。
【13】《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第1页。
【1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
【15】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
【16】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第528页。
【17】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第591页。
【1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1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缘起》,《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2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9页。
【2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9页。
【22】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8页。
【2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香港1964年增附本三版,第2页。
【2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314页。
【25】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26】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3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研究”(项目编号:12JJD770010)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打造大史学学科协同发展范畴 西北大学史学部揭牌成立
12月10日,西北大学史学部正式宣告成立。(摄影:马骞)
西部网讯(记者 彭芬)12月10日,西北大学史学部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王子今史学家工作室”挂牌。史学部成立后,将重点围绕学科交叉方向凝练、学科交叉团队组建、学科交叉平台搭建、学科交叉人才成果评价、跨学科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工作。
西北大学成立史学部 促进学术协同创新
成立大会上,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一级教授王子今,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王亚杰,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共同为“西北大学史学部”“王子今史学家工作室”揭牌。郭立宏为史学家工作室首席专家,史学部主任、执行主任、副主任颁发了聘书。
与会领导嘉宾为“王子今史学家工作室”揭牌。(摄影:马骞)
学部制改革试点是西北大学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学术协同创新、支撑“双一流”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性工作。继生命科学与医学部之后,史学部挂牌成立,标志着西北大学学部制改革探索又迈出坚实一步。
史学部涵盖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院、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中东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北历史研究所)、科学史高等研究院等学院和研究机构,同时吸收中共党史、文学史、新闻史、经济史、哲学史及信息学科相关研究领域参与建设,打造大史学学科协同发展范畴。其中,史学部的核心主干学科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和科学技术史是西北大学积淀深厚的传统优势学科,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声誉。
西北大学在充分赋予史学部自主权的同时,明确学部内各相关教学科研单位在现有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不变、积极推进各自一级学科建设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激发相关学院、科研机构创新动力和学部发展活力,凝练和突出史学学科优势特色,建立健全跨学科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水平学科团队,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增强服务重大战略需求能力,更加有力地支撑学校“双一流”建设。
成立大会结束后举办了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163讲,王子今教授为师生代表作了“秦汉儿童的世界”的专题报告。
西北大学史学部成立大会暨史学家工作室挂牌仪式举行。(摄影:马骞)
史学学科历史悠久 将打造学部制改革示范样板
据了解,西北大学史学学科源于1937年设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在历代西大史学人埋头苦干下,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标志性成果。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考古学取得了A+、世界史取得了B+、中国史和科学技术史取得了B的良好成绩。
对于做好学部制改革试点,特别是史学部未来的建设发展,王亚杰提出四点要求:一要着力交叉融合,推动学术协同创新;二要构建学科生态,促进学科内涵发展;三要大胆改革创新,打造学术创新高地;四要凝聚高度共识,激发学部发展活力。西北大学将举全校之力支持学部制改革试点工作,为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探索有益经验、提供示范样板。
张绪山:历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
近百年来,世界各国许多史学家为捍卫历史学的“科学”地位进行过辩护,但是“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命题迄今并没有得到正解。在20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间,我国正统意识形态接受斯大林“五种社会形态”的僵硬理论,将它诠释的所谓“历史的客观规律”定为一尊,使得以阐明“历史规律”为目的的正统历史学也当然地被视为“科学”。不过,我们注意到,最近又有学者讨论“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这说明在非学术因素干预学术研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以后,这个问题又重新成为人们探讨和认识的对象。那么,历史学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吗?或者说,历史学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
坚持“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其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历史。这个前提决定了历史不能由主观意识来改变,历史学不能由主观认定,而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产物。其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求真,其思想或理论应当是从历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诠释真实的历史,而且要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不断验证;不能“以史注我”,把历史当成主观思想的注脚或例子,任意剪裁历史。那么,史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史学家的求真使命这两个特点,是否能够让历史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呢?
要对“历史学是不是科学”做出清楚判定,一个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明白现在通常使用的“科学”概念所包含的本质内涵。如所周知,“科学”一词出现较晚,直到牛顿(1642—1727年)时代人们有时还以“自然哲学”指称“科学”。不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在牛顿之前的文艺复兴时代已经开始形成。严格意义的近代“科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组成“科学”各学科的具体知识成果,如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一是普遍适用于“科学”各学科的获取知识的全部程序即方法、原则。科学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各不相同,它们之所以都能够被称为“科学”,主要是因为它们遵循获取知识的相同的程序原则。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使用“科学”这个概念时,主要是指科学思维的程序和原则。爱因斯坦(1879—1955年)指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①。换言之,逻辑原则和实验原则是近代科学各学科共同遵循的获取知识的两个程序原则。因此,一个学科是否当得起“科学”这个称号,必须看它获取知识的程序是否遵循这两个程序原则。这两个程序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研究对象不为人的意志而改变,研究过程不容研究者的个人情感插足其间。
史学家追溯历史,主要依据的是文字形式的历史资料。就丰富多彩的历史存在而言,史学家所能看到的文字资料的范围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即使是以文字记载完备著称的“国史”,当史学家的研究进入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时,留存下来的证据材料仍然很不充分;而这些有限的证据材料又都经过了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记载者的思想感情的过滤,与客观的历史事实已经存在一定的乃至相当大的距离;更何况其中一些还受到有意歪曲,使记载下来的历史事实面目全非,以致高明的读史之人往往不得不慨叹“欺人青史话连篇”②,“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③。所以,尽管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但史学家借以追溯历史对象的凭据本身却是不尽客观的。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虽然使史学家可以利用的研究资料范围得到拓展,但考古证据的数量更是非常有限;而且作为历史证据,考古材料本身并不会开口说话,它本身的价值取决于具有强烈主观倾向的研究者的预设和判断。因此,历史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材料,都不具备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那样的客观性。换言之,历史研究的“证据”在客观真实性上的不充分与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绝对客观存在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张力乃至矛盾。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并不决定史学家的研究结果必然具有客观性。史学研究受制于史料的数量和性质,永远无法达到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要求的准确性和客观性的标准。
历史研究成果之所以在准确性和客观性上不及严格意义的科学研究,是因为它所使用的获取历史知识的方法原则不同于严格意义的“科学”。时间是历史演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时间本身的一维性,决定了历史存在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历史证据对以往客观存在的反映不能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通过有目的的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反复验证。虽然史学家们强调,“从历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思想或理论“要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验证”,但史学的所谓“验证”,充其量不过是将其特定历史证据条件下得出的结论“验证”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活动。但是要知道,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活动都不可能复制,不同于自然研究者以可重复性的系统实验对其结论进行的验证。自然运动具有“万世不变”的特点,这是人类社会不具有的。自然科学研究须臾不可脱离的实验原则,在史学研究中没有发挥其功用的天地。史学家在研究活动中所能坚持运用的原则只有一个,即逻辑原则。质言之,历史研究所能做到的,只是最大限度地搜索证据,然后做出相对严密的逻辑推论。但是,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主观上对历史材料的“竭泽而渔”,只具有相对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胡适所坚持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方法④。
历史学研究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史学家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求真,但史学家本身是具有丰富情感的活生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倾向无时无刻不对他的研究发生影响。如果说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鉴别还能较少地受到个人情感因素影响的话,那么他对历史活动内在动因的理解和诠释则无论如何都难以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史学家的研究结论,不仅受制于史学家的个人禀赋、性情、人生阅历、思想观念、对社会、人事的感悟能力等因素,而且更受到他所处时代环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的影响。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这个道理。这可以解释,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年轻时代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问题,何以在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阅历之后往往会突然间豁然开朗,大彻大悟;而对自己年轻时代自认为真理在握的历史认识,往往会在晚年不以为然乃至彻底否定。这也可以说明,对于历史上那些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的人物和事件,何以在不同时期的史学家,或同一时期的不同史学家,甚至同一史学家在其生活的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认识,有时差别之大至于天壤。同一个孔子,在一些时代被誉为道冠古今、德侔天地的“至圣先师”,而在“文革”时期却被称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老二”、“复辟狂”;同一个孔子,某位史学家在“文革”时期将其描绘成醉心复辟的跳梁小丑,而后在新时期又焕然一新将其描绘成了不起的伟大教育家。绝对客观的历史构建不是史学家不想做到,而是不可能也无法做到,原因即在于,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自始至终贯穿着人的情感因素的作用。
史学家所面对的历史资料,类似于考古学家所面对的几片小小的古瓷器碎片,根据这些碎片他可以不太困难地做到起码的一点,即肯定某种瓷器在过去的存在;但要由这几片小碎片推断或复原过去曾经存在的那个完整的瓷器,则是极为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史学家所能做到的,只是根据个人的才情学识推出一种可能性的结论,但这种可能性的结论不仅无法达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准确性(如可以用数学公式加以表达),而且也完全不能通过自然科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重复实验加以验证。这也就可以理解,相同的历史材料在不同的史学家手里,何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形类似于相同的泥、瓦、砖、石等建筑材料,在不同的工匠手里会成为不同的作品:蹩脚的工匠只能建造简单的房屋,而高明的建筑师则可以建造不朽的艺术杰作。如果认为相同的史料必然得到相同的解释和结论,则往往大谬不然。
所以,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的操守和德行往往是能否得出公正结论的关键;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臧否、“生杀予夺”,不仅取决于历史家的好恶喜憎,而且决定于史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正因为如此,“德、才、识”三者被视为一个优秀史学家的必备素质。然而,即使这三种品德都完全具备,其研究结论也未必完全可靠。道理很简单,历史学家的结论不管多么合乎逻辑,它本身无法得到实际验证。这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个人情感的无能为力:一个人是否具备高尚情操,往往并不影响他靠数理推导和实验手段得出的结论;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一个氢原子和两个氧原子在恒定条件下相遇都会生成水这种物质。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的一些科学家,作为法西斯的帮凶,竟然从事活人人体实验这样违反人性的事情,从人类道德的角度,他们无疑是德行欠缺者,是必须加以谴责的,但他们研究活动得到的成果本身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只有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学科那里才能够做到,而历史学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许多人文学者为了抬高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品位”和存在发展的正当性,动辄生拉硬扯地为其贴上一幅“科学”的标签。这种做法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在中国的特殊境遇有关。在20世纪初,“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以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为追求目标,认为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学术、思想等等一切方面的痼疾;为了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实现“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即伦理之觉悟,他们以“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决心,不遗余力地张扬科学,为科学意识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和科学威望的不断高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化人为了改变国人对来自西方的“科学”的畏惧心理,大力鼓吹“科学方法”的普遍适用性,把本来不属于科学范畴的人文学科也强行贴上了“科学”的标签。例如胡适说“国学”是科学,将墨子、朱熹和清代朴学大师都说成是与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巴斯德一样的“科学家”⑤。同样,丁文江则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詹姆士的心理学,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胡适的《红楼梦》研究相提并论,认为这些都是科学⑥。茅盾在1921年声称,文学也是一种科学,理由是文学“有他研究的对象,便是人生——现代的人生……文学者只可把自身就文学的范围,不能随自己的喜悦来支配文学。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没有一毫私心,不存一丝主观”⑦。甚至有人认为“侦探小说的本身是科学的”,原因是“对于情节的叙述,往往使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那就逃不出逻辑的范围”⑧。在当时的新文化人那里,逻辑可以径直与“科学”划等号,一切符合逻辑的思想、学说和学科也就都成了“科学”。“科学”的概念在程序原则内涵上的缩小,造成其外延的扩大,其结果是社会实践中“科学”概念的庸俗化。
不过,即使在那时,也有人在为科学而战斗、捍卫科学威望的同时,清楚地区分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特点。如中国科学界的先驱者任鸿隽就曾指出:“科学者,知识而有统系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今世普通之所谓科学,狭义之科学也。”他又说:“今之科学,固不能废推理,而大要本之实验。有实验而后有正确智识。”⑨可惜的是,这样清醒的认识并没有被大众所知悉和接受,成为大众的共识和常识。
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与技术的落后,使国人的心灵长期遭受着“百事不如人”的折磨。为了培养民族自尊心,“西学中源”论以不断翻新的形式被鼓吹和利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成为国人乐于接受的思维定式,《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被说成是古人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表述。其实,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所教导的只是有关“人事”的学问,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哲学。宋儒“格致”竹子的玄思冥想,明清之际考据之学的纸上功夫,根本不是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与近代意义上(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全不搭界。还有人说:“中国人并非没有科学上的智慧,只是以往没有向科学的路走……平心而论,明朝如果不亡于满清,那么依顺明末思想家顾、黄、王等人的思想,走儒家健康的文化生命路线,亦未始不可开出科学和民主。”⑩这种判断至少有一半是错误的:说中国人具备探索科学和接受科学的智慧,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怀特海1925年所说,科学“这种东西只要有一个理智的社会,就能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11);但是说明朝不亡,国人继承顾、黄、王等人的思想,走儒家健康的文化生命路线,就可以径直走向科学和民主,则是大错;原因在于,无论顾、黄、王等人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文化生命路线,都是内省的修身之学,而从来没有将自然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也从来不是自然界的严肃的研究者和解释者。这些牵强附会的观点,在误导国人对“科学”的认识的同时,也造就了以虔诚而少质疑、模糊而少分析、崇信而少理解的态度为特征的“科学信仰”(12)。
在“科学信仰”依然炽盛而又充斥实用主义意识的今天,“科学”这个名词庶几成了一个流行的时代“咒语”,以致街头算命先生也打出“科学算命”的招牌来招揽生意。在科学崇拜盛行的世风之下,“科学”成为一切学科追求和归附的对象;置于“科学”范畴之外的任何学科,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都会受到质疑。因此,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认为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不完全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特征,当不起完全的“科学”称号,这样的结论必然会对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历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命题的讨论,不仅关系到历史学本身的学科定性,而且也关系到它存在的合理性问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对于历史学等人文学科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讨论,无论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本身并不能成为肯定或否定其存在合理性的理由。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我国几十年人文精神缺失的教训告诉我们,科学和人文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绝不可偏废的。正如一个健康的人应该具备理性和情感两种基本素质一样,理性固然重要,但情感同样不可或缺,理性和情感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不能因为需要理性就否定情感的价值,也不能因为情感的存在而否定理性。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不完全从属于科学,并不是否定这些学科应该存在的根据。人文学科存在的正当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完备的“科学性”,而更在于它们的合理的“价值意义”,即服务于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好坏、善恶、美丑的判断。历史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在追溯、认识人类历史客观存在的层次上,具备了科学各学科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理性思维特点,即严格性和严密性,尽管没有达到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高度。在这个层面上,它具备了“科学”的起码素质,因而能为人类提供展望未来的凭据,使人们相信“鉴古可以知今”、“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的道理。同时,历史学在提供人们追求历史智慧、探求人性本质的心理需求的基础上,能够使人们在对历史存在的感悟和表达中获得愉悦和美感。因此,毋宁说,历史学给人们提供的理性思维手段、灵感智慧和愉悦美感,以及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美善与丑恶的判断准绳,才是历史学存在的主要理由。“读史使人明智”,这句话所要告诉人们的,不仅有真假是非观念,而且更有美丑善恶意识。史学的无穷魅力正在于此。
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江苏常州近代杰出人物简介(第三期)
洪深(1894年12月31日-1955年8月29日),学名洪达,号伯骏、浅哉,字潜斋,出生于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洪亮吉的第六世孙。民国时期导演、戏剧批评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剧作家、导演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电影、话剧的开拓者、抗战文艺先锋战士。一生创作电影剧本38部,创作与翻译话剧剧本55部,导演电影9部,导演话剧55部,著有影剧理论专著《洪深戏剧理论文集》《电影戏剧表演术》等12部。
刘海粟(1896年3月16日-1994年8月7日),名槃,字季芳,号海翁,江苏武进人。民盟盟员,中国近现代中国画家 、油画家、书法家、美术教育家、美术史论家、社会活动家。历任南京艺术学院一级教授、院长、名誉院长,江苏文联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等职务。英国剑桥国际传略中心授予"杰出成就奖"。意大利欧洲学院授予"欧洲棕榈金奖"。
董亦湘(1896年-1939年5月29日),原名椿寿,江苏武进人,中共党员。1924年创建无锡第一个党支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频繁往来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传播进步思想,宣传革命道理。1925年10月,党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与王明开展激烈斗争,受到诬陷和打击。1939年5月被迫害含冤而死。1987年3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万国鼎(1897年12月26日~1963年11月15日),字孟周,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小新桥乡。农史学家,中国农史学科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首届主任。终生旨在农史资料汇集和整理,农业古籍和农业历史的研究。他主持汇集和整理、分类辑成的中国农史资料共613册,4000余万字,并创办我国最早的农史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史研究集刊》,在国内外农史和科技史学界颇具影响。
张太雷(1898年6月17日-1927年12月12日),原名曾让,字泰来,学名复,自号长铗,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派往青年共产国际的使者之一。1927年12月12日,在广州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身亡,年仅29岁,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秦仁昌(1898年2月15日-1986年7月22日),江苏省武进区人。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生前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毕生致力于蕨类植物研究,是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蕨类学之父。早年创建了庐山森林植物园;领导云南金鸡纳和橡胶宜林地勘察和育苗造林工作;修订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系统。先后获荷属印尼隆福氏生物学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吴福桢(1898年-1996年),江苏武进人。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近代农业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他创建我国第一个药械实验所,又是农业昆虫学术团体的创建人之一、棉虫现代防治研究的先驱,对我国农业昆虫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建国后,历任华东病虫防治研究所所长,宁夏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昆虫学会第二届副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第二届理事、第三届顾问。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本名双,后改瞿爽、瞿霜,字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史良(1900年3月27日-1985年9月6日),字存初,江苏常州人。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活动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与奠基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曾任常州市学生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后,联合各种妇女团体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担任理事。1936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因参加与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为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法部部长、民盟中央主席。
王维克(1900年-1952年),江苏金坛人。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居里夫人的学生。爱好文学,酷爱翻译工作,一生译著有数百万字。主要译著除但丁的《神曲》外,还有印度史诗《沙恭达罗》(初版有柳亚子先生题词)、法国名剧《希德》(曾获中法联谊会文学首奖)、《法国名剧四种》、《法国文学史》、俄国《屠格涅夫散文诗》和比利时名剧《青鸟》等。他的主要编著有《热力学原理入《日食和月食》、《自然界印象记》等自然科学书籍。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近代名人,欢迎补充。喜欢就点赞关注小编吧,谢谢大家!
2023年中国台湾高考历史试题,你能做对几道?(附参考答案)
本文转自:史学科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