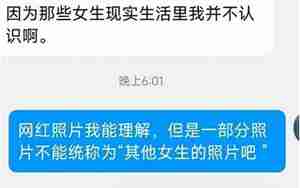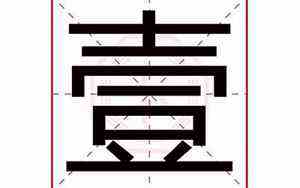埙字怎么念?
国粹古代十大名乐器「埙」演奏曲目合集,闭目清心聆听袅袅不绝
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乐器之一。在可考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确认,埙在战国初就广泛应用于宫廷的祭祀活动中。秦汉以后,埙成了宫廷雅乐乐器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只是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除了在欣赏宫廷雅乐时还可偶或一闻埙乐外,几乎不知道还有埙这样一种乐器了。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公演中埙乐几绝于耳。
古埙
八十年代以来,在演奏家、制作家和作曲家的共同努力下,埙作为乐器有了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制作,喜爱埙乐并且学习、演奏的人越来越多,习埙的热潮悄然兴起。从埙上人们似乎找到了遗失已久的古风,埙正在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大型歌舞剧《兵马俑》以及各地方戏曲等都出现了大量的埙乐作品,并且涌现出《风竹》、《楚歌》、《遐思》等优秀的埙独奏曲。
1.黄金成 - 流水行云 埙2.王次恒 - 寒江残雪 埙3.王次恒 - 苏武牧羊 埙4.王次恒 - 阳关三叠 埙
5.王次恒 - 月下海棠 埙6.赵良山 - 哀郢 埙
7.赵良山 - 楚歌 埙8.赵良山 - 湖乡春晚 埙9.赵良山 - 苦道行 埙10.赵良山 - 骆驼颂 埙赵良山 - 南乡小调 埙12.赵良山 - 长亭怨慢 埙埙
遇见埙早,熟悉却迟。像某些好友,初识只觉美好,而后搁置在岁月里,埋藏在通信录中,辗转一圈,偏又遇着了,还聊得热火朝天,惺惺相惜起来,这就近了。
埙也一样,几年前偶得一个,宝贝似的,放在书架上供着,看着。
那是陪湖北姑娘鱼儿去大雁塔游玩时,只觉这陶埙又雅致,又有历史遗韵,买回一吹,响是响了,嘴却黑了。
便摆在宿舍的书架上,倒添了些许雅意,后来竟跟着我辗转咸阳、北京多地,才又回到西安来。其间还在箱底压了许久,有一天突然就出来了,小儿好奇,拿着赏玩,最终,生命也终结在了他的手里。
就这样,还没来得及仔细的探寻,和它的缘也便尽了,倒是该说一句抱歉,虽说不是古物,毕竟是匠人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
身边却不知不觉出现了许多吹埙的好友,也不知是否我与这乐器当真有缘。或是早在秦汉时,祖上就有那么一位在宫廷吹埙的乐师,或是有位先人曾是民间烧埙的陶匠?总之,辗转一圈,我与这有着七千年历史之物,又有了牵染。
起初,是好友将自己的地方提供给了一个埙社授课,而我那时,恰有一段时间将那里当成了栖身之所,学习写作吃茶看书之地。自然,对这每到周五就蜂拥而至的一堆乌啦啦吹埙之人不怎么欢迎。况且他们正是初学,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吹出十几种音符,每每是听得我心烦意乱,在茶室坐立不安,只想逃离。
后来,却在一次采风时,与其中一位埙社的姑娘同行,姑娘性子温和,特立独行,又有些男儿的豪爽之气。吹起埙来,双眼迷醉,表情肃穆,指尖跳动之时,一个个悦耳的音符就唤出来,连成一串,串成一曲,曲声悠扬婉转,柔长动听,她微微颔首,偶尔随着曲子摇曳,似深思,似陶醉……一下子便被吸引了。
待私下里闲聊时,才知她果真每周五去友人的地方练习,看来是我先入为主的思想过甚,这才没有仔细地辨识来的都是些怎样的人,自然与她,也不相识。可待她询问我是否跟友人一起去看过汉服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竟有好几面之缘了,却是都没有记住,最终因这采风,才真正了解,谁知这一了解,便惺惺相惜了。
此后,偶尔得空,便腻在一起。姑娘喜骑摩托,常戴一顶黑帽,将长发掖在耳后,风雨里来,阳光里去。我便也随着她,戴上墨镜,坐上摩托,在夏日的夜晚,双手环绕抓住她腰部的衣衫,在这长安城,呼啦啦来,呼啦啦去,有时兴奋,也会张开双臂,迎接对面的风,在后视镜里看自己随风凌乱的长发。
长安城的夜,灯火辉煌,却从未如此穿行其中,仿佛一伸手,就能抓住耳边吹拂的风,就能触摸到路边高大的树。
以前,总是趴在车窗上,隔着玻璃,看那些呼啸而过的高楼大厦。如今,穿过小巷,骑行在城墙脚下,累了时,她便拿出埙,在城墙角落,在城门洞里,吹上一曲。仿佛只有这厚重的城墙,才配得上这悠远的埙声,每每这时,我都要想,如若这城墙上还有站立的士兵,他们是否会因这曲子,想起家中的亲人?旁边树梢上歇息的猫头鹰,又是否会竖起耳朵,跟我一样静静地聆听?曾经,长安城的乐师们,又将他们的埙曲,留存在了哪一寸土地上?
她吹得陶醉,我便也听得入迷,随着她的埙声,时而皱眉,时而微笑,有时竟也不自觉哼唱起来。夜里的城墙边少有人烟,除了两个幼小瘦弱的身影,固执地站立在这儿,除了那低沉婉转,古朴浑厚的曲声。曲子是《汉城谣》,我虽不懂韵律,但也从这曲声中,看到了三秦大地远古的沧桑历史,曲中时不时的蝉鸣之声,跟这夏夜,这城墙外的公园,这公园里盛开的莲交相辉映,人也就飘飘然,随着曲声游走了。
每每看她吹埙时,心里便生出向往来,也想要这美妙的曲子,从自己的手指跳动间,从自己的气息游荡中传出来,遂向友人索取来一埙。埙是冯氏十孔陶埙,呈葫芦状,与之前街头所买的相比,自是专业许多,于是爱不释手,自练指法,待能发出每个音符时,又想串串曲子,遂找出曲谱,却发现没吹几声,就头晕目眩起来,赶紧追问姑娘缘故,这才知是用气不对,别人用丹田之气吹,我用肺中的气来吹,也难怪要头晕了。
这三分钟的热度便在不会用气的挫败感中凉了下来。此后,这埙便又搁置在茶桌上,我也便专心做了姑娘的粉丝,只欣欣然看她吹埙了。心中却好奇,这陶器,怎如此轻灵,能将世间一切美妙的音律都蕴藏其中,不禁再次折服于先人的智慧中。
据说这埙是起源于一种叫做石流星的狩猎工具的。古时人们狩猎,常用绳子系一石球投出去击打鸟兽,如若这球体中间是空的,抡起来一兜风便能发出声音,人们觉得好玩,就拿来吹,慢慢地有了埙的雏形。最初的埙大多是用石头和骨头制作的,后来才发展成为陶制,这乐器,也一直流传,到了秦汉后,便主要用于宫廷演奏。只是,历史久远,朝代更替,到了清时,它也一度断代,直到隶人吴浔源偶得埙,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这才又复流传,我也才有机会,跟先祖听同样的声音。
仔细想想,如若时光可以自由穿梭,我们不过是这时光之路上的两个点,先祖们在路的前头聆听这埙曲,我在隔了很远的距离之后听同样的埙曲,只是,我们互相看不到罢了,这埙却成了连接历史之物,同样回荡在天际,仿佛除了舒缓心情,除了陶冶情操,又成了某种寄托。难怪,这姑娘虽有些男儿的豪气,却对埙如此痴迷,一拿在手里,即刻柔情似水起来,这埙就变成了她的爱人,她将心事诉于它说,它也用曲声附和着她的悲喜,就如我用文字抒发心绪一般,我们都有自己的爱人。
如今,这黄褐色的陶埙依旧静静地躺在茶桌上,用它的十个小孔盯着我看,饮下一杯茶后,我不禁又拿起它来,也想试着再交流交流……
埙,被逐渐遗忘的中国天籁
物道君语:
在你心里,埙长什么样?鸡蛋的椭圆形,还是普通的梨形。
在古代,埙不止吹,还有艺术埙,如人面埙,作为一种埙艺留存至今。几千年后,也有一个人把埙做成各种形状,像流水,像高山,像竹林,还像贝壳,像鱼......更改变了埙的音腔结构,使之不仅可以吹古曲,也可以吹流行曲。
他是当代埙艺家,张驷。
贾平凹的《废都》里,夜晚城墙头上会传来一段沉缓悠长的音乐,呜呜如夜风临窗。一个叫庄之蝶的人说:“你闭上眼慢慢体会这意境,就会觉得犹如置身于洪荒之中......听见了一颗露珠沿着枝条慢慢滑动。”
这便是埙声。
埙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距今7000年前的半坡遗址上,就发现了它。埙还曾经进入了宫廷,作为敬天祭拜的礼器,不过时间走着走着,在明代失传于民间。
所以距今二十多年前,相当多人对埙是陌生的。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几个人学埙、吹埙、推广埙,乃至改变埙。
因为他们发现,世上乐器大多唱娱乐,演奏华丽的东西,埙不张扬,也不华丽,发的是土声,地气。如同在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有人锋芒毕露,有人独处静思。
这其中的一个制埙人,便是来自大连的张驷。
他来自一个“陶艺世家”,如今他在大连的山里,已制埙四十年,从找矿石岩彩,到突破造型,校准音节,使音域宽泛,把埙做成了一种艺术品,部分收入博物馆馆藏。
张驷1955年出生,父母和哥哥都做陶,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受父母宠爱,他们不想张驷也走这条辛苦路。
不过采访里,张驷说到,小时候经常钻进家里的馒头窑,给大人们递出做好的陶器,那时就觉得神奇,“同样是一滩泥,玩的泥巴会裂开,但这些烧一烧就结实,还有模有样,有声有响。”
当然其中受过父母反对,他下过乡,考上大学,学的却是自动化,后来进入企业工作。中途好像幡然醒悟一样,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做埙。
但没有基础,只能闷头干,从一把土开始。采访后的一天,正值初冬,66岁的张驷在大连的山谷里找矿石和岩彩。
相传古代制埙人也在秋天取土,调合成泥,但根据现在的气候,这个时间要再冷一点。一场雪落,张驷这才进行野外采集。
“这个时候的土地没有生灵了,是净土。”一掊土也有生命,春夏两季忙着给植物输送养分,只有等到秋才能休息。这时的土质干净了,做出来的埙,声音才比较通透,甚至像水一样清。
不过除了泥土,张驷还要找古人用来画画的岩彩,给自己的埙上色。
那一次采集,半山腰上他找到了两块半透明的石英,上面粘连着蔷薇色的泥土;找到了肌理如丝缎的绿泥石,烧制时会形成晶体;还有最常见矿石是赭石色、木灰色、咖色、褐色......
古人在《考工记》里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与人工釉色不同,自然的泥土,在窑变中的幻化,可能性很大。
有惊喜,如天空落幕后放松的蓝,如深山清泉的灰白,水月白;也有笨拙,像沉稳的松绿、草绿、灰绿.....张驷坦言,这些色彩在陶埙上烧制出来,很难被人喜欢。
就像石头灰蒙蒙的色彩,像冬天的不惊艳,不同华丽的东西总是容易抓人眼球,沉静的色彩总要经过岁月才能欣赏。
不过说来也奇,那些我们熟悉的半坡彩陶,马王堆赋彩浓郁的帛画、漆画,敦煌的壁画,是古代人用岩彩做的画的。而在几百或上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看着它们,既熟悉,又新鲜。
张驷的埙,好像也是这样,放在桌上你看它不惊艳,可是就放着,时间过着,沉默中折射出了不同的光。
张驷提到:“埙是人类第一件从无到有创造的乐器而不是制造。比如竹笛在竹子上做出来,而埙是一把土创造。”其实,埙音也是土造。
野外采集回来,张驷就把矿石砸得大小差不多的一块块,煅烧到800度,使矿石变酥,最后就像照顾小朋友一样碾成粉末,为埙做泥。
之后需要在自然中陈腐发酵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可以用来捏埙。埙上头有孔,是吹奏的口。埙身还有7到10个孔,用来按指法。
不过素胎埙做好后,张驷不着急钻孔调音。而是先拿来塑料袋,把素埙套上半封着,因为土有收缩力,如果干得太快,就会龟裂,只能等它慢慢来。
一般三天时间,素埙半干就可以钻孔。但不能一次钻完,毕竟这时的土只是半干,后续还能收缩,如果钻大了,土再收缩,孔更就大,声音就上不去,吹出来可能像鸭叫。
只能时刻观察,干到一定程度,就去吹,试音对不对,不行继续调音。一次又一次,直到自然条件下,孔洞大小稳定后,那么就可以入窑了。
这个钻空调音的过程,张驷算过日子,大概12天。记得《三字经》里说:“匏 [páo] 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其中“土”,便是埙。埙既成于土,便土声,有地气。
烧窑之余,张驷歇息下来,拿起埙,在旷野边上吹,呜呜咽咽,还挺像贾平凹在《废都》说的,如泣如诉,听着伤心,闻着落泪。
这似乎不大像土的厚重。可什么是土声,张驷也说不出来,只觉得一切准备妥当,心情放松,只需等着窑烧三天三夜。
就像这个季节,繁华落尽,土地也在休养生息,又如人的欲望芜杂也随之褪去,生活是喧嚣浮华也落去,心沉静下来,安享当下。
不得不疑问的是,张驷是怎么知道土的收缩力有多大,又该调多大的孔,得干燥多少天?
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一把一把土捏,一炉一炉烧,一件事情做多了,留心了,自然就会知道。
就这样,张驷做了近40年,获得过陶瓷艺术家奖,金奖、银奖,到现在担任中国陶瓷协会常务理事,或到大连的一些大学上陶艺课,或带徒学陶。
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这样作埙有必要吗?”是他做异形埙。常见是埙,是鸡蛋的椭圆形。张驷还喜欢做牛图腾埙,鸟图腾埙;也做表意埙,高山流水埙,如歌如意埙,待时埙......
这些异形埙,用途不在演奏。因为形状、开孔的位置发生改变,指法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作为制埙人,张驷会吹会指法,对于其他学埙的人,这是不利的。
而在古代也有异形埙,唐三彩陶埙,红陶刻花埙,人面埙……这些都是装饰多于吹奏。所以张驷意不在此,在于探索埙的艺术性、现代性。
他改变埙的音腔结构,使得它既能吹古曲,也能吹现代的流行曲,能吹高音。
这让我想起了二胡,曾经当它是捱呀捱呀的要淘汰的乐器,可一路过来,听它拉起了《起风了》,拉起了《化身孤岛的鲸》,它走进了我们,走进了现代,再想起已然不觉它很老。
很多古老乐器的命运,似乎都是如此,无法适应时代的变化,只能淘汰,消失。这有时不能埋怨时代,因为每一个当下都是要进步,自然就产生了新的乐器,新的审美。
更为要紧的,有没有一些人,因为热爱埙,而想要改进埙,让它走进现代,走进我们。而这些需要代价,就有所必要。
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好在时光的脚步每一寸都有价值。春夏秋冬,一个接着一个季节过去,不怕缓慢,只要坚定,孜孜不倦地,自然会有结果。
就像这土做的埙,它吹着大地的飘零与茫茫,也吹去等待的来年与春天。
文字为物道原创,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