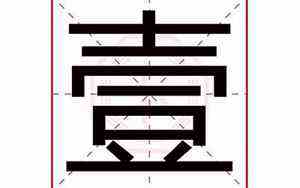本文目录一览:
梦境心理学:梦到已经离世的亲人,往往预示了这3点
苏轼在《江城子》中写到:“夜晚,我在梦中回到了故乡,坐在小轩窗前,看着妻子正在梳理头发。我们相视无言,只有泪水不停地流淌。”苏轼的妻子去世后,他经常怀念她。尤其是在梦中,他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从前,他的妻子还在为自己梳妆打扮。然而,苏轼只能默默流泪,无法开口。也许,唯一可以跨越时空的地方就是梦境。在梦中,你可以是年轻有为的新秀,也可以是年老退休的老者。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梦中与已故亲人相会,一同畅饮,回忆曾经的往事。然而,现实是物质世界,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只有梦境,它超越了物质界限,是我们心灵的精神领域,能够让你穿越时空,前往过去和未来。但需要明白,梦境中的一切都是由潜意识和欲望创造的幻象。有西方科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肉体无法穿越时空,那么为什么不尝试用意识在“梦”的领域中穿越时空呢?虽然这只是一种幻想,但它启发我们思考,在梦境中,一切都相对自由。
既然说“梦境”能够让我们前往未来或者回到过去,为什么它又不具备绝对自由呢?要明白,“梦境”实际上是潜意识和欲望的共同表现。而潜意识和欲望的根源则来自于现实世界。你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会直接影响你在梦境中的体验。这里有一个故事:20世纪,有一位热衷游泳的冒险家,经常游泳在大海和湖泊中。尽管他的亲朋好友都警告他这样做很危险,但他坚持不懈。有一天,他梦见自己在湖边碰到了已故多年的父亲。父亲阻止他下水游泳,但他仍然跳入湖中。就在那一刻,他惊醒了。后来,他在外出购物时遇到了一位朋友,正好这位朋友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将梦境告诉了朋友,并咨询了意见。朋友听后提醒他:“最好不要在陌生的湖泊游泳。选择相对安全的地方游泳,以免发生危险。”然而,他嘲笑朋友的担忧,认为只是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然后,一个月后,这位冒险家在野外湖泊中溺水身亡,成为了鱼的食物。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事故发生前,他梦到了“父亲阻止他下水游泳”呢?梦到这一情节后,为什么他的梦境成为了现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当有人阻止你做某事时,你反而更想去尝试。这会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从梦境心理学的角度看,梦境具有警示作用。换句话说,梦境出现是为了警示我们要小心谨慎,避免大意。西方心理学家认为,梦境是大脑对生活的一种应激训练。如果你梦到某件事或某个人,实际上是大脑在警示你,提醒你要小心处理相关问题。然而,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说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梦境是我们内心情感和回忆的折射。在某种程度上,梦到“已故亲人”是好事。这是潜意识的方式,以亲人的形象提醒我们要小心,不要掉以轻心。另一方面,梦境也可能是偶然事件,不必过分担心。关于梦境,我们应该多角度思考,不同的解释方式也许会给我们不同的体验和启发。
“洋盘”自述:要不是因为美食,我不过就是另一个老外
2005年,24岁的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离开家乡——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又机缘巧合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36餐厅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近20年的生活。从最初跌跌撞撞闯入一座陌生城市,不知道自己能在这里待多久,到骑着挎斗摩托穿越5000公里寻路中国,从躲在外籍人士舒适的“泡泡圈”,到花10年寻访一位手工锅匠,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是讲述他在中国经历的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本文节选自其中“泡泡圈”一节,讲述了“老外”圈子里的“规矩”。
《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美]沈恺伟著,于是译,文汇出版社,2023年10月
外来者会建起自己的世界。有时是有实体边界的,一目了然。不留意的人通常是看不到那个世界的,但对那个世界里面的人来说,它却极其真切。一如雪花球里的小王国,那就是泡泡圈里的小世界。
任何人都能进入圈内的小世界。在华外籍人士的泡泡圈里,餐厅和酒吧都是我们活动的公共空间——但在我们看来,那些都是“我们”的地盘。只要你不介意花冤枉钱,就能在“我们”的超市购物,看“我们”的医生。只要你会说英语,就能一窥在华外籍人士为自己构建起的世界。但如果你真的活在泡泡圈里,那就要遵循一些不言而明的规矩。
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
你来中国多久了?
这听来像是闲聊。我们这么问纯粹是下意识地,问得心不在焉,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究竟要如何推进日后的各类社交互动。但在外籍人士的交往中,这是你能问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接下来的谈话将如何进行。答案是必要的,有助于把彼此归入恰当的类别。答案控制着我们的互动,丰富了我们的交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在打仗。它所暗示的潜台词是“在中国太难了”,所以,谁待在这儿最久,谁就“赢了”。谁最能长久地“忍受”在中国的生活,谁就会成为外籍人士中的“老大”。就像两只狗在嗅对方的屁股。
泡泡圈规则:中国通
即便在外来者中间,也有内行人。这是人的本性。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他者”来帮助我们感受自己的归属感。我们有3套阶级划分法来实现这一点,并依此顺序:以融入中国为标准划分出的阶级,以社会身份划分出的阶级,以语言划分出的阶级。
比如,第一次见面的3名外籍人士的这段对话——
外籍人士A:你来中国多久了?
外籍人士B:哦,我7年前来的。
外籍人士C:哇,这么久了!我是2019年疫情前到的,之后就一直在这里。
外籍人士B(对A):你来这儿多久了?
外籍人士A:我快3年了。
社会秩序已然明确建立起来了。B已荣升“高阶”外籍人士,以其明显的“承受”能力和所谓的“深厚文化知识”在此番竞争中“获胜”。从此以后的所有谈话中,如此获胜的人必会被尊称为“中国专家”,得到的恭维包括“那时候肯定大不一样吧!”这种话。
A已被确立为“中阶”外籍人士,但凡开始谈论对中国的看法,不管什么话题,A都必须先承认B“更了解内情”。比如,“我在这儿的时间没你长,但我认为中国是……”
当然,外籍人士C是可以发表意见的,但不会被大家认真对待,因为他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中国经验”来挑战A或B。而A和C无论如何都不会反驳B。
参与这种社会竞争的包含但不限于在中国待足一年的人。没有最低时限。在中国生活了6年的外籍人士会看不起在中国生活了6个月的外籍人士,以此类推,在中国生活了6个月的外籍人士又会看不起在中国生活了6周的外籍人士。来了6周的老外会自我安慰:反正我不是游客。游客则被彻底忽视。
泡泡圈规则:外籍专家
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在我们各自的母国,社会秩序通常是明确的。有蓝领——公交车司机、护士、园丁、干手工活儿的,也有白领——对着电脑、在办公室工作的人,还有精英——名人、政客、成功的商人。
但是,公交车司机和护士不会成为在华外籍人士。名人和政治家也不会。所以,就由我们来填这个空。
英语老师成了我们圈内的公交车司机和垃圾工。我们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除了会说生来就会的语言,没有其他技能。(这是不对的,也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这里说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群体外籍人士。)他们只比游客高一级——只是不想离开的游客,接受了他们唯一能接受的工作。他们往往是短暂的过客,在中国签的都是短期合同,所以,在前文所说的竞赛中根本没有竞争力。他们赚不到多少钱,因而也得不到多少尊重。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人。(国际精英学校的老师相对而言能得到更多的尊重。)
接下来是外籍中产阶级。他们在媒体——生活方式类的记者地位较低,外国媒体的特派记者地位较高——广告和公共关系公司从业,也会在设计、创意产业或建筑公司工作。他们也可能是小型企业主。
商人阶层高居于圈内社会阶级的顶端,可以说是21世纪的上海“大班”。他们是老板,是迪士尼之类的大型跨国企业的高管。他们持续关注的是GDP增长和消费趋势,会加入商业组织和专门的商会。他们的孩子上的是一年25万人民币的国际学校,都由妻子(通常都是外籍人士)或阿姨照顾。他们住的是独门独户的别墅和豪宅,有车有司机。在中国的这些年,这类人我多少认识了几个,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一有闲暇就抱怨。他们喋喋不休地抱怨阿姨,抱怨西餐,抱怨他们的中国员工。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理解中国,而是来赚钱的。他们想过的生活和在母国的老日子没差别。他们热爱泡泡圈,并且是圈里的国王。
泡泡圈规则:你会说中文吗
外籍人士评判对方的第三个因素是其中文的流利程度。(这一点不适用于那些从小就学过中文的老外。)外籍人士都知道,中文能力最能表现你融入中国的程度,以及对中国有多大程度的认知。中文说得多流利,等同于你有多了解中国。语言就像一种社交货币,我们会掂量掂量,判断出彼此的站位,以及如何在同一个社交空间里分配尊重的额度。中文流利的人会赢得尊重,甚至是来自商人阶层的赏识。
但你开始综合衡量各方面价值时,这个规则会显得不够完善,最终演变成如下情况——
来这里3年但中文说得很好的英语老师,比来这里8年但不会说中文的作家更有社会资本。在这里待了20年却只会说最基本的中文的商人,会因为无法沟通而不断地道歉。他会很没面子。在我们眼里,他是“差劲的外籍人士”,中文能力不足只能证明他把所有时间都耗在泡泡圈里了。
作者拍摄的静安别墅(2006)
用这套公式定位彼此,其实蛮吃力的,而且也是错误的。比起漫画式的黑白简笔勾勒,灰色还不止五十度呢。但概括式的定论总归是有道理的。就个人而言,这套社会等级制度不是由我们任何一个人建立的。就集体而言,这套规则的长期沿用是由我们大多数人共同完成的。
到了某个时间点,我们就不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们的答案——10年、13年、16年——会终止谈话。谈话会变得很尴尬。
我们不再和那些在中国没待够5年或10年的人交往——新来的人对自己的观点和认知坚信不疑,自认是“中国专家”,这就变得很烦人。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越长,你知道的东西就越少。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外籍人士对自己认知中国的自信程度来判断他们在这里待了多久。
经过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然明了:根本没有专家。
2012年在夜店打碟
泡泡圈,是商人阶层在近两个世纪前就建起来的。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特许外国人自开租界。在上海,法国人在他们的地界里种上了悬铃木,建起了花园别墅。英国人和美国人将他们的租界合并形成了“公共租界”,从外滩以西、苏州河以南延伸到黄浦江东北一带。日本人也有一个租界。租界都是泡泡圈,名副其实,只要在圈内,就只受租界母国的法律管辖,并由各自的军队监管执行。
日常生活中,他们使用英语、法语或洋泾浜混合语。商人阶层赌马,建起奢华的住宅和酒店。名人、政客、外国警察、印度门卫……各个阶层都有,和今天的社会阶层不同,当时从最底层的难民和俄国流亡者,到顶层的沙逊家族之类的犹太伊拉克家庭,样样都有。
相对而言,当时的泡泡圈比现在的更大,若按统计数据所得的中外人口比例推算,现在的上海要有100万外籍人士才能和当年持平。但如果单纯看数字,当年和现在的外籍人数差不多。20世纪40年代末,租界回归中国,大部分外国人都离开了,上海的泡泡圈要到21世纪初才又壮大起来,继而又在2020年后因为新冠疫情而急剧萎缩。
这里有送餐服务、医院、诊所、国际学校、迁居中介、签证中介、房产中介、餐厅、酒吧、洗衣店和超市。我可以买到我从小到大在迈阿密吃的早餐麦片,也可以找到穿越太平洋、用集装箱船运送来的含糖苏打水。我可以在新加坡人开的医院里上午看一位美国膝关节外科医生,下午看一位乌克兰精神病学家,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都是菲律宾人。我可以请一个会说英语的阿姨,我去上班,让她帮我打理家务,等我回家后,再让她给我做西餐。唯一的麻烦就是偶尔会遇到不会说英语的人,除此之外,你几乎没什么理由需要离开泡泡圈。
虽然我对泡泡圈百般嘲讽,但我其实也是圈中人。我生病时会去看那些外国医生,做饭时会花重金去买那些进口食材。我用中文对话,但我用英语生活。我懂规矩,是因为我守规矩。要不是因为美食,我不过就是另一个老外。
2009年在虹口骑行
卖掉第一辆摩托车、离开美国去香港冒险时,我知道自己很想学新东西。我在迈阿密的最后一任老板是个以将拉美、加勒比和亚洲食材融入高级烹饪而闻名的大厨。
他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汲取菜式灵感,囤在他的食品储藏室里的东方食材都很时髦,都是我们见都没见过的。在21世纪初的美国,那意味着柚子醋和花椒、鱼露和春卷皮。日本料理和东南亚菜风头正健。中国菜仍然意味着廉价、高糖分和不健康的外卖。
到最后,我越来越沮丧了。这位大厨在我为他工作的10年前就已到达了巅峰,现在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写烹饪书上。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餐饮界先驱,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有一个问题: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白人,从没去过拉丁美洲或亚洲。他只会说英语。他和来自这些国家的人一起烹饪,从而了解那些国家的食物,他以这种方式创建了自己的烹饪事业,但也因此成了一个局外人,只是那些异域美食世界里的访客。我想学更多,想了解我做的菜和我用的食材是从哪里来的,但不是从他那儿学。我想得到第一手经验。
我收拾行李去了南美。因为没找到出路,我抱着尝试的心态来了亚洲。中国并不在我的计划中,当时的世界美食交流活动中也不包含去中国探究美食。把八大菜系粗暴地简化为蜜糖鸡和蛋卷后,我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美食——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
作者在测量小笼包,曾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
我有很多东西要学。在我来中国前,满打满算只吃过3次中餐——不是外卖。
第一次,是我快到法定饮酒年龄那会儿,我的第一个厨师老板在收工后带着全体员工去银苑。我们吃了豉汁蛤蜊、挂在扫帚柜里的烤鸭——因为挂在外面是违法的,他们说必须藏起来——还有粉丝蒸扇贝。我们老板不用菜单就能点菜,对那儿的厨艺赞不绝口,点了满桌子的菜。他是个来自新泽西州的红头发壮汉,和中国没有半毛钱关系。他只是知道什么东西好吃。
第二次,是我在泰国度假那阵子,特意去香港看我姐姐那次。她在那里公干,吃喝可以报销。我们去了九龙的一栋高楼,乘电梯上到30层,走进了一个黑漆漆的房间。射灯照亮了石狮子。穿着黑色迷你裙的女侍应生把我们带到一张可以看到海港的桌前。那是我到过的最豪华的餐厅。我们吃了羊排和咸蛋黄虾球。
2012年作者在亚斯立堂
进入泡泡圈之前,我在中国的生活很奇怪。我什么都不懂。来中国几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所有内衣裤都不见了。我打电话给帮我搬家、帮我请阿姨的公司。因为我和她无法沟通,只能让他们给阿姨打电话。然后,公司向我解释:是,她把所有东西都带回家了;不,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她把东西都带回来了。
那时每周休息一天,我有时会尝试在家里做饭,但常常被食杂店里的东西搞得一头雾水。为什么有6种鸡?为什么有一种鸡是黑色的?挫败又困惑,我就放弃了,去旁边的美食广场吃完了事。
我住在一栋20世纪30年代弄堂房子的3楼。邻居们在一楼共用一个又黑又脏的厨房。有一天,我回家时发现住在一楼的那位残疾的老阿姨正用独臂把活螃蟹一只一只塞进黄酒罐。她以前在工厂做事时出了事故,有一条胳膊被截肢了。那些螃蟹在她门外的塑料桶里放了几个月,像医学标本一样漂浮在浑浊的液体中。到了冬天,她还会把盐渍鸡挂在楼梯间的衣架上。
早上,我出门上班的时候,她会站到门边,用独臂用力拍打贴在门框上的毛巾,在我走过去时冲我大喊大叫。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生气,所以一直没有应答。有天早上,她的动作特别夸张,我担心出事,就打电话给一个中国同事要求帮忙。我把手机递给老阿姨,老阿姨对着电话喊了一通。原来,几星期以来,她一直在高声问我:“侬饭吃过了伐?”她只是想跟我打个招呼。
每件事都太难了。
交到朋友后,一切就容易多了。在朋友们的引荐下,我迈进了泡泡圈。他们告诉我可以在哪里买到鸡胸肉,怎样在半夜叫比萨。他们教我出租车司机讲的中文。我带他们去骑自行车。
但即便我学会了如何在泡泡圈中生存,我也很清楚:自己并不想全天候待在圈里。来中国是我意料之外的事,依然算是个漫长的假期,但我想,来都来了,不如尽可能地多学点。
当时,关于中国美食的英文资源非常少——至今仍不算多——但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读了。我了解了八大菜系和江南美食的历史渊源。我把海鲜市场和水果摊当成教室,学习陌生食材的名称和用途。
我发现了一本关于上海锅匠的书,非常赞赏书里拍摄到的那些匠人。那时我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女朋友。那本摄影书里没有制锅匠人的联系方式,她发现了绣在匠人兄长工作服上的名字,虽然不完整,但她以此为线索找到了他们。那就成了我为第一本杂志写的第一篇文章。我一直和这对兄弟保持联系,直到10多年后他们退休。
有位年长的中国记者江礼旸把我纳入麾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是美食文章作家了;我们每每走进一家餐馆,大家都对他敬慕三分,那场面会让你惊呆!厨师们、经理们无不轻手轻脚地进入餐厅,向这位戴着眼镜、穿着背带裤的矮个子老人鞠躬致意,俯首听令。当他解释这道菜或那道菜为何成功、为何独特、为何失败时,我就坐在他身边;所以,我找来中国朋友作陪,好让他们为我们翻译。
锅匠、江礼旸、会说英语并且巴不得把他们的家乡美食介绍给我的中国朋友们——是他们把我从泡泡圈中拉了出来。如果我想了解中国美食,就必须和中国人交谈,而中国人,按理说都是在泡泡圈外的。这很简单。食物就是我与中国之间的桥梁。
焦点几乎不太会集中在我觉得好吃或恶心的东西上。食物作为一个课题,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味道,而在于——食物是一种语言。了解中国人如何烹饪、中国人注重餐桌上的哪些因素,都能帮到我了解历史和文化,以及孕育出这种人文历史的社会。食物,其实只是个借口。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好奇心强、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会在我们交谈后觉得自己好像刚刚接受了一轮采访。还有一次,第一次见面的人问我是不是在面试他。我对别人、包括别人看重的东西很着迷,还会和我看重的东西对比一番。我不求认同,只求想法。我喜不喜欢吃海参根本无关紧要。但中国人重视海参的事实很重要,因为那能让我明白它的价值。我也不在乎海参的味道如何,我想知道人们怎么会想去吃海参,这能让我明白他们有怎样的世界观。
写作,好像给了我一种许可证,让我可以去问人们一些在正常交往中会显得很过分或很尴尬的问题。这显然是一种掩护,虚掩了我想采访别人的本能倾向。食物只是让我们开始交谈的破冰话题。一开始,我们聊聊你做的炒锅的价格,为什么手工炒锅更好;聊到最后,我竟然知道了城管的善心、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还知道了你女儿坚持要你出钱上大学,好让她的同学们不要认为她家很穷(尽管确实如此)而需要奖学金。
你给我讲了历史(上海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历史),你给我讲了人性(你女儿所代表的工薪阶层的虚荣心;而你愿意纵容她,哪怕早过了退休年龄,还继续做着艰苦的工作),你把自己的人生都讲给我听了。本来,知道一点冷锤碳钢的物理学就能让我满载而归了,结果,你却用这种方式丰富了我的人生。
要不是因为锅,我怎么有机会和你沟通呢?
2015年作者拍摄的手工锅匠陶师傅
18年来,这些走出泡泡圈的短暂经历积少成多。在兰州去拉面学校的一周,变成了拍摄纪录片的两周,又变成了追寻新故事的几个月。上海闹市街头一家独特的零售店,引发了去新疆了解骆驼奶的两星期。
故事不会被挖掘光,相反,我只会发现自己写的故事太少了。我不想躲在泡泡圈里——生活虽安逸,规则却越来越霸道——我想出去。
我想真正地活在中国。
但,假如我在真正的中国过了糟心的一天,也会想回到泡泡圈里。
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了。我一只脚在泡泡圈里,一只脚在圈外。对一些外国人来说,我太中国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我又太老外了。我并不是冲着泡泡圈来中国的,但当我飘出去、融入圈外时又会想念它。我是为中国而来,但也无法全身心全时段地生活在中国。我有很多问题,答案却很少。
前妻出轨再婚,离婚后又来找我复合,我该同意吗?
我父亲去世早,家里只有我妈,我,和我儿子。离婚那年我35岁,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大本事,只想有个知冷知热的女人,过正常的幸福小日子。
2018年,前妻出轨,我们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和电视剧演的一样,她和我吵架,还帮那个男人说话,说离婚后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还说本来就是相亲结婚的,没什么感情基础,醉酒后跟我说也从没爱过我。我很生气,便想离婚,可是别人劝我,孩子小,娶个媳妇不容易,能过就过吧。我原谅了她,可人家还是很拽,俨然一副不想和我好好过日子的态度。依旧和外面的男人来往,花钱也大手大脚,东西要买贵的好的,哪怕今天我只有500块钱,看中的东西也要借几百块买回来。我一气之下按她要求,给了她3万块,离婚了。
我是自己在县城包些小活的包工头,会做饭,会洗衣服,也会照顾人,从不喝酒。可就偏偏摊上个这样的前妻,我承认自己有点窝囊,可是难不成打她一顿?打完呢,孩子怎么办?我家在偏远县城,孩子一大一小,她带走了小女儿,期间她打工一年,女儿一直在我这边,后来她回来把女儿带过去了,在县城租房打工养女儿。这期间我也认识了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也是正在打官司闹离婚,她让我等她。后来前妻不知道为什么提出想复合,我本来不同意,因为太突然,可是我朋友亲戚,包括我妈都劝我: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呵呵,然后我认识的那个女人也劝我复合,然后我就和前妻复合了。
我们没有领证,复合一个月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她还是老说我,我不想让她说,然后两个人就会吵架,大吵几次,别人也来劝过。然后有一天,她说她觉得我已经不爱她了,她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就搬走了,走了大概2个月吧,她就结婚了。我是后来听朋友的老婆说的,她找了个离婚的男人,年龄比我大一点,对方有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家境比我稍微好点儿,因为我的家境结婚后一点也没变,基本上被她败光了。
然后我之前谈的那个女的,想离婚后和我过,我也劝过她能不离就别离,离婚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她说她不怕,说只要有我在就好。
她的孩子判给前夫,可她把孩子要带到18岁,也是两个孩子,我儿子性格和我一样,比较大大咧咧那种,和人家的孩子相处得很不错。我们在一起2个月时,她前夫又反悔了,找到了她哥,说她要是再婚就闹事,让她别想着迁户口。
她去她哥家里,她哥嫂把她骂了,她爸也说她的事管不了,她也39了,我40了,她说她这辈子就这样租房子带孩子过了,然后她就从我家搬出去了。我让她别搬,不行就先领个结婚证,她说她怕前夫没文化的人做事不想后果,她以前被前夫家暴过,她害怕。她说只要我跟她在一起就是事儿,她前夫肯定会来闹事的,我跟她说只要我们俩结婚了就不会有那么多事了。可是她执意搬走了。
结果人家刚搬走没几天,前妻离婚的消息就传给我妈,前妻说她想回来,然后我妈又劝我,为了孩子,朋友也说我认识的这女的以前名声也不好,劝我为了孩子复婚吧。可这些年我对她很陌生了,况且她上班了几年,一毛钱没攒下,说是后面这个男人结婚后也没给过她钱。她现在过得不好,又想回头来找我,我已经不爱她了,我拒绝了前妻,因为我喜欢我谈的那个女人。起码在认识的日子里,她没有为了别人离开我。现在又卡在这里,她也劝我,让我接受前妻,可我想要的是有感情的婚姻,一个幸福的家庭,前妻给不了我。这几年,我手里有点钱,想翻修家里的老院子,或者把空院子卖了,找个能结婚的女人重新买套房。现在我妈又劝我,希望我复婚,真的想想就烦,现在该咋办?麻烦大家发表下自己中肯客观的意见。
丁子姑娘回复:
人可以走错路,但老是走错这一条路,是不是该反省反省了。为什么前妻总是会伤害你,因为你总是给她机会,因为她觉得你很好拿捏,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自己还是孩子的亲妈。如果她真的是好样的,为孩子考虑,就不会败家,放着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了。至于你自己认识的那个女人,信息量少,不做评价。不管怎样,40岁了,自己有赚钱能力,孩子也大了,该怎么舒心怎么活了!
我梦到了前夫的前妻,把我和现任的100元撕了个粉碎
这些年的梦境,一个是原配。一个是现任的前妻。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人会屡屡出现在我的梦境。
现任,即就是还未离家的第二任前夫,在说回益阳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梦到了他的前妻,她把我和现任的100元撕了个粉碎,我恨的她牙痒痒。梦到和他前妻打生死架,是在我驻村的时候,当时现任应该是要把前妻接回去吧。但是事后我才知道。在梦中一次又一次的和她打生死架,撕扯,现实是我们几乎没有见过,见的时候都还能交谈。
第一任前夫应该是这么多年,我内心的意难平吧。昨日我又梦到了他,我和他一起在教我大儿子学英语,one,到ten,我不停的念,不停的念,教我大儿子。然后使劲抓着我前夫的手,在我脸上摩挲。他走了,出去玩,我也跟着他去,去了歌厅,我还是坐在他旁边,然后我一杯又一杯的接着喝酒。后来,他漫无表情的坐到了我身边,我还是抓着他的手。不知道怎么的,突然来了一个女人,我内心是觉得很尴尬的女人,但是说不出她的身份是什么。在梦境,在潜意识里,我是又有丈夫的人,也有小儿子的人。后来,不了了之的,意难平的梦醒了。
醒来之后,仍是意难平。
有多久没见过第一任前夫了?我也记不清多久了。应该有上了年的岁月吧。看我大儿子,我也是挑的他爸爸不在乡下的时间,去看。何况今年我也只才看过几次大儿子。
其实离婚,对于我和大儿子爸爸来说,就等同于对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老死不再相往来。自离婚后,我和他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再也没有用任何方式联系过什么。刚离婚时我的车还会在他那买保险,后来,或许他找了女朋友或是什么。我的保险,他也不再与我买。我想这样的离婚,才叫做真正的离婚,再也没有影响到彼此的生活。
而小儿子爸爸屡屡还会自以为豪的他的前妻三天进天出他的家门,接孩子送孩子,可在我看来,这就是我永远不会再和他复婚的理由。
每每想到这,悲凉感袭来,我也想有一个同我相伴到老的合法的丈夫,我也想一起慢慢变老的情感,可是这两任前夫二人都配不上我这颗珍贵而又长情的心。
我不想人生有太多的动情和麻烦事,也不喜欢总在动情和无情中流连往返,所以,对于那些来来回回的情感我从来没有过,2011到2017我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大儿子爸爸。2018到如今,我又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小儿子爸爸。自认为比那些未婚女干净单纯的多。又自认为比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女人专情,所以如今收起了那颗给了自己太多希望的心。
只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开心快乐。
妻子去世,丈夫一连多日梦见妻子求救,为求真相竟将亡妻棺材挖开
为何如此决绝地去挖开妻子的坟墓?这是陕西的一个小村庄,发生在2019年1月。
老林对着眼前的人愤怒地叱责着,眼中带着愤怒和失望。他的女婿小陈竟然要去挖自己女儿的坟墓!这让老林感到极度的愤怒和不解。
然而,这个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2008年,已经30岁的小陈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发愁。
他的父母是农民,而他自己辗转于不同的城市打工,攒了一些钱后,他决定回到家乡。
开一家小杂货店照顾父母并创造自己的事业。
在陕西的这个偏僻山村里,他的家庭条件已经算是不错了。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媳妇,安定下来。
然而,由于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小陈初中就辍学打工。虽然日子渐渐好起来,但是对于父母来说,他们仍然着急他的婚姻。
虽然有人介绍过姑娘给他,但是最终都没能成。小陈原本已经对结婚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父母的嘱托和他们希望他能有个家庭的呼声,让他再次焦虑不安。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媒人介绍他认识了邻村的姑娘小菊。这个小菊是邻村最小的女儿,年纪和小陈相仿。
虽然有些小残疾,但小陈不介意,两人很快产生了感情,并决定结婚。他们的婚礼在家人和亲戚的祝福下进行,很简单却温馨。
他们很快有了孩子,家庭生活也非常和睦。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带来了意外。
2018年底,小菊突然晕倒,被诊断出患上了癌症。小陈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但是最终妻子的病情恶化,不得不告别人世。
小陈心痛欲绝,但他还有孩子要照顾,还有父母要赡养。他整理了妻子的遗物,将她下葬。
然而,自从妻子去世后,小陈时常做一个连续七天的梦。在梦中,妻子哀求他救救她。
这让小陈心生疑惑和恐惧,他开始担心妻子到底遇到了什么。为了确认真相,他决定去挖开妻子的坟墓。
虽然受到家人的反对,小陈还是决定搬开阻拦他的人,将妻子的坟墓打开。他发现妻子的尸体不翼而飞,而且坟墓内的东西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小陈报警并告上了法庭。经过警方的调查,他们发现附近有一家盗墓团伙,这些人专门倒卖尸体。
盗墓团伙通过打听新丧家庭的信息,找到目标后悄悄将尸体挖走,然后卖给需要的人。而小菊的尸体就是被这个团伙盗取后卖出去的。
这个买主是一对为亡儿子买老婆的夫妻,他们宁可花5万块钱也要买回这个“媳妇”,并且对妻子争夺的态度非常强硬。最终,经过警方调解,小陈将妻子重新安葬,并将盗墓团伙告上了法庭。